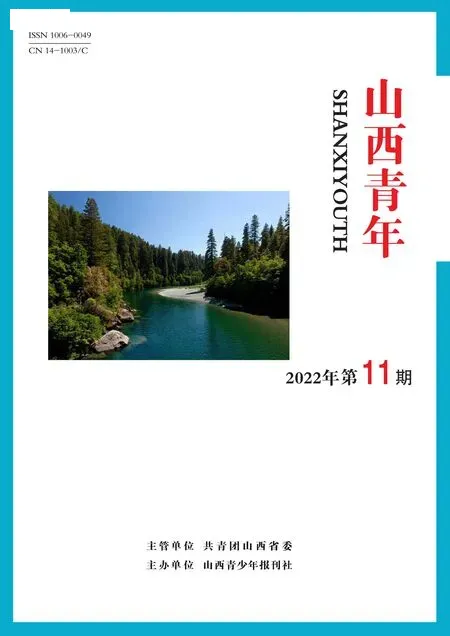由“明室”引發的空間敘事思考
唐晨輝 劉嘉娜 劉 璐
華北理工大學,河北 唐山 063210
空間敘事如同文學敘事都是在傳遞符號信息,在傳遞過程中信息并非直達,而需轉譯。在研究過程中,我想起了發明攝影之前描摹物體時的轉繪儀“明室”。“明室”的工作原理是通過儀器上的三棱鏡,一只眼睛看著描摹對象,一只眼睛看著紙[1]。“明室”整個工作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人眼從一個角度接收符號,繼而接收到符號信息,再將符號解讀于圖紙。羅蘭· 巴爾特以“明室”為名寫了一本關于攝影方面的書。攝影是單一視角將物體或圖像成像的過程,看似是一個直譯的過程;然而,當你揭開靜態圖像的界面,空間向圖像內延展時,二維圖像生成三維空間,空間敘事展開,接收圖像的人由圖像向內窺視空間,觀看圖像的主體轉化為敘事空間的個體,在敘事空間預設框架中游走。米切爾認為:“巴爾特將照片轉喻式地打開到一個與記憶和主觀臨接的領域”。
一、空間敘事結構構成
空間敘事結構是由時間、空間和敘事形成的層面構成的。羅蘭· 巴爾特在談論敘事作品的層次時談到:“敘事作品中區分出三個描述層次,分別是功能層,行動層,敘事作用層[2]。”空間敘事的過程由時間為主線,沿水平向展開,水平軸即為時間軸;繼而或同時行動個體在第二個層面展開,行動在這一層面發生,第二個層面中包含了水平向行動軸;意義隱含在第三個層面敘事層面,意義軸垂直或斜向通過轉喻或暗喻的方式與第一層面的時間軸和第二層面的行動軸聚合產生聯系。時間軸是水平向的,它源于時間的單向性和線性,而行動軸是水平向是因為行動個體受重力因素在空間水平底面上運動。時間主線位于單一線性軸向空間,行動層面是由個體不同行動軌跡與路線生成,意義軸映現于功能層面和行動層面,垂直投射于水平軸上。意義隱喻或轉喻于每一個空間,不同個體解讀不同意義。進一步推演,敘事空間之間連接關系及空間形成的系統就是復雜隱喻關系的敘事層面,也是意義層面。
二、空間敘事的過程分析
空間敘事的過程細分的結果是敘事空間單元的組合,空間敘事是敘事空間單元組合段的連續進程,聚合段隱藏延續其中。羅蘭· 巴爾特認為,“敘事(或敘事片段)的真正樞紐是基本功能單元,是催化劑使其連接[2]。”文學敘事確需催化劑起連接作用,推動敘事進程。在空間敘事中,“催化劑”是行動個體,是有目的性,有主觀意識的行動個體充當觸媒將敘事空間各個連接,維系敘事空間和信息接收者之間的接觸。針對空間單元的組合,巴爾特將基本功能單元及催化劑都歸為功能層,這種劃歸方法是將催化劑的作用上浮至功能層。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空間敘事中“催化劑”也即行動個體可以下沉置于行動層面,時間軸在運行中與之壓聚,并通過意義軸的映現裹挾敘事層的意義。
(一)空間敘事內化與外化過程
時間軸在此過程中退于次要地位,成為隱含項,通過消隱時間軸伴隨行動來尋求意義,情感,氛圍。在文學敘事中,行動個體在敘事層面通過行為邏輯來分析個體行為,塑造個體人物,是內化的過程。然而,在空間敘事層面,人內化意義并非不重要,內化主要研究的是行動個體的功能,盡管有時不作為空間敘事的主要研究對象,外化過程的重要性在于行動通過外化在敘事層面獲得的意義輸出。個體作為觸媒在運動過程中與外部空間作用,完成接收信息—接收信息的認知過程,認知結果向內可以轉化為個人體驗,向外可以轉化為事件。個體運動有方向,有目的,時間有意義,空間敘事過程也在運動過程中完成。
(二)空間敘事的認知過程
人的認知空間的過程是個體與空間產生聯系的過程,人作為觸媒在空間中運動,與空間相互作用,對空間產生認知,并對自己產生反向認知。梅洛· 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一書中提到了一個常常出現的場景:每個駕駛新車的人總要花一段時間來熟悉車身的長寬大小,才能清楚車是否可以通過某個位置,這樣,車的數據就漸漸成了“身體感覺”的一部分。所以,認知是個體對外界空間直觀認識的反應,表達的是空間中個體狀態及個體間的相互關系,在認知層面是無法用因果邏輯來解釋的。陸丙甫認為,認知科學中的“認知”包括“認”和“知”兩個部分,即感知和理解;感知部分是初步的,基本的;理解部分是復雜的,高級的,兩者之間密切聯系[3]。
個體在認知過程中,在接收信息—接收信息后與自身建立符號認知聯系,從個體生存環境,認知范圍中尋求并賦予其意義。在城市空間中的認知,最先開始是識別一些結點,散點式的信息;繼而隨著運動的開始運動軌跡生成,運動過程使得點狀的因素找到聯系,形成線性因素如邊界和路徑等;隨后線性因素不斷增加,線性種類不斷增加,各種線性因素在空間交織形成三維空間網絡,個體有行動生成空間敘事,空間也是敘事的符號載體,個體與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也生成了空間敘事中認知過程。
光線投射在建筑形體上形成的陰影,空間表皮上韻律的漸變,無自然采光通風室內空間形成的壓抑感,在開敞露臺上欣賞周圍景色的愜意,撫觸粗糙外墻觸到的顆粒感,景觀植物散發的不同氣味,個體以身體為媒介,通過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對空間產生認知。凱文· 林奇在研究城市時,將城市空間看作一種直觀可識別的符號,在對城市的認知過程中,個體對城市空間產生直接體驗,也就是“認”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可以識別出城市的路徑、邊界、標志物,區域等;“知”的過程是對感知空間的深層次的理解,是在敘事層面的意義理解。凱文· 林奇在《城市意象》一書中說過,“一個整體生動的物質環境能夠形成清晰的意象,同時充當一類社會角色,組成群體交往活動記憶的符號和基本材料[4]。”在城市空間中,除個體差異外還有共性的因素,城市空間內個體有共有認知,這是在同一文化背景,同一空間內共同譜寫的空間敘事,多個體同享空間,群體共享記憶。
三、空間敘事的邏輯時間內涵
在文學敘事過程中,敘事是通過細節描述進一步進入行動層級,是下沉到了鏈接文本的過程,而空間敘事過程可以在一個空間單元或一個片段處回溯,暫停或加速前進,也可以將空間單元或片段堆疊,前置或后置。這些特性如果在真實時間中是不可能實現的,由此推演,空間敘事中時間層面的時間不是真實時間而是邏輯時間。“邏輯時間連接著片斷內諸核心的邏輯[2]”。邏輯時間聯系不同于真實時間聯系,真實時間不可后退,不可終斷。
在文學敘事中,邏輯時間可以暫停任由不斷增加敘事細節來充盈行動層面的細節單元,從而營造更多意義層面。在空間敘事中,邏輯時間與行動的暫停不會增加原有的敘事空間,敘事空間的增多是通過空間單元或片段的增加來實現的,結構框架增加勢必反向刺激邏輯時間增加。以上原因都會導致時空間隔性,邏輯時間與真實時間也具有間隔性。邏輯時間在時間層面可以暫停,前置或后置,使得意義層面的敘事出現時空不同步現象。敘事空間單元在邏輯時間上有起點和終點的限定,受到兩個點軸向力的壓聚作用。空間組合體并非松散無序的,而是由邏輯時間及行動邏輯統籌的聚合體。起點無法取消,但是終點可以取消,還可以此刻向后發展留有懸念,出現空間敘事的“某時某地”,這種留有懸念的邏輯時間像是射線一般,有起點而無終點,開放結局,無地域,無邊界。戲劇等待戈多被很多評論家稱為一部荒誕戲劇,在這部戲劇中做了一種新型的空間敘事實驗,一方面敘事空間融入了音樂、場景、對話等超文本,使得敘事空間中行動個體同時同步展現;另一方面,在戲劇沖突之后無盡的等待,沒有結局的等待,就是從此時此刻發出的沒有邊界敘事行為,意義由此發散,不同人得到不同解讀,或映射到現實生活,或生成哲學思考抑或根本不明所以。在敘事空間中“懸念”手法也經常被很多設計師(第一敘事主體)應用,例如,建筑師會通過建筑設計中留出窗、平臺來眺望遠方以其延續視線,來獲取意義上的延續,在空間敘事中留出懸念。在北京城市規劃中,以故宮為中心的中軸線并沒有終結于鐘鼓樓而是繼續穿過奧林匹克公園,延伸下去,留著無盡的懸念和無數的可能性。
四、空間敘事解讀過程
“明室”工作過程中,人眼接收到的信息被接受再解讀獲得意義的過程這一過程看似完成,但是新的符號信息被他人接收,接受再解讀又重新循環。德里達說:“從本質上講,不可能有無意義的符號,也不可能有無所指的能指[5]。”符號可以用解釋來實現意義,也可以通過另一個符號再現,符號再現的過程也是原符號消失的過程。在這里意義解讀出的符號已經不同于原符號,解讀意義的三步過程經過了兩次傳輸兩次重新解讀,原符號在新符號中已經消失,并且以一種新的形式呈現出來。新的符號生成后,新的符號載體會經歷接收—接受—解讀生成二次新符號,二次新符號又會經歷接收—接受—解讀再次生成三次新符號,生生不息,循環往復。理論上看,符號能量在動態變化,再循環傳遞,無限衍義;而在現實中,由于接收對象的主觀意愿、能力、時間等主觀和客觀因素,解釋會暫時假停在一個結點,這與懸念恰恰相反。在結點處并非意義終止,而是再解釋下去沒有必要性,于是將可能性潛伏。
(一)空間敘事行為個體與空間互動關系
在空間敘事中,行動個體行為是并行的,多方向,多維度,是一種無整體邏輯的擴展,是通過個體行為與敘事空間之間跨越層面的互動生成意義裹挾,是行動個體外化的過程。外化從行動個體發出,這里所說的行動個體不僅是單個體,也可以是多個體之間,或群體。羅蘭· 巴爾特在談到布雷蒙文學敘事中的人物時說道,“當同一行動系列包含有兩個人物時(通常如此),此系列涉及兩個視角。每個人物,甚至是次要人物,都是他自己系列中的主角[2]。”
(二)空間敘事行為個體與個體的相互關系
在空間敘事中的行動個體通過“看”與“被看”,不斷地在空間敘事過程中生成和發掘敘事的意義層面。正如巴爾特所說的,“無限的人物世界也服從于一種投射于全體敘事的聚合體結構[6]”。不同的行動個體即便是在同一時間,同一環境,同一敘事空間中由于閱歷、態度、情感、心境種種因素會有不同的理解。無法也不能要求所有的解釋都準確達意,所有的接收與接受都無損無缺,所有的理解客觀全面。感知的定向匯集正是單向線性的匯集,無限的單向線性又復合成了非線性的符碼集合。個體的線性與整體的非線性并不矛盾,闡釋對象不同,意義集合范疇自然也不同。
五、空間符號載體的功能與意義
空間敘事過程中的空間描述已存在于預設的三維空間敘事框架結構中,空間敘事過程更多的是行動個體的轉移和解讀過程。人眼將接受的信息解讀于圖紙上是外化的結果,解讀的結果成為新的符號意義的載體。每一個符號載體都是“功能—意義”的聯合體,假設符號載體是完全功能體時,意義體為零度體,此時空間載體僅具有功能性,不具備任何意義;如果符號載體是完全意義體時,這時空間載體僅具有意義性,不具備功能性。這種極限狀態在現實的空間符號敘事中極少出現,空間符號載體通常既是功能體,又是意義體。其功能度與意義度的比例隨條件不同含量也不同。例如,工業遺址改造項目中的工業遺址在出現之初是為工業生產功能而建造,工業建筑及構筑物更多的是功能體,其意義體成分微乎其微;而隨著歷史變遷,產能更替,工業搬遷或淘汰,原有工業生產功能不復存在,此時,工業遺址的意義作用遠大于功能作用。工業遺址改造項目中,普遍做法是保留原有工業遺址而植入新的功能,工業生產原有的設備及廠房等作為一種容器,承載了展覽、文化、藝術等新的功能。改造后的工業遺址成為新的功能體—意義體,又同時具備了新的功能和意義。
綜上所述,空間敘事過程與文學敘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敘事空間通過第一空間敘事主體將自己的經驗或意義編碼映射于敘事空間框架結構中而生成。敘事空間結構框架表象上由多個敘事空間單元組合,實質上是多重敘事空間的聚合。敘事空間“催化劑”也就是行動個體在第二個層面進行符碼接收,接受并進一步解碼第三層面敘事層面的意義。空間敘事由聚合體形成敘事空間建構,顯現于空間組合,敘事意義映射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