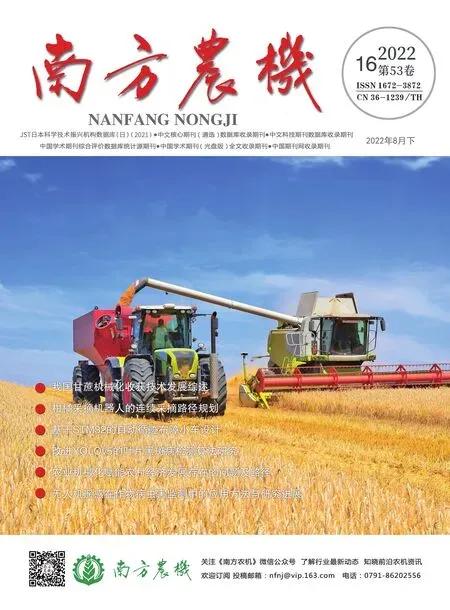貴州生態扶貧的歷程回顧及經驗啟示*
張琳杰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2)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在扶貧開發工作中強調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觀,將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相結合,生態扶貧理念開始逐漸被提出和強調,生態扶貧初步形成了包含生態產業、生態移民、生態補償、生態建設等路徑的制度體系[1-3]。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實施“五個一批”工程,其中要“生態補償脫貧一批”。2018年,國家六部委印發的《生態扶貧工作方案》更加強調了讓貧困群眾從生態保護及修復中獲得更多收入和實惠。生態扶貧工作被進一步重視,作為精準扶貧方略的組成部分,推動我國實現生態文明建設與脫貧攻堅的協同共進。國內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和案例探討了生態扶貧的概念和途徑。一般認為,生態扶貧是將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相結合的扶貧模式,是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區域主要涉及貴州、寧夏、廣西、重慶高山地區、四川藏區、江西贛南等,以及對西部地區和民族地區的研究。在脫貧攻堅和精準扶貧階段,生態扶貧主要采取了生態工程建設、公益崗位設置、發展生態產業、生態保護補償、易地扶貧搬遷等有效模式和途徑,推動了我國農村貧困地區生態治理和貧困治理的雙贏[4]。
1 貴州生態扶貧的歷程回顧
1.1 生態扶貧的萌芽階段(1986—2000年)
1986年,貴州省制定人口、糧食、生態系統性發展戰略。為解決極端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貴州在一些貧困問題突出、自然生態環境惡劣的地區,開展了生態移民和易地扶貧搬遷的先行探索。1988年,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成立了以扶貧開發、生態建設為核心的畢節試驗區,嘗試尋找兩者結合點。畢節試驗區成立以來,將生態建設融入扶貧開發和經濟發展,推動畢節地區走出經濟貧困、人口增長、生態破壞的惡性循環,實現了區域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的同步提升。這一時期,畢節試驗區處于生態扶貧的萌芽階段,由于受到宏觀環境滯脹危機等影響,貴州生態經濟轉型發展和生態化扶貧措施的效果有限。總體上,2000年之前,生態扶貧政策屬于對自然生態資源的生產性利用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還未形成生態產業扶貧、生態保護扶貧等較為成熟和完善的政策[5]。
1.2 生態扶貧的探索發展階段(2001—2015年)
進入21世紀,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思想,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五位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要堅持扶貧開發與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相結合,充分發揮貧困地區資源優勢,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在國家政策的導向下,2005年,貴州提出“生態立省”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2015年,貴州省明確提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并取消10個貧困縣GDP作為政績標準,減輕經濟考核壓力。同時,貴州省委、省政府加大對上述縣區石漠化、森林覆蓋率的審核強度,力求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平衡[6]。
1.3 生態扶貧的全面推進階段(2016—2020年)
2016年,貴州被納入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2017年提出“生態脫貧攻堅示范區”的戰略定位,支持貴州開展生態脫貧制度創新試驗。2017年,貴州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全力實施“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三大戰略行動,強調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同共進。2018年,國家六部委印發的《生態扶貧工作方案》指出,充分發揮生態保護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的作用,標志著我國生態扶貧制度體系的全面建立。在國家行動方案的指導下,貴州制定印發《貴州省生態扶貧實施方案(2017—2020年)》,加大生態建設保護和修復力度,通過實施生態扶貧十大工程,助力貧困人口增收脫貧、穩定致富[7]。
2 貴州生態扶貧的經驗啟示
2.1 因地制宜發展生態產業,拓寬貧困人口增收渠道
貴州貧困地區大多地處生態資源豐裕地區,同時又是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和生態環境脆弱區,面臨生態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安全維護的雙重壓力,生態扶貧成為這些地區減貧脫貧的重要手段。對于生態資源豐裕的貧困地區,因地制宜地開發利用當地的自然生態資源,在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的前提下,發展生態型產業提高貧困人口財產性收入,有效改善當地貧困人口的傳統生計方式。作為全國唯一沒有平原的省份,發展山地高效生態農業成為貴州生態特色產業扶貧的成功模式。貴州充分利用自然生態風光和少數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貴州生態旅游的“貴州模式”。實踐證明,旅游扶貧能夠在短時間內實現貧困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提高貧困人口收入,并且對當地生態環境影響較小,對當地就業起到促進作用,幫助貧困區提高“造血”水平,實現持久性脫貧[8]。生態旅游稟賦較好的地區,旅游扶貧有力帶動產業融合和優化,使當地居民獲得經濟發展的收益。生態旅游扶貧的產業帶動效應強,為貴州貧困地區脫貧致富、邁向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
2.2 創新生態資源利用方式,探索資產性收益新模式
創新生態資源利用方式,利用光照資源、森林資源等開展生態扶貧,探索資產收益扶貧的新模式,助推貧困人口脫貧增收。利用光照資源實施光伏發電項目扶貧,對太陽能資源豐富、電網接入條件允許的地區,將光伏發電與農業種養、生態旅游相結合,有效拓寬了當地農戶的增收渠道。開展森林資源利用扶貧工程,實現生態維護和農民增收的雙贏。依托豐裕的森林資源,大力發展林下經濟,發展林業立體復合型經營,同時通過林權制度改革增加了貧困人口資產性收益。推進森林旅游與生態康養的融合發展,助推貧困人口增收脫貧。創新森林資源利用方式,將貧困戶林地中具有碳匯功能的樹林集中,利用森林資源實施碳匯交易扶貧。依托貴州各地生態資源稟賦,引進企業開發項目,流轉當地農戶土地資源的方式,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的產業扶貧,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的同時,延伸了農業產業鏈。貧困群眾通過入股分紅、園區務工等方式提高收入。農村扶貧效果顯著提升,推動貧困地區實現區域性整體脫貧。貴州六盤水率先開展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通過有效整合農村資源,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成為全國農村改革典型模式,得到大力推廣[9]。
2.3 實施生態保護工程項目,提高貧困人口受益程度
貴州通過實施生態保護工程項目,創新生態建設和生態補償資金使用方式,貧困群眾在生態補償、生態公益崗位等得到政策性幫扶。貴州省退耕還林向貧困地區傾斜,通過退耕還林還草和種植業結構調整,切實加強森林經營,加強造林全過程監督管理,全面保護和恢復濕地資源等方式,大大提高了森林覆蓋水平,減輕了自然生態災害等風險。退耕還林、以工代賑扶貧、生態公益性崗位扶貧等也推動了貧困地區勞動力就業,增加了貧困人口政策性收入,改善了貧困人口的傳統生計模式,實現生態保護與貧困人口脫貧增收的共贏。率先探索“生態護林員+貧困戶”模式,通過聘用貧困群眾擔任生態護林員的方式,為當地貧困人口和家庭提供就業機會[10]。2020年,貴州全省累計選聘了18.28萬名生態護林員,按照生態護林員每人每年收入1萬元的標準計算,每個護林員帶動3人實現脫貧,該政策已帶動50余萬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在維護森林生態系統安全的同時緩解了當地就業壓力。
2.4 易地扶貧緩解生態壓力,改善移民生產生活條件
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工程,為改善貧困地區自然生態系統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搬遷貧困人口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和發展條件。為緩解喀斯特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的省情,因地制宜實施了跨行政區域的搬遷政策,讓遷出地自然生態系統得以修復,同時政策傾斜幫助遷入地人口就業和發展。對于生存環境惡劣的地區,使貧困人口從生態貧困的惡性循環中擺脫出來,對遷出地實施生態修復和治理,大幅提升了自然生態系統質量。對于生態功能重要的地區,貴州實施了自然保護區的易地扶貧搬遷,通過生態移民減少自然保護區生態壓力和生態破壞,同時對搬遷貧困人口進行生態補償脫貧。立足貴州山地高原為主、人地矛盾突出的特點,貴州將易地扶貧搬遷與縣域產業結構調整、城鎮建設統籌考慮,實施城鎮化集中安置為主要方式,引導貧困人口實現再就業,保障搬遷群眾在安置地就業,確保搬遷群眾后續生產生活實現可持續發展[11-12]。城鎮化建設和農村人口轉移,降低了農村土地資源等的開發程度,緩解生態系統承載壓力。異地遷出幫助減輕環境壓力,加快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發揮勞動力廉價優勢。城鎮集中安置有利于產業規模化發展,優化區域人口、產業集聚和空間布局,大幅改善了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
2.5 以大數據賦能綠色發展,有效提升生態扶貧成效
以大數據賦能綠色發展,推動大數據與大生態的協同發展,探索大數據技術與生態環境治理的有機結合途徑。通過建設生態環保大數據等信息化平臺,以海量數據資源為支撐創新治理模式,建立環境在線自動監控系統等,實現生態環境檢測全覆蓋,打造智能化生態治理體系。以貴州石漠化治理為例,通過石漠化在線監控體系,對不同類型石漠化地區進行監控、分析和識別,為石漠化治理提供技術支撐和科學指導,治理成效顯著提高,實現大數據賦能石漠化治理的模式優化。依托大數據先發優勢,推動生態產業化發展,加強生態農產品、地理標志產品的認證和宣傳,打造貴州知名生態產品生產基地,探索了“大數據+生態農業”“大數據+生態旅游”等扶貧模式。在精準扶貧過程中,收集貧困人口、扶貧項目等相關數據,建立貧困人口的大數據檔案和監測指標體系[13]。通過開發單株碳匯精準扶貧大數據平臺,在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的基礎上實現貧困人口增收。
3 結語
生態扶貧是精準扶貧時期實現貴州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資源稟賦良性互動的雙贏策略。貴州在發展過程中長期面臨著脫貧致富與生態保護的雙重任務,貧困治理與生態治理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貴州生態扶貧的實踐探索,在全國同類地區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在生態工程建設扶貧、生態公益性崗位扶貧、生態產業及生態資源扶貧、生態保護補償扶貧、生態移民搬遷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績。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推動貧困地區由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轉變,生態環境保護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將生態扶貧融入到鄉村振興,結合生態扶貧實踐中積累和總結的寶貴經驗,探尋鄉村振興與生態扶貧的互促互進之道,助力新階段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協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