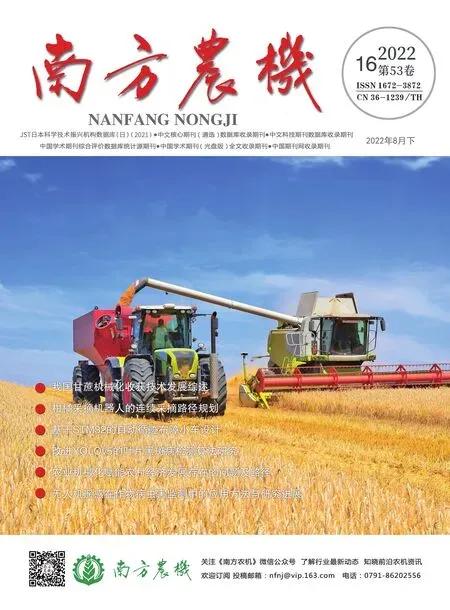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山西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及開發路徑*
徐 佳 ,宿佳佳 ,李笑曉
(晉中信息學院,山西 晉中 030800)
0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2月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指出,農耕文化是我國農業的寶貴財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不能丟,而且要不斷發揚光大。2017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發布,對做好“三農”工作進行了指導。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對確保農業穩產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具有重大指導意義。挖掘、開發和利用農業文化遺產,能夠聚焦鄉村特色產業,傳承優秀農業文化傳統,推動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助力鄉村振興。
1 山西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
山西地處黃河中下游,地形地貌復雜、山川河流匯聚等自然條件使其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是華夏農耕文明的發祥地,故有“五千年華夏文明看山西”之說。山西的傳統農業歷史文化資源豐富多樣,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深入挖掘山西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有利于更好地感受傳統農耕文明的魅力[1-2]。
1.1 歷史文化價值
農業文化遺產是古老的農耕智慧,是傳統的歷史文化,是先民的生產經驗。幾千年農耕文明的歷史在山西書寫:神農、炎帝“嘗遍百草、立食五谷、制作農具、開創農耕”的說法可在山西尋根;下川遺址、曲沃方城遺址等地區出土的文物證明了原始農業從山西發源;農作物種植、種桑養蠶、農業工具的演進等農業發展由山西見證;古籍字畫里的牛耕方法、水利灌溉工程、旱作梯田系統等農業生產從山西輻射……山西的農耕文化歷史久遠,文化遺產內容豐富,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
1.2 生態環境價值
農業活動的開展離不開區域自然環境,豐富的物種資源是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要特征。山西地處黃河中下游、太行山以西,大部分地區被黃土覆蓋。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有利于服務生態,如陽城蠶桑文化系統在水土保持、提高土地利用率、維持農業發展、改善黃河水系等方面都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挖掘、保護山西農業文化遺產,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推動農村生態文明建設。
1.3 產業經濟價值
農業文化遺產在發展特色農產品品牌和品種資源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能夠推動農村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為鄉村振興賦能。山西擁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和傳統生產技法,如2017年被認定為“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稷山板棗栽培技術。2018年,稷山縣板棗生產總量達5 000萬公斤,相關產業總產值超10億元,為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2 000元以上。目前,稷山縣已建成國家級農業觀光示范園區,帶動規模化種植,打造品牌、保證品質;延長產業鏈條,提高板棗產品附加值;此外,稷山縣還積極利用電子商務平臺拓寬板棗的銷售渠道。稷山板棗除在全國暢銷外,還銷往海外十余個國家。這種鏈式文化產業,實現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助力了鄉村產業振興。因此,農業文化遺產中獨特的品種資源和生產技術可為農民增收和產業化經營提供良好的條件,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2 山西農業文化遺產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悠久的農業歷史、豐富的傳統文化和獨特的地理環境等使山西農業文化遺產具有獨特性和巨大的發展潛力。然而,與黃河流域的其他省份相比,山西的農村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群眾還未充分認識到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對其的保護和開發情況也不容樂觀。
2.1 發展現狀
黃河流域承載著燦爛的農耕文明,是中華民族的農業文化中心。古老的黃河自西向東分別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及山東等9個省(自治區),最后流入渤海。據統計,截至2022年5月,該流域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4處(我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總數為18項)、農業農村部認定第六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38處,可見黃河流域留下的農業文化遺產仍在延續。黃河兩岸遍布輝煌燦爛的文化,而山西省入選前六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僅有2處,即山西稷山板棗栽培系統(入選第四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認定名單)、山西陽城蠶桑文化系統(入選第六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認定名單)。根據農業農村部關于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單[3],四川、山東等地的農業文化遺產數量分別為8個和7個,換言之,與黃河流域的其他省份相比,山西農業文化遺產仍有較大的挖掘空間。
近年來,山西積極響應農業農村部的相關發展政策,深入貫徹落實關于“加強農耕文化傳承保護,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要求,對全省農業文化資源進行普查,其中就包括各類農業文化遺產。同時聯合相關科研院所、專家技術團隊加入2022年的普查工作,為該工作提供了強大的技術后盾。可見,政府相關部門在不斷推進傳承優秀農耕文化、發掘豐富農業文化遺產資源的工作,為推動鄉村振興作貢獻。
2.2 存在問題
黃河流域有著得天獨厚的農耕文化資源優勢,農業遺產資源豐富,然而山西地處黃河流域中段,整體經濟發展緩慢,對地區農業文化資源的重視程度、支持力度以及產業模式本身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2.2.1 資源挖掘的力度不足
黃河作為農耕文化的核心區域,有著不可比擬的資源優勢。但各省對經濟發展各有側重,山西對農業文化資源的開發程度明顯不足。作為煤炭資源大省,山西在經濟轉型發展中想要完全擺脫對煤炭資源的依賴十分困難。同時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深受影響。再加之該地區對農業文化遺產的認識程度不高、保護意識不強,即便有豐富的文化遺產,也未將其轉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因此,要進一步挖掘山西本土的傳統農業文化。除了已經進入2016年全國農業文化遺產普查名錄的臨猗江石榴栽培系統(運城)、沁州黃小米種植系統(長治)、壺關旱作梯田系統(長治)、平順大紅袍花椒栽培系統(長治)、神池莜麥種植系統(忻州)等幾項外,其他重要的農業產地以及農業體系同樣承載著獨特的農業歷史文化傳統,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投身其中,做好農耕文化傳承保護與開發利用工作。
2.2.2 多方參與、合力保護的意識不強
2018年山西省農業農村廳劃撥6 000萬元補貼農村農林文旅康產業融合發展,其中一部分資金用于支持農村傳統文化保護、農業文化遺產開發。但由于采取“先建后補”的方式,項目在具體實施中的補助資金有限。2019年山西省財政廳為了保障基層農村文化建設,下達農村文化建設中央及省級資金近2億元。2021年,山西省財政廳更是投入270余億元支持農業發展。然而,對比2022年年初武漢市專門針對浮梁茶文化系統而投入農業文化遺產專項資金,山西省并沒有設立常規的專項資金,即便是政府前期投入了大量資金支持,后期地縣本身的財政壓力也會制約項目的發展。因此,在具體的保障政策方面,政府要為農業文化遺產資源的保護和開發營造更好的政策氛圍,并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助力農業文化遺產項目農產品建設,推動鄉村振興,帶動本省經濟發展。
2022年山西下達農業文化遺產的普查工作,鼓勵各市、縣(市、區)農業農村部門聯合相關科研院所、專家技術團隊組織開展跨地區農業文化遺產資源普查工作。申報的過程對團隊和學術研究的要求較高,需要專家評審和專業人員指導。山西大學、山西農業大學等高校有許多對山西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作出了貢獻的專家學者,但山西高校并未設立專門從事該研究的專業,故該領域實際的專業人才有限,缺乏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的助推力。因此,山西省要加大在資源管理和研究方面的投入,可以借鑒江蘇和浙江等省份的經驗,在申請全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時聘請知名專家學者成立專門的科研團隊,有層次地開展調研并提供咨詢及指導。
民眾對文化遺產重要性的認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優秀農耕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當前,在山西省部分具有優勢資源的區域,農民對于傳統歷史和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比較欠缺,未能做到自覺保護優秀農耕文化。此外,主流媒體的宣傳引導可以增加大眾的認同感,因此也需要借助媒體的力量,加強宣傳引導。
2.2.3 特色農產品的利用能力不高
山西省的蘋果、核桃、陳醋、小米等是全國乃至世界的知名品種,然而,雖然山西省擁有眾多特色農產品,但是缺乏既有深厚農業文化傳統,又可以對生態環境、區域經濟發展、鄉村振興起到推動作用的產業模式。例如,“平遙牛肉”“寧化府陳醋”等老字號雖然擁有知名度,但是并沒有將農產品與其文化價值相融合,優質農產品缺乏品牌特色,故難以占領市場。此外,山西省擁有豐富的雜糧資源、果蔬資源、中藥資源,但是這些特色項目的發展轉型存在難題,即產業鏈條短,產品難以實現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轉變。如平順大紅袍花椒、沁州黃小米等產品不僅是尊重自然規律的優良品種,還承載著厚重的農業文化歷史,但該區域的農業產品深加工創新、品牌效應推廣、相關產業鏈帶動等能力存在明顯不足,缺乏對產品更深層的研究和宣傳,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功能性食品或相關農業旅游的途徑少,難以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助力。
3 山西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路徑
結合山西農業經濟發展實際情況、講好“山西故事”,需充分依托黃河滋養下的山西本土農業文化遺產資源,推廣山西地域文化,推動鄉村經濟發展。
3.1 挖掘農業文化遺產的潛在優勢
山西擁有悠久的農耕歷史文化傳統,其文化底蘊造就了農業文化遺產的獨特價值和開發優勢。除2016年全國農業文化遺產普查結果的項目外,山西省還要加強其他農業生產系統、農業技術方法、農業村落等資源的普查、整理工作。山西是傳統中醫藥文化大省,“山西藥茶”歷史悠久。早在“十三五”時期,山西省就針對晉東南豐富的野生中藥材品種作出了發展規劃;“十四五”時期更是堅持傳統旱作和現代農業相結合,建立以有機旱作和中醫藥產業為特色的集群化發展模式,打造綠色安全、健康營養的中醫藥產品。山西小雜糧品種豐富,素有“小雜糧王國”之稱。以忻州地區為例,該區域的繁峙縣被譽為“中國黍米之鄉”、岢嵐被稱為“中華紅蕓豆之鄉”、寧武是“中國高原莜麥之鄉”……可見該地區農業文化豐富,值得研究[4-5]。此外,山西北部的雁門關是畜牧業發展的重要基地,該地區擁有青貯玉米、燕麥草、苜蓿等優質牧草資源,其農牧系統也值得展開調研。“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谷香”,要充分挖掘山西農業文化遺產的潛在優勢,實現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的有機統一。
3.2 健全多方聯動的合作機制
相比于四川、云南、湖南、江蘇等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數量較多的省份,山西省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開發工作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因此,山西省政府部門及其相關單位更應切實領會國家關于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和鄉村振興戰略的精神,發揮組織引導的作用。在推動農業文化遺產所在地的資源開發和利用中,要充分發揮研究院和專家學者的力量,加強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指導工作,對優勢資源和基礎較好資源的開發進行因地制宜的設計和規劃。發揮已成功入選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的引領與示范作用,對作出貢獻的企業進行鼓勵,吸引民間資本投入更多項目的開發中,形成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的合力[6-7]。要對農業文化遺產相關的農業旅游進行長期監管,促進鄉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此外,還要借助媒體的力量,對項目開發的進展進行宣傳推廣,及時總結遺產保護和傳承實踐中的經驗做法,營造保護、傳承、開發、利用農業文化遺產資源的良好氛圍[8]。
3.3 創新產業融合發展模式
農業文化遺產本身是以農業生產系統為基礎的傳統第一產業(傳統作物和特色品種生產),要基于其文化、生態、經濟等價值,在資源發掘利用的過程中發展第二產業,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同時借助鄉村文化振興和產業振興的政策便利,發展農業文化宣傳和生態旅游、農產品地理標志等第 三產業。例如,曾入選第四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單的稷山板棗栽培系統就積極創新發展模式,以農民豐收節為契機,讓“后稷農耕文化”真正“活”了起來。稷山板棗示范園“標準化生產+銷售深加工+文化節”的產業融合發展模式,為山西省探索其他農業文化遺產資源提供了寶貴經驗。
發展特色農產品,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積極推動農業文化遺產資源區域的品牌建設[9],加強地理標志農產品品牌推廣。通過農產品地理標志,提高農業文化遺產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增強市場競爭力。將蘊含傳統山西農業文化的元素植入特色農產品的品牌建設中,打造耳熟能詳、朗朗上口、充滿歷史底蘊的品牌,讓農耕文化真正推動農產品品牌創新,更好地打造晉字號特優農產品品牌。
發展農業文化旅游,開發具備地方農業文化資源的特色、休閑旅游產品,多層次、多維度地挖掘農耕傳統、鄉村民俗等獨特文化,加大農業文化遺產的推廣和宣傳力度[10]。
4 結語
傳承和保護黃河流域優秀的農耕文化傳統,深入挖掘本土農業文化遺產的潛在價值,大力支持山西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同時積極開展產業融合發展創新模式,形成政府、農業研究所、專家團隊、當地農戶、中小企業等多方聯動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機制,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農產品品牌,發揮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為山西農業經濟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注入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