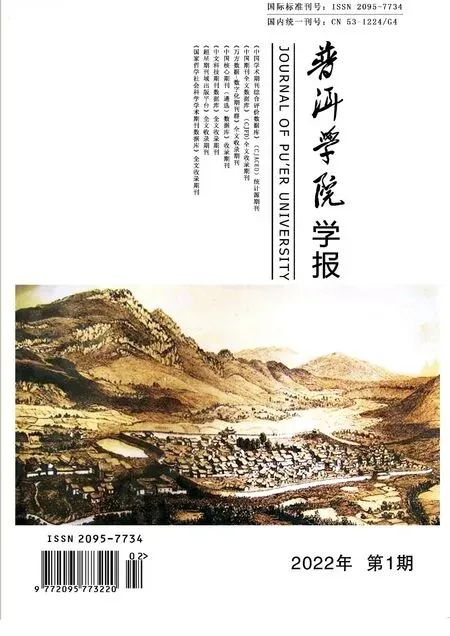莫言小說《生死疲勞》的敘事特征與藝術張力
潘 應
皖西學院,安徽 六安 237012
《生死疲勞》是莫言著名的社會諷刺批判小說。小說敘述了從解放后到20世紀末的50年中,中國農村的故事。小說主要圍繞農村的社會環境進行藝術展現,在敘事主角和敘事視角的設定上,采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大量采用動物和轉生的視角,使故事的闡述更加離奇,也更具有震撼力。《生死疲勞》這種不同于一般敘事方法的獨特藝術,產生了豐富的藝術張力,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解放后一段時間里中國農民復雜的精神世界。
一、《生死疲勞》的創作背景和寫作目的
(一)《生死疲勞》的創作背景
《生死疲勞》的創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莫言先生曾說最先是在腦中醞釀了許久關于主角“西門鬧”的故事,但始終無法給這個故事一個完整的創作思路和創作邏輯。直到先生在旅行的過程中看到了當地一個有名的廟宇,在廟宇的壁畫上了解到“六道輪回”的故事后,才確定了《生死疲勞》的創作模式和敘事模式。而《生死疲勞》這一名稱的來源,則是取自于佛經中的一句“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1]。莫言認為佛經說的是,當人們有欲望的時候,就很難與命運抗爭。因此莫言定下了“生死疲勞”這個名字,希望借由“六道輪回”的框架,通過“西門鬧”的六道輪回,結合每個時代的特點,用動物的視角,感受幾個特定歷史環境下不同的生活狀態。可以說,《生死疲勞》的創作背景起源于莫言對于特定歷史環境的感悟。小說的標題與創作模式的選擇,既源于佛教理論,也暗含了作者自身對于人性的理解。
(二)敘事策略與技巧背后的寫作目的
小說家們創作文學作品,大多是對人生或者某個生活現象產生了感悟,他們希望通過文字的形式,將這種感悟轉換成虛構的故事,故事中又包含著作家的思想情感,如此更加有效地將作家對于事物的感受通過創作傳遞給更多的人。《生死疲勞》的作者莫言,最開始就是想要講述50年間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狀況,國內關于農村發展題材的文學作品數量不少,這類作品大多采用以人為視角進行切入的敘事手法。而國內很多讀者對這類敘事手法產生了一定的審美疲勞。基于此,或許是為了突出作品的特殊性,亦或是為了將主題上升到更加宏觀的層面,莫言選擇魔幻想象的敘事策略,在技巧上靈活又鮮明地借助動物的視角,對農村社會發展階段的各個現象進行文學性的表述。莫言認為,他力求用一種最自由、最沒有局限的語言來表達其內心深處的想法。莫言希望通過這種魔幻的敘事手法,用一種不沉重的方式來圍繞土地這一沉重的話題,闡述農民與土地之間的復雜關系。
二、《生死疲勞》的敘事特征
(一)獨特的敘事主角
《生死疲勞》采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一個被冤枉而死的地主西門鬧經歷了六道輪回,分別以驢、牛、豬、狗、猴的形象轉世,最后又轉世為一個具有不可治愈疾病的大頭嬰兒藍千歲[2]。故事就是從這個有頑疾的大頭嬰兒藍千歲的口中說出,他滔滔不絕地講述著自己身為動物時,在農村里看到的人和事,表達著動物視角中對人與社會的看法。與一般小說不同,《生死疲勞》雖然是以人作為敘事的主體,但實際上的敘事主角卻是不同的動物。這種獨特的敘事主角,令《生死疲勞》在敘事姿態上也比較特殊,簡單來說就是《生死疲勞》的敘事姿態會更低一些,由此充滿了藝術靈氣。地主西門鬧認為自己并不是一個壞人,世人認為他有錯,不過是因為他擁有別人所沒有的財富。于是他帶著枉死的痛苦到陰間索求公道。或許是為了還他一個所謂的公道,西門鬧六次轉世為不同的動物,但都沒有遠離過西門家族土地的范圍。上天給了西門鬧動物的眼睛,他可以隱藏在普世之中繼續觀察人世。莫言塑造了獨特的敘事主角,用荒誕的主角形象隱喻了農民們頑強堅韌的生命力。而形象和內在隱喻在觀感上的沖突,也為讀者們預留了更多的想象空間[3]。
(二)多元的敘事視角
《生死疲勞》的敘事視角比較多元,這里的多元一方面指的是在主線故事中,作者采用了多個敘事主角去闡述故事。另一方面也指的是論述整個故事的過程中,作者并沒有完全以西門鬧和西門鬧的轉世作為唯一的敘述者。《生死疲勞》還出現了以其他人物為主的情節,藍臉、藍解放、作者本人、大頭嬰兒藍千歲都曾經參與主要的敘述。這樣,小說的論述視角比較多元、范圍也比較廣,不會出現過于主觀化的情節。這種多元敘事視角的采用,可以將不同身份的讀者代入其中,敘述的靈活性大大增強,故事的可讀性和趣味性得到提升。《生死疲勞》講述的是中國50年來農村社會發展的故事,而農村社會環境的特征就是人員復雜、競相發聲且人聲喧嘩。多元的敘事視角,可以通過不同角色、不同立場的“口述”,營造一個喧嘩的話語空間,令讀者恍惚間可以切入到書中視角中,和村中人一同思考。
(三)魔幻的情節設置
《生死疲勞》的故事背景是解放后50年間的農村社會,表面上屬于現實類題材。但莫言采用了魔幻的情節設置,將人性和社會的故事,放在一個魔幻的框架之中。這個框架就是“六道輪回”。所謂六道輪回是佛教用語,佛教認為六道輪回是痛苦的輪回,人的痛苦就是因為有貪欲,才使人無法與命運抗爭。作者設置魔幻的情節,表面上令整個敘事邏輯變得更加抽象[4]。但實際上是采用了一種代指的敘事方法,令故事的精神核心能夠表達地更加純粹。小說在所謂的六道輪回魔幻結構中,帶領讀者不停地在人的視角和動物的視角中穿梭,在用魔幻的視角純粹地闡述人性本身、人性與社會的關系,同時去觀察和體悟農村的變遷。在動物的眼中,西門一家、藍臉一家、洪泰岳之間發生的事情都非常夸張,甚至夸張到有些吊詭。但這種吊詭不是為了突出情節的離奇或特殊,而是為了將龐雜喧嘩的苦難加以具象。故事的后期,西門鬧經過六次轉世,已經漸漸放下了他心中的哀怨和怒火,陰霾已經過去,新時代的曙光已經來臨。讀者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角色身上時,也通過閱讀小說一起經歷了農村社會的發展變遷,尤其對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農民和社會的關系會產生深刻的理解。
三、《生死疲勞》的藝術張力
(一)暢快的隱喻
《生死疲勞》作為一部農村題材的當代小說,在敘事上并沒有采用傳統模式,而是使用魔幻敘事手法。這使得作者莫言在書寫的過程中,思維的流動更加暢快肆意。傳統的文學寫作或多或少使作者存在一些顧慮,例如不能出現指向性過于明顯的角色或情節,不能對某個事件或現象進行過于主觀的判斷和描寫等等。這些顧慮是結合現實情境和文學創作既有規律而產生的必然性考慮。雖然很多作家往往對這些社會敏感問題并沒有過多的想法,也沒有想要在作品中刻意傳遞某種思想。但作品的發表往往就伴隨著人們的深度解讀,被誤解也通常被人們認為是一種表達的隱喻。這使得作家們常常被思慮束縛,從而影響他們在創作時的自由,作家們的想象力無法有效展開。對此,作家莫言在思考“西門鬧”的故事時,也是久久囿于如何描寫的思維困境之中。直至看到了寺廟中“六道輪回”的內容,才決定將“六道輪回”作為小說的設定,為自己思維的快意書寫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莫言表示,這種敘事方法就是要用最自由、最沒有局限的語言來表達內心深處的想法。的確,采用了魔幻色彩的隱喻手法后,莫言在表達自己對于鄉土的感情、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時,內容更加暢快大膽。而這種披著魔幻外衣的暢快抒發,自然就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張力,不僅釋放了作者的創作壓力,也釋放了讀者的熱情[5]。
(二)主動的反思
事實上,一般的鄉土文學作品中的主角,都會顯得非常“可靠”。即使是在設定上并不那么可靠的壞人,如果他“壞”的模式比較糾結或者非常徹底,那么讀者也可以認為這個角色非常可靠。并且可以將這個人作為標桿,去分析其他人的言行、性格。但《生死疲勞》與其他作品不同,《生死疲勞》的主角西門鬧不具有這種可靠性。西門鬧作為人而存在的時間較短,讀者甚至沒有時間去判斷這個人的性格和言行。而隨后西門鬧的幾次轉世,又是從藍千歲這個大頭嬰兒的口中說出,這就使得故事變得更加離奇。這種特殊的魔幻風格,會令讀者的思維變得緊張。讀者會主動地記憶前后文,積極驗證前后文邏輯是否對接,藍千歲的言論是否是客觀正確的。這就好比作者直接把道理拆開來呈現給讀者,幫助讀者省去反思和思慮的過程時,讀者就無法產生更直觀和深刻的印象。但如果作者引導著讀者懷疑故事內容,那么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受到的沖擊就會更直觀和深刻。因此,《生死疲勞》所選用的敘事特征,形成了獨特的引人反思的藝術張力。
(三)肆意的反諷
《生死疲勞》采用了多元的敘事視角,也就是敘事格局并未局限在主角的身上,而是穿梭在不同的人物中,借由性格不同、立場不同的人物,繪制了一幅覆蓋全面、包羅萬象的鄉村世界。整部小說中,雖然表達思想觀點的情節細節特別多,但這些批判反諷的話語往往會同時出現在兩個對立者的口中,這就在形式上消解了作者的“態度”,一些比較刺眼的話語不至于引起讀者的反感。因此,《生死疲勞》能夠借助情節或者某個角色的話語權,對不同的階層的不良現象進行反諷。另外,《生死疲勞》并不強調歷史的真實性,并且在描述他人時,會經常使用不屬于這個時代的例子,如形容洪泰岳是打壓過吳三桂的人等等。作者通過變化的敘事視角,大膽地對當時的社會問題進行諷刺,例如作品中對洪泰岳一類人的諷刺。這種看似膽小、實則肆意的諷刺,也賦予了《生死疲勞》獨特的藝術張力。
四、結語
敘事的淺層含義就是說清楚一件事,而大多數作家對于敘事的理解也是如此,即認為敘事只是通過文字來描繪一個場景、說清楚事件。但真正有文學價值與美學張力的作品,絕不僅僅做到了簡單的敘事。莫言的《生死疲勞》就超脫了敘事本身,它利用動物的視角,更加毒辣直白地講述了“那個環境”的真理和規律。《生死疲勞》的敘事視角并沒有完全集中在一個點上,而是不停地在現實和魔幻中穿梭,時而以動物的眼光呈現,時而以人的視角闡述,也會闡述動物眼中的人以及人眼中的動物。這種多元多變的敘事視角,避免了讀者局限在某個思維邏輯內,從而采用更加辯證的眼光去看待某個時代所發生的問題,繼而對歷史、農民、人性產生更加獨特深刻的感悟。綜合來看,莫言的《生死疲勞》的確是一部敘事手法奇特、藝術張力豐富的文學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