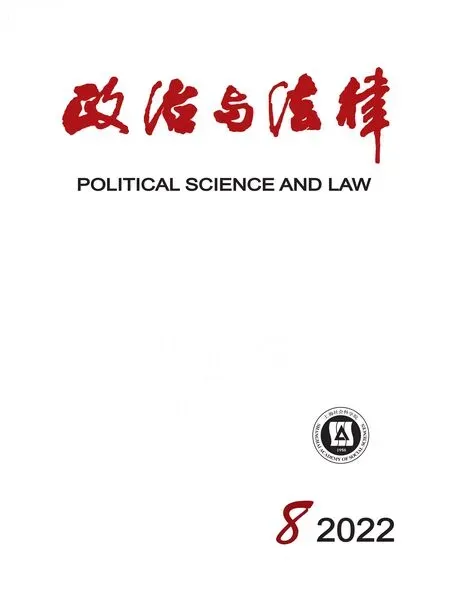論賄賂犯罪的差序法益構造
李世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浙江杭州 310008)
一、問題的緣起
我國《刑法》分則第八章規定的賄賂罪是典型的對合犯,然而,無論是行賄人還是受賄人都不是被害人,因為行賄人自愿向受賄人行賄,受賄人收受了賄賂,而行賄人則獲取了不正當利益。據此,賄賂罪所侵犯的法益必然不是個人法益,而屬于集體法益。〔1〕關于個人法益與集體法益的關系,參見孫國祥:《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及其邊界》,載《法學研究》2018 年第6 期。賄賂罪保護法益的確定,應當穿透行賄人與受賄人形成的交易關系,考察該交易關系在公共層面上的最大射程范圍。
長期以來,我國刑法學界都在積極探尋共通于賄賂罪的保護法益從而建構統一的賄賂罪教義學體系,形成了諸多具有代表性的觀點,〔2〕參見王志成:《懲治貪污賄賂犯罪的有力武器》,載《政治與法律》1988 年第5 期;馬春曉:《廉潔性不是貪污賄賂犯罪的法益》,載《政治與法律》2018 年第2 期;錢小平:《我國懲治賄賂犯罪立法檢討——以積極治理主義為視角》,載《法商研究》2018 年第1 期。概括起來主要有職務廉潔性說、〔3〕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第635 頁。職務行為的公正性說、〔4〕參見黎宏:《受賄犯罪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 條的解釋》,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1 期。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說、〔5〕參見張明楷:《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載《法學研究》2018 年第1 期。職務行為的不可謀私利性說〔6〕參見勞東燕:《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載《法學研究》2019 年第5 期。等。這些學說雖然表述各異,但都將賄賂罪的法益內容聚焦于賄賂與職務行為或與職務密切相關的行為之間的對價關系上。〔7〕參見[日]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三版),成文堂2015 年版,第846 頁以下。這樣,這些觀點在對賄賂罪基本構造的理解上始終沒有跳出行賄人與受賄人所處的風眼區,只是在更側重從行賄人還是從受賄人的視角出發考察賄賂對職務行為的影響這一點上有所區別。
筆者嘗試跳出行賄人的賄賂物與受賄人的職務行為形成的對價關系這一圈子,從客觀中立的第三人視角考察賄賂這一對價關系的對外波及效應及其最大射程范圍,展示賄賂犯罪的差序構造,在此過程中說明賄賂罪侵犯國家法益的性質及其法益的具體內容。
二、既有觀點的癥結:忽視賄賂犯罪的差序構造
國家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呈現出了“國家——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民”這一金字塔型構造。我國有學者借助韋伯的支配社會學這一分析工具闡釋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雙重身份。具體而言,國家支配的權力及其手段不是交給官員個人的,而是分派給 “職位”,官員能夠代表國家行使支配的范圍以職位的權限為界,國民個體對官員的服從也以官員的權限為界。〔8〕參見楊利敏:《論韋伯社會理論中現代國家的特質與實現》,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 年第2 期。于是,擔任公職的人員不可避免地具有雙重身份,即作為公共職位的占有者與作為對私域享有自主權的個人,正是由于公法上的人格寄居在具有私欲的個人身上,才會出現腐敗問題。〔9〕參見勞東燕:《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載《法學研究》2019 年第5 期。
可以說傳統的關于賄賂罪保護法益的各種觀點基本上都是從因賄賂而形成的權力與金錢之間的交易關系這一點出發來論證的,因此這些觀點具有公因式可以提取,那就是禁止這種權錢交易關系的形成。筆者完全認同賄賂在形式上表現為職權與金錢的交易關系或對價關系,或國家工作人員以權謀私。然而,如果將賄賂罪的保護法益求諸于禁止這種權錢交易,則可能產生以下疑問。
第一,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說是對賄賂這種現象的直觀描述,禁止權錢交易只是隱藏于賄賂罪構成要件背后的行為規范,該行為規范雖然指向將來的法益保護,但其本身無法直接作為賄賂犯罪的法益內容,否則將陷入循環論證。〔10〕行為規范是面向將來的法益保護而設定的,因此在判斷是否違反行為規范時,應與法益相關聯進行判斷。參見[日]高橋則夫:《刑法總論》,李世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 頁以下。
第二,公職不可謀私利性說的更準確表達其實是國家公職人員的不可謀私利性。然而,如果將此作為賄賂罪的保護法益,則可能將國家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貪腐人格作為刑事制裁的目標,從而存在違背行為刑法基本立場的嫌疑。具體而言,公職不可謀私利性說的主張者認為,受賄犯罪的交易關系并不是發生在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而是發生在受賄人的職位所蘊含的公權與其所撈取的私利之間。〔11〕參見勞東燕:《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載《法學研究》2019 年第5 期。從該觀點出發,只要國家公職人員基于貪念收受財物即可認定受賄罪的成立,因此,事前受賄、事后受賄、斡旋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感情投資受賄等行為類型均可納入處罰范圍,國家公職人員是否實際上為他人謀取利益也在所不問。然而,這種表面上具有廣泛解釋力的觀點是建立在國家公職人員貪腐人格的基礎上,據此,收受財物的外在行為只是這種貪腐人格的外化而已。然而,如果脫離了為賄賂犯罪的客觀不法提供支撐的存在論構造,單純用“以權謀私”的貪腐人格這一意義上的主觀不法填充賄賂犯罪之不法內涵的話,將導致賄賂犯罪實行行為的空洞化,陷入主觀歸罪的泥潭。〔12〕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有學者以扒竊為例指出我國刑法從客觀主義向主觀主義回歸,從行為刑法向行為人刑法轉型的端倪,但該觀點仍然首先在存在論與規范論二元區分的范疇內肯定扒竊“裸”的事實存在并肯定其主觀不法,然后再進一步考察扒竊行為的主體性人格表現。參見梁根林:《但書、罪量與扒竊入罪》,載《法學研究》2013 年第2 期。
第三,職務行為的公正性說認為規定賄賂犯罪的目的在于防止將職務行為與賄賂置于對價關系之下,從而在賄賂的影響之下做出職權行為,進而不公正地行使裁量權。據此,賄賂犯罪的處罰對象是:由接受賄賂這種手段行為所引起的對職務行為公正性的侵害及其危險。〔13〕參見[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 版),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719 頁。相比于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說和公職不可謀私利性說,職務行為公正性說已經邁出權錢交易圈子的第一步,以該交易關系的存在為震中,試探性考察交易的外部影響。但遺憾的是,該學說歸根結底還是將“公正性”的內容束縛于公職人員實施的職務行為上。
據此,賄賂犯罪背后的行為規范是禁止賄賂,即禁止行賄人與受賄人通過賄賂形成交易關系。然而,法益內容是確立該行為規范最終將要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行為規范本身。那么,在確定該目標的過程中就有必要考慮與該行為規范相關的出場人物,首先當然是作為加害人的行為人以及作為被害對象的被害人,但并不僅限于此,而是從各自的關系人出發擴散到區域社會等公共層面上,進而,擴散到社會及國家層面上,犯罪就是這種從私人的事情到公共的事情派生出來的,這也是刑法應當被認定為公法之所在。〔14〕參見[日]高橋則夫:《刑法總論》,李世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 頁以下。簡言之,法益內容的確定就是探尋從加害人與被害人的互動關系延伸出的對于區域社會、集體社會乃至國家的逐層影響。這一點對于諸如故意殺人罪這種被認為是侵犯個人法益的犯罪尚且有指導意義,更不用說對于賄賂犯罪這種公認的侵犯國家法益的犯罪。
需要說明的是,將刑法置于公法框架下考察的話,任何犯罪在事實上都會形成“加害與被害的互動關系——社區——社會——國家”這一波瀾效應。而法益是在該事實性效應的基礎上規范性確立行為規范所指向的目標。于是,對于諸如故意殺人罪這種典型的侵害個人法益的犯罪而言,無論是立足于個人還是社區還是社會抑或是國家,對國民的生命法益的保護都是其共同目標,換言之,法益內容在因殺人行為而形成的差序構造中是重合的。但對于諸如放火罪等侵害社會法益的犯罪而言,在因放火行為而形成的差序構造中,禁止實施放火行為對于個人與社會顯然具有不同的意義,不特定多數人的公共安全顯然包含并超越個人的人身安全。進而,在諸如賄賂犯罪這種侵害國家法益的犯罪中,在由賄賂形成的差序構造中,從平行的社會一般人、全體國民或國家的視角來看,賄賂具有不同的不法內涵,需要分別考察,但最終將統合于維護國家這一抽象人格體的存在根基這一點上。
具體而言,賄賂犯罪呈現出以權錢交易為核心的差序構造:通過賄賂形成的權錢交易關系處于最內層;接著向外擴展到第二層,即以行賄人為標準的平行的社會一般人所處的區域社會;進而波及第三層,即由全體國民所組成的集體社會;最后蔓延到作為抽象人格主體的國家層面。據此,賄賂罪的保護法益應放置于該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中進行考察。只有精確求得賄賂對不同層面的影響內容,才能建構起賄賂犯罪的不同層次的法益體系,進而在刑事政策上檢驗賄賂行為的出罪與入罪,并在解釋論上作為賄賂犯罪構成要件解釋的指針。
以下,筆者嘗試考察賄賂形成的權錢交易關系輻射到社區、社會、國家所形成的差序格局,并分別探討在各個層面上的不同法益內容以及由此形成的解釋學結論。
三、重構賄賂犯罪的法益體系
如前所述,從賄賂犯罪的差序構造出發,賄賂犯罪的法益內容也應放置于以下漸進式的三重構造中進行逐層考察。
第一重是賄賂對于區域社會的影響。具體而言,跳出行賄與受賄形成的對價關系這一圈子,立足于與行賄人處于同等社會地位即平行的社會一般人的視角,以賄賂關系形成當時的客觀情況作為判斷資料,考察該對價關系具體損害了平行的社會一般人的什么利益,或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
第二重是賄賂對于集體社會的影響。也就是考察賄賂形成的對價關系對于包括平行的社會一般人在內的全體國民所在的各個行業所產生的影響。
第三重是賄賂對于作為抽象的法律秩序人格化的國家產生的影響。這一層面的法益是建立在前兩個階層法益的基礎上,但又應當具備從國家的視角出發進行考察的內容。
(一)賄賂破壞了平行社會一般人獲取生存和自由發展資源的機會公平性
1.人的生存發展本能與資源的有限性
盧梭認為,人最首要的天性是無論如何都會維持自身的生存。〔15〕參見[法]讓–雅克·盧梭:《社會契約論》,李陽譯,作家出版社2016 年版,第5 頁。哈特以此作為不證自明的公理,推導出以下五個具有遞進關系的推論,具體而言:①維持人類生存的資源是有限的,獲取資源的過程需要付出人類的勞動,然而,②每個人獲取資源的能力有強弱之分,于是,人類在爭奪資源的過程中就很容易陷入互相傷害和算計的狀態,③意志堅強的人類甚至可以為了更為長遠和巨大的利益而犧牲目前的較小利益。于是,要避免人類自身最終走向毀滅,相互之間就必須保持自制與協力,然而,④純粹道德層面的約束顯然無法確保這一點,因為人類的利他性是有限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也是有限的。據此,⑤國家在分配資源的過程中有義務確保人與人之間大致的平等性。〔16〕參見[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許家馨、李冠宜譯,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1-176 頁。科幻小說家劉慈欣借小說人物葉文潔之口提出了宇宙社會學的兩條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斷增長和擴展,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參見劉慈欣:《三體II·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 年版,第5 頁。
在以上五個層層遞進的推論中,推論①可以說是產生賄賂現象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資源是無窮無盡的,也就不需要賄賂國家公職人員,或者說賄賂行為也不可能被視為犯罪。而推論③則從行賄人的視角出發描述賄賂的表現形式。前四點推論顯然可以作為反對功利主義的理由,具體而言,功利主義認為,對現存制度的檢驗標準和新制度的規范,便是功利原則或最大幸福。〔17〕參見[英]邊沁:《政府片論》,沈叔平等譯,商務印書館2017 年版,第33 頁。將該觀點貫徹到底的話,賄賂一方面給受賄人直接帶來財產的增加,另一方面通過受賄人職權的行使給行賄人帶來相應的資源,同時還不直接損害其他國民的財產利益,這完全符合功利主義的表達形式。然而,世界各個國家普遍地將賄賂認定為犯罪就是反對該觀點的明證。羅爾斯在尖銳批判這種功利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構建了國家分配正義的基本原則,可以說是對上述推論⑤的操作化。
2.從分配行政的視角看機會公平的實現
羅爾斯揚棄了古典的社會契約論以及功利主義,他認為契約的目標并不是選擇建立某一種特殊的制度或進入某一特定的社會,而是選擇確立一種指導社會基本結構設計的根本道德原則,即正義原則。〔18〕參見[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版,譯者前言第5 頁。據此,羅爾斯并不側重從實體上論證正義具有怎樣的內涵,而是試圖從程序上建構一條通往正義的途徑。具體而言,訂立契約的“原初狀態”純粹是一種假設的狀態,這一狀態的基本特征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正義的原則正是在這種“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后被選擇的。〔19〕參見[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 頁。在此假設狀態下,羅爾斯建構了正義的兩個基本原則:第一,平等自由原則;第二,差別原則與機會公平原則。〔20〕參見[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7 頁。
然而,這兩個正義原則并不是平面耦合式地堆放在一起,而應以詞典式次序排列。具體而言,在第一個原則中確立了自由的優先性規則,因此自由也只能為了自由的緣故而被限制,這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不夠廣泛的自由必須加強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體系;第二種是不夠平等的自由必須可以為那些擁有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與此相對,第二個原則的表述本身也確立了正義優先于傳統的功利主義所倡導的效率原則和最大限度追求利益總額的原則;而在第二原則所派生出的兩個子原則中,機會公平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這又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機會的不平等必須擴展那些機會較少者的機會;第二種是過高的儲存率必須最終減輕承受這一重負的人們的負擔。〔21〕參見[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7 頁。
由此可見,在這階層式的尋求正義之路的程序建構中,平等自由原則是正義的基礎,差別原則是正義的實現方式之一,機會公平原則是最終的落腳點和試金石。然而,機會公平本身是以機會的提供和分配為前提,而最終的分配者必然是超越個人層面的國家。凱爾森認為,國家,作為通過其機關而行為的主體、作為歸屬的主體或者作為法人,都是法律秩序的人格化。〔22〕參見[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291 頁。然而,這一虛擬的人格體所開展的活動都必須通過個人來實施,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問題就是一個歸屬問題,關于歸屬的標準,凱爾森認為:將人的活動歸屬國家,歸屬一個看不見的人格者,就是將作為國家機關活動的那種人的活動,和規定這一活動的秩序的統一體聯系起來,作為一個人格者的國家只不過是這一統一體的人格化而已,然而,只有人,或者更加正確地說,只有人的行為,才可能是法律調整的對象。〔23〕[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284 頁、第292 頁。奧托·邁耶指出:國家是一個有序的集合體,是人民為在人類發展史中展示并發揚其特征而聯合成的,為此,集合體及其目的的實現而進行的活動可以稱之為行政,即行政在最概括的意義上是指國家為實現其目的而進行的活動。〔24〕參見[德]奧托·邁耶:《德國行政法》,劉飛譯,商務印書館2016 年版,第1 頁。根據目的的種類又可以將行政作用劃分為以維持國家或公共團體的存續為目的的秩序行政、以整備和形成秩序為目的的整序行政、以生活考慮而提供給付為目的的給付行政。〔25〕參見[日]南方博:《行政法》(第六版·中文修訂版),楊建順譯,商務印書館2020 年版,第30 頁。然而,這種分類雖然便于就不同類型的行政活動或不同的行政法部門展開高效的法學思考,但這歸根結底只是一種立足于國家與私人兩級關系的“中觀”視角的考察。〔26〕參見王天華:《分配行政與民事權益——關于公法私法二元論之射程的一個序論性考察》,載《中國法律評論》2020 年第6 期。而且,這一分類也是建立在夜警國家的形象基礎上的,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在于確保市民的自由不受國家公權力的任意侵犯。〔27〕參見[日]鹽野宏:《行政法》,楊建順譯,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9 頁。伴隨著全能主義國家觀念的式微與服務行政理念的興起,國家的角色定位與行政的作用也正被重構。其中有力的觀點認為:現代政府本質上是一個公共機構,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人們可利用其具有規模效益優勢的強制力量,保護個人權利和節約交易費用,政府的職責在于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28〕馬慶鈺:《關于“公共服務”的解讀》,載《中國行政管理》2005 年第2 期。
據此,分配行政的觀念應運而生,所謂分配行政,并非與秩序行政、給付行政并列的另一個行政法部門,而是將秩序化與給付的現象囊括起來,嘗試打通秩序行政與給付行政的壁壘,它是私人間分配斗爭的表現,但這種分配斗爭不是通過私法秩序中的手段,而是以行政的決定來終結的,據此,古老的雙極行政關系擴張為三極或者多極法律關系。〔29〕參見[德]斯密特·阿斯曼等著:《德國行政法讀本》,于安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6 頁。我國有學者指出:“分配行政”是與現代行政任務的變遷相適應的,宏觀的、事關行政的現代性的一種理論觀念,如果說傳統行政法主要是解決公益與私益(國家與私人)之間沖突的“抵觸法”,那么現代行政法則是以公共性為媒介的私益間的“分配法”。〔30〕參見王天華:《分配行政與民事權益——關于公法私法二元論之射程的一個序論性考察》,載《中國法律評論》2020 年第6 期。
從分配行政的宏觀視角出發,代表國家實施符合相應行政目的之行政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化身為公共產品這一資源的分配者,而處于這一地位的分配者必然被要求基于客觀中立的立場公平公正地分配資源。理由如下。
第一,根據我國《憲法》第2 條及第27 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我國《公務員法》第2 條更是直接規定公務員是人民的公仆,負有清正廉潔、公道正派的義務。
第二,我國《憲法》第33 條第2 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據此,平等權成為公民享有的、被憲法確認的基本權利。這一方面建立起公民抵制國家侵犯平等權的防御機制,也是羅爾斯提出的正義第一原則的基礎;另一方面也賦予國家積極建立保障公民實現其基本權的義務,〔31〕參見陳征:《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功能》,載《法學研究》2008 年第1 期。因為每個公民因其個體的先天性差異或后天性因素導致公民在獲取生存和自由發展的資源過程中事實上處于不平等狀態,據此國家有義務調整這種不平等狀態,至少確保公民獲取資源的機會公平性,這成為羅爾斯正義第二原則的基礎。
第三,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國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
3.賄賂損害了平行社會一般人獲取公共資源的機會公平性
如上所述,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國民為了追求生存和自由發展必然形成相互競爭關系,而每個國民獲取資源的能力和途徑并不均衡,為此,國家有義務對該局面進行調整,以保障憲法確認的公民所享有的平等權。作為調整措施的行政行為固然多種多樣,但都應以追求機會公平為目標。從分配行政的視角出發,作為代表國家分配公共產品這一重要資源的主體,國家工作人員應保持客觀中立態度,以確保每個國民在資源分配中公平地獲得相應機會的權利。當某一國民為獲取更多的生存和發展資源而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一旦國家工作人員接受該賄賂物,便可能為其利用職務便利為行賄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提供強勢的行動理由,為此,國家工作人員在分配公共資源上本來應保持的中立客觀立場產生動搖。〔32〕拉茲認為,在對一切事情進行考慮之后,一個人總是應當出于一個不敗的理由而行動。參見[英]約瑟夫·拉茲:《實踐理性與規范》,朱學平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34 頁。伴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這一立場的動搖最先波及到與行賄人處于同等的資源競爭地位的其他平行的社會一般人這一群體,也就是說打破了這一群體進行自由競爭的局面,侵害了這一群體獲取生存和自由發展資源的機會公平性。
很顯然,賄賂是否侵害機會公平性的判斷取決于以下兩個數值的比較,即,①假設不存在賄賂關系,與行賄人處于同等地位的競爭群體獲取相應資源的可能性及其份額大小;②在賄賂關系的影響下,該競爭群體事實上獲取相應資源的可能性及其份額大小。從事后判斷的視角出發,當且僅當②的數值大于①的數值時,才能認定機會公平性受到實際損害。然而,僅從事后的視角出發進行判斷容易導向結果主義,忽視了刑法樹立行為規范的功能,也必然不當縮小賄賂犯罪的成立范圍。因此,在機會公平性的判斷上,首先應立足于事前判斷,即從平行的社會一般人的立場出發,立足于賄賂關系成立當時,以行賄人和受賄人形成的賄賂關系為判斷資料,判斷賄賂關系是否具有侵害機會公平性的危險。在此基礎上再從法官的立場出發,立足于裁判當時,以賄賂關系發生之后的事實作為判斷資料,判斷賄賂關系對機會公平性產生的實際損害。〔33〕關于事前判斷與事后判讀的對應原則,參見[日]高橋則夫:《刑法總論》,李世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58 頁以下。具體而言,在是否侵害機會公平性的判斷上,應考慮以下情形。
第一,對價型賄賂,即行賄人本來沒有獲得相應資源的可能性或可能性小,但以獲得該資源作為請托事由向相應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從而獲取了本來應屬于其他同業競爭人員的資源。換言之,行賄人所獲取的不正當利益可以直接歸屬于賄賂關系的存在。
第二,雙重保險型賄賂,即行賄人憑借自己的實力本來就應該或有較大的可能性獲取相應的資源,但為保險起見而向相應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并最終順利獲得相應資源。例如,在王林行賄案中,被告人王林雖具備相應資格并具有優勢,但為在職務調整、提拔中謀取競爭優勢,給予他人好處費17萬元。〔34〕參見云南省安寧市人民法院(2020)云0181 刑初第146 號刑事判決書。在這種情形中,如果單純堅持事后判斷,就很可能得出并不損害機會公平性的結論,然而,這一結論顯然不具有妥當性。筆者認為,這種雙重保險型賄賂是否損害平行社會一般人的機會公平性的判斷,可以參照共犯理論中幫助犯的認定規則。具體而言,從因果共犯論出發,只有當參與人實施的行為對于正犯實現的構成要件結果具有物理促進力或心理促進力時,才能認定幫助犯的成立,當否定參與行為對于正犯結果的因果促進力時,應進一步考察該參與行為對于正犯是否具有心理促進力。〔35〕參見[日]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編:《注釋刑法總論》(第一卷),有斐閣2010 年日文版,第890 頁。在雙重保險型的賄賂中,基于行賄人本來存在的相對于其他競爭者的競爭優勢,賄賂對于損害其他競爭者的機會公平性的物理促進力并不明顯,因此應進一步考察心理促進力的有無。德國學者普珀將心理因果關系理解為對他人的行動提供理由,進而指出:“當行為人給他人提供了做出某種決定的理由,則這一行為與所做出的決定之間便是存在因果關系的。即便他人做出決定還出于其他的理由,也仍然不影響因果關系的判斷。”〔36〕See Puppe,Die ErfolgszurechnungimStrafrecht,2000,S.58-59,轉引自徐凌波:《心理因果關系的歸責原理》,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18 年第4 期。將該行動理由說適用于雙重保險型的賄賂,可以容易肯定賄賂的提供對于損害機會公平性的心理促進力。這是因為:國家工作人員很難無偏私、沒有先入之見地完全從客觀中立的觀點出發酌情作出決定,而是會慮及自己收受的財物,帶著內心的負擔去作出決定。〔37〕參見車浩:《行賄罪之“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法理內涵》,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2 期。而一旦國家工作人員本來應保持的客觀中立的立場發生動搖,當然損害了其他競爭者的機會公平性。
第三,感情投資型賄賂,即一方先通過利益輸送,與國家工作人員建立起感情關系,而相隔較長的時間距離之后,再向國家工作人員提出請托事項但并不附隨財物給予。〔38〕參見車浩:《賄賂犯罪中“感情投資”與“人情往來”的教義學型塑》,載《法學評論》2019 年第4 期。在這種情形中,對于是否侵害平行社會一般人的機會公平性的判斷顯然應立足于事前判斷而非事后判斷,因為介入了“感情”這一因素,使得公共資源分配與金錢之間的對價關系并未直接顯現,而只是具備侵犯機會公平性的可能性。據此,應分以下兩個步驟進行考察。
第一個步驟是判斷行為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行為是否可以被評價為一體化的感情投資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感情投資一般都呈現出小額多次的特點,因為大額的財物給予很容易直接被認定為賄賂,而一兩次的小額財物給予尚不足以和國家工作人員建立起穩固的感情。于是,小額多次的財物給予是否可以被評價為一體化的感情投資行為關系到賄賂犯罪實行行為的認定。具體而言,在行為人同一行為意思支配下實施的,具有時空上密接性的,共同指向于非一身專屬性法益的復數行為,可以被視為一體化的行為。〔39〕參見李世陽:《刑法中行為論的新展開》,載《中國法學》2018 年第2 期。于是,可以被評價為私人之間為維持或增進感情之表達方式的財物給予行為,一開始就應當被排除在刑法的評價范圍之外。
第二個步驟是判斷感情投資行為侵犯機會公平性的危險程度。具體而言,當收受財物的一方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時,需要進一步考察財物給予方是否以建立雙方之間的感情為媒介,歸根結底是為了將來借助國家工作人員所具有的分配公共資源的職權實現增進私利之目的。在該行為意思支配之下多次反復實施的小額財物給予行為就具有共同指向于侵犯平行社會一般人之機會公平性的抽象危險性,從而具備行賄的實行行為性。但此時對機會公平性這一法益的侵犯程度尚未達到具體危險程度,因此不足以發動未遂犯的制裁規范,只有當感情投資人基于之前一體化的財物給予行為而向國家工作人員提出了具體請托事由時,對機會公平性的侵犯才達到具體程度,也才值得至少發動未遂犯的制裁規范。〔40〕筆者認為,實行行為=實行著手≠未遂犯成立。關于實行行為、實行著手、未遂犯之間的關系,參見[日] 高橋則夫:《刑法總論》,李世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91 頁以下。我國有學者指出,感情投資行為以“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為目標,處于實害犯與抽象危險犯之間,屬于一種具體危險犯。參見車浩:《賄賂犯罪中“感情投資”與“人情往來”的教義學型塑》,載《法學評論》2019 年第4 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感情投資性的賄賂而言,一旦通過一體化的感情投資行為確立行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感情關聯,國家工作人員對于行賄人的公共資源分配傾斜并不限于行賄人第一次提出的請托事由,而是將長期影響到此后一體化的請托事由,從而持續性地侵犯機會公平性。
(二)賄賂破壞了國民對于憑借自己實力獲取相應公共資源的信賴利益
如前所述,從平行的社會一般人的視角出發,賄賂犯罪侵犯了其獲取生存和自由發展資源的機會公平性。關于是否侵害機會公平性的判斷應堅持事前判斷與事后判斷的對應原則,因此,對這種機會公平性的侵犯不以實害后果的發生為必要,而以具有受到侵犯的具體危險性為足。然而,不論是對機會公平性產生實害還是危險,都只是相對于與行賄人處于同等競爭關系的平行社會一般人而言。當超越這一群體的立場,從包括平行社會一般人在內的全體國民的視角出發來看行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賄賂關系時,賄賂侵犯機會公平性這一觀點的解釋力將受到挑戰。例如,①在事后受賄的情形中,如果國家工作人員事先并未與請托人約定事后受賄,而是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對公共資源進行了公平分配,行賄人在當時并未獲得額外的機會或份額,而只是在事后甚至在國家工作人員退休之后主動給予財物。此時,難以解釋這種賄賂關系對于平行的社會一般人參與公共資源分配的機會公平性的危險。②國家工作人員主動索賄,并且一開始就不打算為對方謀取利益。在這種情形中,雖有賄賂關系的存在,但賄賂提供方非但沒有獲取額外的公共資源,反而單純失去了相應賄賂物,其他平行的社會一般人也并未減少獲取公共資源的機會或份額。
據此,單純從與行賄人處于同等競爭關系的平行社會一般人的視角出發,已經難以觀測到賄賂關系波及的范圍之全部,有必要跳出區域社會,進而從全體國民的視角考察賄賂犯罪所侵犯的法益。這是因為,從集體社會的視角出發將形成以下兩個不同維度:第一,形成賄賂關系的行賄人與受賄人這兩個主體均被抽象化。即行賄人被抽象化為參與社會分工、扮演不同角色的所有國民;受賄人被抽象化為代表國家行使提供及分配各種公共資源的國家機關。于是,從區域社會視角出發考察的處于特定行業的平行社會一般人與具有分配特定公共資源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關系,擴散到了社會大分工之下的所有國民與代表國家意志的國家機關之間的關系。第二,從關注個體的機會公平性是否得以保護這一微觀視角轉向國民對于國家機關公平地分配各個領域的公共資源的期待這一宏觀視角。也就是說,賄賂關系對于平行社會一般人獲取公共資源的機會公平性的危險外化為國民對于國家機關的信任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信賴利益說得到國內外不少刑法學者的支持。例如,德國學者羅克辛教授認為,一個受賄的政府官員將嚴重地動搖一般公眾對國家行政管理的可信賴性的信心,因此對這種行為必須使用刑事處罰來懲罰。〔41〕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 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 頁。日本刑法學界雖存在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說與職務行為的公正性說之間的爭論,但不論主張哪種觀點,一般都把國民對于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或公正性的信賴作為法益的一部分。〔42〕參見[日]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第2 版),黎宏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573 頁。我國學者張明楷教授認為,賄賂犯罪侵害了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其包括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本身和國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43〕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下)》(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11 頁。此外,也有學者主張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應包括國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及公正性的信賴利益。〔44〕參見孫運梁:《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應包括信賴利益》,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19 年第2 期。然而,如前所述,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只是對賄賂侵犯的行為規范的描述,其本身并不能直接成為賄賂犯罪的法益,換言之,普遍存在的賄賂正是因為職務行為被收買了,國民當然不享有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的信賴利益,否則便是以刑法的名義要求國民相信賄賂并不會發生。與此相似,國民也不享有對職務行為公正性的信賴利益,因為如果將所謂“社會信賴”理解為“不要有腐敗”的國民內心期待的話,則所謂社會信賴就演變成了禁止賄賂的行為規范被嚴格遵守的狀態,并非禁止賄賂所保護的利益。〔45〕參見[日]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評論社2016 年版,第598 頁以下。我國學者更是一針見血指出:對公權力的不信任是現代法治社會的進步表現,動用刑法手段讓人們信賴職務行為的公正性,有南轅北轍之嫌。〔46〕參見黎宏:《賄賂犯罪的保護法益與事后受財的定性》,載《中國法學》2017 年第4 期;熊琦:《刑法教義學視閾內外的賄賂犯罪法益》,載《法學評論》2015 年第6 期。
由此可見,國民并不享有對于職務行為保持不可收買性或公正性這種應然狀態的信賴利益,國民對國家機關所享有的信賴利益來源于:根據由職務行為這一分配公共資源的手段形成的利益格局,自由選擇最大限度獲取生存和自由發展資源的方案。德國學者盧曼指出:只有當人們能夠依循一定的預期去行動時,才能免于頻繁進行利害權衡之苦,從而最大限度地減低社會成本。〔47〕參見[德]盧曼:《法社會學》,賓凱、趙春燕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82 頁。然而,當賄賂關系存在時,雖然可能直接為行賄人及受賄人帶來相應利益,但從全體國民的視角來看,無疑擾亂了人們的行動預期,無限增加了社會交易成本。關于這一點,德國學者阿爾布萊希特有以下精辟論述:腐敗就意味著慣常附著于交易的成本被哄抬;此外,一個與腐敗如影隨形的結果就是不信任(Mi?trauen),因為一旦有了腐敗,便再無法看清是何人基于何種目的而作出了該決定;究其根本,則因決斷的依據顯然已不再是業績或功勛,而是外人無法理解的關系與聯結;最后,通過腐敗作出的決定無法監控,因為它遵循的不是國務或者行政活動本應奉行的標準,而是其他各種心機與算計(Kalküle)。〔48〕參見[德]漢斯·約格·阿爾布萊希特:《德國賄賂犯罪的基本類型與反腐刑法的最新發展》,韓毅譯,載魏昌東、顧肖榮主編:《經濟刑法》(第14 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 年版,第57 頁以下。
據此,從維持穩定的交易模式,最大限度減少社會交易成本的立場出發,國民應受法律保護的信賴利益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于自己能夠憑借自己實力獲取相應資源的信心。換言之,國民可以相信獲取生存和自由發展資源所依靠的是自己的努力與決斷力,而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在分配公共資源時給予的特殊照顧。
第二,對于其他資源競爭者不任意增加交易成本的信賴。賄賂關系的形成可能讓行賄人短時間內高效率地獲取公共資源,這必然引發其他資源競爭者的模仿,并擴散到其他行業領域,從長遠來看,任何一起賄賂案件的發生,都將增加全體國民獲取資源所需的成本。
第三,對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分配公共資源時應當保持中立客觀立場的信賴。具體而言,國家工作人員代表國家行使各種分配公共資源的職權,并不是任何國民都可以成為國家工作人員的,根據我國公務員法的相關規定,公務員的任用,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應當具有符合職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還應當忠于人民,勤勉盡責,清正廉潔。這無疑以法律的形式賦予國民相信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分配公共資源職責時將會客觀公正的信賴利益,這種信賴利益將作為國民的行動預期而支配國民的生活。
需要說明的是,這三種信賴利益并不是各自分立,而是具有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具體而言,第一種是對內的信賴利益,而第二種與第三種均是對外的信賴利益,但對外的信賴利益的維護歸根結底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對內的信賴利益,最終促成個人的自由發展,實現個人的價值與尊嚴。〔49〕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主張的分配正義觀仍具有指導意義,即根據各取所值的原則,按照各自的價值進行分配,正義就是一種比例。參見《亞里士多德全集》(第8 卷),苗力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100 頁以下。我國《憲法》第33 條第3 款規定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以及第38 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為這種各取所值的分配正義觀提供了憲法根據。其中,第二種信賴利益用于指導對行賄罪的解釋,而第三種信賴利益則用于指導對受賄罪的解釋。
以下,筆者嘗試將這三點信賴利益的具體內容適用于事后受賄、主動索賄的解釋。
1.事后受賄破壞了國民信賴他人不任意增加獲取資源成本這一合理期待
我國刑法并未明文規定事后受賄罪,但在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3 條規定,履職時未被請托,但事后基于該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的,應當認定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犯罪的,依照受賄罪定罪處罰。應當說明的是,事后受財可以分為兌現事前約定與事前無約定這兩種情形。由于兌現事前約定的事后受財行為并不是賄賂犯罪的實行行為,在請托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形成約定之時,已經建立起分配公共資源的職權與金錢之間的對價關系,對平行的社會一般人獲取資源的機會公平性形成具體危險,足以發動未遂的賄賂犯罪的制裁規范,事后受財只是對事前已經形成的對價關系的確認而已,將其認定為賄賂犯罪并不存在任何法理上的障礙。因此,問題的焦點聚集在事前無約定的事后受財這種情形上。有學者從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公正性這一立場出發認為這種情形原則上不成立受賄罪,因為如果沒有事先約定,行為人就不可能具有收受賄賂的認識,更不可能具有將職務行為置于不公正裁量之下的危險。〔50〕參見黎宏:《賄賂犯罪的保護法益與事后受財的定性》,載《中國法學》2017 年第4 期。如果單純從事后判斷的視角來看職權的行使與財物的給予這兩者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這種觀點具有合理之處。然而,如前所述,應跳出行賄人與受賄人的觀察視角,從平行的社會一般人、社會大分工之下的全體國民乃至國家的視角出發,對行賄人與受賄人通過賄賂形成的對價關系是否侵犯其他國民獲取資源的機會公平性進行事前判斷。據此,不僅行賄人與受賄人被抽象化,對價關系本身也被抽象化,即不再要求某一財物與某一具體的履職事由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財物與過去、現在及將來履行的分配公共資源的職權之間可能形成的對應關系。其中的判斷資料就包括國家工作人員事前的履職是否客觀中立、雙方之間的人際關系、受財者在受財當時的身份、財物價值大小等,而判斷的標準就是,這種事后受財是否破壞了國民之間相互保有的對于他人不任意增加獲取資源成本的信賴。
據此,要將事后受財排除在賄賂犯罪的范圍之外,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切斷職權行使與財物給予之間形成對價關系的可能性。具體而言,可以考慮以下情形:國家工作人員事前的履職客觀中立,在履職過程中并未考慮將來據此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以此為前提,①事后他人在與國家工作人員的正常人情往來中給予社會觀念上可被接受的財物;②國家工作人員在受財當時已經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以后也不可能再享有分配公共資源的職權,例如已經辭職、退休或者入獄。第二,該事后受財行為不足以引發其他國民的效仿,從而在整體上提升國民獲取資源的成本。這是因為,在司法實踐中有不少事后的財物給予只是將國家工作人員之前正常的履職事由當作一個借口,據此開啟感情投資模式,為將來的請托事由做鋪墊,這種情形當然應認定為受賄。
2.被索賄者未獲取不正當利益的出罪理由
我國《刑法》第389 條第3 款規定,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而根據《刑法》第385 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索取財物顯然是法定的受賄方式之一。這樣的話,從直觀來看,被索取賄賂者不構成行賄的理由僅僅在于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然而,如前所述,如果跳出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形成的對價關系這一視閾,分別從平行的社會一般人及全體國民的視角出發考察賄賂犯罪的保護法益,那么行賄人是否獲得不正當利益并不是衡量是否構成行賄的標準。只有具備侵犯平行社會一般人獲取公共資源的機會公平性之危險的行為才能被評價為賄賂犯罪的實行行為,其中,行賄行為對于機會公平性的侵犯主要體現為損害了他人對其不任意提高獲取公共資源成本的信賴利益,而不是單純的行賄人最終獲得不正當利益。據此,可以說是行賄的行為樣態決定了行賄的成立與否,由行賄給行賄人帶來的不正當利益并不是行賄罪的構成要件要素。在這個意義上,應當說我國刑法所規定的行賄罪是一種短縮的二行為犯,即行賄罪規定的“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一種間接目的,只有行賄才是構成要件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是否實現既不影響行賄罪的成立,也不影響犯罪既遂的認定。〔51〕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工作人員接受賄賂后沒有利用自己的職權在分配公共資源時向行賄人傾斜,或者正確地行使自己的職權向行賄人分配了相應份額的公共資源,都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參見張明楷:《論短縮的二行為犯》,載《中國法學》2004 年第3 期。
從該結論出發,在對我國《刑法》第389 條第3 款的解釋上,首先應確立的前提是本條款所規定的“不是行賄”是指不構成行賄罪。然而,在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中,不構成犯罪的出罪事由可能是構成要件不該當,也可能是不具有違法性,還可能是缺乏有責性。于是,可以對《刑法》第389 條第3款的適用進行以下分類討論。
第一,國家工作人員明知他人有具體的請托事由,以此為由向對方索取財物,被索賄者基于理性考慮接受了國家工作人員的索取并輸送了相應的財物,但最終被索賄者謀求的不正當利益并未兌現。〔52〕例如,時任某法院副院長職務的王鵬翔主動聯系鄭官順,要求有償出借100 萬元人民幣給鄭官順,鄭官順雖沒有借款需求,但為今后能請托王鵬翔提供幫助,遂答應王鵬翔的要求,許諾支付2%的月息。參見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浙02 刑終第484號刑事裁定書。在該情形中,被索賄者構成行賄罪。這是因為,這種情形與行賄人一開始主動向國家工作人員提供財物的情形并無不同,兩種情形均基于雙方的意志自由形成了對價關系。從社會一般人的視角出發,主動索賄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行使處于賄賂的影響之下,機會公平性顯然受損;而當被索賄者在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做出向國家工作人員輸送財物的選擇時,顯然也破壞了國民對其保有的作出拒絕決定的期待與信賴利益。于是,這種情形在形式上具備行賄罪的構成要件,在實質上侵害了行賄罪的保護法益,值得發動行賄罪的制裁規范對其加以譴責。
第二,被索賄者本來就具有獲得相應份額的公共資源的資格和能力,但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分配該公共資源的權限向對方索賄,否則就阻礙對方利益的實現,被索賄者雖向國家工作人員提供了賄賂但最終并未獲得該利益。〔53〕例如,在“程某某無罪二審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原判認定上訴人程某某為獲得審計報告向潘炯江行賄8 萬元并送給審計人員吳某某5 萬元,系被索賄,且在案證據不能證明程某某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其行為不符合行賄罪的構成要件。參見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2014)黔南刑二終字第94 號刑事判決書。這種情形應否定行賄罪的成立,這是因為,被索賄者本來就具有憑借自己的努力與實力獲取相應公共資源的信賴利益,國家工作人員的索賄令其信賴利益落空并不得不增加成本。此時,國民不享有對被索賄者拒絕國家工作人員索賄的期待與信賴利益,因為作為第一重的對內信賴利益已經被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索賄者侵犯,如果轉而賦予國民信賴被索賄者拒絕索賄的信賴利益,無異于將賄賂的責任轉嫁到包括被索賄者在內的全體國民身上,這無助于恢復被賄賂所侵犯的行為規范,也無助于培養國民對于法規范的忠誠。〔54〕積極的一般預防論著眼于長遠,將法益侵害大小、行為的規范違反性及其程度、一般人效仿犯罪的可能性等作為刑罰適用的依據,追求社會政策方面的價值。參見周光權:《新行為無價值論的中國展開》,載《中國法學》2012 年第1 期。
第三,當國家工作人員勒索賄賂的行為對被索賄者意志自由的壓制達到與敲詐勒索同樣的程度時,不論被索賄者最終是否獲得不正當利益,都不應認定為行賄。具體而言,敲詐勒索罪是一種利用被害人意思瑕疵的財產犯罪,也就是說被害人是在受限的意志自由狀態下處分了財產。我國有學者認為處分自由有雙重含義:①反抗有用,即被害人的妥協和配合是行為人獲得財物的必要條件;②應能反抗,即不妥協的代價沒有超出被害人的承受范圍。〔55〕參見車浩:《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之界分:基于被害人的處分自由》,載《中國法學》2017 年第6 期。在國家工作人員索賄的情形中,只要被索賄者事實上拒絕給予財物,索賄者就當然無法獲取財物,也就是反抗是有用的。因此判斷的重點應放在被索賄者是否應能反抗,而這里的應能反抗是一種應當能夠反抗的規范性判斷,即“面對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等與財產之間的選擇權衡,可以允許一個人為保衛財產付出多大的代價,涉及個體的自我決定權與刑法家長主義之間的關系。此外,當外部壓力以公權力面貌出現時,被害人的處分自由是否受到壓迫,也不得不考慮到法秩序對于公民形象以及法民關系的期待等應然性命題。”〔56〕參見車浩:《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之界分:基于被害人的處分自由》,載《中國法學》2017 年第6 期。如果將該判斷標準適用于索賄的情形中,那么在判斷被索賄者是否應能反抗時應考慮兩個因素:首先是被索取的財物與可能獲取的期待利益或喪失的既得利益的大小關系,當前者顯著大于后者時,反抗則存在困難;其次是國家工作人員的索賄行為給被索賄者帶來的心理沖擊與持續焦慮。具體而言,作為國家公權力代表的國家工作人員本應一方面對國民處于正常狀態的基本權利保持尊重與克制態度,另一方面對遭受侵犯的基本權利提供保護與救濟手段。于是,當國家工作人員竟然借用國家公權力勒索財物時,從社會一般人的視角來看,對于被勒索者而言顯然難以以孤獨的個體對抗以國家暴力機器為后盾的公權力代表。
(三)賄賂犯罪累積性地侵犯國家這一抽象的人格體的存立根基
前文從平行的社會一般人及全體國民的視角出發對賄賂犯罪所侵害的法益進行考察,然而如果僅僅停留于這一層面,顯然無法清晰說明為什么賄賂犯罪是一種侵犯國家法益的犯罪,也無法為日益擴張和重刑化的賄賂犯罪提供理論根據。具體而言,①同樣是賄賂犯罪,為什么對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賄賂犯罪的處罰比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商業賄賂犯罪的處罰要重得多,〔57〕廣義上的商業賄賂包括商業活動經營者之間的狹義商業賄賂和公務性商業賄賂,本文僅指狹義商業賄賂。參見劉遠:《商業賄賂犯罪的概念與立法》,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6 年第5 期。將答案求諸于身份的不同顯然是一種循環論證;②對于形成賄賂這一對價關系的行賄人與受賄人的刑罰輕重也不同,對受賄人甚至可以判處死刑的根據是什么;③在斡旋受賄罪中,斡旋者本人的職權并未與行賄人的財物形成直接的對價關系,卻仍然以受賄罪論處,其根據何在;④在介紹賄賂罪以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犯罪的主體已經不再要求具備國家工作人員這一身份要素,這種犯罪擴張的合理性根據是什么。
顯然,在以上四種情形中,背后有一股強大的“對賄賂犯罪用重刑,擴大賄賂犯罪處罰范圍”的刑事政策力量在推動,馴服這股刑事政策力量的最好方式是將其納入以憲法為頂點的整體法秩序進而融入對相關犯罪的解釋之中。在此過程中,具有憲法關聯性的法益概念,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必然發揮批判立法與解釋的功能。〔58〕參見張翔:《刑法體系的合憲性調控——以“李斯特鴻溝”為視角》,載《法學研究》2016 年第4 期。既然賄賂犯罪是一種侵犯國家法益的犯罪,就有必要進一步超越國民的視角,從國家這一被虛擬化的人格體的視角出發,觀察賄賂對其產生的影響。我國《憲法》第1 條第2 款就開宗明義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任何侵犯國家法益的犯罪都必然具有破壞國家制度的實質內容,否則將會導致以國家的名義任意侵犯國民的基本權利。〔59〕參見車浩:《刑事立法的法教義學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載《法學》2015 年第10 期。在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中,行為人通過對本應保持客觀公正的職務進行持續性污染,使國家的正常職能陷入無法順暢運行的狀態,間接而緩和地從內部瓦解國家政權的存立根基。誠如德國學者Adriano Teixeira 直截了當指出:越來越多的構成要件指向于保護一個制度本身,賄賂犯罪的保護法益就是保障國家制度不因腐敗而瓦解,在這個意義上,賄賂犯罪是一種累積犯(Kumulationsdelikt),因為對于制度的破壞并不是由偶然的一兩次犯罪直接導致的,而是大量的賄賂行為的出現。〔60〕VgI.Adriano Teixeira,Das Unrecht der privatenKorruptionimgeschaeftlichen Verkehr,2017,S.132.
據此,從國家的視角出發,可以說對包括賄賂犯罪在內的職務犯罪的處罰是出于國家自我防衛的需要。根據我國《刑法》第20 條的規定,正當防衛的成立需要同時具備防衛的前提事由與防衛行為在防衛限度內這兩大基本條件。當然,該法條規制的是國民的防衛,但當把國家視為虛擬化的人格體時,該條款仍然可以類推適用于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賄賂犯罪的不斷擴張可以視為防衛事由的擴張,而賄賂犯罪的重刑化可以視為防衛限度的降低。賄賂犯罪的累積犯的罪質特征為賄賂犯罪的擴張提供正當化根據,而賄賂犯罪的重刑化仍然要受制于比例原則。以下,筆者嘗試以上述四個問題為素材,將該論點進一步具體化。
1.商業賄賂止步于對市場公平秩序的侵犯
根據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7 條的規定,可以把商業賄賂概括為經營者為謀取交易機會或競爭優勢而向交易相對方或有能力影響交易的單位或個人提供賄賂的行為。由此可見,商業賄賂表現為金錢和商機之間的交易,侵犯的是以高質量的產品和優質的服務贏得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與此相對,以國家工作人員為交易方的賄賂則表現為金錢和公共資源的交易,在侵犯平行社會一般人獲取公共資源的機會公平性的同時,還侵犯了國民對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信賴利益,并進而漸進式破壞國家政權的存立根基。這樣的話,商業賄賂犯罪的刑罰輕于賄賂犯罪的根據就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商業賄賂中,由于交易的雙方均為經營者,即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者提供服務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即便其中一方處于優勢地位,也不具有像國家工作人員那樣面向全體國民分配公共資源的權限。據此,商業賄賂的保護法益的射程范圍就被限定在平行的社會一般人的圈子內。
第二,從長遠來看,在商業賄賂中處于優勢地位的一方也無法一直保持這種優勢地位或提供對方需要的商機,而分配公共資源的權限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此賄賂犯罪對法益的侵犯具有持續性特征。
第三,商業賄賂的起刑點高于賄賂。很顯然,《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商業賄賂的前置法,刑法應作為最后的保障手段出現,而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賄賂犯罪而言并沒有前置法,刑法沖在最前線。
據此,當賄賂行為發生在商業領域時,應嚴格區分作為妨害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的商業賄賂與作為職務犯罪的賄賂犯罪。前者歸根結底是一種侵犯社會法益的秩序犯罪,而后者則是侵犯國家法益的職務犯罪。區分的關鍵就在于賄賂行為僅僅止步于對公平的市場交易秩序的侵犯還是進一步侵犯對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秩序。
2.受賄罪的刑罰重于行賄罪的合理根據
如所周知,行賄罪和受賄罪是一種對合型的必要共犯,然而,如果要將處于對向關系的雙方參與人均納入處罰范圍,則應具備共同的法益侵害內容并符合法規范的保護目的。〔61〕例如,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均共同侵犯了人身不可買賣性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法益。與此相對,刑法規定販賣毒品罪,但并未把單純為了吸食而購買毒品的行為認定為犯罪,以及規定了組織賣淫罪、容留賣淫罪等,但并未將賣淫行為認定為犯罪。從作為最終被害人的國家的視角出發,受賄罪與行賄罪在對國家政權的存立根基的侵犯上達成了最低限度的共同內容。即便如此,受賄罪的刑罰顯然比行賄罪重,這種刑罰上的加重應外化為不法程度的升高或譴責可能性的增加,否則罪刑均衡原則將受到挑戰,甚至刑罰的正當性本身也將存疑。如前所述,從國民的視角出發,受賄罪與行賄罪在對外信賴利益的侵犯上有所區別,前者側重于對國家工作人員應以客觀中立的立場公平地分配公共資源的信賴,而后者側重于對其他國民不任意提高獲取公共資源成本的信賴。這兩種信賴利益的大小難以比較,但當以國家的視角分別考察其與受賄人及行賄人之間的關系時,一方面這兩種信賴利益找到了可供比較大小的參照系,另一方面也為加重對受賄人的譴責提供根據。
如前所述,國民對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公平分配公共資源的信賴利益具有法定性。與此相對,國民對于其他國民不任意提高獲取公共資源成本的信賴并不是一種法定的信賴利益,而是一種約定的信賴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或索取賄賂對于信賴利益的侵犯程度要高于國民主動向國家工作人員提供賄賂,即不法程度更高。在此基礎上,從國家法人說的立場出發,國家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關系形同被代理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關系,當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時,也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其對于與國家形成的信賴關系的破壞,從而為譴責可能性的增加提供基礎。〔62〕關于“國家法人說”的批判性考察,參見王天華:《國家法人說的興衰及其法學遺產》,載《法學研究》2012 年第5 期。
由此可見,即便是對合犯,即便侵犯的法益具有共通性內容,由于其侵犯法益的行為樣態以及行為人一身專屬的可譴責性不同,刑罰的輕重也各不相同。
3.從累積犯的罪質特征看賄賂犯罪的擴張
所謂累積犯,是指單個行為基于事實上的原因,對于所保護的法益不能產生損害,但如果類似行為大量實施最終會導致法益侵害,因而有必要對該行為予以禁止。〔63〕參見張志鋼:《論累積犯的法理——以污染環境罪為中心》,載《環球法律評論》2017 年第2 期。由此可見,累積犯要獲得處罰必要性,該行為必須具備引起他人大量模仿的動力,即如果不禁止特定行為,就會對他人實施類似的行為具有現實性影響,這對立法者設定累積犯具有決定性作用,這種現實性影響,通常被稱作“真實的累積效應”。〔64〕參見張志鋼:《論累積犯的法理——以污染環境罪為中心》,載《環球法律評論》2017 年第2 期。據此,累積犯的成立應受到以下條件的限定:第一,累積犯所侵害的法益是一種集體的、以未來為導向的法益,因為對個人法益的侵犯是一種現實的危險或實害,以此為由即可單獨受刑法評價,而無需進一步關聯他人的侵害行為。第二,該行為的實施是個體獲得生存和自由發展資源的捷徑,由此必然引發他人的模仿,即這種行為具有傳染性。第三,如果該行為不被禁止,模仿的速度與規模將呈幾何級增長態勢,維系全體國民生存和發展的資源將在短時間內耗盡,進而必然產生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危機并引發秩序的混亂。第四,設立累積犯的目的在于預防被法所保護的集體法益的損害借由大量的、類似的個體行為而走向現實化,換言之,當該集體法益實際受損或滅失,一切已經太晚。以上四點,可借用古人韓非子的名言加以闡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步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65〕出自《韓非子·喻老》。
從上文主張的賄賂犯罪的差序構造特征以及與此相對應的三重保護法益出發,賄賂犯罪是一種累積犯的結論已經清晰可見。這一罪質特征的確定一方面為擴張賄賂犯罪的構成要件類型提供刑事政策根據,另一方面又為賄賂犯罪的邊界確定提供解釋論基礎。具體而言,將賄賂犯罪納入累積犯這一分析框架下進行檢視時,可以得出以下三個推論。
第一,是否將某一行為納入賄賂犯罪這一家族性罪名中,取決于該行為對于賄賂犯罪的保護法益的侵犯是否具有真實的累積效應。從本文所主張的賄賂犯罪的三重法益構造出發,行為是否破壞處于第二重法益的信賴利益,是檢驗是否具有真實累積效應的試金石,因為一旦某一行為破壞了國民對于他人及自己保有的信賴利益,該行為就開啟了向全體國民傳染的開關,并進而危及國家法益。
第二,行為人一旦實施被納入賄賂犯罪范圍的行為,即可視為對目前為止所有賄賂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狀態的承繼,因此對累積犯的處罰并不違反個人責任原則。〔66〕在這個意義上,伏爾泰的名言“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是對累積犯的責任承擔的最好詮釋。
第三,累積犯的罪質特征為預防性的刑罰擴張提供正當性根據,但刑罰的分配仍受制于比例原則。
從以上三個推論出發,我國刑法所規定的斡旋受賄罪、介紹賄賂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等犯罪被作為獨立的賄賂犯罪類型,具有正當性。〔67〕雖然我國刑法經數次修正并擴張了具體的賄賂犯罪類型,但有學者指出這是一種罪刑規范結構的退變,反而從較為合理“嚴而不厲”走向失衡的“厲而不嚴”。參見梁根林:《中國反賄賂刑法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一個比較分析》,載《中國法律評論》2017 年第4 期。
首先,在斡旋受賄罪中,本人的職權與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通過斡旋這一粘合劑形成了一個整體,共同成為金錢交易的對象,自此,作為賄賂犯罪的其中交易一方的職權范圍就不再限定于本人,而是從本人的職權出發迅速向橫向及縱向擴張,從而形成一張穩固的、長期可用于與金錢交易的職權網絡。〔68〕值得關注的是,我國有學者認為我國《刑法》第388 條規定的受賄罪的主體屬于被其利用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瀆職行為的共犯,具體來說是“類似教唆犯”的角色。這一觀點從共犯論的視角出發論證斡旋賄賂者受處罰的根據和必要性,但無法清晰解釋為什么斡旋賄賂以賄賂罪論處而不是以瀆職罪的共犯論處。參見黎宏:《受賄犯罪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 條的解釋》,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1 期。據此,可以將斡旋受賄罪解釋為一種實質預備犯,也就是說斡旋這一預備行為單獨作為受賄罪定罪處罰是對受賄這一行為的正犯化,這一解釋一方面符合賄賂犯罪的累積犯特征在刑事政策上的刑罰擴張需求,另一方面也為刑罰權的任意發動進行合理限制,即斡旋行為必須侵犯了受賄罪的法規范保護目的,在法益侵害程度上能與受賄行為做同等程度的評價。〔69〕關于實質預備犯的解釋論建構,參見梁根林:《預備犯普遍處罰的困境與突圍》,載《中國法學》2011 年第2 期;陳興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罪名沿革與規范構造》,載《清華法學》2021 年第1 期。
其次,在介紹賄賂罪中,通過介紹人的居間撮合,本來沒有相向而行傾向及機會的國家工作人員和請托人相向而行并完成職權與金錢之間的交易。于是,從國家工作人員、介紹人、請托人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出發,介紹人成為具備雙重共犯身份的人。具體而言,在介紹人為請托人提供金錢與職權的交易機會這一意義上,介紹人成為請托人行賄的幫助犯;與此相對,在介紹人慫恿國家工作人員接受金錢并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這一意義,介紹人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教唆犯。據此,即使介紹賄賂者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由國家工作人員這一身份所附帶的對賄賂犯罪保護法益的侵害可能性也連帶作用于介紹人。〔70〕參見周嘯天:《身份犯共犯教義學原理的重構與應用》,載《中外法學》2016 年第2 期。由此可見,介紹賄賂罪本身是狹義共犯的正犯化,介紹行為獲得了獨立于行賄與受賄的地位。
最后,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及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中,本來形成賄賂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與金錢之間的交易關系擴散為職權形成的影響力與金錢之間的交易關系。據此,在利用影響力的賄賂犯罪中,形成了國家工作人員本人、關系密切人、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請托人這四方關系。具體而言,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借助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形成的實際影響力,獲得了類似于國家工作人員的斡旋權能,利用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為請托人謀取非法利益,借此收受或索取請托人財物。由此可見,可以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歸入斡旋賄賂罪之中。但由于關系密切人利用影響力的斡旋無法像國家工作人員本人的斡旋那樣形成橫向及縱向的用于與金錢交易的職權網絡,因此在違法程度及責任程度上顯然輕于斡旋受賄罪。
據此,賄賂犯罪的家族性罪名呈現出不斷擴張的趨勢,這種擴張是在國家這一抽象法人格體基于自我防衛的需要這一刑事政策驅動之下進行的,可以預見,賄賂犯罪在立法上還將進一步擴張。然而,為防止立法上漫無邊際地擴張,一方面,賄賂犯罪的犯罪化應符合國家自我防衛的需要,也就是對國家法益形成持續性的、形成積累效應的侵犯,國家據此發動與法益侵害急迫性程度相對應的防衛措施;另一方面,對既有的立法,根據其法益與罪質,構建起穩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教義學規則。
(四)三重法益之間的關系
如前所述,如果將刑法置于公法范疇中,對于所有的犯罪而言,最終都必然面臨國家與“加害—被害關系”的對決,這樣才能最終修復犯罪行為對被害人、社區、社會及國家產生的損害,恢復包括被害人在內的全體國民對于繼續遵守行為規范的信心。而法益便是以刑法的名義禁止該犯罪行為所欲達成的規范目標。當法益屬性為個人法益時,犯罪行為對于社區、社會及國家的波及效應僅對于制裁規范的發動有影響,對行為規范所追求的規范目標并無影響。與此相對,當法益屬性已經超越個人層面時,犯罪行為對個人之外的社區、社會及國家的損害也應納入行為規范所禁止的內容之中。當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益屬于國家法益時,對國家這一抽象人格體的保護成為樹立該行為規范的最終目標。然而這一法益內容本身未免過于空洞和抽象。為此,必須闡明達成這一最終目標的途徑,即考察犯罪行為對社區、社會及作為最終被害人的國家的實害內容,據此構建起以保護國家這一抽象人格體的存立根基為最終目標的法益體系。于是,對于賄賂犯罪而言,不論是受賄罪還是行賄罪,歸根結底都是對國家政權存立根基的侵害,但在行賄人與受賄人形成賄賂關系的過程中,基于公職與金錢之間的掛鉤程度、行賄人或受賄人的主動程度、受賄人利用職務便利的程度、行賄人獲得不正當利益的程度等因素的不同,作為賄賂犯罪之不法評價對象的賄賂關系的樣態也不盡相同。與此相應,賄賂犯罪具有了不同的不法內容,有些賄賂犯罪側重于對機會公平性的侵犯,有些則側重于對國民憑借自身實力獲取公共資源這一信賴利益的侵犯,但所有的賄賂行為都累積性地侵犯國家政權的存立根基。這為設置不同的賄賂犯罪構成要件類型提供了合理根據。
四、結 論
賄賂犯罪作為一個種類的犯罪,應當有共通于所有賄賂犯罪的保護法益,以發揮立法批判功能及司法解釋功能。〔71〕參見張明楷:《論實質的法益概念——對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機能的肯定》,載《法學家》2021 年第1 期。在賄賂犯罪的保護法益上,既有的廉潔性說、不可收買性說、公平性說、信賴利益說、不可謀私利性說等觀點立足于賄賂犯罪是一種侵犯國家法益的犯罪這一共識上進行了諸多建設性探索。但這些觀點都存在將行為規范本身當作法益內容的問題。從“個體→平行的社會一般人→全體國民→國家”這一差序格局并從分配行政的視角出發可以清晰說明賄賂犯罪侵犯國家法益的不同層次及其內容。據此,筆者初步認為賄賂犯罪的背后潛藏著以下三重漸進式的差序法益。
第一重保護法益,從與行賄人處于同等的資源競爭地位的平行社會一般人的視角出發,賄賂犯罪侵犯了其獲取維系生存和自由發展的公共資源的機會公平性。應從事前判斷的視角而非事后判斷的視角判斷機會公平性是否受侵犯,因此不論對典型的對價型賄賂還是雙重保險型賄賂抑或是感情投資型賄賂,都侵犯了機會公平性。
第二重保護法益,從全體國民的視角出發,賄賂犯罪破壞了國民對于憑借自己實力獲取相應公共資源的信賴利益,這里的信賴利益由國民對于自己的努力與實力的內部信賴利益和對于他人不任意提高獲取資源成本及作為公共資源分配者的國家工作人員保持客觀公正立場的外部信賴利益構成,其中,外部信賴利益歸根結底是服務于內部信賴利益的實現。據此,事后受賄罪因侵犯外部信賴利益、阻礙內部信賴利益的實現而具有法益侵害性;未獲取不正當利益的被索賄者因沒有破壞他人的對外信賴利益,讓全體國民繼續保有對內信賴利益,因此不具有法益侵害性。
第三重保護法益,從國家的視角出發,賄賂犯罪累積性地侵犯國家的根本制度。國家從自我防衛的必要性出發有理由組織對賄賂犯罪的反擊,但在法治國家,刑罰權的發動應受合憲性控制。據此,作為賄賂犯罪擴張類型的斡旋賄賂罪應納入實質預備犯的解釋框架下,而介紹賄賂罪是狹義共犯的正犯化,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一種準斡旋受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