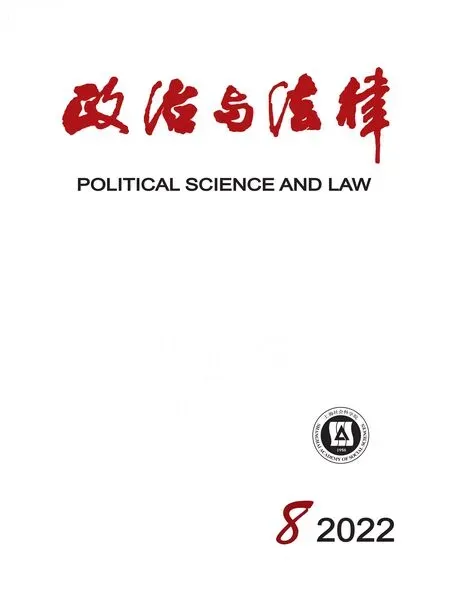在游擊和正規法制之間尋找生存空間:根據地政權法制實踐的新思考*
侯欣一
(天津財經大學法學院,天津 300222)
一、游擊式法制或正規法制:現實提出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限于自身條件和中國的國情,對革命問題思考得多,對如何執政則缺乏系統性思考,只是籠統地強調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1927 年4 月12 日,國民黨反動集團叛變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中國共產黨從殘酷的現實中認識到,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革命。起初,一些革命武裝以燒殺為手段回擊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殘酷屠殺。對大革命中湖南農民運動進行過細致觀察的毛澤東頗為警覺,意識到任這種現象存在下去,會失去民眾的支持,還可能使剛剛組建的工農武裝演變為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軍,因而及時發文制止,“除了最反動的長官、豪紳地主,經過當地的蘇維埃或革命委員會宣布他的罪狀執行槍決,以及焚燒反動的豪紳地主的房屋外,此外秋毫無犯”〔1〕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5 頁。,盡可能地將理性和法制融入革命。
1927 年11 月,彭湃在廣東潮汕地區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地方政權——陸豐、海豐縣蘇維埃政府,選舉產生了海豐縣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和海豐縣蘇維埃裁判委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武裝力量的保衛、政權的有效運行,三者合一,終于有了穩定的鄉村革命根據地。此后,鄉村革命根據地需要法制的觀點,逐漸被中國共產黨人所接受。但革命年代,法制并非核心議題,加之根據地政權創建之初,一切以俄為師,制度移植特征明顯。直到20 世紀30 年代初,伴隨著法制實踐活動的拓展,下列問題才逐漸凸顯,需要中國共產黨自主給予回答。
(一)如何把握鄉村環境戰時條件與法制建設的關系
法治事關政體與國體。鄉村革命根據地政權創立后,在國體上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政體上則放棄了晚清以降歷屆政府推行的三權分立原則,選擇了蘇式工農兵代表會議制,簡稱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是根據地法制建設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其特點是議行合一。謝覺哉說,工農兵代表會議“兼有立法、司法、行政之權,推翻三權分立制,三權分立有很多毛病”。〔2〕《謝覺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35 頁。然而,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農民并非無產階級革命的主體,貧窮也并不能天然引發革命。此外,偏僻的農村和戰爭環境能否容納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能否保證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有效運行?
一方面,蘇區時期的根據地政權中,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產業工人和士兵可以忽略不計,因而,農民能否承擔起管理政權的重任成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說,俄式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對于戰爭環境下的中國農民來說,技術過于復雜,短時期內很難真正掌握。有調查報告反映,湘贛蘇區的“群眾對于蘇維埃的認識很微弱,只知道埃政府(蘇維埃政府的簡稱——引者注,下同)是他們的政府,而不知道‘埃政權’的內容,一般農民都應有實際參加政權的權利,就是常常要召開群眾大會代表大會討論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并不知道政權有二,一為代表會議,一為執委會,不知道代表會議才是合法的政權機關,而執委會不過是代表會議閉會后,受代表會委托的執行代表會議的處理日常事務的機關,更不知在一哄而聚的群眾大會之中能討論問題,必須假手于代表會議。他們以為選出幾個人坐在機關里,就叫蘇維埃,所以各級機關時常只有執委會議(甚至執委會還少開,只有主席、財務、赤衛或秘書只幾個人處理一切),而沒有代表會議。”〔3〕《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 年2 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49 頁。不僅如此,由于缺乏民眾的廣泛參與和監督,歷史上普遍存在的貪污腐敗問題又以新的方式出現:“沒有代表大會做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斗爭不堅決,到處發現……”〔4〕《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2-73 頁。
另一方面,殘酷的戰爭環境也無法預留出足夠的時間讓共產黨一點點地去啟發教育農民,使他們明了、掌握參與政權的意義和正確方式。在此背景下,共產黨可以選擇的辦法無非兩個。一是把自己的主張簡化成若干口號,借助運動的方式向農民去灌輸。但這種方式的效果如何存在疑問。《申報》記者陳賡雅曾深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采訪,對蘇區民眾留下了如下觀感:“一為不怕死……;二為殘忍性,殺人不算事……;三為創造性。”〔5〕陳賡雅:《湘皖鄂贛視察記》,引自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7 頁。二是以黨代政。蘇區時期“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權威,政府的權威卻差得多。這是由于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6〕《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2-73 頁。顯然,這些做法和現象有其特定的歷史時代性,不能簡單以今天的法治視角加以評說。
(二)立法應該追求簡單實用還是體系完備
在根據地政權法制建設中,1930 年3 月召開的閩西工農兵代表大會值得特別關注。這次大會在立法方面特點鮮明:一是制定了《政府組織法》《土地法》《山林法》《借貸條例》《工會法》《勞動法》《優待士兵條例》《商人條例》《取締牙人條例》《取締紙幣條例》《保護青年婦女條例》《婚姻法》《保護老弱殘廢條例》《合作社條例》《裁判條例》《稅則》等一批法律法規,涉及政權創制及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彰顯了對完備法律體系的追求;二是具體到每一部法律法規,則又可以發現其內容和文字大都較為簡陋,突出實用。
隨后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事實上僅存在了三年多(1931 年11 月至1934 年11 月,此后首都瑞金被國民黨軍隊占領),卻制定了130 多件法律法規,涉及憲法、選舉法、組織法、行政法(包括公安、民政、文化教育科技、民族政策)、經濟法(包括財政、稅收、金融、經濟政策)、勞動法、軍事法、民商法、刑事法、訴訟法、司法制度等,其中包括《國徽、國旗、軍旗的決定》《國家銀行暫行章程》《消費合作社標準章程》《生產合作社標準章程》《中國工農紅軍優待條例》《工農紅軍紀律暫行條例》《中國工農紅軍獎懲條例》《內務條例》《勞動感化院暫行章程》等,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備的法律體系,但在具體內容上仍然保持了閩西蘇維埃政權的做法。
形式、內容簡陋,成熟度不高,單行法眾多,進一步強化了法律工具論的理念,但門類相對齊全則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法制的系統化要求。這種看似矛盾的處理方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決策者在立法方面的兩難。
(三)是否需要創制獨立的審判機構
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審判是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早期中國共產黨對此亦有認識。1930 年3 月,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宣告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隨即公布了《裁判條例》。《裁判條例》規定,在正式審判機關成立之前,臨時以鄉政府為初審機關,區政府為復審機關,一般案件經縣政府判決后,即為完結,但重要案件,得上提到閩西政府審判。《裁判條例》文字簡略,卻充滿了對創制常設審判機關的向往。1931 年11 月7 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12 月13 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處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機關的暫行程序》,指出:“自從革命戰爭三次勝利,蘇維埃政權已經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鞏固,在這個時候,蘇區中有一件急于要做的事,就是建立革命秩序,保障群眾的權利。”為此規定:“各級地方司法機關在未設立法院之前,得在省縣區三級政府設立裁判部,為臨時司法機關,除依據前列各項原則處置反革命外,并解決一切刑事和民事的案件。”〔7〕林衛里主編:《閩西蘇區法制史料匯編》,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內部資料(2008 年),第72 頁。或許是意識到了設立裁判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2 年1 月又起草了《革命法庭條例(草案)》,準備以更為簡便的革命法庭暫代裁判部。該條例草案規定:“革命法庭為蘇維埃政府司法機關,管理一切訴訟公訴事宜之審判與判決。縣級革命法庭對案件之判決,必須經過省級批準始能執行。”〔8〕林衛里主編:《閩西蘇區法制史料匯編》,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內部資料(2008 年),第73 頁。然而該草案未通過。1932 年6 月9 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再頒布法律位階更高的《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規定“裁判部為法院未設立前的臨時司法機關,暫時執行司法機關的一切職權,審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訴訟事宜”,〔9〕林衛里主編:《閩西蘇區法制史料匯編》,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內部資料(2008 年),第74 頁。重新強調設立相對規范的裁判部。
革命法庭也好,裁判部也罷,都不是常設的法院,區別只是后者比前者組織化程度略高而已。實際情況是,直至紅軍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的法院仍然未能建立起來,需要審理某一具體案件時則以臨時性的“蘇維埃法庭”處理之。1937 年7 月12 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成立,中國共產黨終于有了自己的正式法院組織。法院組織的設立可謂一波三折。這固然可以用農村和戰時環境解釋之,學界也確實是這樣做的,然而,當視線平移到其他領域則又可以發現,同樣是戰時環境,但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大禮堂、新的紀元、國家銀行、國旗、國徽、軍旗、印章、首都、紀念碑、貨幣、各種報刊等,一個現代國家需要的外在標識幾乎一應俱全。其他領域可以做到,為什么設立法院就如此艱難?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對司法問題的忽視。當然,引發忽視的原因應該是司法知識不足所致。
(四)程序是否可以靈活對待
根據地政權甫經成立,執政者便一再告誡各級官員,政府、審判機構工作需要手續和程序。如1932 年9 月福建省蘇維埃裁判部發布通令,指出:“過去各級政府及地方武裝送給本政府裁判部的犯人,很多沒有案卷和材料,只有一個名單,或者只是簡單地寫著‘反動土豪’‘反動富農’‘偵探’‘土匪’等等極簡單的名詞,致使裁判部審判犯人時發生許多困難,而且容易弄錯,以致對于蘇維埃政府的信仰發生不好影響。接本訓令之后,如各級政府再像從前那樣把犯人送來而沒有一點材料,本政府將不接受,即日送還原處。希各級政府及地方武裝注意!”〔10〕林衛里主編:《閩西蘇區法制史料匯編》,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內部資料(2008 年),第156 頁。
1934 年4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專門法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對審級、沒收敵人財產的手續、判決書、上訴、死刑核準等問題做了程序性規定。
不過,與此同時,根據地政權又一再強調對待程序要靈活處理。如1933 年3 月15 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第二十一訓令《關于鎮壓內部反革命問題》,要求面對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大舉進攻,“邊區各縣的裁判部,對于已捕犯人,應迅速清理,凡屬罪惡昭著證據確實的分子,首先是這些人中的階級異己分子,應立即判處死刑,不必按照裁判部暫行組織和裁判條例第二十六條須經上級批準才能執行死刑的規定,可以先執行死刑后報告上級備案。至于中心區域,同樣要將積案迅速解決,不準仍然堆積起來,稽延肅反的速度。即在中心區域,若遇特別緊急時候,亦得先執行死刑,后報告上級”。〔11〕林衛里主編:《閩西蘇區法制史料匯編》,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內部資料(2008 年),第252 頁。1934 年5 月,中共中央、中央人民委員會給根據地黨和蘇維埃發出指示信,強調審判人員“一切對反革命表示縱容與寬恕的行為,都要受到黨和蘇維埃的嚴重的打擊和處罰”。〔12〕林衛里主編:《閩西蘇區法制史料匯編》,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內部資料(2008 年),第275 頁。
面對生存危機,出于鎮壓敵人的需要,對審判程序采取靈活處理極為必要。但靈活處理的不應該包括證據標準和死刑執行程序。此外,只要程序可以不必堅守,理由便會多種多樣,且理由一定正大光明,如為了方便民眾等。〔13〕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曾公開講:“在第一屆參議會討論邊區施政綱領時,我們就提出建立便利于人民的司法制度,一切為著人民著想,真正為群眾解決問題,故訴訟手續非常簡單,著重于區鄉政府的調解和仲裁,沒有什么審級、時效、管轄的被限制,案件處理也比較迅速。”參見雷經天:《關于改造邊區司法工作的意見》(1943 年12 月18 日),陜西省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號15。蘇區時期,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存在,只是還沒有上升至一般的理論層面。
二、游擊式或正規法制:一場未能真正展開的爭論
在根據地政權歷史上,最早明確提出正規法制與游擊式法制兩種不同建設思路并付諸實踐的,是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政府。
(一)游擊式和正規法制的劃分
抗戰爆發后,大批接受過現代科學教育、習慣了城市生活的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其中包括李木庵、張曙時、魯佛民、朱嬰、何思敬等一批系統接受過現代法學教育,且在國統區從事過法律工作的共產黨人。他們的到來,既給中國共產黨增添了新的活力,也對邊區的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邊區領導人對法制重要性有了新的認知。中共黨內以董必武、謝覺哉等為代表的一批法制擁護者也希望抓住這一時機,推動邊區法制建設走上正軌。
1939 年6 月21 日,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邊區政權工作實際負責人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要“建立正規的法治,克服政治上的游擊現象”,〔14〕《謝覺哉日記(上)》,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09 頁。首次提出“正規的法治”這一概念,并將其與“政治上的游擊主義”進行對應。1940 年3 月毛澤東亦指出:“邊區的革命秩序還做得不夠。”1940 年8 月8日,董必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加強陜甘寧邊區政權建設,并建議將邊區建成中國的模范區域。〔15〕《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版,第157 頁。
這些個人建議最終出現在政府文件中。1941 年4 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工作報告中指出:自第一屆參議會成立以來,邊區民主建設、司法制度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然而,邊區民主不是沒有缺點的,相反,缺點還相當大。主要是民主的質量雖然高,民主的制度卻未正規化。”“邊區新秩序什么都有了,卻很多沒有法定與正規化。”同時,陜甘寧邊區政府指出:“因為司法人才的幼稚,成文的法令尚少,雖然在新民主主義政治的籠罩下,卻未能建設起新民主主義成文與深入的司法制度。而和平三年,個別地方還有不按司法程序處置人的。因為沒有成文法,輕點重點,可以意為。個別地方發現不尊重人民自由權利的事,司法機關未能徹底糾正。”〔16〕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3 輯),檔案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6 頁、第228 頁。如何糾正?報告提出必須走“正規化”的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文件最早將“正規”“正規化”與政權、與法制關聯在一起進行表述。
1941 年10 月,陜甘寧邊區召開了邊區歷史上第一屆司法工作會議。邊區法制室主任張曙時強調:“游擊作風,已經不適合現在,現在一切需要正規化。”〔17〕《邊區司法會議開幕林主席蒞臨訓話》,載《解放日報》1941 年10 月9 日,第4 版。11 月15 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魯佛民的文章“對邊區司法工作的幾點意見”,認為邊區“司法干部對法律知識缺乏研究和修養;一般干部未能吸收過去司法工作中的寶貴遺產;對邊區風俗習慣,未能徹底了解;了解案情,偵查案情,各方面的技術不過硬;狃于過去游擊作風,蹈常習故,保守老的一套,不求進步;成文法不夠用,民法尚可援用比附,刑法則不然,處理案件,處處遇到棘手”。〔18〕魯佛民:《對邊區司法工作的幾點意見》,載《解放日報》1941 年11 月15 日,第3 版。
同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在對邊區政府工作報告的審議決議中指出“各級的民主制度和保障人民人權財權的工作與秩序還不夠正規化”,要求邊區政府“切實糾正上述缺點,使邊區抗日民主政治秩序以及稅收制度進一步的正規化,以周密完備地保障人民人權、財權和政治自由”。〔19〕《陜甘寧邊區參議會》(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 年編),第101-102 頁。
(二)正規法制的推行和爭論
顯然,“正規法制”和“游擊式法制”概念的出現并非個人語言使用之習慣,而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時代背景。這一現象揭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即在使用者的認知中法制有其客觀標準。循著這條線索一路追尋下去并仔細辨析,則又可以發現一些更有價值的問題。
一是使用“正規法制”概念者,既包括系統接受過現代法學教育且在法制領域工作的從業者,也包括未接受過現代法學教育卻從事法制工作的領導人,但兩者對待“正規法制”的態度又略有差異:前者大都堅持、認同正規法制,排斥游擊式法制,因而很少使用游擊式法制的概念,如非要使用無一例外是否定性評價;后者不僅接受正規法制的概念,而且會使用游擊式法制的概念,對后者少有價值評判。換言之,把法制分為正規和游擊式兩種類型的大都為政治家。
二是使用“正規法制”概念者均將其與秩序關聯在一起,且往往采用的是“法治”而非“法制”的表述,即將“正規法制”作為實現秩序的手段。使用游擊式法制概念者基本將法制作為革命的工具。
三是使用“正規法制”概念者,其認知中對法制的最低要求是有法可依和司法制度完備。
帶著這種認知差異,陜甘寧邊區于1940 年底開始了“正規法制”之實踐。實踐分前后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由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主導,以適當完善司法制度為主要任務。1942 年6 月,雷經天離職前往中央黨校學習,李木庵代理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在此前后,魯佛民出任了邊區政府秘書處秘書、負責協調處理法院審理的重點案件;張曙時任邊區法制室主任;朱嬰任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秘書。換言之,新近從國統區遠道而來的習法者掌控了邊區與法制工作有關的所有部門。“正規法制”實踐由此進入后一個階段。實踐涉及立法機關建設、加快立法、探討審判機關與政府的合理關系、完備司法制度等諸多方面。〔20〕參見侯欣一:《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司法改革研究》,載《法學研究》2004 年第5 期。在“正規法制”推行的同時,對未來中國影響深遠的延安整風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1943 年整風運動進展到了審干階段。審干即對新近從國統區來到邊區者進行政治審查。1943 年7 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邊區“司法工作檢查委員會”,著手對李木庵等人以及他們主導的“正規法制”實踐進行審查。審查工作由原司法人員為主導,經過審查最終定性:所謂正規法制“就是要把邊區的司法工作依照著國民黨的一套去做”。〔21〕《改造邊區司法工作的意見》(1943 年12 月18 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
(三)反對者之理由
“正規法制”實踐,在邊區司法系統內部引發了較大爭議。反對者有如下主張。
第一,農村環境既不需要內部組織復雜的司法機關,也無財力承擔“正規法制”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中共中央及西北局機關報《解放日報》公開發表社論《簡政要從思想上貫徹》,指出,“正規化”,是要達到那樣理想的地步,要求我們的組織要那樣的齊全,我們的分工要那樣的細密,我們的人員要那樣的專門,我們的辦事要那樣的科學,照這些同志所設想的“正規化”,那就要把我們的政權機構變成一副比現有的更為龐大而復雜的組織。可是這些同志卻忽略了一件“小事”,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是落后的農村環境與抗戰的困難時期,這種正規化雖然是好的,可是今天的條件還限制著我們,不能實現,如果勉強去做,那就只有變成形式主義。〔22〕《陜甘寧邊區政權建設》編輯組:《陜甘寧邊區的精兵簡政》(資料選輯),求實出版社1982 年版,第72 頁。社論并不是專門針對正規法制實踐所發,但其反對在鄉村搞政權正規化的態度則十分明顯。
第二,“正規法制”意味著教條主義。在根據地歷史上,政權建設正規化始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國以后,表現為對蘇俄制度的簡單移植。遵義會議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一九四二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強調要理論聯系實際,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李木庵等人推行的“正規法制”,在反對者看來就是照抄書本上的法律制度,暫且不論內容是否合理和必要,單就方法論而言就必須加以批判。
第三,“正規法制”就是要使邊區的法制回到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反對的理由中,最大的殺手锏是政治上的批判。如邊區司法檢查委員會對朱嬰的審查結論認為:“他在法律方面,要邊區政府與國民政府完全一致,解除我們保衛邊區政權與人民利益的有利武器。他在組織方面,要邊區的司法機關完全脫離邊區政府的領導,直接受國民政府中央的管轄和支配。他在干部方面,要完全任用友區來的專門人才,將邊區原有的干部完全調換造成‘清一色’的系統,以此來分割邊區整個的政權,實現消滅邊區的陰謀事實俱在,這絕對不是過分的估計。”〔23〕《高等法院雷經天院長關于邊區司法工作檢查情況和改造邊區司法工作的意見》(1943 年9 月30 日至1943 年12 月),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
反對的理由如此眾多,1943 年底“正規法制”實踐被緊急叫停。
三、新型正規法制:一種更新的提法和實踐
“正規法制”不能搞,“游擊式法制”又無法滿足邊區政權建設的需要。如邊區司法人員反映說,由于成文法律不足,“判決時群眾提出質問根據什么法律,便無以為對”。〔24〕《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42 年3 月—9 月工作報告》(1942 年10 月),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于是,1944 年初,陜甘寧邊區政府又提出了一個新概念:新型正規法制。也就是把正規法制再分為舊型正規法制和新型正規法制兩種。
“新”“舊”何以劃分?官方認定的標準為:一是能否忠實于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整風運動期間,經過不斷學習,李木庵對“新型正規法制”的深刻體悟是,“我們是政治領導法律,政治在前,法律在后;大后方是法律在前,政治在后”,〔25〕《關于邊區司法工作檢查情形》(1943 年9 月),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可謂一語中的。二是能否滿足人民的需要。邊區政府領導人習仲勛強調:“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權中的一項重要建設,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樣,是替老百姓服務的,這樣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實實把屁股在老百姓這一面坐得端端的。舊的司法機關的屁股就不在老百姓這一方面坐,是坐在少數統治者的懷里。”〔26〕習仲勛:《貫徹司法工作正確方向》,載《解放日報》(1944 年11 月5 日),第2 版。林伯渠綜合上述兩點,指出:“舊型正規化,是與邊區政治和邊區人民完全相違背的東西。既然是同邊區政治和邊區人民完全相違背的東西,那么多要求一分舊型正規化,就不能不多鬧一分獨立性,經費要獨立,干部要獨立,領導系統也要獨立。舊型正規化,又是漢奸、特務分子用來掩蓋他們破壞活動的幌子……我們需要正規化,但我們所需要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新型正規化,適合于邊區政治發展和人民需要的新型正規化。”〔27〕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7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456 頁。在中國共產黨人法制建設中,一直強調人民性,強調對日常生活常識的尊重。至于何為常識、何為法律常識,則較少得到剖析。參見姚建宗:《法律常識的意義闡釋》,載《當代法學》2022 年第1 期。
政治標準相對而言容易確定,但新型正規法制的具體制度樣態則需要從業者去摸索。
(一)改造民意機關
抗戰爆發后,為了適應國共第二次合作之需要,并從形式上體現國家的統一,中國共產黨擱置了蘇區時期的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于1939 年1 月召開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通過了《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規定“邊區各級參議會為各級民意機關”,擁有十一項法定職權。該條例第十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參議會“選舉邊區政府主席、邊區政府委員及邊區高等法院院長”,“監察及彈劾邊區各級政府之政務人員”。〔28〕張希坡編著:《革命根據地法律文獻選輯》(第3 輯、第2 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96 頁。這兩款內容究竟該如何理解,即陜甘寧邊區政權是議行并列,還是議行合一,實踐中曾經出現過兩種不同的傾向。
1944 年3 月25 日,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高干會議上指出:“議行并列亦即二權并列的二元論,在前年高干會上也曾受到批判,但因為各級參議會的選舉條例及組織條例,非依法定手續,不便修改,這問題在組織上迄今尚未徹底解決。議行并列的思想,在二屆參議會以前即已存在,二屆參議會至前年高干會議期間,則思想上的分歧與組織上的混亂,更加發展了。”為此,林伯渠進一步指出:“我們必須從二元論回到一元論,即從二權并立論回到民主集中制。必須承認參議會和政府都是政權機關,都是人民的權力機關。對政府而言,參議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會議),而在參議會閉幕期間,由參議會選出并對參議會負責的政府,就成為該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29〕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8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4 頁。
最終解決辦法是不再墨守成規。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對組織條例做了大幅度修改:“第二屆參議會修正的特點:(1)允許當選為政府委員的議員不辭去議員職;(2)允許政府有訂立單行法規及緊急措置權;(3)取消鄉級議行分立;(4)延長各級參議會開會期;(5)正式指明各級參議會為人民代表機關。”謝覺哉特別強調說:“第一屆的條例則全抄舊民主國家的憲制,不合新民主政權組織需要。”〔30〕《謝覺哉日記(下)》(1945 年4 月8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783 頁。換言之,應公開允許邊區政府委員繼續擔任參議會議員,從根本上改變議行并列之格局。林伯渠則認為,只有如此才能糾正此前出現的問題,“如偏重形式,輕視內容,如議行并列,強調正規化等”。〔31〕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8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108-109 頁。
(二)賦予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立法權
嚴格劃分立法權限是現代法治的又一基本要求。1939 年通過的《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第十條第七款規定,參議會“議決邊區之單行法規”。1944 年以后,為了適應新型正規法制嘗試的需要,陜甘寧邊區在立法權限上進行大膽突破。
第一,允許政府制定單行法規。第二屆參議會后“允許政府有訂立單行法規及緊急措置權”。這一變動值得特別留意。此后,由邊區政府制定的單行法規數量開始增多,效力則與參議會制定的法律法規完全相同。如1944 年2 月23 日,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命令,頒布《陜甘寧邊區地權條例草案》:“查陜甘寧邊區根據地地權草案,業經本府委員會會議通過,應予頒行。此條例頒布后,收入于‘抗日根據地政策條例集’中之‘陜甘寧邊區地權條例(草案)’應廢止。其他一切有關土地問題的法令如與本條例有抵觸者,概以本條例草案為準則。”〔32〕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8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70 頁。
該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本條例由邊區政府公布施行,俟下屆參議會追認之,其解釋之權屬于邊區政府。”這就在形式上符合了法制的基本原則。即便如此,還有兩點須提及。一是并未對政府的立法權限進行確定。實際情況是諸如地權、婚姻、稅收等基本法律,政府均可以自行制定。如1944 年6 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農業統一累進稅施行條例》等。二是有權制定單行法規的政府,包括邊區政府、專區和縣等各級政府。1943 年1 月,邊區曾發布命令規定:“各行政督察專員:茲為統一政令,照顧政策起見,嗣后各專員公署、縣政府,如頒布地方法規,須先呈報本府批準,方可公布,希依照執行并轉令所屬各縣,一律照準執行為要。”〔33〕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7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40 頁。
第二,允許審判機關編制判例。為解決邊區現行法令不足的問題,林伯渠于1944 年強調,審判機關應“根據歷史經驗,將好的判例加以研究整理,發給各級司法機關參考”。〔34〕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8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 頁。為此,邊區高等法院于1944 年7 月編制了《陜甘寧邊區判例匯編》。盡管學界對于該匯編是否具有法源的性質存在爭議,〔35〕有關陜甘邊區判例匯編性質的討論,參見汪世榮等:《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石: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 年版)中的相關章節。但其對審判活動的影響則毋庸置疑。
(三)“司法半權”
在陜甘寧邊區,“司法半權”是個頗為流行的提法。“司法半權”是指各級司法機關行政上隸屬于同級政府領導,但獨立審判。李木庵主持邊區司法工作期間,朱嬰曾嘗試增強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引起了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的高度警惕。1943 年4 月25 日,邊區政府制定《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草案》,明確規定:“司法機關為政權工作的一部分,應受政府統一領導。”1944 年以后,邊區政府一再重申,邊區司法工作應確立在下面兩個原則之上:(1)司法與行政一致,司法機關受政府直接領導;(2)司法機關審判案件,要根據邊區政府的政策、法令,照顧邊區人民的實際生活,不抄襲舊型法律。邊區政權是邊區人民自己的政權。因此,“司法獨立”就完全失去它原有的積極意義,邊區的司法工作就應該在邊區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進行。這就是邊區新民主主義司法基本特點,也就是邊區司法工作的正規化。〔36〕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7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458-459 頁。
(四)司法人員革命化、大眾化加適當專業化
選擇什么樣的人從事司法工作,是根據地政權一直思考的問題。根據地創建之初,為強化對敵鎮壓,曾有過“裁判尚擇取兇惡的人來充當,沒有注意選擇頭腦清楚而堅決的分子”的現象,〔37〕《永定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日刊》(1930 年5 月21 日),載林衛里主編:《閩西蘇區法制史料匯編》,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內部資料(2008 年),第148 頁。但很快就被制止。雷經天主張使用工農革命干部,把革命性放在第一位,“關于干部,我以為經過土地革命斗爭鍛煉出來的工農干部,雖然他們的文化程度較低,不懂得舊的法律條文,但他們的政治立場堅定,與群眾發生密切的聯系,能夠負責地為群眾解決問題,給予教育培訓,就是邊區司法干部的骨干”。〔38〕雷經天:《改造司法工作的意見》(1943 年12 月18 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李木庵主持邊區司法工作期間則大力推行司法人員專業化,注重司法人員的專業知識和能力。經過不斷嘗試,1944 年后,邊區政府明確規定:“司法干部,尤其是領導人員與審判人員,必須選擇忠實于革命三民主義,愿意切實聯系群眾與公正不私的干部充任之。”〔39〕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8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 頁。也就是說,最終確立司法人員的選用標準為革命化、大眾化加適當專業化。1944 年綏德分區召開司法工作會議,習仲勛發表講話,“在我們這里,假如有一個司法人員,仍然是斷官司‘過堂’板起面孔,擺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糟糕了”。〔40〕《習仲勛文集(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 頁。
(五)案件處理方式審判與調解相結合
主張新型正規法制的領導人一再強調,新型正規法制之下,程序不是第一,經驗不是第一,解決實際問題才是第一,人民滿意才是第一。〔41〕《謝覺哉日記(上)》(1943 年12 月4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557 頁。但對于審判人員來說,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一種機制把社會中不斷涌現的糾紛處理好,讓人民滿意。此外,這種解紛機制還必須是制度化的或準制度化的,是正規的、而非游擊式的,從而證明“新型正規法制”的正當性。
對司法機關而言,解決糾紛的辦法不外乎判決和調解。前者對程序嚴密性和完整性要求較高,稍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人民的不滿,走入舊型正規法制的道路。后者又過于隨意。如何解決?1943 年后,陜甘寧邊區司法系統嘗試塑造一種審判加調解的新方法——馬錫五審判方式。1944 年1 月6 日,林伯渠在邊區政府委員會報告工作中向司法機關提出明確要求:“訴訟首先必須力求簡單輕便,提倡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以便教育群眾,判決書必須力求通俗簡明,廢除司法八股。”〔42〕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8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 頁。也就是將審判與調解進行結合,而非將審判與調解割裂,此即邊區司法人員尋找到的新型正規法制的糾紛解決機制。在邊區領導人看來,“根據簡單、明了、易學、易行的原則,重新厘定科學的公文程式。徹底廢除舊的文牘主義,揚棄繁瑣的貴族式的公文程式。這些華而不實的廢物,是舊的官僚師爺們盤踞要津,阻撓新的優秀干部和廣大人民參加政權的一種工具”。〔43〕彭真:《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1941 年),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30 頁。馬錫五審判方式滿足了農村環境的需要。
對中國共產黨法制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夠判斷,上述制度樣態中的諸多內容成為了未來中國法制建設的基本元素。
四、擱置新型正規法制:糾偏抑或完善
新型正規法制概念的提出和實踐,既意味著根據地政權對舊型正規法制和游擊式法制正當性的否定,也提醒著人們法制必須具有一定的形式和標準,法制必須有利于社會秩序的形成。
(一)冷靜后的思考
鄉村和戰時根據地的法制究竟該如何搞,對從業者來說是一個需要他們直接處理的真實問題。整風運動之后,法制領域的工作人員,特別是法制領域的領導人又開始了新的思考。謝覺哉日記中的兩段話頗有代表性:“仿吾同志來談,將于近日返回晉察冀,仿吾問我在此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他說陜甘寧邊區工作還在‘亂摸’,如文教之‘民辦公助’方針,司法之‘調解為主,審判為副’,政制上之最高權力機關等。又說有些問題知道了為甚不速改?我說亂摸是不可避免的,要在摸了之后知道是‘亂’。逐漸改進,使之以后摸,減少亂。”〔44〕《謝覺哉日記(下)》(1945 年10 月4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842 頁。“羅邁(即李維漢—引者注)同志談:中間人士對我們有兩點懷疑;解放區是否有言論自由;解放區是否有法治。兩點懷疑不是全沒根據,言論自由、法治,我們很需要,有好處,沒壞處。由于有些同志的狹隘,又缺乏法治的訓練與習慣,因而給人以可懷疑的印象,應從己糾正,莫徒怪人。”〔45〕《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11 月24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30 頁。
作為陜甘寧邊區政權與法制建設的領導人,謝覺哉、李維漢等人的感觸自然很深。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思考,1945 年以后新型正規法制的概念很少再有人使用。不僅如此,1945 年10 月至12 月,陜甘寧邊區利用兩個月的時間召開推事、審判員聯席會議,集中討論邊區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開幕式上,謝覺哉發表講話指出:“目前邊區司法狀況,找到了道路,但還很落后。”〔46〕《謝覺哉日記(下)》(1945 年10 月18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848 頁。
(二)落后之表現
道路正確,但還很落后。謝覺哉的話為觀察、思考這一時期乃至此后根據地政權的法制實踐提供了思路。“道路方向”即黨的領導和人民滿意,已經明確,接下來的工作便是梳理根據地政權法制實踐中存在的落后現象,以便對癥治療。為了更加準確再現根據地政權法制實踐的狀況,減少轉述中的理解不當,以下筆者將直接引用謝覺哉等人的觀察和結論。
第一,對制度重要性認識不足。謝覺哉說,邊區政權建設“有成績、有經驗卻不能抽出規律定為制度,以鞏固其經驗擴大其成績,又從此基礎上取得新的經驗,以改進其制度。是我們急待克服的弱點。也曾立過制度,有因客觀條件限制未能實施,有失在未能堅持,有則制度本有毛病”。〔47〕《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6 月29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936 頁。也就是說有制度,但效果卻不盡人意,其原因如下。
首先,制度本身有問題。如制定制度時僅考慮了執行者自己的方便。“正規,有時間限制的,不可把他人的正規做我的正規,但我應有我的正規,否則亂。戰爭時不是不需要制度,或不可能建立制度,而是要適合戰時的制度。目前制度的缺乏表現于:人民十分需要而沒有給:公糧負擔,攤派下的,沒有定則;法庭判案以意為之,不援引條文或無條文可援用;財政沒有好的制度。有制度不完全:……脫離群眾,不知人民的需要;……求自己便利,忘了人民便利與政務便利。”〔48〕《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10 月27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21-1022 頁。
其次,制度系統性差難以實施。“方針——施政綱領有了,具體實施的法制,搞得頗少。新的法制:根據綱領,根據實際,參考歷史(中外已有的)不易搞,不是不能搞。租佃條例、地權條例、調解條例,經過研究的當屬可用,有些太粗糙。”〔49〕《謝覺哉日記(下)》(1945 年7 月23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819 頁。
再次,沒能處理好制度與思想、精神的關系。強調思想正確、強調發揮精神作用是中共黨建的基本內容。但萬事皆有度,不能因此忽略了制度的基礎性作用。“思想與制度并重,思想不搞通,誰來遵守制度,沒有制度,思想也靠不住。”〔50〕《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7 月28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952 頁。“關于批評干部作風中之強迫命令,捆人,罵人——硬;得過且過,敷衍不理——拖;沒有條理——亂,是很不好。但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辦法,急起來了,就捆人家一繩子;搞不清楚,就索性隔下,沒有記錄、總結,任何事都從新辦起,我們不能加上他以軍閥、官僚的帽子,因為他們沒有沾染不良傳統;更不能說他們沒有智慧,他們是一塊美玉沒有琢磨。這應是‘硬’‘拖’‘亂’的主要來源,不治好這病源,光只下命令,不準硬、不準拖、不準亂,更使他們不知如何是好。”〔51〕《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9 月23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988-989 頁。
顯然,制度與作風并非同一個問題。“作風不好,可使制度落空,有好制度可使作風不墮。”〔52〕謝覺哉:《民主政治的實際》(1940 年4 月24 日),載《謝覺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47-348 頁。上述言論表明,謝覺哉等人對思想、精神與制度的關系已有了合理的認識,但要徹底改變則并不容易。
第二,對游擊作風習以為常。謝覺哉認為,在根據地政權法制實踐中,游擊作風由來已久。其表現為過度依賴經驗:“不太喜歡讀書的同志,謂書本上的多不合現在,我們應該從現實出發。但看了今天的現實,忘記了昨天的現實;看了此地的現實,忘記了彼地的現實,因而也就不能分析現實,駕馭現實,而為現實所沖動。前進,碰壁,回轉來又碰壁。”〔53〕《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12 月10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38 頁。“政權工作尤其財經工作,因為無知,吃的虧很不少,還不在于無知,在無知而自以為知。”〔54〕《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1 月9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890 頁。單純的無知尚好解決,如果以無知為有知解決起來就困難了。還有就是只顧眼前,缺乏長遠規劃。陜甘寧邊區時“政府建筑辦公廳為的要合署辦公,房子起好了,各廳搬來了,合署辦公卻忘了。為著供給統一而搬來,合并伙食單位,但供給仍任其不統一,行政處只‘推’而不‘攬’,審計制度行之已久,似嫌棄麻煩而無形取消,合作社條例早有了,可是至今仍沒有”。〔55〕《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6 月29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936 頁。其結果是“我們有二十多年的政權建設經驗,惜沒有搜集,更說不上總結。許多事得重搞,甚至革命就是為著政權的基本觀念亦有時模糊”。〔56〕《謝覺哉日記(下)》(1948 年5 月29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205 頁。
第三,缺乏守法習慣。“有了法制禁令就得遵守。減租交租,減息交息,累進稅率,禁走私、禁鴉片、禁酒糖等。法禁不當,可請求修改:未修改前,不得變動。執行法令的政府系統,先有守法觀念,法是強制的,不許不執行。也有曲折,如姑念無知、初犯、事出有因,但這回繞了下回不行。如執法機關自己也動搖,那就危險。”〔57〕《謝覺哉日記(下)》(1945 年7 月23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820 頁。謝覺哉等人為此不斷呼吁。養成守法習慣,除了克服特權觀念和嚴厲執法外,還需要形成一種社會氛圍。根據地法制實踐中存在著一種特有現象,即一方面不斷強調政府和民眾都要守法,另一方面又鼓勵各級政府通過政治動員的方式超越法令,并形成了一種看似自洽的理論:“法令規定人民的義務,也規定了人民的權利。照法令應該做的,不容你不做,這是義務。如果超過法令或法令所未許的,強我做,我可以拿法令來自衛,這是權利。政治動員則依靠宣傳鼓動,依靠人民的積極,不折扣的完成或超過法令所規定的事。法令是強制的,政治動員是自愿的,法令規定的是最低限度,不允許不及格;政治動員則越能超過限度越好,但并不能強人超過。拿擴兵征糧說罷,丁多的家必有人應征,獨子可不應征,這是法令;須應征的和不須應征的,都踴躍要當兵,如潮樣般涌入兵營,這就靠政治動員。某些地方不依據擴兵征糧的法令,民眾不知道應該做到怎么才符合法令,過此即為超過。而工作者‘提早超過’‘大量超過’的錦標主義,又把‘制定’‘攤派’的臨時命令,代替了政治動員。”〔58〕謝覺哉:《民主政治的實際》(1940 年4 月24 日),載《謝覺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47-348 頁。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極為擅長政治動員的政黨,在工作中提倡“提早超過”“大量超過”,易造成守法者被視作覺悟低的錯覺,不利于守法習慣的養成。
之所以如此,根據地的領導人也在思考:“革命,是推翻反革命的法的(維持反革命秩序的),所以革命者不愛談法。革命的法要在革命建設稍有成績之后才有,所以又不遑談法。”〔59〕《謝覺哉日記(下)》(1945 年1 月22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737 頁。
(三)重提正規法制
抗戰結束后,根據地政權的法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
第一,陜甘寧邊區時期。1945 年底,邊區高等法院代院長王子宜強調,應將尊重程序上升為審判工作的基本原則。他說,“審判原則:全面調查,虛心研究,重視證據;保證被告人有充分辯護之機會”。〔60〕習仲勛:《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司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45 年12 月30 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習仲勛也公開承認:我們過去司法工作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就是還沒有根據邊區的實際搞出一個規模、一些制度和一些法律,把政策搞得更對些,這幾年來都沒有走上正道”。〔61〕習仲勛:《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司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45 年12 月30 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1946 年2月13 日,李維漢向林伯渠等建議:“今后應該適當地強調并逐步實行法治。為此,立制釋令。必須慎重,以期制立令行;又必須培養守法觀念,輔以賞罰。因我們長期同國內外敵人進行非法斗爭,許多人缺乏守法習慣,對此必須有所改變。”〔6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版,第534 頁。
為此,1946 年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法律問題研究會。6 月22 日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開會,“決定:一、下周楊家嶺西北局分別召開邊憲草討論會。二、即發五五憲草修正案給委員研究。三、召集研究與起草小組——錫五同志召有關同志研究修改民法、刑法、訴訟法等;景范召集有關同志研究與起草縣鄉自治法、邊區專屬組織法等等;覺哉召集財經有關同志研究與起草財務、行政、合作社、公司、稅務等條例。”〔63〕《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6 月22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933 頁。根據地政權的法制實踐有了新的進展。但時隔不久,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全面內戰,陜甘寧邊區以完善必要形式為主的法制建設被再次擱置。
第二,華北人民政府時期。經過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中共黨內一些人對建設正規法制的愿望變得更加強烈。1948 年5 月,華北人民政府即將成立,劉少奇強調:華北聯合政府快成立了,刑法先就舊的改下施行,民法也可以這樣,邊做邊改。有總比無好。先急需穩定秩序,財產要有保證,使人民樂于生產建設,華北大部分地區沒有敵人了,也許敵人永不會再來了,可以建立正規的法制了。〔64〕《謝覺哉日記(下)》(1948 年5 月25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203-1204。有了上述認識,華北人民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建立起了更加規范的司法制度。〔65〕參見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編:《華北人民政府法令選編》,內部資料(2007 年)。
(四)關注的問題與工作重心
梳理這一時期根據地領導人對正規法制的強調和做法,可以發現其關心之處主要有四點。
第一,完善必要的形式和手續。法制離不開必要的形式和手續,中國共產黨人對此有了深刻的認識。陜甘寧邊區為了推行人民調解制度,曾提出調解為主、審判為輔的方針,在司法系統內部遇到了一些阻力,“有些同志不同意這個方針,認為它不符合司法正規化的要求”,〔6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版,第535 頁。最終改為刑事案件審判為主、民事案件自愿調解。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告誡各級官員,“現在政府各部門都成立起來了,這個政府是由游擊式政府過渡到正規式的政府。正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規的制度和辦法。過去好多事情不講手續,正規化起來,手續很要緊。有人說這是形式,正規政府辦事就要講一定的形式,不講形式,光講良心和記憶,會把事情辦壞的。當然,我們不是形式主義者,我們不要過去反動政府那樣繁瑣的公文手續,但有一點是必要的,就是遇事要向上級報告。必須克服過去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無組織無紀律狀態。今后大家會看到一些過去沒有過的制度和辦法,大家不要不高興”。〔67〕董必武:《建設華北,支援解放戰爭》(1948 年9 月26 日),載《董必武法學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 頁。
第二,統一領導。在根據地領導人的觀念中,法制與統一領導,與堅守政治紀律密不可分。換言之,講法制就不能各自為政,特別是戰爭時期。1943 年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命令,指出各級政府在實際工作中,還存在“本位主義,不顧大局的現象,還存在有獨斷專行,不尊重統一領導的現象;還存在有對政策和法令陽奉陰違不守法紀的現象,因此,統一權力,統一領導就成了今天政權機關中的主要問題”。〔68〕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7 輯),檔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95 頁。1948 年10 月23 日,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發布通知,規定各級司法機關建立月報制度,強化對下級司法機關的監督和領導。〔69〕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編:《華北人民政府法令選編》,內部資料(2007 年),第156-157 頁。
第三,強化政府和司法機關的權威。根據地政權鼓勵民眾參與司法活動,但經過不斷嘗試之后,則開始明了民眾參與司法活動必須有限度。習仲勛說:“在下邊解決的問題,據我看真正群眾調解的還不多,老百姓中誰也解決不了誰的問題,誰也不聽誰的話,真正解決問題的是去向政府。村里還是村主任來調解,有些勞動模范、公正人士、積極分子,但調解的不多,同時實際上也不可能都讓這些人來做,他們調解就出問題。比如綏德有些勞動英雄給人家調解,人家也不服,所以實際上真正做調解工作的還是區縣政府。”〔70〕習仲勛:《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司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45 年12 月30 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為此,必須適當強化審判機關的權威。1946 年8 月21 日,王子宜代院長主持召開邊區高等法院第101 次院務會議,通過《陜甘寧邊區法庭規則》,強調法庭在審判案件中的重要性、強調當事人必須遵守法庭秩序。
第四,徹底否定舊的法律制度,徹底打碎舊的司法機關。對舊型正規法制進行批判之后,徹底否定國民黨政權的法制成為根據地政權法制建設的一種方向、一種思維方法。對此做法的優缺點,謝覺哉有過客觀評價:“解放區職權機構——從內戰到現在,它和舊政權機構無繼承痕跡,雖然尚不完善,但自為風氣,沒有舊衙門的一切氣味。但應注意,它是沒有去接收舊的而是與舊的對立,先存于農村或山上,今后蔣政權大坍,要去接收。接收后又把它打碎的經驗,我們還沒有。”〔71〕《謝覺哉日記(下)》(1947 年6 月7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104 頁。
上述做法和想法最終形成了一種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1949 年初,中國共產黨最終勝利已成定局。2 月28 日中共中央發布《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宣布終止國民黨政權的法制在根據地內的合法存在。同年10 月,根據地政權完成了從局部執政到全面執政的使命,而如何建設法制以及建設一種什么樣的法制的歷史命題則留給了新的共和國。
五、結 語
根據地政權的法制實踐是一種介于“游擊式法制”和“正規法制”之間的特殊樣態,以形式簡陋、針對性強、不墨守成規等為基本特征。導致這一樣態出現的原因眾多,是農村環境、戰時狀態等客觀因素,片面移植蘇俄體制導致革命受挫的歷史教訓以及對現代法治認識不足等主觀原因,黨內政見分歧等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缺少任何一點,這一樣態都無法形成。根據地政權的法制實踐給后人留下許多啟示,以下兩點尤為重要。
第一,深化對法治理論的理解。鄉村革命根據地需要法制,中國共產黨對此有著基本共識,但對法制的理解則差別極大,于是有了游擊式法制、正規法制、舊型正規法制和新型正規法制等眾多的提法。在大多數根據地領導人看來,法制建設如同打仗,可以靈活,可以機動,有用就行。于是,才有“游擊式法制”和“正規法制”之分。即便是“正規法制”,在多數人看來,其內涵也不外乎完備法律體系、健全完善的司法制度、合乎自己要求的執法人員以及全民守法而已。
何以如此?謝覺哉說:“我們生長在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的國度里,又不是每個人對民主和法治的制度都有研究。相反,還帶有不少封建專制社會的殘余,向往民主,卻不知道民主怎么做;或對民主很重視,而對于與民主分不開的法治,又隨便的很。必須注意法治精神和民主作風的養成,要由上而推行到下,要重視大的,也不能忽視小的。”〔72〕謝覺哉:《我們應該有的作風》(1942 年8 月),載《謝覺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555 頁。“我們有些同志就輕視政權,不愿做政府工作,不研究政權的建立。推翻舊的是很痛快的,但建立新政權卻是一件復雜的艱難的麻煩的工作。延安有很多‘家’,但政治家卻很少,卻不容易。”〔73〕謝覺哉:《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議上的講話》(1941 年11 月3 日),載《謝覺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504 頁。此乃肺腑之言。由于對法治認識不足,加之過于關注實用,一些涉及法治的基礎性問題尚須普及。1946 年,為了建設正規政府,陜甘寧邊區準備制定政府組織法:“鹿鳴同志來談政府組織如何起草問題。我意根據實際,各廳處職權重行審查。那些是權,可以這樣做;那些是職,必須這樣做。職可以包括作風、工作制度等進去。”〔74〕《謝覺哉日記(下)》(1946 年8 月16 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964 頁。職、權、責分明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如果法律制定者對此尚無清楚的認知,制定出來的法律自然無法真正實施。
第二,增強實現法治艱巨性的心理準備。推行法治需要對法治的深刻的理解,更需要解決真問題的恒心。根據地政權的法制實踐中不乏“肅清游擊主義的殘余,建立革命秩序,養成法治習慣”〔75〕《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42 年3 月—9 月工作報告》(1942 年10 月),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5。的追求;不乏主動要求黨員、黨組織帶頭遵守法律的自覺,如提出:“政府在黨領導下所頒布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號召,我們的黨組織和黨員首先應當服從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響應那些號召,成為群眾中愛護政府的模范。政府有名無實,法令就不會有效。政府要一定有權。”〔76〕董必武:《更好地領導政府》(1940 年8 月20 日),載《董必武法學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3 頁。但由于近現代中國歷史進程過于曲折,且瞬息萬變,部分領導人不得不對政策和法律頻繁調整;缺乏對規則、程序的尊重,重結果輕程序;特別是未能合理劃分權力,使一些問題重復出現,乃至人們習以為常。實行法治絕非易事,不僅需要自覺,而且需要有解決真實問題的恒心,對此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