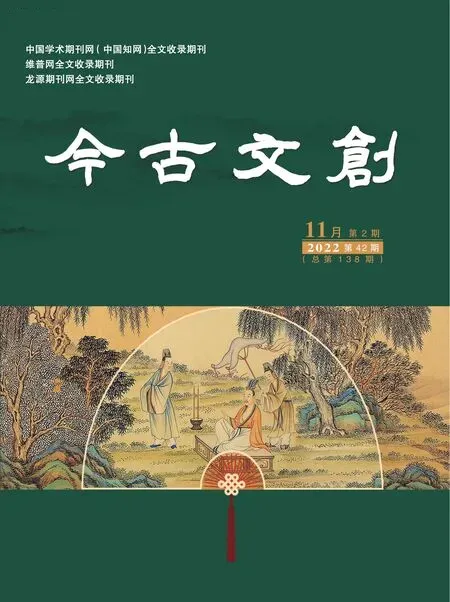試論《萬尼亞舅舅》中的悲劇性
◎鄔嘉琦
(上海師范大學 上海 200234)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是十九世紀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以短篇小說享譽世界,但他同時也是一名優秀的劇作家,其戲劇創作有獨具一格的魅力。《萬尼亞舅舅》是一部四幕鄉村生活即景劇,于1897年公開發表,這也是第一部搬上中國舞臺的契訶夫戲劇。盡管與契訶夫同時代的作家和批評家認為這是一部悲劇或正劇,但契訶夫本人卻將其歸類為喜劇。這部劇作是根據契訶夫之前的作品《林妖》改編而來,《林妖》中的森林主題以及主人公關于森林的議論都移植進了《萬尼亞舅舅》中,不過契訶夫將劇作的主人公從醫生改成了萬尼亞舅舅,萬尼亞的經歷使得劇作更具悲傷情調。《萬尼亞舅舅》寫的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戲劇的情節沖突不強烈,但外在沖突的淡化并不意味著沖突的減弱,而是實現了沖突的內化,人物的內在沖突取代情節沖突成為戲劇的主要沖突[1]14。盡管劇作中喜劇元素的加入沖淡了悲劇的氛圍,可劇中人物的悲劇性卻無法被徹底消解,《萬尼亞舅舅》展現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深刻悲劇性。
一、生存環境被破壞
《萬尼亞舅舅》中的悲劇性首先在于通過生態的被毀壞而顯現出來的新舊文明沖突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舊的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讓人們無所適從,他們對被破壞的森林和毫無改進的生活質量無能為力,他們在生活面前流露出迷惘和困惑,使得戲劇染上一種悲傷的情調。劇中人物阿斯特羅夫有不少關于生態環境的獨白,人們面臨的困境正是由阿斯特羅夫的長篇大論揭示出來的。他在劇作中是一名家庭醫生,他來到莊園是為了醫治謝列勃里雅科夫的腿痛,與以往不同的是,契訶夫在劇中用了很多的筆墨來描寫這一醫生形象,因此有學者認為阿斯特羅夫是契訶夫的代言人,阿斯特羅夫關于森林和自然的長篇獨白實質上體現出的是作者本人的生態思想。
契訶夫本人是醫生出身,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醫生的人物形象,但只有《萬尼亞舅舅》里的阿斯特羅夫醫生才真正成了契訶夫的代言人。契訶夫通過阿斯特羅夫醫生之口說出的保護森林的長篇獨白,也可能是我們能夠讀到的最早的由作家發出的保護生態環境的呼喚[6]35-36。
除去醫生這一職業以外,阿斯特羅夫在《萬尼亞舅舅》中還是自然的“守護神”,通過阿斯特羅夫的話語可以看到人類活動對大自然造成的無情破壞,“在俄國,森林經常遭受斧斤的摧殘,樹木已經減少了幾十億。野獸和禽鳥再也沒有藏身之處,我們的河流也日見涸竭,優美的風景一去不復返,這一切,都是由于居民沒有足夠的良知,又太懶惰,不肯彎一彎腰,從地底下去采取燃料”[5]17,阿斯特羅夫話語中呈現出的是當時俄國的真實狀況,隨著資本主義不斷發展,工業文明肆意入侵大自然,森林、草原、河流都能見到工業文明帶來的破壞,這些地方也出現了工廠和煙囪,人類的足跡讓生態環境不復從前。
啊!如果在森林伐倒的地方,現在通了公路,通了火車;如果鄉下到處都蓋滿了工廠、手工場和學校,那我就會完全同意你的話。要是那樣。毫無疑問地,農民會健康起來,富足起來,也更有了知識。然而,現在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啊!在我們這個地區,你所看見的,到處照舊是沼地、成群的蚊子,照舊沒有公路,照舊到處是貧窮,到處流行著傷寒、白喉和火災……[5]17
阿斯特羅夫醫生發出這樣的吶喊是因為工業文明的發展使得人們的生存環境被破壞,而生態被破壞之后也僅僅是破壞,森林的犧牲并沒有換來人類生活的便利,也對生活質量的改進沒有任何幫助。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沖突在契訶夫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體現,這是因為他創作的時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資本主義文明在俄國迅速發展,工業發展過快讓人們沒有時間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沒有在經濟和自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雖然農奴制的廢除沖擊了俄國固有的社會意識形態,但新的社會基礎和意識形態尚未成型”[7]22。《萬尼亞舅舅》中表現的就是這樣一種困境,人們尚未適應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但同時還要面對大自然被破壞的現實,關于人與自然的如何相處這一問題,他們還沒有找到好的解決辦法,于是只能在迷惘苦悶中尋找出路。
此外,“在契訶夫的作品中,樹木和森林的被砍伐,意味著對于人類心靈家園的野蠻破壞”[4]46,阿斯特羅夫關于森林的獨白展現出的不僅是生存環境的被破壞,同樣也象征著人類精神家園的失落。若是精神家園不復存在,靈魂沒有了歸宿,那么人的心理狀態也會變得搖搖欲墜。
二、理想的破滅
這部劇作的悲劇性還體現在其同名主人公萬尼亞的經歷中,他的遭遇表現出的是一條理想破滅之路,表現在三個方面,謝列勃里雅科夫真實面目的顯露對萬尼亞來說是信仰的倒塌;撞見葉列娜和阿斯特羅夫的幽會意味著萬尼亞對美好愛情的向往被現實打碎;而當萬尼亞對枯燥無味的日常生活進行反抗時,他的反抗卻以失敗告終。
首先是信仰的倒塌。萬尼亞在人生寶貴的二十五年里沒有做成什么事業,他將所有的精力都用于為姐夫謝列勃里雅科夫操勞。萬尼亞要為姐夫打理莊園里的一切事宜,他除了那份二十五年以來沒變化的工資之外就什么也沒有從姐夫手里得到了。而當謝列勃里雅科夫教授每次發表了什么新的文章,萬尼亞和家人就要整夜整夜地讀,甚至教授的每一篇文章他們都背得下來,他將謝列勃里雅科夫當作偶像般的人物。可直到姐夫退休,沒有了教授的名頭,萬尼亞才發現自己崇拜了這么多年的偶像其實什么也不是。
這么些年里,他所寫的和所教的,整個都是讀過書的人老早就知道了的,而沒知識的人卻又一點也不感興趣。這就等于說,他整整講了二十五年的廢話。可是你看他又多么自以為了不起呀!多么裝腔作勢呀![5]10
謝列勃里雅科夫回到這個莊園里除了痛苦和沉悶什么也沒有帶來,當謝列勃里雅科夫的假面被揭下,庸人實質暴露后,萬尼亞的精神世界瀕臨崩潰。二十五年來,謝列勃里雅科夫對萬尼亞來說早就超越了“具體的人”,成了信仰一般的存在,而現在的萬尼亞面臨的更是信仰的毀滅。萬尼亞不止一次地為過去的生活感到悔恨,他在悔恨中呼喊:“我把以往的光陰浪費得多么愚蠢啊,不然的話,我在現在這個歲數上已經沒有能力再做的事情,早都可以實現了,我一想到這里,就悔恨、憤怒得再也睡不著覺啦!”[5]14,“我把自己的生活糟蹋了!我有才能,我有知識,我大膽……要是我的生活正常,我早就能成為一個叔本華,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了……”[5]60。偶像的坍塌以及信仰的消失對萬尼亞來說意味著對過去二十五年生活的全盤否定,二十五年的青春煙消云散了。
其次是愛情的消散。萬尼亞對謝列勃里雅科夫的妻子葉列娜有好感,她在萬尼亞平淡的生活中激起了漣漪,萬尼亞為葉列娜感到不幸,“故意窒息自己的青春和勃發的感情,卻沒有人認為這是道德的啊”[5]11,不過葉列娜卻不需要他的同情。令萬尼亞沒想到的是阿斯特羅夫醫生也對葉列娜有好感,葉列娜對萬尼亞沒有一點愛情,但是她卻傾心于阿斯特羅夫,在她看來阿斯特羅夫醫生和她是同樣類型的人,“伊凡·彼得洛維奇,我覺得,為什么他和我都是你的這么好的朋友呢?就是因為,他和我,都是很煩悶的,都是不滿意于生活的人啊。是的,都是很煩悶的”[5]19,在萬尼亞和阿斯特羅夫之間,她絲毫沒有考慮過萬尼亞,直接選擇了阿斯特羅夫。之后葉列娜和阿斯特羅夫的幽會還被萬尼亞撞見了,這對萬尼亞本就岌岌可危的精神狀態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謝列勃里雅科夫這一信仰在萬尼亞的心中轟然倒塌之后,葉列娜成了萬尼亞生命中新的希望,如今就連對愛情的小小期望都被現實撞個粉碎,萬尼亞的苦悶心情達到了極點。
最后是掙扎的失敗。在苦悶和平庸的日常生活面前,萬尼亞也做出了反抗。導火索就是謝列勃里雅科夫企圖變賣莊園,在這一事件中,萬尼亞對謝列勃里雅科夫感到徹徹底底的失望,過去的二十五年變得毫無意義,一切都成了虛無,萬尼亞向謝列勃里雅科夫怒吼,“你毀了我的生活!我沒有生活過!我因為你的過錯,犧牲了我自己最好的年月!你是我的最可恨的仇人!”[5]60,萬尼亞失去理智,在瘋狂的狀態中舉槍企圖射擊謝列勃里雅科夫,在幕前幕后各開了一槍,但是兩槍都沒能打準,他對庸常生活的這次反抗以失敗告終。隨后萬尼亞又試圖服嗎啡自盡,好在被阿斯特羅夫醫生和索尼雅及時攔下來了,他內心的矛盾沖突得不到解決,但是卻不得不面對令人難以接受的現實。
三、無意義的等待
契訶夫在《萬尼亞舅舅》中使用的是“圓周結構”,劇作的第一幕和第四幕發生在同樣的場景中,故事從開始到結束人物的生活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契訶夫一反傳統戲劇的結構模式,人物一登場就明白自己的處境,劇情的緩慢推進只是為了證明這種處境的存在。人物的命運可能會出現某種變化,但人物的尷尬處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2]28。
當謝列勃里雅科夫和他的妻子離開莊園之后,萬尼亞和索尼雅又過回了以前的生活,他們還是日日辛勞。在送別謝列勃里雅科夫時,萬尼亞許諾以后還會定期把收入寄給他,“一切都會和先前一樣”[5]73。唯一發生了變化的就是萬尼亞的心境,進行過抗爭之后還要面對失敗的結果,他對改變現狀無能為力,接下來的生活對萬尼亞來說或許更加難挨,“他既然找不到出路,也找不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只好又重新開始替教授做那種他現在十分痛恨的工作。一個曾經一度體驗了精神解放的人,又不得不重新戴起了奴隸的枷鎖”[3]242,在短暫的精神覺醒之后萬尼亞要面對的是更深的痛苦,他在現實生活面前只能妥協。
索尼雅沒有對生活發出過抱怨,面對舅舅萬尼亞的苦惱,索尼雅始終在耐心安慰,當一切都歸于平靜之后,也是她在勸導萬尼亞勇于面對,告訴他休息的一天總會到來,美好的生活總會出現。
我們要繼續活下去,萬尼亞舅舅,我們來日還有很長、很長一串單調的晝夜;我們要耐心地忍受行將到來的種種考驗。我們要為別人一直工作到我們的老年,等到我們的歲月一旦終了,我們要毫無怨言地死去,我們要在另一個世界里說,我們受過一輩子的苦,我們流過一輩子的淚,我們一輩子過的都是漫長的辛酸歲月,那么,上帝自然會可憐我們的,到了那個時候,我的舅舅,我的親愛的舅舅啊,我們就會看見光輝燦爛的、滿是愉快和美麗的生活了,我們就會幸福了,我們就會帶著一副感動的笑容,來回憶今天的這些不幸了,我們也就會終于嘗到休息的滋味了[5]77。
索尼雅這番話看似是對生活滿懷期望和信心,是樂觀精神的顯現,實際上折射出的卻是濃重的悲傷與無望,有學者指出,“索尼亞對生活的信念,并非因為她理解了生活的真正意義,而來源于她的宗教忍耐精神”[2]28。正是這種忍耐精神,才讓人覺得索尼雅這個人物身上也是具有悲劇色彩的,她的青春也同樣窒息在莊園里,沒有外出社交,只有每天的辛勤勞動。索尼雅在六年里一直愛著阿斯特羅夫,但她從未向阿斯特羅夫表白過心意,阿斯特羅夫也未曾注意過她,在阿斯特羅夫愛上葉列娜時,索尼雅對于愛情的幻想就已經破碎了。她總是在等待不知道是否存在,不知道何時才會到來的東西。
萬尼亞和索尼雅對休息的等待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沒有人知道是否存在休息的時刻,誰也不知道美好的生活究竟什么時候才會出現。他們一直都在等待,但什么也沒有等來,這種無望的等待正是劇作悲劇意味的體現。
四、結語
《萬尼亞舅舅》整個故事沒有太大的跌宕起伏,描寫的是萬尼亞一家的日常生活,但其中的意味卻又超出了日常瑣事的范疇,表現出的是人們面對生活的苦悶與疑惑。《萬尼亞舅舅》中戲劇沖突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人物內心的矛盾與沖突,戲劇沖突被內化了。《萬尼亞舅舅》與那些重視情節的戲劇比起來更加關注人的精神狀態,與人物的動作相比更加注重表現人物的心理和思想,可以看作是對屠格涅夫“抒情心理劇”的繼承。這部劇作寫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個一切都在發生轉變的年代,盡管這部作品是在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思潮中創作出來的,但其中已經顯示出了某些現代主義戲劇的特征,像是萬尼亞和索尼雅的無望等待,其中透露出了荒誕的色彩。契訶夫在《萬尼亞舅舅》中加入了一些喜劇的成分,讓劇作中的悲劇色彩顯得不那么濃重,但劇作中表現出的悲劇性卻不容忽視。森林被砍伐、自然被破壞不僅僅是生存環境的被毀,這在契訶夫的戲劇中代表的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失落,人們找不到出路,于是陷入痛苦和煩悶之中。萬尼亞在劇中的經歷指向的是一條理想破滅之路,在信仰倒塌、愛情破碎后,就連對生活的掙扎都顯得那么無力,萬尼亞掙扎的失敗正是說明其內在沖突難以得到解決,只能向現實妥協。而索尼雅勸慰萬尼亞的一番話看似是她樂觀精神的體現,實則蘊藏了濃重的悲哀之情,在生活面前無力反抗,因此只能忍耐痛苦,將希望寄托于不知何時才會到來的美好生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