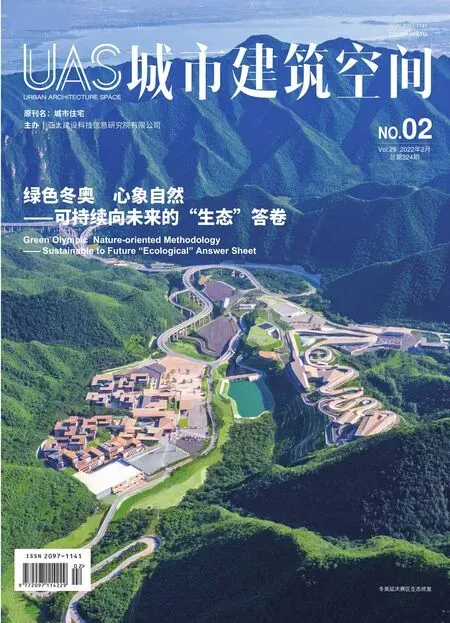基于現(xiàn)象學的城市小微公共空間更新研究
——以枇杷山正街社區(qū)某小微公共空間為例
李弘力
(重慶大學建筑城規(guī)學院,重慶 400030)
0 引言
城市空間微更新興起,對于土地的利用從增量轉(zhuǎn)為存量,這是一種順應時代需求的轉(zhuǎn)變。在此背景下,城市公共空間作為城市意象、公共活動、知覺體驗的重要場所,呈現(xiàn)出向“小”與“微”轉(zhuǎn)變的趨勢,而這種轉(zhuǎn)變是由土地資源、經(jīng)濟、相關政策等所決定的。
但是目前對于城市公共空間體系中小微公共空間的關注仍然不足。雖然此類空間不能像大型公園、綠道、城市廣場等為公共空間體系提供結(jié)構支撐,但卻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最為緊密。小微公共空間是城市居民與外部空間發(fā)生頻繁互動的場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現(xiàn)象學使用質(zhì)的、描述的、直觀的方法看待與解決問題。這樣的特點雖然使其難以介入尺度更大的公共空間體系,卻非常適用于人本尺度的小微公共空間,為小微公共空間提供理論與方法的指導。小微公共空間目前面臨3個層次的問題,即人生活在怎樣的空間中、這樣的空間意義何在、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與環(huán)境相處。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的現(xiàn)象學分別回答了這3個問題:人生活在以本質(zhì)性的模糊為特征的世界中,人通過“筑造”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并獲得自身存在的價值,人通過綜合知覺與環(huán)境互動并產(chǎn)生生活的體驗、記憶與意義。
1 研究對象與理論基礎
1.1 小微公共空間
城市小微公共空間是公共空間體系中最末端的部分,也是一種基于人本尺度的特殊類型。從廣義上講,它是一種基于人本空間尺度和類型-形態(tài)視角的對城市公共空間進行最小尺度范圍篩選的空間類型[1]。
1.2 現(xiàn)象學理論
現(xiàn)象學進入到人居環(huán)境領域大體有兩種傾向,一種受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現(xiàn)象學影響,主要討論存在、棲居、場所等;另一種受梅洛-龐蒂知覺現(xiàn)象學的影響,主要關注身體、知覺、記憶、體驗等。而海氏與梅氏的哲學思想又深受現(xiàn)象學創(chuàng)始人胡塞爾的影響。
1.2.1 胡塞爾的生活世界
現(xiàn)象學的創(chuàng)始人胡塞爾如此定義現(xiàn)象學:“現(xiàn)象學:它標志著一門科學,一種諸科學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但現(xiàn)象學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思維態(tài)度:特殊的哲學思維態(tài)度和特殊的哲學方法”[2]。現(xiàn)象學強調(diào)面向事物本身,即不帶任何理論成見地去看待事物。
“生活世界的最基本含義當然是指我們各人或各個社會團體生活于其中的現(xiàn)實而又具體的環(huán)境”[3]。“如果我們的出發(fā)點是知覺性的世界,并且,我們研究通常在我們周圍的對象……它們都以本質(zhì)性的模糊為特征”[4]。
如何認識世界決定了改造的態(tài)度。胡塞爾現(xiàn)象學喚出了新的設計思路,即不帶任何設計理論成見地做設計。既然生活世界是科學世界的基礎,設計的最終目標就應落點于具體的人的體驗。這也不難理解為何功能與形式合理的方案也常帶來糟糕的體驗。也能因此發(fā)現(xiàn)城市建設中出現(xiàn)的很多問題是由于設計師抽象與簡化地理解世界后又把其當作世界的全部實際建構出來。
1.2.2 海德格爾的棲居
“世界黑夜的貧困時代久矣。既已久長必會達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時代貧困”[5]。這一貧困恰是精神上的。在當今這個技術大爆發(fā)、生活快節(jié)奏的時代,精神貧困的嚴重性不減反增。
海德格爾認為棲居與筑造并非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它們的本質(zhì)關聯(lián)為筑造即棲居,筑造即存在。所以他說“①筑造乃是真正的棲居;②棲居乃是終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③作為棲居的筑造展開為那種保養(yǎng)生長的筑造與建立建筑物的筑造”[6]。因此,筑造本身就是一種棲居,也是人存在的方式。
人的存在有賴于筑造,現(xiàn)今“筑造”這一件事已經(jīng)托付于從事設計工作的人,設計師擔起了“作詩”的重任。橋橫跨兩岸聚集起周邊形成場所,也因此將蒼穹、大地、諸神與終有一死者保藏。那些帶給人場所感的地方是“定性的”“整體的”現(xiàn)象,不能約簡其任何的特質(zhì)[7]。作為筑造者的設計師需要設身處地地思考使用者的感受,綜合考慮整體現(xiàn)象。這種整體現(xiàn)象包括:具有人造和自然要素的特定景觀;一種可為場所承受的活動模式;一套同時是個人又是共有的意義。以此出發(fā)創(chuàng)造充滿意義的場所,幫助終有一死者與環(huán)境互動、實現(xiàn)定居。
1.2.3 梅洛-龐蒂的知覺
知覺現(xiàn)象學認為知覺是認識之始。知覺是人體器官解釋和組織感覺以產(chǎn)生有關世界的概念的一個富有意義的體驗過程[8]。梅洛-龐蒂繼承了胡塞爾哲學中關于生活世界本質(zhì)性模糊的思考,并進一步強調(diào)了身體的重要性,重視身體在世界中的體驗。
當我們借由身體在世之時,在同一地點的人們便能抵達他們共有的意識基礎,這樣的知覺與自身獨有的知覺體驗相融合便得到了綜合的知覺。人與空間的關系也就此建立。我們和空間的關聯(lián)其實并不是一個不帶肉身的主體與一個遙遠的對象間的那種關聯(lián),而是一個居于空間中的主體和他所親熟的環(huán)境或曰場所間的關聯(lián)[9]。
知覺是整體性的,整體大于部分。梅洛-龐蒂用大世界與小世界進行比喻,整體性的知覺體驗便是“大世界”,具體的感官體驗是“小世界”,他認為“小世界”是向“大世界”開放的。這意味著在研究人與空間的聯(lián)系時,并非只能關注被稱作“聯(lián)覺”的整體性,也可以從不同的具體的“小世界”入手,最終通達整體,這樣能保存每一種感官的特殊性。從梅洛-龐蒂知覺現(xiàn)象學出發(fā)的空間設計導向一種人與環(huán)境間的互動關系的設計,打開了設計的新視角。
2 基于現(xiàn)象學的小微公共空間設計
2.1 生活世界——場地解讀
枇杷山正街社區(qū)位于重慶市渝中區(qū)兩路口街道,是典型的山地老舊社區(qū),社區(qū)共計1 551戶,老年人在社區(qū)人口所占比例為11%,并且流出流入人口約占總?cè)丝诘?/3。盡管周邊配套設施較完善,生活氛圍較濃厚,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設施越發(fā)顯得老舊,人口逐漸流失,社區(qū)正在失去活力。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進行城市微更新,使這里的居民產(chǎn)生認同感與歸屬感,實現(xiàn)再“定居”,迫在眉睫。本次設計以枇杷山正街某典型小微公共空間為例,用現(xiàn)象學方法對該場地進行更新,使之成為觸媒激活枇杷山社區(qū)的活力。
該小微空間是山城梯道空間,垂直于等高線南北向聯(lián)系枇杷山正街與枇杷山后街,兩街高差為10.7m。梯道的西側(cè)為院壩,院壩中有一幼兒園和菜館,梯道的東側(cè)通過天橋連接菜市場入口。該空間服務對象主要為周邊居民。經(jīng)不同時段的多次觀察,居民均停留在枇杷山正街與后街上,會搬上木凳與塑料凳打牌、下棋與聊天。在場地中居民幾無停留,埋頭費力提菜上下梯坎。對周邊居民進行訪談并采訪居委會,掌握了居民對停留空間與設施缺少的想法。
從居民的體驗角度出發(fā)可發(fā)現(xiàn)核心問題是場地無法滿足居民的需求。具體表現(xiàn)在:場地有功能卻缺氛圍,活動多為通行等必要性活動。以此分析出發(fā),提出兩點設計策略:煥活場地氛圍、優(yōu)化活動類型。
2.2 詩意棲居——設計方法
2.2.1 以藝“在場”煥活場地氛圍
場地失落,除承載必要性活動外,無人問津,處于一種哲學上的“不在場”狀態(tài),即場地雖然被頻繁使用卻未在周邊居民的心中占有生活的位置。因此要重新“在場”,需要先讓居民意識到該場地應是一個場所,繼而在日常的使用中產(chǎn)生對該場所的認同與歸屬。
本設計以藝術化的方式介入。這種介入保留場地原有的特征,加入新的體系并解決場地現(xiàn)有的問題。將藝術置入,營造更具活力的場所氛圍,不僅是煥活該場地,也以該場地的更新帶動周邊社區(qū)空間的活力,甚至激活片區(qū)的活力。如同在巴黎的城區(qū)中置入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在該場地設計時也置入獨立于場地的另一藝術化的景觀裝置,打造老梯坎上的“蓬皮杜”,實現(xiàn)居民對場地的注意,煥活場地的氛圍。
2.2.2 以模“作詩”優(yōu)化活動類型
活動類型的優(yōu)化分為兩類,改善必要性活動的體驗與增加自發(fā)性活動的開展。海德格爾認為人的生活方式?jīng)Q定其存在,“筑造”是棲居也是存在。枇杷山正街廣場的這塊場地的問題雜多,設計采用模數(shù)化的方鋼架這一簡單設計要素為場地“作詩”。在老舊社區(qū)的小微公共空間中置入一個新的體系,用方鋼管為架,利用梯坎兩側(cè)的空隙搭建起獨立于現(xiàn)有結(jié)構的構架,以此置入新的空間、新的功能和新的活動。
模數(shù)化的鋼架使場地梯道的兩側(cè)空間得以利用。梯道東側(cè)利用鋼架上搭起的平臺提供原本需要卻不存在的休憩與交流空間,并且也作為菜市場功能的延伸,承載社區(qū)農(nóng)場的功能,進一步激發(fā)場地活力;場地西側(cè)利用鋼架、平臺與玻璃提供兒童游樂、家長等候與交談、菜館外擺等功能。梯道中部架有小型升降平臺與觀景平臺,為老年人提供便利,也為居民提供了觀江的空間。
2.3 知覺綜合——體驗設計
2.3.1 糾纏的目光
視覺系統(tǒng)是人的知覺活動中最為活躍的感覺系統(tǒng),為人提供最多的感覺信息。視知覺的設計應追求“糾纏”的體驗。視覺設計不能是單純的圖像化刺激,而應考慮到身體與場地的聯(lián)系。人在場地中行走與停駐,同時不同的人也參與其中,共同形成視覺上的糾纏體驗,最終激發(fā)人的情感體驗、喚起人的回憶、領悟到某種意義。
枇杷山正街廣場地設計時充分利用長梯道,增加穿行時動態(tài)的視覺變化,以緩解疲勞感。為此,在梯道兩側(cè)順應場地周邊條件,安排合理的功能,布置不同特質(zhì)的平臺與模塊。居民在通行時兩側(cè)有不同的事件發(fā)生,形成不同的場景,產(chǎn)生步移景異的感受。
梯坎兩側(cè)方鋼架上的休息平臺,則通過高低錯落的布置,以及其上模塊的遮擋,處理靜態(tài)的視線關系,形成看與被看的關系,產(chǎn)生糾纏的視覺體驗。同時考慮到夜間的照明問題,通過燈光模塊的置入,在夜晚提供安全溫暖的氛圍,使夜晚的通行體驗提升。燈光模塊中部分通過聲音產(chǎn)生互動,提升場地在夜晚的活力,也調(diào)動視與聽的聯(lián)覺,加深使用者的體驗與記憶。
2.3.2 協(xié)奏的聲息
聽覺提供給人僅次于視覺的感知信息量。自然的鳥叫蟲鳴與電閃雷鳴,街道中嘈雜的人聲與汽車的鳴笛聲,都印刻在人的頭腦中。因此,聲音的設計通常作為其他知覺的“配角”進行協(xié)奏。就如在古寺游覽時聽到鐘鳴,在雨天的園林中休憩聽到雨打芭蕉,聲音會加深人對某一場景的記憶。
聽覺的設計有意為之而似未經(jīng)設計。方鋼的清脆聲響,會被一旁幼兒園的孩子發(fā)覺。雨天,雨滴與鋼材協(xié)奏,加強人對天氣的感知。場地的空間設計接納了一旁的菜館,使其外擺空間融入場地之中,鼓勵菜館的營業(yè),使之能在每天的特殊時段傳出熱鬧的聲響,暗示時間也提示著歸家,加深使用者對場所的記憶。同時,聲音融入燈光模塊,聲光模塊更能激發(fā)人的興趣,鼓勵人與景觀的互動,加深對場所的記憶。
2.3.3 場所的氣息
氣味的知覺在室內(nèi)空間很難體驗,在室外空間設計時應充分利用。不管是人間的煙火味還是自然的氣息,都可以用來刺激人的感知。正因氣味體驗的稀少,才使得人在接收到氣味時更能注意到。人們常會駐足尋覓不經(jīng)意間聞到的花香,會厭惡飄出的臭味捏緊鼻子。不經(jīng)意可能產(chǎn)生美,而濫用或可招來厭惡,因此在設計嗅覺時應謹慎。
該場地的氣味設計從兩個方面實現(xiàn):一是利用一旁的菜館在每日特定時段傳出的菜香,提示路過居民時間的流轉(zhuǎn),并且引導一種歸家團聚的情感;二是利用芳香植物的營造,在夜晚或特定季節(jié)帶來自然的芬芳。通過在植物模塊中栽種迷迭香、鼠尾草等植物,提示居民進入到一個場所中,使這里“在場”。
2.3.4 生命的觸感
厚重的生命力不僅由擁有生命的動植物帶來,也可以由那些“扎根”在某一地區(qū)的傳統(tǒng)建造材料帶來。這樣的材料擁有歷史感,深入到當?shù)氐奈幕校舸嬖诋數(shù)厝说纳顚佑洃浝铩R虼耍谟|覺的設計中避免使用模仿某種材質(zhì)的材料,要考慮到人的觸摸,并且看的同時內(nèi)心也在觸摸,材料的虛假會疏遠人與生活的距離。
對梯道的青石保留并構筑新的鋼結(jié)構體系正是出自這樣的考慮,不破壞原有的生命的觸感并將其保存。并且,鋼材更多作為結(jié)構的材料,平臺與模組的材質(zhì)使用與人更親近的木材。觸覺并非僅是皮膚的知覺,當人通過目光掃過場地時也是在“觸摸”,木與青石拉近了人與場地的距離,喚起人深層意識中的感知。
3 結(jié)語
基于現(xiàn)象學進行空間設計,并非不顧緣由地把人的各種知覺全部調(diào)動,這種走馬觀花式的知覺設計同樣危險,同樣偏離了我們的生活本身。設計師的目的是幫助終有一死者在這片大地上定居。定居依賴于人對世界的“詩意”體驗,這種體驗的源泉是“真”,是對生活世界的真實知覺。知覺的設計是希望喚醒人本就存在的多樣感受,不被如今視與聽的流行趨勢裹挾,意識到我們的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