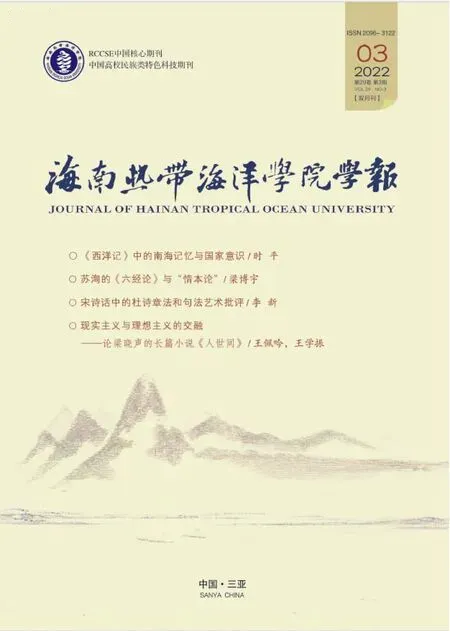論蘇軾關于韓愈的評說
阮 忠
(海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海口 571158)
蘇軾元祐七年(1092)知揚州軍州事而論韓愈,實出偶然。時值潮州太守王滌新建韓愈廟,求取廟的碑文,請蘇軾執筆,故有蘇軾的《韓文公廟碑》,一稱《潮州韓文公廟碑》。
韓愈死于公元824年,蘇軾生于公元1037年。這相距的200多年間,李唐王朝亡了,天下分裂而有五代十國。五代十國先后也亡了,趙宋收拾山河重歸一統。世事變遷,滄海桑田,蘇軾越過時空和韓愈的關聯:一是儒學,二是古文。蘇軾之師歐陽修服膺韓愈,也服膺古文古道。歐陽修主持了嘉祐二年(1057)的科考,讀了蘇軾的科考文《刑賞忠厚之至論》《謝歐陽內翰書》后,感喟當避開一條路,讓蘇軾出人頭地。蘇軾在《刑賞忠厚之至論》里尚儒者之仁,是他濟世思想的核心;在《謝歐陽內翰書》里重三代兩漢之文,是他古文取法的方向。二者趨于韓愈的思想和古文路數。他對歐陽修充滿敬意,說歐陽修“名冠當代,才雄萬夫”[1]1348“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1]1345。而歐、韓的關聯,蘇軾說了一句:“歐陽子,今之韓愈也。”[1]316這同時也是對韓愈的推崇。盡管他早年在《韓愈論》《揚雄論》里對韓愈的人性論等很有批評。
祭文重情,墓志銘重事,蘇軾為韓愈作的廟碑文,則在悼念中情、事、理相兼,在追懷之際淡化了悲哀。其文問世,所有的祭韓愈文都黯然失色,所有的韓愈評說都不及蘇軾評說有光彩。
一、 匹夫而為百世師說
《韓文公廟碑》開篇極富氣勢,所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1]508,用筆超然。前此,戰國孟子說過“圣人百世之師也”[2]976,他以伯夷、柳下惠為圣人,隨后說:“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況于親炙者乎。”[2]976孟子以伯夷和柳下惠為圣人,意在他們的人格對后世的深刻、久遠影響,其產生的上行下效作用,正是蘇軾在給潮州太守王滌信中說的教化。而所謂“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禮記·中庸》崇尚的“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3]1458,這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
蘇軾的“百世師”“天下法”說與之一脈相承。他認為“匹夫”能如是,是因為其言行關乎天地的自然變化和社會的興盛衰亡。這種人肩負了天地的、歷史的使命,求作為而生,死亦不朽。蘇軾有《論孔子》《子思論》和《孟子論》。《論孔子》說孔子進言魯定公“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1]149,因而涉及墮季氏三都與齊景公時三桓不臣事。《子思論》則說孟子之后儒者相爭,致使“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1]95,所幸子思撰述都是圣人的微言篤論,天下同是而無人非議,不像孟子以性善論自以為是地行于天下。《孟子論》則說孔子死后,諸子不得孔子源流,唯孟子“深于《詩》而長于《春秋》”[1]97,可謂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蘇軾這三篇言及孔子的文章中所言“百世師”“天下法”之說,不是針對孔子,而是針對韓愈,所以南宋朱熹讀了第一句就大為不快,棄而不讀。
蘇軾隨后扭轉話題,講了申侯、呂伯、傅說的故事。相傳周宣王的大臣申伯、周穆王的大臣呂侯是嵩山所生。《詩經·大雅·崧高》講甫與申為山岳所生的故事,“崧高維岳,駿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4],此二人是周王朝的輔佐。《離騷》里“說操筑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5]講的傅說故事,這傅說相傳是商高宗武丁的國相。蘇軾用了《莊子·大宗師》里傅說輔佐武丁而有天下的說法,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6]。蘇軾講這三個人的故事,強調“古今所傳,不可誣也”[1]508,照應剛說過的“匹夫”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天地的造化。
然后,蘇軾引了孟子的名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1]508,孟子的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2]200-202。他對孟子很有好感,曾說:“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1]316孟子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蘇軾這里也用了“五百年”的概念,且跳過了韓愈說的孟子之后有荀子和揚雄。他贊賞孟子的“浩然之氣”,說面臨“浩然之氣”,富貴、智謀、勇猛、論辯都蒼白無力,它超越了依人而存在的富貴、智謀、勇猛、論辯,讓人看到的不僅是蘇文如潮的奔涌,而且還感受到他的言外之意,即匹夫能為“百世師”、一言能為“天下法”,還在于自我的修養。
蘇軾還說過:“韓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余年后便斷得如此分明。”[1]2035他把韓愈和荀子、揚雄區分開來,在談韓愈時也讓人看到了他的識見。不過,蘇軾不滿意韓愈的“性三品”即上品為善,下品為惡,中品為可善可惡,行善則為善,行惡則為惡,說韓愈:“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1]110但這并不妨礙他對韓愈的高度評價。
韓愈的出現既順了天時,越五百年而興;又養浩然之氣,自我修為。蘇軾說得很粗略,沒有具言韓愈重教化。他的“匹夫說”,意在韓愈原本是一介匹夫。他曾將韓愈的示兒詩和杜甫的示兒詩相較,說韓愈這首長篇五古寫的“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樞”“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7],正是匹夫之道,不像杜甫所言都是圣賢事。韓愈在中唐不顧流俗,悍然作《師說》公開為人師,傳道、授業、解惑。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被貶潮州,那時的潮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試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7]因此,他在潮州半年多時間里置鄉校、施行孔子的德禮教育,潮人印象深刻,兩百多年后重修韓文公廟,請蘇軾擬碑文,都與韓愈的此舉有關。
蘇軾就韓愈廟說的“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關乎天地造化、時運盛衰、淵源有自和社會影響,這對韓愈倒也切合,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二、 道喪文弊的“起濟”說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蘇軾在《韓文公廟碑》里說:“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1]509這話言簡意深。
在時間和朝代上,從東漢到韓愈生活的中唐,中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和初唐、盛唐,歷時近六百年。王朝更迭之際的“道喪文弊,異端并起”,韓愈在《原道》里說,周道衰微,孔子死后秦焚書,黃老之說興于西漢,佛教興于晉、魏、梁、隋。儒學的道德仁義呢?“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歸于墨;不入于老,則歸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甚至老子、佛教之徒都說:“孔子,吾師之弟子也。”[8]2662所以韓愈不禁感嘆:“噫!后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8]2663韓愈是堅定的奉儒者,但他不是高深的儒學理論家,也沒有系統的、邏輯嚴密的儒學論。蘇軾說他對于圣人之道,好其名而未樂其實。因為“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1]114。韓愈尊孔孟,并非好其名而未樂其實。韓愈曾說讀孟子書,方知孔子之道尊,“求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8]2776。而且,信守孔孟最核心的仁義思想,排楊、墨、佛、老,這話應分開說:孟子時楊、墨之道恣縱天下,排楊、墨的是孟子;韓愈時,佛、老之道并興,排佛、老的是韓愈。
東漢末年,儒學衰敗,道教興起,佛教東漸,儒學不再獨尊。于是有玄學重老莊,有梁武帝重佛教,唐初乃至中唐,儒、道、佛三教并行,相融亦相斥。韓愈梳理儒學之道的傳播,說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8]2665。這讓韓愈對異端即道、佛有深切的痛恨,甚至說“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8]2665,要讓道、佛之徒還俗,把道經、佛經燒了,把道觀、寺廟改造成民房。然后“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8]2665。這與孟子仁政、王道的社會理想相吻合。
儒學道喪卻有文弊與它同行,道文相攜,文以載道,道喪自然文弊。蘇軾和韓愈有同樣的想法,學文也是學道。韓愈崇尚儒學之道,與崇尚三代兩漢之文一體,他在《答李翊書》中說自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8]1455。所以,他求道醇時,也求文之醇,這文就是古文,或說三代兩漢之文。但在東漢后,文風漸變,散體古文慢慢衍生出駢體文,講聲律、對仗、用典、華麗。西晉陸機作《文賦》說文章寫作的技巧,是駢體文成熟的重要標志。其后有了南朝駢文的鼎盛,并延續至隋和盛唐,古文卻衰落了。“文弊”之說就針對此。蘇軾在《韓文公廟碑》里列舉了唐太宗貞觀的開國之興和唐玄宗開元的繼統之盛,貞觀的房玄齡和杜如晦,曾助唐太宗得天下,因善于謀劃有“房謀杜斷”之說,后均官至宰相。姚崇和宋璟則助唐玄宗走向開元盛世,亦官至宰相。蘇軾說他們未能挽救“道喪文弊”的局面,殊不知李唐奉老子為祖,自然信道,而唐太宗開國之初就信佛,在這種情勢下,韓愈想求儒學一尊,想以古文傳道是艱難的。但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奮起以古文抗爭,以儒學之道爭勝,使中唐古文勃然而起。
匹夫韓愈少年喪母,繼而父親與世長辭,于是依傍兄嫂,不幸哥哥韓會又死了,嫂子鄭氏把他拉扯成人。他曾上書給崔元翰,說自己“今所病者,在于窮約,無僦屋賃仆之資,無缊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8]1181。又向友人崔立之訴說,自己“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8]1262。這樣艱苦的生活以致他在中進士后,因遲遲未能得官時難以忍耐,一個多月內三次上書宰相求官。韓愈艱難地走上政壇和文壇,舉起“古文”的旗幟推行古道,曾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8]1500。一時間天下文人靡然相從。北宋歐陽修說韓愈倡古文,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人唱和,排逐百家,上接漢、周,使“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9]。到蘇軾說“三百年于此”,其實只有270年左右,而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1]509,正是因為韓愈興古文,改變了八代即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的文風,使儒學道統到他這兒得到承續,儒學之道得以復興。
北宋立國之后,文壇即生尚唐之風,北宋初年詩壇三體“白體”“晚唐體”“西昆體”都以唐人詩為范式。而在古文風氣上,先有柳開、石介尚韓崇儒,后有歐陽修把尚韓崇儒推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記舊本韓文后》是尚韓的重要篇什,檢討了韓文在北宋初年的命運:歐陽修少時,盛于世的是楊億、劉筠時文,憑時文可取科第而擅名聲。他及第后,與尹師魯等人倡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余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10]1056。蘇軾在嘉祐二年(1057)隨父親蘇洵出眉山到汴京應試科舉時,歐陽修知禮部貢舉,興韓愈古文,排斥“太學體”的奇險怪異之文。蘇軾在這時候深受歐陽修賞識走上政壇和文壇,他對韓愈和歐陽修古文別有會心。如韓愈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蘇軾寫了《跋退之送李愿序》,還說:“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執筆則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1]2057這話有調侃的意味,但崇韓無疑。并說:“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后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1]1423-1424蘇軾不像歐陽修,歐陽修還看得上皇甫湜、孫樵的古文,而在他眼里,唐代古文唯有韓愈。他還說:“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1]2210曾要自己的侄孫蘇元老熟看兩漢書和韓、柳文。
蘇軾受韓愈影響,為文也好平易暢達。他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1]2069這種文思泉涌而又順應自然的寫作狀態,在《韓文公廟碑》里得到體現,行所當行,止所不可不止。至于“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1]509的桂冠,只有韓愈擔當得起。蘇軾自己承襲韓愈的古文之風,好儒好道且不排佛,但在治國理天下上,亦像韓愈堅執儒學,晚年在海南了得“海南三書”或說“經學三書”,即《易傳》《書傳》和《論語說》,系統闡發自我的儒學思想,成為他在經學上最高成就的代表。
三、 忠勇關乎盛衰說
這里說韓愈的忠勇關乎盛衰,只取了蘇軾“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1]509里的“忠勇”,他說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也關乎盛衰。這一點前面提及,不再贅言。蘇軾說韓愈忠勇,涉及兩方面的問題,即“忠犯人主之怒”和“勇奪三軍之帥”,其中很有故事。
韓愈一生,兩次遭貶都在于一片忠心。他中進士后三次寫信當朝宰相求官,求官不得,無奈去汴州宣武軍節度使董晉的麾下做了一個觀察推官,管理文書。不料遭汴州兵亂,又到徐州武寧節度使張建封門下做推官,直到貞元十八年(802)才在京城做了朝廷的四門博士,次年升遷為監察御史,時年35歲。(貞元十九年)適逢天旱人饑,韓愈上了《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說京郊諸縣因干旱、早霜以致莊稼幾近無收,百姓“棄子逐妻”“坼屋伐樹”“寒餒道途,斃踣溝壑”[8]1611民不聊生,得罪權臣,被貶為陽山縣令。韓愈第二次被貶是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迎佛骨供奉宮中,他上《論佛骨表》,明知唐憲宗奉佛以求長壽,他逆向而行,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帝王多長壽,自佛法傳入中國,奉佛之帝往往是“亂亡相繼,運祚不長”[8]2288。還有百姓相隨,焚頂燒指,解衣散錢,棄業佞佛,傷風敗俗,社會衰微,實在不是小事。唐憲宗閱表大怒,險些要了他的性命,最后把他貶為潮州刺史,讓他在艱困的環境中痛苦自省。
“勇奪三軍之帥”說的是唐穆宗長慶二年(822),韓愈奉命去鎮州宣撫王廷湊兵亂,李翱在《禮部尚書韓公行狀》里提到這件事。當時成德節度使田弘正被殺,深冀節度使牛元翼被圍攻,王廷湊勢頭正盛。韓愈奉命前往,危險萬分。唐穆宗擔心他遭遇不測,派使者趕來勸他慢行,韓愈說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驅馬疾馳至叛軍軍營,面對刀劍威逼,侃侃陳辭,曉以利害,王廷湊最終率軍放下武器,歸順朝廷。韓愈只身匹馬平定廷湊之亂。這與他兩次遭貶事一樣關乎朝廷興衰。
蘇軾與韓愈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他曾評價歐陽修:“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1]316而他自己熙寧四年(1071)有《上神宗皇帝書》,對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提出批評,希望神宗皇帝能夠“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1]729,忠心可與韓愈比肩,但思想的表達沒有韓愈那樣激烈、銳利。他在知揚州前,以詩諷刺新法、又在《湖州謝上表》里以自貶自損的語氣嘲諷新黨中人,遭了北宋最有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眾人營救,逃了死罪,被貶黃州。那時,他在性格上的不肯隨順,同樣表現在日常語言上:“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1]376這和韓愈相類,只是不及韓愈常與世俗不合,與權貴針鋒相對。至于他的遭遇比韓愈更慘,為“烏臺詩案”所累,貶黃州后,又遭老賬新算,晚年貶惠州和儋州,而韓愈的貶陽山與貶潮州之間并無關聯。蘇軾曾在《江城子·密州出獵》里有過“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之念,欲去西北邊境建立功勞,終究沒有韓愈那樣有英雄氣的平亂之舉,直到知定州時,一展軍事才能:“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污甚者配隸遠惡,然后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眾皆畏服。”[11]從這里來看,一介書生或說身為士大夫的蘇軾也是有果敢威嚴的。
把蘇軾和韓愈作這樣簡單的比較,是想說明蘇軾的忠勇氣質和韓愈有相近的地方,曾經小視韓愈人性論和儒學上論理不精的他,在這里仰視韓愈的人格和精神。說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這樣的話,深感韓愈雖為一介儒生,超越凡俗,為一般人不能及。所以蘇軾不禁在《韓文公廟碑》后的銘詩里說韓愈:“公昔騎龍白云鄉,手抉云漢分天章,天孫為織云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1]509肯定韓愈的貢獻。
作為一介儒生,韓愈的忠勇像他在文、道上表現出的人生精神一樣,彰顯了他的君子人格,權勢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的所為并非為己,而是為人,與社會盛衰緊密相系。
四、 “能者天”“不能者人”說
讀《韓文公廟碑》,少有人關注下面這番話: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云,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1]509
蘇軾在這里論韓愈回到具體的生活及常理。他說到的“天人之辨”,是從先秦天人感應過來的。天人相合,故有天的意志論、人格論、最高統治者論以及用賞善罰惡掌控人世間的蕓蕓眾生論。隨后有天人相分,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說。但人們終究沒有拋棄天人感應,所謂的“天不容偽”正是天人感應理念下的推斷。天真誠,既不作偽,也不容偽。人則是“無所不至”,真誠者有之,虛偽者也有之。他說人的智慧可以欺騙王公大人,但欺騙不了小豬小魚,用的是《易經·中孚》的典故。原典說:“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王弼注稱:“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賤之物,信皆及之。”[12]意思是占卦得小豬小魚則吉利,就因為真誠,隱逸、微賤者無欺。他這話細品很有深意,假的終歸水落石出,原形畢現。但他沒有具言指的是誰。隨后蘇軾又在《韓文公廟碑》里說了一句:“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明言用武力可以得天下,但得不了普通百姓的心。宋哲宗治下,天下大體承平,無武力爭奪天下之事。蘇軾主張深結天下之心,科考時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就主張罰過乎義則去,賞過乎仁仍存,是他的宅心仁厚。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有限的,最需要的是精誠,這也是常理。以此為理論前提,蘇軾進而在《韓文公廟碑》里說韓愈為君為民的一片精誠有三:
一是“能開衡山之云,而不能回憲宗之惑”。前者從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詩“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8]213化用出來。蘇軾以此為喻,說韓愈能開世俗迷霧。如世俗在避諱、求學上的迷霧,但“不能回憲宗之惑”,即不能阻止唐憲宗奉佛,迎佛骨于宮中供奉。韓愈的命運因《論佛骨表》頓變,貶潮州而遠離了長安。
二是“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謗”。這說他做潮州刺史時,當地人為鱷魚所禍,韓愈作《鱷魚文》,以刺史的身份驅離鱷魚,并說如鱷魚冥頑不靈,“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8]2318,以盡殺之。蘇軾說他能夠為民驅害,但他不能制止皇甫镈、李逢吉的毀謗。當唐憲宗想赦免韓愈時,素惡韓愈耿直無忌的皇甫镈,怕他重得任用,進言道:韓愈終究太狂疏,姑且量移。這使韓愈沒有直接回到長安,而是任內移置,改任袁州刺史。李逢吉則借韓愈和李紳不和,把韓愈從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降職為兵部侍郎。
三是“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韓愈可在朝廷做一個本分的官吏,以俸祿養家糊口,但他性情率真、好沖口直言與為君為民的忠誠融合在一起,導致他宦海浮沉,命途多舛。于是蘇軾說韓愈能順應天時,不能順應人事,主要是他對人事的違迕,包括給唐憲宗上《論佛骨表》,為李賀寫的《諱辯》,為李蟠寫的《師說》,公開與皇帝、世俗抗爭,不顧及自己的孤立無援。蘇軾在這一點上步韓愈后塵,處世往往不合時宜,故不能安居于朝廷,連流貶也在變更中越來越僻遠。
蘇軾說韓愈的能者天,不能者人,是對社會很大的諷刺。盡管韓愈在人為上的能力有限,但蘇軾還是很稱道韓愈,不同于前面貼近生活的評價,他居然把韓愈神化了。這是針對有潮州人認為韓愈在潮州不足一年(韓愈元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到潮州,七月十三日得到赦免,十月改授袁州刺史,在潮州僅半年余),并不眷念潮州說的。蘇軾持不同的看法,他在《韓文公廟碑》里說:“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愴,若或見之。”[1]509韓愈死了,但他的靈魂即思想在人間,就像水在地下一樣,無所往而不在。再從潮人說,建韓廟有對韓愈的崇敬和懷念,潮人信韓思韓,以致“焄蒿凄愴,若或見之”。“焄蒿凄愴”出自《禮記·祭義》的“焄蒿凄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3]1325。蘇軾這里說潮人以最精美的物品祭祀韓愈,仿佛重見了韓愈一樣。這“若或見之”意出《論語·八佾》的祭神如神在,以見人對神的真誠和情感親近。而有這種情懷的當然不光是潮人,也有非潮人的廣泛崇敬和懷念。歐陽修就說:“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10]1057僅此可見一斑。所以,他以“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1]509責問,說韓愈并非專屬于潮人。
《韓愈廟碑記》后蘇軾用古風作銘文,便于潮人祭祀時歌唱,卻也是蘇軾心底的歌。他用屈原《離騷》的筆法,極力夸耀韓愈超人的本領,讓巫陽下凡請他上天。韓愈離開人間之際,百姓以雞骨占卜,并獻上牦牛、美酒、鮮荔枝、香蕉等祭奠韓愈。韓愈長留在后人的心中。蘇軾以此頌揚韓愈,說韓愈能者天、不能者人,暗示了對社會的批判。他晚年被貶儋州時說“吾平時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1]2274,可見其對韓愈的同情理解至深,也是因性格、秉性的認同,在灑脫地祭韓愈時,有深沉的人生悲哀,盡管他以韓愈為百世師。蘇軾對韓愈充滿崇敬,因蘇軾自身的影響力,他的韓愈評說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