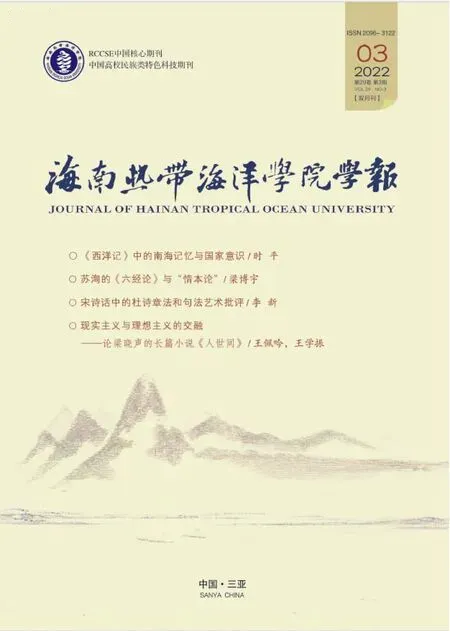古典、日常與異域想象
——楊振聲小說中的海洋書寫
趙劉昆
(吉林大學 文學院,長春 130012)
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成與西方海洋文明的擴張密不可分,尤其是五四文學,不論是其“極端自由”的語言形式、飽滿噴張的情感意涵,還是其現代意識的生成與發展,都離不開西方海洋意識的作用。五四一代作家紛紛用不同的文體鮮明而深刻地表達了自己對海洋的認知,海洋成為五四一代作家表現理想的有效形式之一。郭沫若、冰心、廬隱等人均是其代表。生于山東海濱的楊振聲則代表了五四一代作家海洋書寫的“北方氣候”。關注現代意識的同時,楊振聲更加注重挖掘海洋的“中國氣質”與日常屬性。
一、 《漁家》:楊振聲小說海洋書寫的發端
《漁家》發表于1919年3月《新潮》第1卷第3號,是楊振聲較早的文學作品。同期《新潮》還刊載了葉紹均的小說《這也是一個人》、陳達才的論文《物質文明》等,皆以鮮明的批判和反思著稱。作為一個具有整體風格的文化場域,《新潮》的每一個文本無疑都具有某一共同性特征,而這一特征既與其辦刊理念密切相關,同時又對其中的文本起著某種主題化的規范作用。《〈新潮〉發刊旨趣書》是《新潮》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文章,它指出了中國社會當前的現狀是“蓋中國人本無生活可言,更何有社會真義可說?若干惡劣習俗,若干無靈性的人生規律,桎梏行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謂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無從領略。猶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義,茫然未知”[1]33。并深感“此真今日之大戚也”[1]33,因此他們提出了《新潮》的辦刊目標之一是“同人等深愿為不平之鳴,兼談所以因革命之方”[1]33。不難看出《新潮》自創辦之初就已確立的宗旨乃是要揭露社會現實中的弊病,加以批判,并試圖尋求改良社會的“革命之方”。這種具有規定性質的“宣言”無疑代表了《新潮》的選稿標準,而《漁家》之所以能夠在《新潮》發表,無疑是其帶有揭露和批判性質的主題與《新潮》的選稿標準相契合的結果。
但一個文本的生產過程往往是極其復雜的,不得不考慮其產生的時代語境與作家的具體情況。《漁家》發表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正是“問題小說”“鄉土小說”快速發展的時期。“科學”“民主”“自由”等西方文化觀念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孜孜追求的總體性理念。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語境之下,《漁家》自然攜帶了時代的某種特性。也正如《新潮》刊名所表明的那樣,《漁家》無疑是一篇被時代“新潮”所裹挾的文學作品,其最大的文學價值無疑正是其對時代的主觀記錄與想象。可以毫不諱言地說,在題材上,《漁家》同時融合了“鄉土小說”和“問題小說”的思想主題,揭示了動蕩時代生命的無秩序狀態。而從時代的總體性出發,也不難看出其中隱含的“批判”和“啟蒙”主題。正是在諸多力量的合圍之下,《漁家》中的海洋書寫困于啟蒙話語之中,被強大的主題化力量所裹挾,并未呈現出更多的可能性。《漁家》聚焦于一個以漁為生的傳統家庭,在簡明的敘事節奏中講述了一個因天災人禍而交不起“漁旗子稅”的家庭走向崩潰的悲劇。在《漁家》中,海洋化身為一種“母性力量”,成為漁民物質和精神的“母親”,漁民所有的欲望和需求都必須經由這一客體獲得滿足。但現實往往呈現出一種匱乏癥狀(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它表現為漁民(海洋的子民)無法從海洋(客體)處獲得充足的資源。而事實上并非如此,海洋的給予是一種定額定量分配,就一般情況而言,漁民的收獲足以滿足自己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存在匱乏的問題。問題在于作為“中介”的苛捐雜稅抽取了漁民之利,這自然造成海洋-漁民之間供需失衡。更為糟糕的是,還有一些非穩定因素(在文中體現為小偷)加劇了這種失衡。也就是說,是一種人為的“非自然”狀態打破了正常的平衡,而追溯其根本原因,無疑指向了破壞這一穩定結構的“不治”。進而可以得出結論,是當時統治的混亂與軍閥混戰造成了社會的失衡,進而導致了“漁家”的悲劇。而“漁家”經過“普遍化”之后,具有了更大的社會效應。《漁家》的批判鋒芒,顯然不僅指向了統治者,也同樣指向了“漁民”。是“漁民”的軟弱縱容了統治者,使其能夠肆無忌憚地對其進行剝削,并公然改變原本的社會規則。因而僅僅批判統治者是不夠的,還必須喚醒被壓迫的國民,并重塑其民族性格,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惡性循環,從而再次回歸到古老的自然法則之中。
由此可見,《漁家》中的海洋書寫是與“批判”和“啟蒙”話語纏結在一起的,它顯示了楊振聲海洋書寫最初的發端狀態——一種介入現實的批判意識和啟蒙意識。但在宏大的時代話語的籠罩之下,讀者依然能夠發現其中流淌著一種“陰沉”的詩意,而這似乎也成為《漁家》美學理念的微弱顯現。“在五四文學中,楊振聲的濱海漁家小說可謂較早地展現了海邊實景,在其最早的小說《漁家》里,海——那個春雨連綿的海——給人以模糊、虛寫的感覺”[2]95。那些被夜色包圍的黑色的雨,陰沉沉地打落在脆弱的屋檐之上,女人補著殘破的漁網。隔著窗戶,遙遠的波濤激烈地翻滾著,露出夜晚的一點光亮。混合著孩子的哭聲、饑餓的匱乏,一副混亂、破敗而又詩意叢生的畫面躍然紙上。海洋的柔和中包含了多少無奈、委屈的哭泣?蘊含了多少人生的喜怒哀樂?隱藏了多少次漁民的生離死別?而這一切都已無法言喻。海洋顯然已成為一種具有母性的包容主體,是無數苦難的盛裝容器。這樣一種具有異質色彩的海洋書寫顯然是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影響,其中的陰郁、黑暗、混亂都是當時社會動亂的一種表征。楊振聲顯然是想借此表達自己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批判,所以其陰郁的海洋美學也就服從了批判和啟蒙的總主題。但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漁家》中的海洋書寫并不是對西方海洋文明的盲從,相反,它是一種傳統理想的復歸。
二、 《玉君》:浪漫、憂郁與古典
《玉君》是楊振聲的代表作,也是他將海洋書寫推進到另一個深度的文學作品。與《漁家》中相對單一的批判和啟蒙相比,《玉君》中的海洋書寫在繼承《漁家》的基礎上有了更為深刻、復雜的開拓。《漁家》的風格是一種陰沉、實在的批判,而《玉君》則因其戀愛關系的引入而顯得更為氣質化,從而更多地呈現為一種浪漫、憂郁和古典的表達。
(一)浪漫
“浪漫”有兩種理解:其一,就其生活與現實中的意義而言,它指的是一種帶有主觀性質的曖昧與幻想,是一種情調和氛圍;其二,文藝理論中的“浪漫”往往指浪漫主義。浪漫,“原指與現實生活頗為不同的傳奇故事、不平凡的愛情故事,后引申為帶有強烈感情色彩、富有詩意、充滿幻想的故事情節和畫面……浪漫主義的本質特征是按照理想中認為應該如此的樣子來描繪生活,描寫對象或描寫理想化的對象,表現作者的激情”[3]。在描述楊振聲小說中海洋書寫的浪漫特征時,所使用的概念是文藝理論中所界定的概念。《玉君》中海洋書寫的浪漫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玉君》中的海洋帶有一種夢幻式的虛擬性質。“楊振聲的小說《玉君》講述的是濱海漁家的生活,其中記述了出洋歸來的林一存的一個幻夢”[2]94“仿佛是在埃及的東岸,赤圓的落日,如夜火一般,照得沙漠都通紅。從天邊的椰樹間,跑出一群野人來,飛隼一般的快,直撲到我面前來捉我……”[4]59這種對海洋的想象穿插在對現實海洋的描述之中,它顯示了作者試圖以想象擺脫現實困境的努力。而這種想象的夢幻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林一存與玉君、菱君的關系注定只能像一場幻夢一樣無疾而終。浪漫的背后隱藏的恰好是五四落潮以后青年人普遍的懷疑、幻滅之感。青年無法從黑暗籠罩的大地找到光明的出路,便只能轉而投向廣袤的海洋,期望以死亡和回歸求得徹底的解脫。
第二,《玉君》中的海洋是與死亡相聯結的。楊振聲愛海卻“并不止于外在的觀賞流連,而是自覺把自己的生命與大海聯系在一起”[5]15。海洋的包容性無須贅言,當大地不能容納青年的理想時,海洋便成了另一種可代替的選擇。只不過這種選擇是神秘而殘酷的,因為它與死亡聯結在一起。投海自殺是一種文化隱喻,成為殉節這一崇高行為的表現形式。因而在實施這一行為時,雖然是出于生活所迫的無奈之舉,但更為明顯的事實是,投海這一行為被賦予了象征意義,它的交換對象是崇高這一道德品質。通過投海這一行為,主體反抗的姿態和情緒得以傳達,在引起他者關注的同時也獲得了一種道德意義上的認可。因此從根本意義上來說,投海是一種想象性行為,它并不意味著真實的反抗,而是出于自我人格建構的需要,因此它是一種變相的獲取道德歸依的方式。“他們剛把漁船攏岸的時候,聽到有人啼哭的聲音。他們撲著那個聲音前進,聽到咕咚一聲,接著澌澌的水聲,他們知道是有人撞下水去,就趕緊的過去救,好不容易找到了,撈上來一看,是個女子……燈下一看,見她面色僵白,頭發濕垂在兩肩上,不是旁人,正是玉君。”[6]38玉君的投海是出于無奈,也是希望能以死亡的方式從博大的海洋中重新獲得力量,以抵抗現實的威脅和壓迫。但結局往往難以遂愿。《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沉淪》中的主人公“我”的投海也都有一種象征和修辭的意義,這無疑是與大海本身的隱喻性質有關的。海洋的包容、柔和是一種母性特征,與中華文化的包容有異曲同工之妙。玉君投海自盡是想投入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母體之中,并期望從中獲得力量,但封建化和固定化的文化傳統明顯已不具有這樣的屬性,因而海洋的隱喻無疑指向了文化的更新。玉君所投入的文化母體,是一個流動的、更新了的傳統文化的母體。玉君希望歸依和從中獲得認可的道德,也不再是傳統的舊道德,而是以更新了的文化傳統為基礎建構的新道德。
第三,《玉君》中海洋書寫的浪漫還表現為一種對異域世界的想象。異質文化的神秘和新奇總是能激發人的好奇與想象,尤其是對于那些未能實際體驗異質文化的人而言,這種異質性就更具有吸引力。但任何想象都有現實的根基,都不是憑空產生的。當杜平夫遠渡重洋抵達埃及時,林一存大致也料到他的行程已到埃及,他在夢中便有了對埃及東海岸的一系列幻想,顯得神秘而朦朧。“忽的汽笛一聲,大家都吃了一驚,轉頭看時,見一只載客的小汽船,飛箭似的,從西面駛進港來。平夫把那只船惡狠狠地看了一眼,臉上忽地老了十幾年似的”[7]7,這種體驗無疑是未經歷過西方世界的一種帶有預見性的情感體驗。等平夫抵達法國之后,林一存、玉君和菱君無疑都把以浪漫著稱的法國視為精神的避難所,而法國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無疑是西方式海洋的實存。所以他們對法國的想象,無疑就成為對西方異域世界的想象,成為對另一種海洋文明和海洋世界的個人理解。
(二)憂郁
在思想情調上,憂郁是浪漫的一種延伸,它是主體在喪失客體后無法獲得客體代替物時所產生的一種不穩定的情緒和心理狀態。在五四落潮之時,這一客體往往就是主體在五四時期追求的文化理想。在楊振聲的小說中,它具體體現為一種更新的傳統文化的失落,以及無法找回失落文化理想的抑郁狀態。“大海只能作為理想的象征,作為一片浪漫虛遠的前景,鋪展在遠方,引人流連徘徊、躊躇遠眺。”[5]18林一存認為在浪漫中所構想的那個異域世界所代表的文明實際上并不適合中國人,因而當玉君、菱君紛紛踏上異鄉之路時,他選擇了獨自一人留在祖國,做一頭耕地的“老牛”。無疑,對西方的失落是林一存失落的原因,也成了他無法獲取客體而憂郁的原因。最終林一存成為一座自我隔絕的孤島,而海洋也失去了其精神故地的意義。
看呀!那墨黑的烏云從海上冒出來,遮蓋了半天。快起大風啦!噯呀!那嗚嗚的風頭撲過來了,妤冷!看,那海鼎沸到什么樣子!千山雪流,萬壑珠飛。水直奔騰到陸上來!怎么?海水都濺上身來了!好冷好冷!……這里暖和!盆大的太陽赤熊熊地炎在頭頂上,四望的草木都烤焦了。荒沙萬里,映日閃爍。熱的要不得,渴的要不得。……看!那里飛奔過來一只箭豬,是向我來的。張了血盆一般的嘴。赤了白刃一般的牙撲上來。可怕可怕!看他站起來了![6]25
海洋成為一個可怕的,將要吞噬主體的兇惡之徒,處于孤立無援的主體瘋狂、迷亂,竭力哀求,卻得不到任何回應,孤獨感再次襲來,憂郁像烏云一般再次籠罩在主體上空。
(三)古典
古典并非一種實指,而是作為一種氣質存在于《玉君》的海洋書寫中。首先,《玉君》中對海洋的描寫表現出一種古典性質,具體體現為古典式詞語的使用,如“細濛濛雨在海上打起千萬個白波,洗淋淋沉重的載客小舟”[7]18。“白波”“小舟”都是古典詩詞中常用的詞匯,在現代白話文中使用這些古典詞匯,往往能使語句更具古典意味。此外,楊振聲在描繪海洋時,常用“清碧”“遠接天邊”“白日”一類詞語,無疑也增添了《玉君》中海洋書寫的古典氣息。其次,這種古典性質體現為對古典意境的營造。如“不久海上生起烏云,飛上天空,把月遮了,月光從云縫中穿照下來。海上也漸起微波,風吹海浪,打在海岸石洞中,聲調悲壯,震人心脾”[4]80一句,描繪出一幅壯闊而又震撼的海洋畫面。再如,“腳下輕飄飄的像蹈著棉絮似的,出了園子,走下山坡,一直走到海岸,坐在一塊石頭上。天是空的,水是空的,山也是空的,天地一切都是空的,死的,沒有情意的”[7]36,這句將主觀感覺投射到萬物之中,整個海洋乃至世界都呈現出一種空寂的意境,而這種意境,無疑已被古人言說過很多次了。
當然,古典最重要的體現是對傳統文化及其精神世界的回歸。“中國文化主流強調入世觀念,大多數中國文人的理想是達則兼濟天下,積極關注社會人生。但是當理想受挫,他們又往往轉而獨善其身,海洋遂成為他們逃避世事、尋求解脫的心靈寄托”[8]“中國人認為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著真正的美。”[9]“這是長期以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國人順應自然規律的審美情趣流露”[10]63。海洋不僅是失意時的暫棲之地,還是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故鄉。因而當五四落潮之后,知識分子便選擇了棲身于更新的傳統文化之中,它的古典意味正在于這更新的意味,古典成為一種流動的詩意,成為一種氣質性的氛圍。當玉君失落后,她可以選擇投入海洋之中;當林一存陷入生活的煩惱中時,他也會選擇到海邊散步,感受大海的寬闊,從海洋中獲取精神力量。因而海洋就成為主體的精神故鄉,它從《漁家》的物質客體升華為一種精神性力量,成為一個精神的母體。
“海洋里的生物不僅是人類食物的一部分,而且飽含了人類的某種精神向往。……中國民間流傳的人魚傳說則顯現出人與神的對話乃至人與神共舞的天地,這是人類祈求幸福的一種方式,也是人格理想與道德完善的路徑。”[10]64《玉君》中也涉及一些漁歌和漁民的風俗,這些無疑都是他們表達對精神故鄉歸依的一種神圣儀式,通過儀式的完成,他們實現了心理的宣泄,獲得了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可以說,中國的哲學智慧許多是通過“水”這一意象傳達出來的,而海洋作為“水”的總體形態無疑是其力量的聚集,因而那些包含在“水”中的智慧無疑都一一在海洋中得以呈現。林一存正是運用海洋的智慧一次次化解了自己的死亡危機,玉君也是,而菱君則因海洋的浸潤而擁有了自然、柔美的品質,呈現出一種天真狀態。這些無疑都是海洋影響的結果。所以,《玉君》中的海洋不僅是主體的精神故地,還是主體化解生命危機的智慧來源。
三、 生命強力的展現:楊振聲后期的海洋書寫
楊振聲后期小說的海洋書寫是圍繞著漁民的生活展開的,表現他們依海為生、因海而斗、以海復仇的一生,塑造了粗豪、原始、頑強甚至野蠻的漁民群像。在對海洋的書寫中,小說表現了漁民蓬勃張揚的人物個性,展示了原始的頑強生命力,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希望借助這種頑強生命力達到反抗封建倫理道德、重振民族生命力的目的。
(一)蓬勃張揚的個性
楊振聲小說中的海洋書寫表現了富有個性與生命張力的漁民的一生。這種張揚的個性剛好與海洋本身蓬勃的精神相契合。海洋是生命之源,是生命原初的自然起點,也是不受塵世羈絆的自然整體,因而海洋本身就體現出一種自然的個性精神。久受浸潤的漁民們依海為生,每天都要和海洋打交道,因而他們的性格自然會受到海洋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一種氣質上的根本性影響。這就形成了漁民們自然不羈的個性和對遠方與自由的向往。《搶親》中的辛大是一個豪爽耿直的漢子,因受不了趙二的欺弄,便深夜召集數位好漢,奔向趙家莊搶親,最終奪回了屬于自己的幸福。《報復》也有類似的情節結構,但結局卻大不相同。小翠媽先后收了高二和劉五兩人的彩禮,最后把小翠嫁給了高二,高二和劉五的矛盾自然就產生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在一次海難中,高二冒著生命危險救了劉五,劉五后又幫助喝醉的高二保住了錢包,二者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便緩和了許多,最終兩人和解了。不難發現,這些漁民的個性是受海洋磨煉的結果。在危機四伏的海上打魚,如果不能當機立斷,不能吃苦耐勞,沒有頑強的意志,是無法在海上立足的。正如《拋錨》中所展示的那樣,在海上混跡,憑的就是拳頭和義氣,而不是什么倫理道德。
當然,其中一些問題也同樣值得我們思考,那就是這些小說中的女性話語處于空缺狀態,女性幾乎成為一種“不在場”,似乎只是充當了“工具人”的角色。與男性粗豪俠義的鮮明個性相比,女性顯得軟弱,而且幾乎沒有什么存在感。除了《拋錨》中的何二姑與男人一樣具有了同等粗豪的個性特征和生命意識之外,其他作品中的女性都被男性的個性聲音所淹沒。由此不難意識到其中的邏輯,即普通的、一般的家庭婦女所具有的品德就是封建倫理框架下的三從四德,而那些逸出正統之外的風塵女子則是為主流所不齒的,因而她們成為例外。但這種邏輯的貫徹并不徹底,也并不總是一致,這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楊振聲面對女性問題時復雜和矛盾的心態。在他后期小說的海洋書寫中,女性只存在“女孩”與“婦女”兩種身份,且都被倫理化,不具有性別的獨立性,不能不說楊振聲對女性的認識是較為傳統和復雜的。他也希望能夠借此擺脫傳統封建倫理對女性的囚禁,使其擺脫“物”的狀態,但楊振聲顯然又不想把女性完全解放出來,使其具有和男性同等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局限。
(二)原始生命力的展示
楊振聲在其后期的海洋書寫中賦予男性生命以野性和強力,任生命酣暢自由地舒展。其主要特征為雄野粗豪、豁達灑脫、熱情勇武、放蕩不羈、充滿血性,盡情展現生命的蓬勃元氣和陽剛之美。與沈從文一樣,他“對生命的朝氣,生命的力量,生命中自然本然的元氣和精神十分贊賞”[11]。在《拋錨》中,穆三雖仗著自己身強力壯,卻只欺負那些頗有些能力的富戶,在割漁網的時候,他也選擇了險惡狡猾的劉三下手,而當情人因自己的連累要被“拋錨”時,他又奮不顧身以自己的犧牲換取何二姑的生命。這種敢作敢當、崇尚武力、頗有劫富濟貧風范的性格儼然已成為一種具有典范性質的生命形式,成為漁民眼中所崇敬的事實強者,而形成這一性格的原因,無疑是滋養其生命的海洋與海洋文化。“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點的,反映一定民族思想情感、精神風貌、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總合。它更多地表現在人性人情、民風民俗、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審美情趣、價值觀念等非理論形態方面。”[2]132山東沿海一帶崇武尚力,自古便出野蠻剽悍、狂放不羈、崇尚自由的英豪,加之這一地區民風剽悍[12],由此形成了當地獨特的文化價值形態。所以楊振聲在表現小說中人物的粗豪性格時,明顯是受了故鄉蓬萊民間文化的影響,而這種民間文化的孕育,也主要歸功于海洋的作用。
漁民的生存是海洋的饋贈,同時也是與海洋搏斗的成果。大海中險象環生,稍不留神就會葬身大海。這對一個人的意志而言是極大的考驗,在這樣的環境中,軟弱者是無法生存下去的。也正是在與大海的搏斗中,漁民們普遍具有一種粗豪野蠻的性格,這是當地惡劣的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搶親》中的辛大如果軟弱了,就會失去自己的幸福;《報復》中的高二如果軟弱了,就會喪失尊嚴;《拋錨》中的穆三如果軟弱了,就會失去自己的生命。而這一切無疑都是基于生存的考量,都是一種實用主義的直接體現。比如小說中的人名,其命名方式簡單、直接,似乎只是為了起到一種區分作用,而并未摻雜更多的文化意蘊。在一個以武力為尊的社會環境中,最大的道德就是武力,而不是倫理。
(三)以生命強力反抗封建倫理道德
楊振聲小說中的漁民,是一群無視封建道德的浪人。在他們的世界中,真正的道德不是封建倫理,而是體現為生命實質的強力。楊振聲借助這樣一種視角,悄然打破了封建倫理的束縛,為人的個性自由與生命張揚找到了一個合理的依據。他在小說中謳歌贊揚這些粗豪野蠻的漁民,為他們自由、豪放、張揚的個性所鼓舞。他相信民族生命力的未來就蘊含在這些漁民的精神之中,因為他們是擺脫了封建束縛的域外之民,是不受正統文化統治和支配的異端,其中隱藏著一種新的倫理和道德精神。他認為可以通過提取這種精神達到改造民族精神、重振民族之魂的目的。在《荒島上的故事》中,小說開頭就點明了抗戰的時代背景。作者安排主人公武誠見證了一次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并激起了他心中無限的憤恨,于是他決定復仇。他載著自己的新船,告別了溫暖的家,在大海深處以沉船的方式與敵人同歸于盡。海洋成為武誠復仇與展現生命強力的憑借之物與見證者。在這里,“海洋書寫融入政治寄寓后更為深沉,政治寄寓則在海洋書寫的襯托中平添一絲恢宏”[13]。而這種復仇精神,其本身就是生命強力的體現,作者希望能借助這種精神,喚起國人更為堅韌的抗戰意志,實現“抗戰建國”的民族重任。
結 語
楊振聲小說中的海洋書寫以《漁家》為發端,經《玉君》的發揮和拓展,至《搶親》的轉折性深化有了較為豐富的提升。從《漁家》單一的批判和啟蒙的主題化書寫,到《玉君》浪漫、憂郁、古典的多重深化,直至《搶親》等一系列小說中生命強力的展現,楊振聲通過海洋書寫展示了他對民族性格的發現、批判、啟蒙、深化和重構。貫穿在楊振聲海洋書寫中的是其內部不竭的生命意識和動力,他試圖借助原始的生命強力以反抗封建倫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