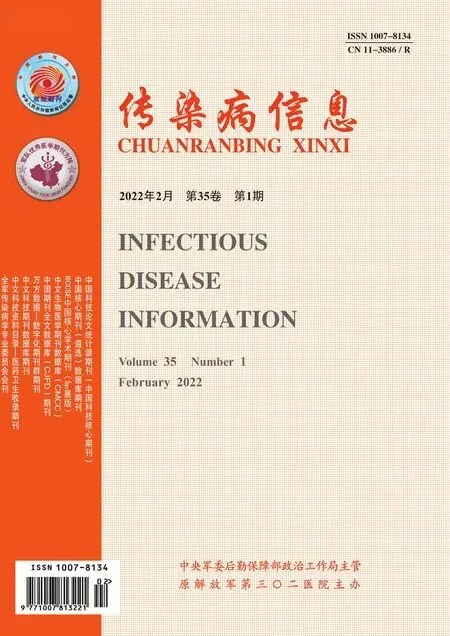腸道微生態(tài)與肝細胞癌關系的研究進展
劉哲睿,賈曉東,陸蔭英
1 概 述
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世界上第六大常見癌癥類型和第四大癌癥相關死亡原因,約占原發(fā)性肝癌的75%~85%[1]。HCC通常繼發(fā)于慢性肝病和肝硬化,乙型肝炎(乙肝)、HCV感染、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黃曲霉素和馬兜鈴酸等都是誘發(fā)HCC的危險因素[2]。由于HCC早期診斷困難、起病隱匿和易復發(fā)轉移等特點,大部分患者確診時病情已經進展至中晚期,迄今為止,HCC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低于20%[3]。目前,索拉菲尼仍是中晚期HCC患者治療的首要選擇。雖然臨床治療HCC逐漸使用如阿特珠單抗聯(lián)合貝伐單抗等新興治療手段,但效果仍不理想,因此亟需對HCC潛在發(fā)病機制進行深入研究,以期開發(fā)出針對HCC患者更有效的治療方式。
腸道微生物群是人體中最大的微生物系統(tǒng),目前認為腸道中的微生物數(shù)量超過1014個,其中包括細菌、病毒、真菌和古生菌[4]。腸道微生物群與宿主間的共生關系在維持機體正常生理功能方面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機體免疫系統(tǒng)異常、腸道微生物群紊亂及環(huán)境改變等因素的影響下,腸道微生物群與機體間的共生關系發(fā)生改變并可能誘發(fā)包括癌癥在內的多種疾病[5]。由于腸道和肝臟間存在的天然解剖結構,即“肝-腸軸”的存在,腸道菌群在HCC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也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6],因此深入了解腸道菌群與HCC發(fā)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對未來HCC診斷標準的制定及治療方案的選擇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本文就目前腸道菌群影響HCC的機制和包括抗生素、益生菌、糞菌移植及免疫治療在內的腸道微生物相關HCC治療方式展開綜述,旨在深入闡述腸道菌群及HCC發(fā)生、發(fā)展間的關系,為HCC的預防及臨床診治等方面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2 腸道微生態(tài)影響HCC的機制
目前認為,絕大多數(shù)的HCC患者繼發(fā)于慢性肝病,腸道菌群紊亂及菌群易位能夠促進肝臟炎癥、纖維化及肝硬化的進展[7]。研究已證實,在肝硬化患者中腸道微生物群紊亂和腸屏障破壞會導致HCC的發(fā)生[8],因此,目前針對腸道微生態(tài)在影響HCC的發(fā)生、發(fā)展中的機制研究,主要集中在腸屏障破壞導致腸道微生物的肝臟易位和腸道微生物群紊亂兩方面。
2.1 微生物相關分子模式與HCC 目前認為慢性肝病導致的腸屏障破壞使得多種微生物相關分子模式(microbiota-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MAMPs)易位,通過循環(huán)進入肝臟從而促進HCC的發(fā)生[1]。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是革蘭陰性菌細胞壁的組成成分,有研究報道在HCC小鼠模型和HCC患者的血液循環(huán)中均發(fā)現(xiàn)高水平的LPS[9]。高水平的LPS可能導致細菌易位并促進肝臟炎癥反應,此外,慢性肝病患者腸通透性升高導致LPS的高循環(huán)水平,也被證實可以促進慢性肝病的進展并導致HCC的發(fā)生[10]。據(jù)報道,LPS是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 TLR)4的一種重要配體[11]。作為一種模式識別受體,TLR4可以識別MAMPs,從而調節(jié)機體對腸道微生物群的免疫應答[12]。研究發(fā)現(xiàn),TLR4在HCC患者的腫瘤組織中過表達[13],同時動物模型也揭示了LPS/TLR4在促進HCC的發(fā)生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研究發(fā)現(xiàn)低劑量LPS刺激的野生型化學誘導HCC的小鼠模型比無菌小鼠表現(xiàn)出更為嚴重的腫瘤表型[14],Naugler等[15]發(fā)現(xiàn)TLR4-/-小鼠在化學誘導所致的HCC中腫瘤發(fā)生率、腫瘤大小及數(shù)量與化學誘導的野生型小鼠組相比均顯著降低。對其機制的深入探索闡明,活化的TLR4可以通過肝細胞、肝星形細胞和庫普弗細胞激活NF-κB和STAT-3,產生促炎細胞因子IL-7、IL-1β、IL-6以及TNF-α,從而促進HCC的發(fā)生[1]。此外,TLR4還可以通過肝星形細胞上調促癌蛋白表皮調節(jié)素、肝細胞生長因子以及雙向調節(jié)蛋白的表達,從而誘導HCC細胞的增殖[14]。
此外,革蘭陽性菌的主要成分脂磷壁酸(lipoteichoic acid, LTA)也參與HCC的發(fā)生。LTA是TLR2的重要配體之一,TLR2被證實在機體應對革蘭陽性菌的先天免疫中發(fā)揮重要作用[16]。研究發(fā)現(xiàn)TLR2在與LTA結合并激活后,可以激活肝星形細胞表達衰老相關表型,Loo等[17]發(fā)現(xiàn)肥胖導致機體腸道LTA含量的上升,可以活化肝星形細胞上的TLR2,使肝星形細胞表達衰老相關表型并通過調節(jié)COX-2信號、前列腺素E2的活性與水平從而抑制其抗腫瘤免疫作用,形成促進腫瘤進展的腫瘤微環(huán)境,并最終導致HCC發(fā)展。綜上,腸道微生物可以通過其自身的MAMPs作為配體激活肝臟中的TLRs,從而通過免疫應答或表達產物進而影響HCC的發(fā)生、發(fā)展。
2.2 微生物代謝物與HCC 除了腸屏障損傷導致的MAMPs通過“肝-腸軸”促進HCC的發(fā)生、發(fā)展外,腸道微生物紊亂同樣在HCC的發(fā)生、發(fā)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膽汁酸作為一種重要的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其在HCC發(fā)生、發(fā)展機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Kitazawa等[12]發(fā)現(xiàn)由于飲食或遺傳因素導致的肥胖,會使機體腸道微生物群發(fā)生紊亂,革蘭陽性菌含量升高,并最終導致其介導的脫氧膽酸(deoxycholic acid, DCA)含量上升。與LTA作用機制相似,DCA同樣可以激活肝星形細胞TLR2,表達衰老相關表型進而導致促炎因子釋放并促進HCC進展[17]。DCA還可以通過調節(jié)肝竇內皮細胞CXCL16的表達從而介導NK細胞的募集。Ma等[18]通過對HCC小鼠模型進行抗生素或膽堿胺處理,抑制腸道菌群對初級膽汁酸的代謝能力或抑制膽汁酸的生理功能,發(fā)現(xiàn)初級膽汁酸可以上調肝竇內皮細胞CXCL16的表達,從而使其對NKT細胞的募集能力增強,后者通過CD1d依賴途徑發(fā)揮對腫瘤細胞的殺傷作用,而作為次級膽汁酸的DCA通過抑制肝竇內皮細胞對NKT細胞的募集從而促進HCC的進展。此外,Yamada等[19]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導致的HCC小鼠模型中發(fā)現(xiàn),DCA可以通過激活肝細胞中mTOR信號通路介導HCC的發(fā)展。總之,DCA可以在衰老相關表型的調控、NKT細胞募集以及mTOR通路的激活等方面發(fā)揮促進HCC發(fā)展的作用。
另一種細菌代謝產物——短鏈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也被證實與HCC的發(fā)生、發(fā)展密切相關。如在SCFAs中,丁酸和丙二酸可以通過表觀遺傳機制誘導調節(jié)性T細胞,調節(jié)肝細胞的增殖和分化,抑制肝臟炎癥[20]。然而,Singh等[21]發(fā)現(xiàn)富含丁酸飲食雖然能夠減輕小鼠的炎癥反應,但同時也會導致小鼠肝內膽汁淤積的發(fā)生率顯著升高,并促進HCC進展。雖然現(xiàn)有研究證實SCFAs在HCC的發(fā)生、發(fā)展中確實發(fā)揮著一定作用,但作用機制還未被明確闡述,需進一步研究探索。
3 腸道微生態(tài)治療與HCC
目前,針對腸道微生物群與HCC發(fā)生、發(fā)展的機制探索主要集中在動物水平,仍須在臨床患者中對其進行驗證并深入探索其下游效應機制。但現(xiàn)有研究提示了腸道微生物群的紊亂以及腸屏障的破壞與HCC的發(fā)生、發(fā)展間密切相關。因此,在維持機體正常的腸道微生物群以及防止出現(xiàn)微生物群的失調等方面,對HCC的治療方式進行探索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目前,隨著對腸道微生物群、“立肝-腸軸”以及HCC間關系的研究逐步增多,以腸道菌群為導向的抗生素療法、益生菌治療、糞菌移植療法以及聯(lián)合免疫療法等已在HCC的臨床治療方面顯示出了獨特優(yōu)勢。
3.1 抗生素治療與HCC 目前,有研究者在探索腸道微生態(tài)失調與HCC間關系的動物模型中發(fā)現(xiàn),聯(lián)合使用廣譜抗生素可以減輕小鼠的腫瘤耐受并減緩HCC的發(fā)展[22]。對化學誘導HCC的小鼠模型聯(lián)合使用氨芐霉素、新霉素、甲硝唑和萬古霉素的四聯(lián)抗生素,可以顯著預防小鼠HCC的發(fā)生[14],提示抗生素具有對HCC的預防作用。Yoshimoto等[23]也發(fā)現(xiàn),在對高脂飲食誘導HCC的小鼠進行四聯(lián)抗生素干預同樣具有顯著的抗腫瘤作用,此外,對小鼠進行革蘭陽性菌特異性清除的萬古霉素干預,也會顯著減輕高脂飲食誘導的HCC的進展,提示抗生素療法具有治療HCC的潛力。抗生素利福昔明也已被證實可以促進腸道有益微生物如雙歧桿菌、糞桿菌和乳酸桿菌豐度的增加,同時不會過度改變腸道微生物特征[24]。此外,Dapito等[14]發(fā)現(xiàn)利福昔明可以減緩DEN/CCL4誘導的小鼠HCC腫瘤數(shù)目,提示其作為抗生素在通過腸道菌群干預HCC方面具有潛在的治療作用。然而,雖然抗生素在HCC的治療方面已展現(xiàn)出了積極的作用,但臨床上長期使用抗生素同樣存在多種潛在的風險,如腸屏障損傷、腎臟毒性、抗菌素耐藥及多藥耐藥感染等[25-26]。因此,具有HCC臨床治療潛力的低風險抗生素仍需進一步的探索及研發(fā)。
3.2 益生菌治療與HCC 益生菌是一類定植于人體腸道,改善宿主微生物生態(tài)平衡并對宿主有益的活性微生物[27]。機體的益生菌主要包括丁酸梭菌、乳酸桿菌、雙歧桿菌、放線菌和酵母等,通過促進有益菌的生長并抑制有害菌來維持腸道菌群平衡,減少腸道炎癥,改善腸屏障功能并抑制HCC的發(fā)展[28]。除了傳統(tǒng)的益生菌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外,目前對于包括梭狀芽孢桿菌Ⅳ、梭狀芽孢桿菌ⅩⅣa以及艾克曼菌在內的“二代益生菌”的研究正逐漸興起[29]。
益生菌可以通過多種途徑降低HCC發(fā)病風險。首先,益生菌能夠促進具有抗腫瘤作用的腸道微生物的生長。如Li等[30]發(fā)現(xiàn)使用一種混合了鼠李糖乳桿菌、大腸埃希菌Nissle 1917以及VSL#3的混合抗生素,能夠促進小鼠腸道中具有生成抗炎代謝物作用的菌屬如普雷沃菌屬和顫螺旋菌屬的生長,促進腸道內抗炎Treg/Tr1細胞分化,并通過下調肝臟TLR誘導的炎癥反應來抑制HCC的發(fā)生。此外,Elshaer等[31]在硫代乙酰胺誘導肝硬化的Wistar大鼠模型中發(fā)現(xiàn),早期給予植物乳桿菌干預,可以顯著抑制肝細胞TLR4、CXCL9和PREX-2表達,從而抑制肝硬化向HCC的進展。
其次,益生菌能夠通過表觀遺傳調控宿主基因表達水平,從而抑制HCC的發(fā)生、發(fā)展。Heydari等[32]對氧化偶氮甲烷誘導的小鼠癌癥模型進行嗜酸性乳酸桿菌和雙歧桿菌干預后發(fā)現(xiàn),小鼠血液中RNA-155、miR-221、肝臟中的Bcl-w和KRAS等致癌基因的表達顯著降低,同時miR-122和抑癌基因轉錄因子PU.1表達顯著上調,提示益生菌能夠通過激活特定基因和microRNA表達在小鼠HCC的發(fā)生中發(fā)揮積極作用。有研究發(fā)現(xiàn)嗜酸性乳桿菌與釀酒酵母形成的一種益生菌混合物,可以通過激活肝細胞中沉默信息調節(jié)因子1的表達,協(xié)同防止CCL4誘導的肝纖維化[33],此外,類植物乳桿菌可以減少Wistar大鼠肝臟中由于糖尿病導致的DNA損傷[34]。上述研究均提示益生菌通過減緩肝臟疾病進展從而在預防HCC的發(fā)生中發(fā)揮積極的作用。
第三, 益生菌可以通過預防慢性HBV和HCV感染來幫助減輕HCC的發(fā)生風險。Lee等[35]在體外細胞實驗中發(fā)現(xiàn),用青春雙岐桿菌提取物處理HepG2細胞可減少HBV載量和細胞變性。此外,在HCV感染者中糞腸球菌可以降低血清肝損傷標志物ALT和AST水平,雖然其對HCV載量的影響并未出現(xiàn)顯著趨勢[36],但已表明益生菌可以通過預防HBV和HCV感染促進肝功能的恢復,并有助于減輕HCC的發(fā)生風險。未來,仍需進一步對相關益生菌及其深入機制進行探索。
最后,益生菌能夠通過改善肥胖來預防肝臟的脂質毒性。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中,補充嗜酸乳桿菌和乳酸乳桿菌可以改善肝損傷[37]。有研究表明,使用益生菌可顯著降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體質量和總脂含量,并能夠通過下調促炎細胞因子TNF-α來減少肝臟炎癥[37],從而預防HCC的發(fā)生。
此外,益生菌療法還具有安全、便宜及個體差異化等優(yōu)勢,因此,進一步探索新型益生菌療法和機制在HCC的預防及治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3.3 糞菌移植療法與HCC 糞菌移植(fecal microbial transplantation, FMT)是一種將健康人類糞便中的功能菌群移植到特定患者的胃腸道中,從而重塑有益于機體的腸道菌群的一種新技術,已受到廣泛關注[38]。FMT具有操作簡單,療效高等優(yōu)點,目前已廣泛應用于腸易激綜合征、胰島素抵抗和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等疾病的治療[39]。在肝臟中的初步研究表明,F(xiàn)MT在代謝綜合征、重癥酒精性肝炎以及肝性腦病中也具有一定療效[40-42],同時,F(xiàn)MT還可能通過調節(jié)腸道微生物群、減少某些細胞毒性代謝物或炎癥介質的產生,恢復失調的腸道菌群并可能影響HCC的進展[43]。但到目前為止,關于FMT與HCC間的確切機制及治療方式仍在探索當中。FMT療法還存在供、受體間疾病傳播,患者耐受以及無法預知的免疫反應等相關問題[43],亟需更多的研究來確保其在HCC治療中的實用性及安全性。
3.4 腸道微生態(tài)與HCC免疫治療 近年來,通過腸道菌群改善免疫治療中患者的免疫應答受到廣泛關注[44]。如在黑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腎細胞癌和尿路上皮癌治療中,已有大量研究證實腸道菌群能夠顯著改善癌癥患者對免疫治療的應答情況[45-46]。有研究對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有無應答的黑色素瘤患者的腸道菌群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梭狀芽孢桿菌、瘤胃球菌屬和糞桿菌屬在應答組患者腸道中豐度升高,擬桿菌屬豐度則在無應答組患者腸道中顯著富集[47]。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有著更高豐度的糞桿菌和其他厚壁菌門的黑色素瘤患者,能夠更好的應答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蛋白4 (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 CTLA-4)的免疫治療[48]。黑色素瘤患者單獨口服雙歧桿菌的療效與PD-L1抗體治療效果相似,但當兩者聯(lián)合治療時幾乎能夠完全控制腫瘤生長[49]。
以具有調節(jié)免疫系統(tǒng)發(fā)揮抗腫瘤活性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為主的免疫療法,在HCC的臨床治療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50]。其中,CTLA-4和PD-1/PD-L1抗體在HCC的治療方面同樣起到關鍵作用[1]。Zheng等[44]對PD-1治療表現(xiàn)出不同應答水平的HCC患者腸道菌群進行對比分析,發(fā)現(xiàn)無應答組患者腸道中變形菌門豐度逐漸增加,而應答組患者腸道中則呈現(xiàn)出艾克曼菌和瘤胃球菌屬的大量富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腸道微生物群能夠影響癌癥免疫治療的效果[44-46,49]。腸道菌群的改變可能會直接影響早期接受PD-1抗體治療的HCC患者的藥物療效及預后水平[44]。關于調控腸道菌群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多項實驗也在逐漸開展[1],有望闡明腸道微生物與HCC免疫治療間的關系從而推進開展更為有效的臨床HCC治療方式。
總之,腸道微生物群通過調節(jié)癌癥患者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反應,在癌癥的免疫治療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甚至能夠改變患者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應答情況。然而腸道微生物群與HCC患者免疫治療間的關系仍未被完全闡明,尚需進一步的研究進行探索。
4 展 望
隨著微生物技術的進步,腸道微生物群和HCC之間的關系逐漸被闡明。目前大多數(shù)關于腸道微生物群與HCC發(fā)生、發(fā)展間關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動物模型中。由于人體腸道微生物群組成受到諸如抗生素、疾病以及飲食等因素影響,動物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人體腸道微生物的動態(tài)變化,因此人體腸道微生物群與HCC之間的關系仍需在人體內進一步探索及驗證。雖然目前尚不清楚動物模型和其他腫瘤患者中腸道微生物群的抗腫瘤免疫應答效果是否同樣適用于HCC的治療,但腸道微生物群逐漸顯示出其成為HCC輔助治療策略的潛力。重塑腸道微生物群是否能夠逆轉腸道穩(wěn)態(tài)失調HCC患者對免疫治療的應答效果仍需進一步闡釋和研究。此外,對于腸道微生物群在HCC治療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對糞菌移植療法及益生菌療法的研究,有助于推動HCC的防治及個體化精確治療,有望在未來成為治療HCC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