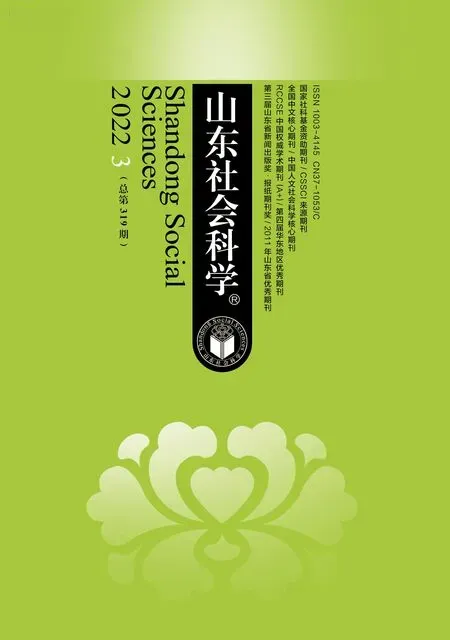鄧攸“棄子保侄”故事的文本演變
——以元明清戲劇為例
劉 璐
(山東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以兩晉人物故事為表演主體的戲劇,統稱為“兩晉戲”。元明清戲劇中的晉人戲,主要以《世說新語》為底本繼承與改編。據筆者統計,晉人戲不下一百五十種,其中事出《世說新語》者多達五十七種。(1)主要參照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版;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趙景深輯:《元人雜劇鉤沈》,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俞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匯編》,黃山書社2006年版;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鄧攸,東晉士人,入《晉書·良吏傳》。其事跡最早見于《晉陽秋》,“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2)轉引自《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頁。。后鄧粲《晉紀》、劉義慶《世說新語》、何法盛《晉中興書》均載鄧攸“棄子保侄”事,《世說新語》錄全事如下:
鄧攸始避難,于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后,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世說新語·德行第二十八》)(3)[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頁。
鄧攸“棄子保侄”情節是元明清戲劇中的熱門改編對象:一方面,其研究對《世說新語》在后世俗文學中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世說新語》作為較早、較完整記錄鄧攸故事的史料,無疑是此故事在后世各類文本,尤其是戲劇文本中影響最深廣的源頭之一。但目前可見的戲劇作品存貌羼亂,鄧攸故事佚多存少,學界尚未作出厘清。故本文將從《世說新語·德行》“鄧攸棄子”條出發,對元明清戲劇中的“鄧攸故事”縷述原委。
一、以《世說新語》為發端的“鄧攸棄子”故事
首先,我們需要對“鄧攸棄子”的本事進行還原和厘清。棄子事發生于鄧攸逃離石勒途中。據劉孝標注引鄧粲《晉紀》:“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4)[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頁。《晉書·鄧攸傳》則言:“永嘉末,沒于石勒。”(5)[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頁。故鄧攸為石勒所擒時間約為晉懷帝司馬熾永嘉年間,即307—313年。《晉書》亦有其他記載,但與此推斷不合。比如稱鄧攸逃離石勒大營棄子保侄是在“石勒過泗水”(6)[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頁。之時,史載:“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卞)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晉書·卞敦傳》)(7)[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七○,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74頁。卞敦“退保盱眙”之事《資治通鑒》系于太寧元年,即323年,在祖逖亡故之后第二年,祖逖亡于321年,“石勒過泗水”距離永嘉年間較遠,此其一。其二,鄧攸離開石勒后,先“至新鄭,投李矩”(8)[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頁。。三年或更長時間以后,密投荀組:“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為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征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后密舍矩去,投荀組于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9)[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頁。荀組亡故于322年,鄧攸又如何在321年(祖逖亡,石勒侵逼淮泗)后,投靠李矩三年多,且再投荀組?其三,《晉書·食貨志》載:“(太興)二年(319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10)[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六,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91頁。此時鄧攸已離荀組,渡江被元帝封為吳郡太守。故《晉書》稱鄧攸逃離石勒為“石勒過泗水”之時難以取信。
年湮世遠,我們嘗試從其他相關人物入手考察。首先,鄧攸在荀組處三年后,晉愍帝司馬鄴曾征其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晉愍帝在位期間為313—316年,316年為最晚征辟時間,往前至少推三年,故鄧攸棄子投靠李矩最晚不超過313年。其次,鄧攸去新鄭投李矩,必是李矩屯于新鄭之后,《晉書·李矩傳》載:“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后移新鄭。”(11)[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六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06頁。故李矩屯新鄭定在永嘉二年(308年),劉淵攻平陽后幾年。則鄧攸棄子的時間大致在308-313年之間。考慮到鄧攸逃難時為步行:
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后猶當有兒。”婦從之。(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12)[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頁。
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晉書·鄧攸傳》)(13)[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頁。
職是之故,鄧攸投奔李矩路程應不會太過遙遠,甚至可能在石勒大軍距李矩不遠之時。胡三省注云:“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14)[北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一六,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525頁。前文已論,石勒逼近卞敦所鎮泗口在321年以后,故鄧攸逃離石勒大營這次應為侵逼他地陣營,非幾年后淮北地區淪陷的戰役。泗水河在今濟寧市,與新鄭隔界而望,距離較近,兼石勒曾在永嘉五年(311年)襲擊李矩:
石勒親率大眾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眾,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晉書·李矩傳》)(15)[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六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06頁。
李矩大破石勒之軍,后被晉元帝拜為河東太守。巧合的是,鄧攸在被石勒所獲前,亦“出為河東太守”。故鄧攸逃離石勒大營很可能在石勒襲擊李矩這一戰役前后,根據河東太守官職的繼任情況,鄧攸也較為可能在李矩迎戰石勒之后、加封河東太守之前被捕。總而論之,鄧攸棄子保侄故事的發生時間,極有可能在永嘉五年(311年)左右,這符合“永嘉末”的史書記載。鄧攸夫妻無法同時攜兩幼子逃難,便“棄己子,全弟子”,這是“鄧攸棄子”故事發生的主要時間、事件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世說新語》獨錄鄧攸棄子故事,而在魏晉時期,棄己子以保全他子的行為夥矣沉沉,并非個例。宦門高族有:漢末劉平更始之亂中為保全弟劉仲遺腹女,“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16)[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卷三九,中華書局 2000年版,第871頁。。夏侯淵在兗、豫大亂時,因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17)[晉]陳壽:《三國志》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頁。裴松之注引《魏略》。。民間有:余杭婦人荒年“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18)[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七八,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61頁。;武康兄弟“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19)[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七八,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61頁。。若以《世說新語·德行篇》首條“陳蕃禮賢”條為時間上限,夏侯淵事在此之后,且在鄧攸事前,其“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的行為,與鄧攸何異?獨錄鄧攸,則意在故事人物忠孝仁義的精神內核,而非棄己子的具體行為。這種文化價值的外化需要人物載體,以最大程度地發揮此內核的涵容性與影響力。《世說新語》讀之有味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選擇當世非常規事件的典型人物。非常規事件即未成為當世人的普遍行為操守與處事態度,甚至有些驚世駭俗(如“任誕篇”)的故事題材;而典型人物則是故事主腦,是一類非常規事件中最具代表性、接受程度最高的主人公。鄧攸乃晉世“人倫之表”(20)[南朝宋]劉義慶撰, [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53頁。,除“棄子保侄”事外,仍有諸多可錄入“德行”的事跡。其一是“孝”:“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21)[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8頁。按照彼時喪服制度,喪父服斬衰三年,喪母服齊衰三年,喪祖母服齊衰不杖期一年,若無重計,七年足矣,居喪九年,可觀至孝。其二是“義”:鄧攸深陷石勒之時,胡人失火反污鄧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嘆息宗敬之”(22)[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頁。。以德報怨的行為可見鄧攸心胸,也窺鄧攸急智。后鄧攸逃離石勒所乘牛馬,或有胡人饋贈。其三是“仁”:他赴任吳郡,自帶米糧,“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離開吳郡時,更“不受一錢”。(23)[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2340頁。如此忠、孝、仁、義之人,出仕便被“舉灼然二品”(24)[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8頁。,是晉世德行雙修的代表人物,故“棄己子全他人之子”事例雖眾,但以鄧攸最具代表性。綜合個人聲譽和影響力考慮,劉義慶將“鄧攸棄子”布局于“德行第一”,事出有因。
劉義慶《世說新語》敘述“鄧攸棄子”故事的結構安排也應引起重視。“鄧攸棄子”條僅一句介紹棄子事:“鄧攸始避難,于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更多的筆墨則放在鄧攸過江納近親為妾的爭議行為上。鄧攸作為“人倫之表”入德行篇,所錄之事卻罔悖人倫,《世說新語》言約旨深,如此安排,值得思考。我們知道,棄子的結局是鄧攸終生再無子嗣,晉人普遍認為是“天道無知”的結果,謝安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25)[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5頁。。而《世說新語》點出無子的直接原因乃納近親為妾,鄧攸“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晉代制定律法,首次把“五服”制度納入國法范圍,作為判斷是否構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輕重的標準。晉律特別強調嚴禁近親結婚,同姓成婚不僅要受到世俗的非議,而且觸犯當朝法律。《晉書·刑法志》規定:“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26)[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927頁。可見鄧攸納外甥女為妾的行為在晉世后果尤為嚴重。首先,《世說新語》對“鄧攸棄子”的文本安排,不以“無子”情節作為文本結局,給予讀者的直接閱讀感受便是強調是鄧攸棄子的“因”釀成近親納妾的“果”。在晉當世,強調鄧攸失節,比其無子更具有宿命色彩。其次,“不孝有三,無后為大”(27)楊伯峻編著,蘭州大學中文系孟子譯注小組修訂:《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2頁。,鄧攸至孝,卻能在明知絕后的情況下知恥自懲,盡力彌補,不再蓄妾,亦十分難得,微瑕可磨。因此,“鄧攸棄子”之所以入“德行篇”不僅在“棄己子,全弟子”,更在無意犯錯之后寧愿無后,“不復畜妾”。
綜上,在以《世說新語》為發端的故事設計與傳播中,“棄子保侄”情節逐漸成為鄧攸其人最具代表性的元素,進入史書、文賦、詩歌、戲曲,在后世各種文本中展現出較深廣的影響力。
二、清前的“鄧攸棄子”故事:無子之嘆的單一符碼
“鄧攸棄子”故事,在當世以褒揚為主流,《世說新語·賞譽第八》第一四○條載:“謝太傅(謝安)重鄧仆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28)[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5頁。至南北朝時期,鄧攸德業名聲仍蔚然可尊,南朝徐陵有曰:“公養孤之恩,愛甚鄧攸,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又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29)[南朝陳]徐陵:《徐孝穆集箋注》卷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北朝庾信亦有:“豈直鄧攸清白,見稱五鼓之歌;劉寵廉能,名為一錢之郡。”(《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志銘》)(30)[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全集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36頁。從一定意義上說,鄧攸仍以人倫標桿的形象出現在此時的文學作品中。
鄧攸故事進入唐代詩歌,則以“無子之嘆”為具體表現形式。作家的關注目光從鄧攸“棄子保侄”的高義品行轉移到“伯道無兒”的人生宿命結局,通常是自我生命軌跡的映射。如白居易老而無子,遂將鄧攸引為異代知音:
教他伯道爭存活,無子無孫亦白頭。(白居易《同夢得和思黯見贈,來詩中先敘三人同讌之歡,次有嘆鬢發漸衰,嫌孫子催老之意,因繼妍唱,何兼吟鄙懷》)
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白居易《題文集柜》)
劉綱有婦仙同得,伯道無兒累更輕。(白居易《酬贈李煉師見招》)
有室同摩詰,無兒比鄧攸。莫論身在日,身后亦無憂。(白居易《閑坐》)
以上諸語可見,白居易在老而無兒的情況下,以鄧攸無子亦白頭,伯道沒有身后憂來不斷寬慰自我。其五十八歲老來得子,然幼子阿崔三歲夭折,如此大起大落之下,白居易又引鄧攸自嘲:“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哭崔兒》)比起現實經歷,精神層面的耦合是白居易屢次在作品中提及鄧攸的原因。杜甫、杜牧、韓愈、李商隱等著名詩人亦不乏對鄧攸無子的提及。在文壇大家的引領下,“鄧攸無子”作為內涵較為單一的固典,逐漸消減了鄧攸其人及鄧攸“棄子保侄”故事“忠孝仁義”的精神內涵。
而從較豐富的“忠孝仁義”故事內涵到較單一強調“無子”結局的轉變,確然在清前戲劇作品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清前涉及鄧攸事的戲劇至少有七種,比較成型的本子有兩種。一是元代女真作家李直夫《鄧伯道棄子留侄》雜劇,又作《吳太守鄧伯道棄子》。《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并見著錄,佚。《錄鬼簿》載賈仲明詞,將此劇列為李直夫諸劇之首:“蒲察李五大金族,鄧伯道,夕陽樓,勸丈夫。虎頭牌,錯立身,怕媳婦。諫莊公,潁考叔。俏郎君,謊郎君,各自乘除。渰藍橋,尾生子,教天樂,黃念奴,是德興秀氣直夫。”(31)[元]鐘嗣成等:《錄鬼簿(外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頁。趙景深《元人雜劇鉤沈》自李玉《北詞廣正譜》中輯殘曲兩支:
[越調][青山口]這里是那里?百忙里,百忙里,取甚的?你欲回待回怎生回?亂軍中是怎地?人也未來無信息,他來尋空隙。咱這壁那壁廝喚只,咱行里坐里廝等只。嬸子兒回去落便宜。既然事已,一句也再休提。咱疾也麼疾則宜疾,遲也麼遲不宜遲。前街后巷,鬧炒交馳,這的是搶攘之際,又不是歌舞筵席。
[雙調][梅花酒]不是我自間阻,俺父親有官祿,您父親有聲譽,俺兄弟有名目,咱父母命先卒。您爺爺一身故,痛煞煞廝囑咐:“將侄兒好抬舉。”我怎肯巧支吾?說著后氣長吁,提起來淚如珠,不由人不憂慮。遭兵火,離鄉閭,拋家業,受驅馳。做娘的甚活路?做兒的甚情緒?則是這幾句言語。(32)趙景深輯:《元人雜劇鉤沈》,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79-80頁。
趙景深認為:“[青山口]乃描寫奔逃時之狀況。‘廝喚只’‘廝等只’頗似‘嬸子兒回去’因而失散之情景。[梅花酒]曲則為‘遭兵火,離鄉閭’后鄧伯道對其侄兒所述之言詞,故排列在后。”(33)趙景深輯:《元人雜劇鉤沈》,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80頁。進一步定位,[青山口]屬越調,《太和正音譜》明確注[青山口]為第二折,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認為:“元劇以一宮調之曲一套為一折。普通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34)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頁。一折之內,宮調不變,故[梅花酒]入雙調必不屬第二折。兼趙景深據《北詞廣證譜》尚有[游四門]曲推論此劇第一折為仙呂。據李占鵬《元雜劇宮調的構成類型與組合方式》(35)李占鵬:《元雜劇宮調的構成類型與組合方式》,《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2003年12月。可推,第一折為仙呂,第二折為越調,劇中又有雙調的組合方式,雙調一般在第三折或第四折,以第四折的可能性較大。故鄧攸向侄子回憶逃難情形的[梅花酒]應接近此劇之末,可見整個雜劇故事主要圍繞“鄧攸棄子”的具體情節敷演出來,敘述方式整體上采取順敘手法。其次,由殘曲還可知,李直夫在雜劇中增添了鄧攸弟媳這一角色,卻又設計了弟媳失散的情節。《世說新語》未曾提及弟媳其人,《晉書·鄧攸傳》也只論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但有“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為辭”(36)[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頁。一句,知弟媳確在石勒營中。此劇為使鄧攸夫婦無法帶兩兒一起逃走合理化,讓弟媳這一成人角色與諸人走散,營造出力所不支的危機情境,襯托“棄子保侄”艱難決定的不得已。李直夫后,清末京劇譚派藝術的創立者譚鑫培,將此故事改編為著名京劇《桑園寄子》,主人公用鄧攸弟媳代替鄧攸妻子,依然保留了弟婦被賊寇沖散的情節。另外一種比較成型的戲曲是明代無名氏《鄧伯道棄子抱侄》傳奇,劇本佚,作者失考,明徐渭《南詞敘錄》著錄。
除兩種以鄧攸為主要人物敷演的戲劇,還有涉及鄧攸故事的戲劇五種,它們或多或少都帶有鄧攸元素。一類是戲劇主人公有子卻因故失子,如元代鄭廷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雜劇第四折:“[紫花兒序]一個那顏回短命,一個那盜跖延年,一個那伯道無兒。人都道威靈有驗,正直無私,現如今神祠東岱岳,新添一個速報司,大剛來禍無虛至,只要你惡事休行,擇其這善者從之。”(37)[明] 臧懋循選:《元曲選》,明萬歷刻本。“伯道無兒”唱的是主人公周榮祖,因家中錢財被賈仁盜走,被迫將親子賣與賈仁獲取錢資,戲曲最后不但將錢財物歸原主,兒子賈長壽也認祖歸宗,伯道無兒變有子的大團圓結局。同類型還有元無名氏《周羽教子尋親記》南戲,存《六十種曲》本,作《尋親記》。
如果說上述第一類鄧攸棄子戲因劇本殘缺粗見故事梗概,那么第二類的整體特征則更為明顯,情節與《世說新語》所記若合符節。戲劇女主人公均為家中獨女,曲中常有“鄧攸無子之嘆”。如南戲《荊釵記》,故事源于貢元錢流行一生無子只得錢玉蓮一女:“嗟吁獨負鄧攸憂,一子難留。且求佳婿續箕裘,是亦良謀。”(第五出《啟媒》)(38)[元]柯丹邱著,中山大學中文系五五級明清傳奇校勘小組整理:《荊釵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頁。他將獨女許配給貧寒書生王十朋。兩夫婦歷盡艱辛,生死不渝,錢玉蓮雖為女兒身,卻有著男兒難及的傲骨。面對繼母逼迫改嫁的困境,她毅然投江:“無奈禍臨頭,今朝拼死休,如癡似醉任漂流。”(第二六出《投江》[糖多令])(39)[元]柯丹邱著,中山大學中文系五五級明清傳奇校勘小組整理:《荊釵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2頁。她的愛情不依附于父母之命,而是超越生命的自我抉擇。可謂鄧攸雖無子,生女更勝男!明湯顯祖《牡丹亭》傳奇,女主人公杜麗娘也設定為家中獨女,其父親杜寶將老儒陳最良聘為西席:“有女頗知書,先生長訓詁。”(第五出《延師》[鎖南枝])“我伯道恐無兒,中郎有誰付?”(第五出《延師》[鎖南枝])(40)[明]湯顯祖著,徐朔方、楊笑梅校注:《牡丹亭》,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6-17頁。此處化用韓愈《游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41)[唐]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宋蜀本。之句。“中郎女”即漢代蔡邕之女蔡琰,杜寶因無子而急于望女成鳳,“伯道暮年無嗣子,女中誰是衛夫人”(第三出《訓女》)(42)[明]湯顯祖著,徐朔方、楊笑梅校注:《牡丹亭》,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9頁。,他以蔡文姬、衛夫人這些著名才女為標桿嚴苛管教獨女,以封建禮教壓制人的天然欲望,以致獨女杜麗娘傷情而死。杜麗娘肉身雖死,但她追求愛情理想的信念不滅,最終以情超越生死,向死而生。明無名氏《贈書記》傳奇,孤女賈巫云亦是“父母雙亡,弟兄寡偶”(第三出),她叔父“滿腔中都是貪婪”(第三出[鎖春寒]),霸占巫云家產。賈巫云為逃避宮中征選,女扮男裝,力壓一眾男兒,輔助淮陽刺史傅子虛招安楊家女將,立下不世軍功。賈巫云的戲劇形象,襯托其叔父“嘆哥哥(似)伯道無男,(我是他)手足之親豈等閑,論家資今朝該我專權”(第三出[瑣窗寒])(43)[明]毛晉編:《六十種曲》,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的小人嘴臉。
三、清代戲劇中的“鄧攸棄子”故事:德行之士的大團圓
清代戲劇中的鄧攸故事,與前代相比,留存較完整,鄧攸故事忠孝仁義的精神內核重新受到重視。以鄧攸棄子保侄為主要情節鋪設的戲劇有兩種:一是清初無名氏《百子圖》傳奇,存綴玉軒鈔本。《曲海目》《曲考》《今樂考證》《曲錄》著錄。近人蔣瑞藻《花朝生筆記》云:“明人作《百子圖》雜劇,乃謂攸子雖棄,為他人所得,后復歸于攸,子孫眾多,元帝為繪《百子圖》,以紀其盛。”(44)蔣瑞藻著,蔣逸人整理:《小說考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頁。從故事情節看,蔣瑞藻所言雜劇與今存清《百子圖》傳奇內容一致,很可能為同戲。二是清周樂清《如鼓》雜劇,存山東圖書館藏稿本,全稱《賢使君重還如意子》,乃《補天石傳奇》第七部,《曲錄》著錄。《世說新語》“鄧攸棄子”條敘事簡約,給戲劇作家留有巨大創作空間。《如鼓》情節較單薄,并無太強烈的戲劇沖突,屬文人閑適劇,適于案頭欣賞,共四出。《百子圖》傳奇則多達二十四出,故事人物也被賦予當代色彩,迎合當時審美作了改動。
清代鄧攸戲有如下三大特點:
[油葫蘆]這一個鳩形鵠立鶴同癯,這一個目昏不見來時路,這一個口喑說不出多言語,這一個耳雙聾走向隅,看了這衰翁弱息身傴僂,怎能夠春風一例起三吳!(46)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85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311頁。
鄧攸未得皇令,便開倉放糧:“愿以一身擔罪,庶免萬姓流亡!”(第三出《繪賬》)(47)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85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頁。在《百子圖》傳奇中,他為平民強思萱翻案,怒斥宦官走狗:“你這狗輩敢行刁,俺只是定罪從公無愧怍,怎容伊胡亂!”(第八出《原情恩釋》)(48)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142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頁。一個不折不扣的好官,前期舍小家成就大義,如今大義反哺小義失子重圓,如毛宗崗所言,“斯皆以天數俯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49)[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齊煙校點:《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齊魯書社2014年版,第213頁。,契合市民階層期盼良吏的美好愿景。
《百子圖》中,鄧攸不但尋回失子,而且子孫百數。這樣的結構安排有一定歷史原因。早在《詩經·大雅·思齊》中,便有“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50)[南宋]朱熹集注,趙長征點校:《詩集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43頁。,文王生百子的傳說。在民間,百子千孫是祥瑞之兆,兼有皇室引領此風,清朱彝尊曾記:“百子圖者、龍文五彩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51)[清]朱彝尊:《感舊集序》,《曝書亭序跋》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頁。清吳震生《生平足》傳奇改編自南朝梁李遷哲廣娶滕妾,兒女百十的故事:“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余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仆侍婢閽人守護……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52)[唐]李延壽:《北史》卷六六,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6頁。清代傅山評曰:“男女六十九人,數日福報爾爾。”(53)[清]傅山著,尹協理主編:《傅山全書》第8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頁。此語足見多子多孫是積善之福報。鄧攸清廉明德,以清人所觀,應有百子之福。
另一方面,“補恨”亦有作家個人內因推動,可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我之塊壘。周樂清《補天石傳奇自序》中提到寫作的直接原因:“余曩閱毛聲山評序《琵琶傳奇》,云:‘欲撰一書,名《補天石》,歷舉其事,皆千古之遺恨,天欲完之而不能,人欲求之而未得者。’雖未見其書,而覽其條目,已爽心快膈,如食哀梨,使人之意也消。”(54)蔡毅編:《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1104頁。清初戲曲評點家毛聲山于《琵琶記·自序》中道:“擬作雪恨傳奇數種,綜名之曰《補天石》。”(55)侯百朋編:《〈琵琶記〉資料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頁。并列出十種擬作戲劇目錄,其五乃《鄧伯道父子團圓》。周樂清遍尋此劇三十載未果,未免“后人過屠門而大嚼,以虛臠快意”(56)蔡毅編:《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1104頁。,親自以毛之目敷演八劇。這是《如鼓》創作直接動因。然而,周改十劇為八劇,留鄧攸故事,更主要的原因是托虛筆對精神世界的主觀重構,達到“竭人事而彌縫”(57)蔡毅編:《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1104頁。的目的。周樂清本人三代單傳,曾連夭兩子,雖自知“天亦有難言之者”(58)蔡毅編:《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1104頁。,禁不住俯仰“問天何不畀區區”(《哭泳兒三首·其二》)(59)[清]周樂清:《靜遠草堂初稿》,桑兵主編:《清代稿鈔本》第28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頁。?幼子“生育他鄉埋異地”(《哭泳兒三首·其三》)(60)[清]周樂清:《靜遠草堂初稿》,桑兵主編:《清代稿鈔本》第28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頁。的現實情境,與鄧攸失子于逃難途中何異?自己同鄧攸般為官清慎,“幸得官民洽”(61)[清]周樂清:《靜遠草堂初稿》,桑兵主編:《清代稿鈔本》第28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頁。,卻也期盼一個“鼓圓”結局!現實無法實現,便只得在戲中淬煉補心之石:“[梅花郎]無兒伯道,自來稱循良,豈得無征應。民還子,子即民,就里機關天幸,是民是子能平等,(便要他)死還魂,天也肯!”(《如鼓》第四出《鼓圓》)(62)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85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頁。
清代鄧攸戲第二大特點,即剪掉不利于鄧攸形象的駢拇枝蔓,主動消解鄧攸故事中的負面元素,擺脫緊張的父子關系,塑造完美的德行之士。鄧攸棄子保侄故事中,爭議最大之處并非“棄子”,而在“縛子”。劉孝標注引《晉中興書》:“攸棄兒于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系兒于樹而去,遂渡江。”(63)劉孝標注引《晉中興書》。[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頁。唐修《晉書》沿用此情節:“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樹而去。”(64)[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39頁。后世評者對此龂龂相角:
其子追及,縛于道旁。夫追而不及,尚當憐之,追及矣而縛于道旁,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是歟?(南宋俞德鄰《佩韋齋集》卷一七)(65)[南宋]俞德鄰:《佩韋齋集》卷一七,《天祿琳瑯叢書》景元本。
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系之樹,有人心者刻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兒。豈天道無知哉?晉之好名,至此極矣。(明郎瑛《七修類稿》)(66)[明]郎瑛:《七修類稿》,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頁。
鄧攸逃難,棄其子而攜其弟之子,“其子朝棄而暮及,攸乃系之樹而去。”噫,甚矣!攸意以為不棄其子,無以顯其保全弟子之名,好名如此,不仁可知。……小人哉,攸也!斯人也而可以入《良吏》乎?(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67)[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一,清乾隆五十二年洞涇草堂刻本。
將兒系于樹上,剝奪生命個體的生存可能,非棄子,是殺子。鄧攸將他人生命納入“我”這個主體的犧牲范圍,“子”成為“我”的客體,“縛子”是“我”之本體犧牲,子的主體性被抹殺。固然在清世,仍是“孝高于慈”的父權社會,饑困時期,“民鬻子女”(68)[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九九,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802頁。也是常事。但清代戲劇作家已意識到雖“父慈”這塊遮羞布不能全然扯下,“縛子樹上”的情節,若不加修飾,不利于受眾對大團圓結局的共情。而這種加工修飾,《百子圖》與《如鼓》又有區分。
[淚介](老旦)雖然如此,但我兒哭,追已及,相公竟將他系縛樹間,未免太狠了。

為使“縛子”情節更加合理化,增添鄧攸人情味,周樂清一方面美化石勒治軍嚴明,“知道賊中紀律頗嚴,不許輕肆擄戮”;另一方面夸贊兒子“吾兒雖小,性頗伶俐”。劇中鄧攸在難兩全之下,仍竭力為棄兒尋出一條活路,至此,“縛子”反成救子,無損鄧攸之慈。
《百子圖》則選擇直接刪去“縛子”情節:“(尾)看他眼睜睜緊緊扯衣襖。(外)我行一步反回三次。(老扶外勸介)相公你保重身軀且忍悲。(老作回顧大哭下)”(第一五出《棄子立信》)(70)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142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頁。經作家裁剪,鄧攸不但沒有因兒子呼啼追之而“縛子”,且“行一步反回三次”,表現出棄子后內心的極度掙扎。同時犧牲鄧攸妻不舍孩兒的慈母形象,反勸鄧攸保重身軀且忍悲。作家為鄧攸設計“棄子”后諸多小動作,自然流露出拳拳父心,將鄧攸故事中唯一的負面因素抹去,塑造出完人形象。清孔尚任《桃花扇小識》曰:“傳奇者,傳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則不傳。”(71)[清]孔尚任:《桃花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而“奇”情節的產生離不開關鍵道具的推動,道具為棄子掙得生路的可能性越大,鄧攸形象中“不慈”元素則消解的越多。《百子圖》中,鄧攸贈子鄧賓古鏡一枚:“我有祖傳辟邪古鏡一面,不免系在他身上,少盡父子之情。”(《百子圖》第一五出《棄子立信》)(72)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142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頁。百姓強思萱撿到鄧賓,撫養成人,多年后又憑此辟邪鏡,使鄧攸父子團圓相認。以鏡為媒,失子團圓的戲劇情節,《百子圖》并非孤例。清朱佐朝《軒轅鏡》傳奇、清無名氏《渾儀鏡》傳奇、清朱云從《龍燈賺》傳奇、清高奕《春秋筆》傳奇均有以鏡認親的情節設計。(73)清朱佐朝《軒轅鏡》傳奇、清朱云從《龍燈賺》傳奇、清高奕《春秋筆》傳奇三劇故事情節相類。
特點其三,情節多而不亂,雙線并行,互為襯托。作家借他人之口渲染鄧攸形象忠孝仁義的精神內核,語言俚俗,質樸真情。《如鼓》共四出:《酬乘》《賜泉》《繪賬》《鼓圓》。設計鄧攸棄子保侄主線的筆墨甚少,前三出著力于鄧攸清正廉潔,為官愛民的良吏形象,故離任時百姓爭來相送:

可以說,沒有前期鄧攸德惠及民,就不會有闔郡老少作曲送別,更不會在送別人群中恰巧尋回失子:“歡慶這鼓兒打得離亭成樂境,樂境比黃泉得再生,再生何幸。”(《如鼓》第四出《鼓圓》[玉連環])(75)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85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頁。所有關鍵情節,都借百姓之口歌頌出來,側面描寫為主,水到渠成。
《百子圖》則設置兩個對照組:鄧攸與強思萱,鄧攸兒鄧賓(后改名作鄧金)與鄧攸侄鄧綏。鄧攸線與強思萱線四遇四救:鄧攸救下被設局謀妻的強思萱,此為一遇一救,自此,官與民際遇交匯,主線與支線有了情節糾葛;第二遇二救乃強思萱報恩,因緣際會救下被石虎所獲的鄧攸;第三遇三救是強思萱救下棄子鄧賓,撫養成人;第四遇四救,強思萱救下被負心侄鄧綏逼至絕境,欲跳溪自盡的鄧攸,最終更是慷慨地把功成名就的養子鄧金拱手相還。作家塑造的強思萱形象,在筆墨與豐滿程度上,比鄧攸毫不遜色。雖開篇好賭愚笨,被騙得因妻殺人,于小節有虧,但他牢記救命之恩,三救鄧攸,于大節無損。強思萱是作家為鄧攸立起的一面鏡子,映出鄧攸“世尊爺爺,盤古以來,沒得個樣好人個哉”(第二三折《見鏡思兒》)(76)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142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9頁。的精神內核。而第二組以子鄧金與侄鄧綏互相比勘。劉孝標注引《晉中興書》載:“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77)[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頁。侄為伯叔父應服喪齊衰不杖期,喪期一年。由史可窺,鄧綏后應是待鄧攸至孝。明戲曲理論家王驥德認為:“戲劇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78)[明]王驥德著,陳多、葉長海注釋:《王驥德曲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頁。《百子圖》中的鄧綏被塑造成一個不孝喪德之人,分走資產不認叔父,恨得鄧攸直罵:“恁的沒心肝,恁的沒心肝,恰似中山狼一般!”(第二一出《負恩逐伯》)(79)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142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 第405頁。在鄧綏的反襯下,鄧金完全不同,其子孫百數、盡列朝堂,更為養父強思萱告老返鄉盡孝,正如鄧攸所嘆:“(尾)他無兒偶繼榮華驟,(拭淚介)我有子反成無后。”(第二二出《投溪遇故》)(80)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142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 第413頁。李漁曾批明清傳奇:“后來作者,不講根源,單籌枝節,謂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事多則關目亦多,令觀場者如入山陰道中,人人應接不暇。”(81)[清]李漁著,陳多注釋:《李笠翁曲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頁。《百子圖》雖多達二卷二十四出,但頭緒紛而不亂,人物多而不雜,雙線并行刻畫鄧攸周邊人物,各居其位,共同烘托鄧攸忠孝仁義的形象,對戲劇主題作多樣生發。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以《百子圖》為代表的清代鄧攸戲,不失是較為成功的文學創作。
四、結語
如姚斯所言,“文學系列中的演變更替只能成為一種歷史的連續性,而新舊形式的對立也能使人們認識到它們特殊的調節”(82)[德]姚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頁。。鄧攸故事在后世流傳中,忠孝仁義的精神內核顯而又隱,隱而又顯,是隨著不同時期興盛的文本形式與文本特點而變換的。南北朝時期,去晉世不遠,鄧攸“人倫之表”的主流評價余韻猶在。隨著鄧攸故事的傳播,鄧攸本身符合封建統治者的統治理念,被后世雅、俗文學家共同關注。雅文學家不斷接力,將鄧攸無子固定成詩歌創作中的文化符號,故鄧攸故事最初進入戲劇這種俗文學,在元雜劇和明傳奇中通常作為故事背景,襯托戲劇中女子“弱女更勝男”的人格魅力。進入清代,在整個社會處于紛挐惶駭的文化高壓下,這種文人心理上的創作緊張情緒,不僅彌漫在上層官僚之間,民間文人為保與清廷文化政策相融無礙,也會主動選擇相對安全的創作題材。鄧攸“棄子保侄”的高義行為與福澤一方的良吏身份,不失是一個較好的選擇。同時,俗文學在市民階層興起后還承擔著正統歌詩所無法替代的政治教化功用,更要符合民眾的價值評判。“因為我們沒有宗教,沒有救贖,沒有來生的許諾,我們可能真的需要在此生就實現終極正義,否則我們會陷入絕望,而且還會引發絕大的道德危機。”(83)鮑鵬山:《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472頁。觀眾對良吏鄧攸無子的普遍不滿,對善無善報的遺憾排斥,也使鄧攸故事與屈原故事、荊軻故事等成為“補恨”作品的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