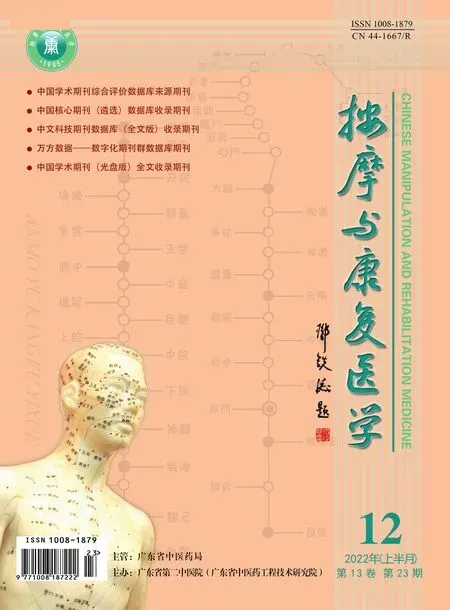基于《黃帝內經》肌痹病因探討其針灸治療*
吳云云,唐純志
(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405)
肌痹是指發生于肌肉的痹證,其病因癥治主要見于《素問·痹論》《素問·長刺節論》《靈樞·周痹》《靈樞·官針》等篇目之中,肌痹對應了現代臨床中多種不同類別的疾病,如軟組織痛癥、風濕免疫疾病[1]等,其針刺治療方法也別具特色。筆者在精讀相關原文及歷代注家闡釋的基礎上,根據《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對于痹證的病因-癥狀表現-治療方法的相關論述,以病因為核心,分析肌痹的臨床表現及針灸治療方法。
1 肌痹的發生
《內經》中關于肌痹的發生主要見于《素問·痹論》:“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痹”,在這一定義中包含了病位在于“肌”、發病時間為“至陰”(即長夏時節)、病因為“風寒濕三氣”三大要素。其中病因不僅指風寒濕三邪,還包含了風寒濕三邪何者為主導而產生的不同情況。根據風寒濕三邪的多少,肌痹可以表現為不同的病癥。內經對痹證的分類中,根據病因進行分類形成的“三痹”是痹證最基礎的分類,皮痹、肌痹、脈痹、筋痹、骨痹五種痹證(后世稱為“五體痹”)則是風寒濕邪侵襲人體,停留在人體由外至內五種不同層次所產生的五種痹證,這是根據“痹”的深淺(即病位)對痹證的一種分類。概括而言,風寒濕邪侵襲人體肌肉所生成的痹證即為肌痹,肌痹發生的季節常在長夏時節。
2 肌痹的臨床表現
2.1 風勝則肉不仁《素問·痹論》中以“在于肉則不仁”來表述在于肉的痹證的臨床表現,后世醫家據此推斷肌痹的主要表現為肌肉不仁[2]。《素問·風論》曰:“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于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靈樞·刺節真邪》曰:“留而不去,則痹。衛氣不行,則為不仁”。上述關于“肌肉不仁”的條文互參,不難看出肌痹表現為不仁主要是由于風氣侵入分肉之間,阻礙營衛的正常通行,衛氣不行,不能將精微物質帶到局部肌膚則會導致肌肉失于濡養而產生“不仁”的癥狀。巢元方在《內經》的基礎上,總結了風寒導致肌肉不仁的機理,并將不仁形容為“搔之皮膚如隔衣”的感覺,楊上善、馬蒔、張介賓等注家則將不仁大致概括為不知痛癢寒熱的一種表現。當風寒濕邪中以風邪為主導,侵襲于人體的肌肉,以致于分肉間的營衛之氣不行,血氣不能流通,就會形成肌膚不知痛癢的“不仁”的表現。此外,根據風邪善行數動的特點,后世醫家認為行痹的主要特點為痹痛游走不定。因此,以風邪為主的肌痹也有可能表現為痹痛的游走不定。其臨床特點與《靈樞·周痹》中“上下移徒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的周痹相似,一些醫家認為周痹表現出“游走不定”的特點也是風邪為勝所致,仍屬風痹之類[3]。
2.2 寒勝則痛 若侵入肌肉的邪氣以寒邪為主,肌痹就可能表現為以疼痛為主。如《素問·長刺節論》“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痹,傷于寒濕”即認為肌痹的主要表現為“肌膚盡痛”。此處的肌膚包含了“肌肉”與“皮膚”兩個層次,此時邪氣停留的主要部位應為肌肉,由于邪氣侵入人體是由外而內,邪氣到達肌肉層時表皮必然已經受到寒邪的影響,肌肉與皮膚兩者又是相互鄰近的結構,因此邪氣的停留會對兩者均產生影響,此時的肌痹可能會表現為肌肉與皮膚兩者的疼痛[4]。肌痹的這一表現也符合“寒氣勝者為痛痹”、“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寒痹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等論述。
2.3 濕勝則屈伸不利 長夏時節是肌痹的易感時節,脾屬至陰,主肌肉,在季節中應于長夏,濕為長夏主氣,故而在長夏時節侵襲人體的邪氣中,濕邪是占據主導的,因此也可以認為肌痹是一種常見于長夏時節、人體感受以濕邪為主的邪氣,留存于肌肉而產生的一種病癥。濕邪致病具有重著、粘滯、趨下等特性,如《素問·生氣通天論》“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說明濕邪侵襲頭部,會產生頭部昏沉的癥狀,濕邪留滯于人體筋肉,會產生肢體屈伸不利等表現。《靈樞·大惑論》在論及皮膚、分肉與衛氣的相互關系時提到“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皮膚濕”在《針灸甲乙經》中寫作“皮膚澀”,似是認為“濕”為“澀”之誤,“澀”亦恰好與原文中的“滑”相對應。然而從濕邪致病特點而言,“皮膚濕”可能是指濕邪由外侵襲人體,根據濕性粘滯、易阻礙氣機的特點,一旦濕邪深入聚于分肉之間,則會導致衛氣運行障礙,繼而會產生皮膚澀滯、肌肉不仁、四肢酸楚沉重等“分肉不解”、“行遲”的臨床表現。《素問·痹論》又言“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說明由濕邪引起的痹證也可能會表現為“汗出而濡”。總而言之,以濕邪為主侵襲人體肌肉引起的肌痹其主要臨床表現可能有:肢體重著不移、肌肉不仁、汗多、四肢緩弱、肢體屈伸不利等。
2.4 脾病則肌肉痛“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肌痹的發生除了與外感的風寒濕邪相關外,也存在內因。《靈樞·五邪》中說“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說明脾胃有邪氣停留,引起脾胃病的同時也會引發肌肉的痛癥,更進一步佐證了“脾主肌肉”的內涵以及脾胃與肌肉之間的病理聯系,兩者之間在病理上有相互傳變、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肌痹形成的內因主要在于脾胃,由各種原因導致的脾胃虛弱,會影響營衛在機體的正常運行,使得外邪易于侵襲人體而產生各種痹證。
3 肌痹的針灸治療
3.1 膀胱經祛風堪效《素問·玉機真臟論》曰:“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因此,風邪主導引起的肌痹可以用熱熨法、灸法或針刺等。《素問·風論》認為風邪循足太陽膀胱經散布在分肉之間,干擾了衛氣的運行,從而產生了肌痹麻木不仁的癥狀。因此,對于風邪為主引起的肌痹,可以選用足太陽膀胱經的穴位進行針刺治療,也可以選用其他善驅風寒之邪的穴位如風府、風池等。此外,《靈樞·周痹》中記載的眾痹的疼痛特點與風邪侵襲的“游走性疼痛”相似,因此可以采用治療眾痹的“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的治療原則,即在疼痛及疼痛過的部位選穴針刺。《素問·繆刺論》“凡痹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左刺右,右刺左”則說明除了在疼痛的分肉間針刺之外,還可以用“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的繆刺法進行治療[5]。
3.2 寒則熱之,刺法為先《素問·長刺節論》“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痹,傷于寒濕。刺大分小分,多發針而深之,以熱為故,無傷筋骨”一句主要介紹了寒邪為主引起肌痹的主要表現與治療方法。寒者熱之,其治療方法主要是使用各種方法對局部進行溫熱刺激。如以多針深刺的方法針刺于分肉之間(大分小分),通過手法刺激使局部產熱或使熱聚集于局部,從而緩解疼痛癥狀。如《靈樞·官針》中的揚刺與浮刺,揚刺共有5針,是一種深刺與淺刺結合、正刺與斜刺結合的多針刺法,主治“寒氣之搏大者”。浮刺則是一種斜向淺刺針法,主治“肌急而寒”,即寒邪停留在肌肉表層的一種表現。《素問·玉機真臟論》提到的熱熨、灸法、針刺等方法同樣適用于寒邪引起的肌痹,如《靈樞·壽夭剛柔》亦云:“刺寒痹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素問·玉機真臟論》與《靈樞·壽夭剛柔》兩篇互參,可以推測《靈樞·壽夭剛柔》中的“火灸刺”中包含的刺法應該是“以火焠之”,類似于今日的火針等針刺方法。《靈樞·四時氣》“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一句則提出了針對寒濕久留的病癥,火針可以選取“三里”穴來治療,三里位于肢體肌肉豐厚之處,以火針治療不但可以直達病所,還能循經絡溫補脾胃之氣以驅散寒濕之邪。
3.3 濕則求經穴之功《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中提到“音主長夏,長夏刺經”,濕邪為長夏主氣,因此對于長夏時節感受濕邪引起的肌痹,可以根據痹證所在的部位,選取對應經脈的“經穴”來進行治療。有的醫家從治未病、“子行母氣”的角度來解釋《內經》中應時針刺的五輸穴選用規律[6]。筆者認為,長夏時節的肌痹多因外感濕邪侵襲引發,四時邪氣外感屬實邪為主,濕氣侵襲會對脾的功能造成影響,“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而對脾臟本身應該用補益之法,針刺脾經輸穴可以振奮脾胃之氣以抵御邪氣;對于外感而來之邪氣,則選用其“子穴”(脾經或肺經經穴)施以瀉法,以祛除邪氣,并防治病邪傳變入他臟引發變證。從經穴的位置來看,經穴位于輸穴與合穴之間,《靈樞·邪氣臟腑病形》云“滎輸治外經,合治內府”,故而經穴既能疏外經又可調內府[7],對于長夏時節感受濕邪引起的肌痹這種易于由外而內傳變的疾病較為適合。
3.4 治痹之本,本于脾胃《靈樞·五邪》“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皆調于三里”中關于邪氣-脾胃-肌肉的病傳關系與《素問·痹論》相反,認為病邪積于脾胃,會導致肌肉的痛癥,這種肌肉痛癥應該會類似于脾痹所表現出來的肌肉病癥,治療上可以參照肌痹的局部對癥針灸治療方法,但產生邪氣的原因可能是內生的或由他臟傳變而來的邪氣或其他病理產物停滯于脾胃,進而影響到肌肉;或是由于脾胃虛弱,不能運化水谷精微,肌肉失于濡養,衛氣不能抵御外邪,而使外邪能夠輕易進入肌肉而產生肌痹,總之這類病癥均可以用“三里”穴來進行調節。足三里為胃的下合穴,具有調理脾胃、補益氣血等作用,是治療脾胃病的主穴,體現了“治病必求于本”的治療思想。
3.5 分刺、合谷刺治肌痹速效 合谷刺是《內經》論述中用于治療肌痹證的刺法,此法針刺的深度在分肉之間,行針軌跡形如雞爪。《素問·調經論》言“病在肉,調之分肉”,治療肌痹以合谷刺法直接針刺于分肉之間,是針刺于病所的治療方法,趙京生認為外經病的表現直觀易明,治療時可以直接針灸病處,操作上則更關注針具對局部組織所造成的直接影響[8]。風寒濕邪侵襲肌肉形成的肌痹,通過合谷刺法直接針刺于分肉之間,以局部較大范圍的針刺刺激調動局部氣血,疏通營衛運行通道,驅邪外出。此外,《靈樞·官針》中還有針刺于分肉之間的分刺法,分刺法與合谷刺法一樣能夠治療肌痹,《內經》并未描述分刺法的具體操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合谷刺法屬于分刺法的范疇,因兩者均針刺于分肉之間,而分刺法是對針刺于分肉之間的刺法的整體概括。《素問·長刺節論》中的刺大分小分之法亦屬于分刺法范疇,其具體操作是在大分小分“多發針而深之”,“多發針”與治療寒邪的多針刺法的要求相符合,“深之”則要求針刺要有足夠的深度。
3.6 員針治肌痹有功《靈樞·九針十二原》曰:“員針者,針如卵形,揩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以瀉分氣。”《靈樞·官針》曰:“病在分肉間,取以員針于病所。”故而,風寒濕邪散于分肉之間引起的肌肉不仁可以用員針治療。以末端卵圓的員針“揩摩分間”來引導衛氣正常運行,激發衛氣的“衛外”功能驅邪外出。由于員針末端圓頓,無法刺入人體,故而其治療深度不及采用毫針等針具行分刺、合谷刺,但勝在不需要刺入人體,在體表施術時可覆蓋的范圍較廣,因此員針可能更適合病邪較為淺表的肌痹及皮痹。
4 小結
肌痹是一種發生于肌肉的痹證,多由風寒濕邪外感侵襲人體并停留在肌肉所致,根據邪氣停留的位置、占主導地位的邪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臨床表現,主要包括肌肉疼痛、肌肉不仁、肢體沉重、屈伸不利等。對于以外經病為主要表現的肌痹,在取穴和治療上,以局部取穴為主,根據病邪的深淺、范圍的不同,可以選擇員針、毫針等不同的針具,選擇浮刺、揚刺、分刺、合谷刺等不同的刺法;根據外邪的性質,風寒為主可以選用火針、艾灸、藥熨,濕邪為主,可以選用五輸穴中的“經穴”和“輸穴”。對于各種原因導致的脾胃病伴有肌痹的表現,除了要在肌肉局部采用對癥治療的針法,還要針刺足三里等穴位調節臟腑功能。《內經》中關于肌痹的內容十分豐富,對于肌痹等疾病的針灸臨床治療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值得仔細研讀并進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