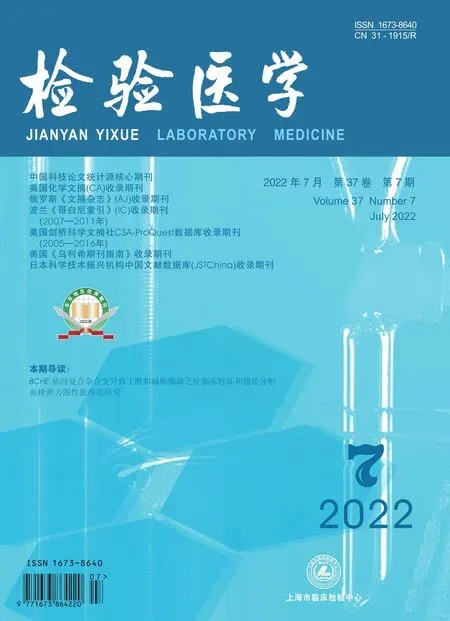血培養陰性血流感染影響因素及實驗室檢測研究進展
陳晗璐, 吳盛海
(1. 浙江中醫藥大學第四臨床醫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6;2.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檢驗科,浙江 杭州 310006)
血流感染是指病原微生物侵入血流引起的播散感染,可造成感染性心內膜炎、感染性休克、播散性血管內凝血等嚴重的臨床后果,病死率高。血培養作為診斷血流感染的金標準,可以鑒定病原體,并提供抗菌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對指導臨床醫生進行抗感染治療意義重大。隨著自動化細菌培養系統的引入,血培養的價值逐漸得到臨床的廣泛認可。然而,血培養的陽性率并不高,有相當比例的血流感染患者血培養結果呈陰性[1]。有學者對住院患者的血培養結果進行統計,發現血培養陽性率僅為8.37%~12.51%[2-3]。采血前使用抗菌藥物、苛養菌本身生長緩慢且對營養要求較高,以及一些胞內寄生菌的感染等均可導致血培養結果呈陰性。血清學試驗、聚合酶鏈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下一代測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等分子生物學技術的使用,是血流感染病原學實驗室診斷的有效補充。
1 血培養結果的影響因素
1.1 分析前因素對血培養結果的影響
分析前因素指血培養樣本在送達微生物實驗室前,對血培養結果有影響的所有因素,包括行血培養的臨床適應癥,血培養樣本的采集時間和采集過程中皮膚的準備和污染的預防,以及采集時血培養瓶的套數和采血量等。
1.1.1 抗菌藥物的使用 采血前使用抗菌藥物是降低血培養陽性率的獨立影響因素[4-5]。德國1項針對膿毒癥患者的前瞻性臨床隊列研究發現,未接受抗菌藥物治療的膿毒癥患者血培養陽性率為50.6%(78/154),已接受抗菌藥物治療的患者血培養陽性率僅為27.7%(112/405)[5]。美國1項對行血培養的住院患者進行的前瞻性隊列研究發現,普通住院患者的血培養真陽性率遠低于急診科和重癥監護病房患者的血培養真陽性率,培養前72 h內無抗菌藥物暴露可以有效提高菌血癥和心內膜炎患者血培養陽性率[6]。雖然膿毒癥患者在進行抗感染治療前進行血培養有利于病原體的檢出,但鑒于早期廣譜抗菌藥物的使用可以有效降低膿毒癥患者的病死率和預防感染性休克,以及部分醫院試驗條件的限制,臨床醫生往往會優先考慮早期抗感染治療,而不是進行血培養。
1.1.2 采血量不足 采集足量的血液樣本進行血培養對血流感染病原體的檢出至關重要,采血量越大,血培養陽性率越高,血流感染的診斷率也就越高。1項評估了345例膿毒癥患者血培養采血量及其結果的研究發現,每多采集1 mL血液,血培養的陽性率可增加1%[7]。相關機構建議的采血量為每瓶8~10 mL,但在實際操作中常難以達到[7]。采血相關培訓的缺乏、重癥或嬰幼兒患者采血困難等因素均可導致血培養采血量不足[8]。一般情況下,實驗室通常采取目測的方式評估采血量,但這不適用于樣本量較大的微生物實驗室,因此有研究建議通過測量血培養瓶的重量來評估采血量,以提高血流感染的診斷效率[8]。
1.1.3 血培養樣本延遲上機 目前,絕大部分實驗室是采用全自動儀器進行血培養監測,血培養樣本延遲上機與血培養陽性率降低密切相關。相關指南[9]建議血培養樣本從采集到進入自動血液培養系統的時間不應超過2~4 h,制造商也提出接種的血培養瓶應該盡快運送至實驗室處理。然而,大多實驗室無法提供24 h服務,工作時間以外采集的血培養樣本在進入微生物實驗室之前通常會在室溫下儲存較長時間。意大利1項大型的回顧性研究發現,在工作時間采集并處理的血液樣本血培養陽性率為13.0%,而在實驗室關閉期間采集并延遲上機的血液樣本中,只有10.8%的血培養結果呈陽性,且樣本采集到上機的時間每延長1 h,血培養陽性率會下降0.3%[9]。
1.2 生長緩慢的苛養微生物對血培養結果的影響
目前,在接種量及接種方式符合要求的情況下,自動化血培養系統已經能夠分離大多數可以生長的病原體,但HACEK(Haemophilus,Actinomyces,Cardiobacterium,Eikenella,Kingella)菌群、營養變異鏈球菌(Nutritionally Variant Streptococcus)、念珠菌等生長極為緩慢的苛養微生物,仍是引起血培養結果呈陰性的重要病原微生物。這些病原侵入血流可引起病程緩慢、臨床癥狀不典型的血流感染,引發血培養陰性感染性心內膜炎(blood culture-negative endocarditis,BCNE)[10]。
1.2.1 HACEK菌群 HACEK是一組由嗜血桿菌屬、放線桿菌屬、心桿菌屬、艾肯菌屬和金桿菌屬組成的革蘭陰性桿菌群,可在人口咽和上呼吸道定植,在一定條件下可引起菌血癥和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但流感嗜血桿菌很少從IE患者的血液樣本中被培養出來,通常被排除在HACEK菌群之外[11]。瑞典1項針對菌血癥患者的回顧性研究結果顯示,每年因HACEK引起的菌血癥和IE的發病率分別為5.2例/百萬和1.2例/百萬[12]。在丹麥,HACEK引起的IE占此類病例的1.4%~3.0%,其中嗜血桿菌屬感染最為常見,其次是放線桿菌和金氏桿菌感染,年發病率分別為0.16例/10萬、0.11例/10萬和0.08例/10萬[11]。適當延長血培養時間可增加HACEK的檢出率,在需氧條件下進行血培養,HACEK通常可在5 d內被檢測到,繼續延長血培養時間至>5 d并無太大意義[10,13]。傳統的培養方法對HACEK菌群的鑒定具有不確定性,采用PCR檢測血液樣本中的細菌需要設計針對各個種屬的特異性引物,而對16S rRNA基因擴增后進行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FLP)分析,可以在沒有特異性引物的情況下鑒定每種HACEK細菌,16S rRNA測序也是鑒定HACEK細菌的可靠方法,但受到成本和設備可用性的限制[14]。
1.2.2 營養變異鏈球菌 營養變異鏈球菌是一組兼性厭氧細菌,包括孿生球菌、顆粒球菌、毗鄰貧養菌,是人類口腔、生殖道、泌尿道和腸道正常菌群的一部分,一定條件下可侵入機體引起菌血癥和IE。營養變異鏈球菌感染在鏈球菌感染相關的IE病例中約占3%~5%,與其他鏈球菌相比,營養變異鏈球菌引起的IE臨床病程緩慢,且具有更高的病死率[15]。齲齒是營養變異鏈球菌進入血流的主要途徑,患者通常在發現幾個月前行牙科治療或發生齲齒[10]。營養變異鏈球菌的傳代培養需要在瓊脂中補充維生素B6或半胱氨酸,亦可在血瓊脂平板上點種金黃色葡萄球菌來支持其生長[16]。
1項回顧了12年中26例營養變異鏈球菌菌血癥病例的研究結果顯示,血培養報告陽性的時間為2~11 d,其中有7例報陽時間>5 d,超過大部分微生物實驗室進行常規血培養的時間,因此可以合理推測有其他BCNE或膿毒癥患者感染了該病原,建議實驗室將臨床醫生高度懷疑為IE患者的血培養時間延長至10 d[17]。PCR-RFLP分析、16S rRNA測序等分子技術對鑒定營養變異鏈球菌也非常有意義,且對于BCNE,離體心臟瓣膜病原體靶基因檢測的敏感性遠高于常規血培養[15]。
1.2.3 念珠菌 隨著移植手術的免疫抑制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惡性血液病和癌癥等患者的增多,非致病真菌感染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18]。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白念珠菌仍然是引起侵入性真菌感染最常見的菌種,但非白念珠菌感染的比例正逐漸上升。中國醫院侵入性真菌監測網(China Hospital Invasive Fungal Surveillance Net,CHIF-NET)的5年監測結果顯示,念珠菌菌血癥最常見的菌種是白念珠菌(32.3%),以下依次為近平滑念珠菌(28.9%)、熱帶念珠菌(17.5%)和光滑念珠菌(11.5%)[19]。
真菌感染的臨床診斷通常依靠培養和組織病理學檢查。由于血培養對血源播散性念珠菌病的敏感性<50%,且念珠菌生長緩慢,念珠菌病的治療常常會被延遲[14]。分子生物學技術可以為血培養結果為陰性的患者提供有價值的補充診斷信息,有研究利用泛真菌引物擴增18S rRNA基因的轉錄間隔區(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ITS),在100個血培養陰性樣本中檢出3個陽性結果[18]。
1.3 其他不能常規培養的病原體
伯納特立克次體(Coxiella Burnetii)、巴爾通體(Bartonella)和惠普爾滋養體(Tropheryma whipplei)是“真正的”血培養陰性病原體,現有的血培養技術尚不能對其進行常規培養和鑒定。有研究結果顯示,在引起真正BCNE的病原體中,伯納特立克次體占28%~37%,巴爾通體占12%~28%,惠普爾滋養體占6%,且都與特定的危險因素暴露或接觸史有關[20]。
1.3.1 伯納特立克次體 伯納特立克次體是引起Q熱的病原,該菌為細胞內寄生,在真核細胞中復制,體外細胞培養中的倍增時間為20~45 h[21-22]。伯納特立克次體感染范圍廣泛,從節肢動物到人類均可感染。家養反芻動物是其主要宿主,也是人類暴發疫情的主要傳染源。人類最常見的感染原因是吸入了感染動物在分娩或流產后產生的細菌氣溶膠,直接接觸受感染動物的胎盤、流產物和皮毛、糞便等也可能被感染。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該菌能在土壤中存活很長一段時間,且氣溶膠至少可以被風輸送30 km,可造成遠離主要受污染地區的Q熱,所以也可以造成近期沒有動物接觸史的人感染[21]。伯納特立克次體在實驗室常規培養技術下不能生長,當出現提示Q熱癥狀時,血清學檢測是一線診斷方法,主要檢測方法有間接免疫熒光試驗、補體固定試驗、酶聯免疫吸附試驗[21-22]。目前,基于PCR的檢測方法也已被應用于臨床樣本中伯納特立克次體的檢測。
1.3.2 巴爾通體 巴爾通體是一種細小的細胞內革蘭陰性細菌,在免疫功能良好或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中均可引起感染[22]。該菌侵入紅細胞可以逃避免疫反應,在宿主紅細胞內持續存活導致菌血癥,是巴爾通體感染的特征之一。有研究結果顯示,這種菌血癥往往是低水平的,可持續數月,甚至數年,沒有或只有亞臨床癥狀,最終可發展為IE,但這一結論尚未得到流行病學或實驗數據的驗證[4]。漢塞巴爾通體(Bartonella henselae)通常感染家貓和野貓,通過貓抓、咬或貓蚤傳播給人類,在感染HIV的患者中常會引起貓抓病、細菌性血管瘤和肝脂肪瘤。金氏巴爾通體(Bartonella quintana)則通過人虱傳播,引起戰壕熱、發熱性淋巴結病和細菌性血管瘤。金氏巴爾通體和漢塞巴爾通體是巴爾通體引起IE的2個常見菌種[4,22]。
巴爾通體感染的血培養結果通常為陰性,需要結合血清學、PCR、DNA測序和切除的心臟瓣膜組織的病理學檢查進行診斷。瓣膜組織巴爾通體DNA的PCR擴增對于巴爾通體心內膜炎診斷具有重要意義,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PCR檢測也可以采用全血、血漿或血清樣本進行,敏感性為58%,特異性為100%[4]。
1.3.3 惠普爾滋養體 惠普爾滋養體感染可引起一種不常見的慢性全身性疾病——惠普爾病(Whipple's disease),其早期表現為多關節炎、體質量減輕、貧血,隨后是腹痛、腹瀉和惡病質,體格檢查常發現淋巴結病變和色素沉著。惠普爾滋養體感染可導致BCNE,多見于男性患者;因惠普爾滋養體種系與土壤細菌相近,有學者懷疑人類經口腔途徑感染惠普爾滋養體[23-24]。有研究結果顯示,健康人的胃液、唾液以及污水樣本中均可檢測到此菌的DNA[24]。因此,惠普爾滋養體可能存在于相當一部分人群中,但不會導致其患病,其PCR檢測結果需與臨床癥狀和當地流行病學資料相結合來解釋[24]。
2 血流感染的實驗室檢測進展
傳統的血培養是將采集的血液樣本注入血培養瓶內,通過自動血培養儀進行增菌培養,當儀器監測到培養瓶內有微生物生長時,會發出報警提示,大部分陽性樣本會在3 d內報陽,實驗室技術人員將報陽樣本涂片行革蘭染色鏡檢,將鏡檢結果作為危急值報告給臨床醫生,同時轉種固體培養平板,大概需要24 h生長出純的單克隆菌落,以區分單一感染和混合感染,然后進行常規生化鑒定和藥物敏感性試驗,10~18 h獲得最終鑒定和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所以,從采集血培養樣本到發出報告,往往需要3~5 d時間。
為了縮短樣本周轉時間,盡早得到鑒定和體外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實驗室一般會通過富集陽性血培養瓶中的病原體,利用基質輔助激光解吸電離飛行時間質譜(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 MS)和熒光原位雜交技術(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進行細菌鑒定。MALDI-TOF MS用于病原菌鑒定在我國各級醫療機構臨床微生物實驗室已廣泛開發,但對混合感染的鑒定仍存在困難[25]。PNA-FISH通過模擬DNA探針與病原內的16S rRNA序列和酵母菌內的18S rRNA序列進行快速、特異的雜交,用于鑒定最常見的革蘭陽性菌、革蘭陰性菌和念珠菌。因可用的PNA-FISH探針數量有限,且富集的菌量至少為105CFU/mL,限制了其臨床使用[26]。Accelerate Pheno系統使用自動樣品制備和細菌固定化方法,以顯微鏡鏡檢為基礎,利用FISH探針進行單細胞分析來進行細菌鑒定和藥物敏感性試驗,已經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認證,并在歐美等國家應用[27]。
上述新技術的使用縮短了樣本周轉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血培養的臨床應用價值,但前提必須是血培養陽性。對于血培養陰性的樣本,目前只能依賴血清學和分子生物學技術進行檢測。
2.1 血清學檢測
血清抗體檢測是診斷感染的經典方法,急性期和恢復期血清抗體滴度呈4倍及以上上升是診斷感染的金標準[16]。在血培養結果呈陰性的情況下,血清學抗體檢測是感染診斷的有效補充。2項評估BCNE血清學檢測的研究結果顯示,1 093例患者中有624例可通過血清學檢測診斷[20]。有研究結果顯示,當存在危險因素(生活在流行地區、職業接觸、食用未經巴氏殺菌的乳制品)暴露時,可增加布魯菌病血清學檢測[10],但不建議對軍團菌、支原體和衣原體常規進行血清學檢測[20]。
人感染伯納特立克次體時,免疫反應會誘導機體產生Ⅰ相抗體和Ⅱ相抗體。Ⅱ相抗體可在臨床癥狀出現后7~15 d被檢測到,在3~6個月內下降,檢測間隔3~6周采集的2份血清樣本的Ⅱ相抗體滴度IgG或IgM增長4倍以上可診斷為原發性感染,Ⅱ相抗體滴度IgG≥200和/或IgM≥50對原發性感染亦有重要的診斷價值。Ⅰ相抗體滴度IgG≥800則與慢性Q熱有關,且與伯納特立克次體IE陽性預測值高度相關[21]。然而,1項比較了來自英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的3個醫療機構Q熱病例血清學檢測結果的研究發現,3個醫療機構對結果判讀的一致性只有35%[21]。這反映了血清學雖然是伯納特立克次體病原體的首要診斷技術,但因其解釋的主觀性,尚無法形成統一的判定標準。
巴爾通體也可通過血清學方法診斷,抗體滴度>800提示與IE相關,陽性預測值為95%,但抗體滴度<800并不能排除心內膜炎[16]。值得注意的是,衣原體和巴爾通體存在交叉反應,當血清學診斷懷疑衣原體感染時,應重新評估以排除巴爾通體感染[10,16]。
2.2 病原16S rRNA檢測
鑒于病原體培養成本高、產量低和周轉慢的特點,全血樣本核酸擴增成為血培養方法的有益補充,可以檢測血培養遺漏的微生物,并縮短病原鑒定的時間,有較大的臨床價值。然而由于其高敏感性和可能存在的污染風險,應謹慎解釋陽性結果,且檢測結果需與臨床診斷相符[28-29]。
病原16S rRNA檢測可作為臨床懷疑血流感染,但血培養陰性患者的補充檢查。有學者利用16S rRNA檢測101例重癥患者血液樣本,檢出了血培養遺漏的至少6個陽性結果,比使用常規血培養更為敏感[30]。由于采用的是16S rRNA通用擴增引物,病原體不能被鑒定到種,須使用特定細菌的特異性引物來進一步鑒定可疑的病原微生物[20]。有研究用質譜技術測定每個PCR擴增片段的質量,計算核苷酸堿基組成,并與數據庫進行比對,實現了病原菌的鑒定,這種廣譜PCR和電噴霧電離串聯質譜(electrospray ionization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ESI-MS)相結合的方法可以完成病原微生物的鑒定[31]。1項回顧性研究結果顯示,PCR/ESI-MS與血培養結果的符合率為85.7%[32]。
2.3 實時PCR
實時PCR是在PCR反應體系中加入熒光標記探針,利用熒光信號積累實時檢測整個PCR進程,最后通過標準曲線對未知模板進行定量的方法。有研究結果顯示,實時PCR使BCNE患者血液中病原體的診斷效率提高了24.3%,新檢出的病原體主要包括腸球菌、鏈球菌、人型支原體和惠普爾滋養體[28]。
以IS1111為靶點的特異性實時熒光PCR被認為是臨床樣本中伯納特立克次體最敏感的檢測方法,可在感染伯納特立克次體2周內、血清抗體尚未呈陽性時檢出患者血液中的伯納特立克次體。另外,采用凍干法濃縮從臨床樣本中提取的DNA,能夠進一步提高該檢測方法的敏感性,在原發性Q熱患者中,凍干法處理可使實時熒光PCR對血清學檢測陰性樣本的敏感性提高44%,對早期血清學檢測陽性樣本的敏感性提高30%[21]。
2.4 多重PCR
多重PCR又稱多重引物PCR或復合PCR,是在同一PCR反應體系加入2對以上的引物,同時擴增出多個核酸片段的PCR技術。
FilmArray系統采用巢式多重PCR技術,集樣品制備、擴增、檢測和分析于一體。可檢測血流感染相關的24種病原體靶標和3種抗菌藥物耐藥基因,雖然目前大部分相關研究集中在對于血培養瓶報陽后的檢測,但對血培養陰性的樣本,仍有一定的實用價值[33]。由于巢式PCR的高靈敏性,不能排除環境或血液樣本中存在病原體核酸而出現假陽性結果。曾經出現的腸球菌和銅綠假單胞菌假陽性結果,以及目前依舊存在的變形桿菌假陽性問題,均提示巢式PCR擴增陽性血培養液核酸靶標的局限性[34]。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于2017年批準了相對較新的革蘭陽性球菌iCubate系統(IC-GPC),該系統是基于熒光信號檢測的多重PCR和微陣列雜交,除肺炎鏈球菌外,所有目標菌鑒定和耐藥基因檢測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均>95%[34]。
2.5 NGS
基于PCR的檢測方法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的先驗信息,但這些信息并不總是存在。對于未知樣本或新的病原體,無偏移的DNA測序顯然更高效。傳統的測序方法不適用于混合物的分析,且成本高、耗時長,而NGS不僅能以高靈敏度和高通量對異質混合的遺傳物質進行測序,還能同時獲取藥物敏感性信息,為在沒有任何先驗信息情況下進行全面的病原體檢測帶來了希望。然而全血樣本中病原體DNA的含量通常較低,宿主DNA與病原體DNA的比值常高達108∶1,因此將NGS直接應用于全血樣本的病原體檢測仍具有挑戰性。近期有研究報道了快速消耗全血樣本中的人類DNA,并使細菌DNA富集的方法,使菌血癥的快速診斷成為可能[35]。
3 總結與展望
機體屏障功能的完整性受到破壞和機體免疫力下降均是導致血流感染發生的危險因素,血流感染引起的膿毒癥是住院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通過持續監測患者的臨床癥狀、生命體征、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水平和降鈣素原水平等,可初步判斷是否發生血流感染。但進行血培養獲得病原體信息依舊是診斷細菌性血流感染最重要的證據,也可以為臨床抗感染治療提供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
目前,在診斷血流感染以及進行后續抗感染治療過程中依舊存在諸多問題。(1)感染的診斷是否成立。由于手術、藥物、腫瘤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都會引發與血流感染類似的癥狀和體征,所以獲得明確的病原體信息顯得尤為重要,但能夠明確病原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進行的常規血培養陽性率不足20%,所以很多學者在探索如何進一步提高陽性病原的檢出率。(2)提供靶向抗感染治療信息的及時性。早期、足量的靶向抗感染治療不僅能改善患者預后,降低病死率,也可以減少患者住院時間和醫療成本。但進行體外藥物敏感性試驗必須采用活的病原體,而病原體的生長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很多學者在探索如何富集足量的細菌來進行早期的體外藥物敏感試驗,以提示臨床進行早期的干預治療[25]。(3)由于血流感染的診斷和治療涉及到機體、病原和抗感染藥物使用等方面,且目前采用的診斷技術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進行不斷的探索和優化,包括質譜技術、NGS的應用指征及結果解釋。
除上述主流技術外,基于快速聲學分離和富集的微芯片PCR檢測系統[36]、基于無標記抗體微陣列的離子共振成像系統[37]、基于大小識別而無標記的彈性慣性微流控技術[38],以及T2磁共振技術等[34]快速檢測血液中病原微生物的新技術給血流感染的快速病原學診斷帶來了新的希望。T2磁共振技術是將病原體特異性DNA進行PCR擴增,然后將擴增產物與探針修飾的超順磁性納米顆粒雜交,雜交后會使納米顆粒聚集,通過T2MR誘導檢測信號的變化來檢測目的片段。為提高血流感染的診斷效率,在致力于開發、優化更為有效的技術的同時,也需進一步對感染的發生、發展,以及體內播散機制進行研究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