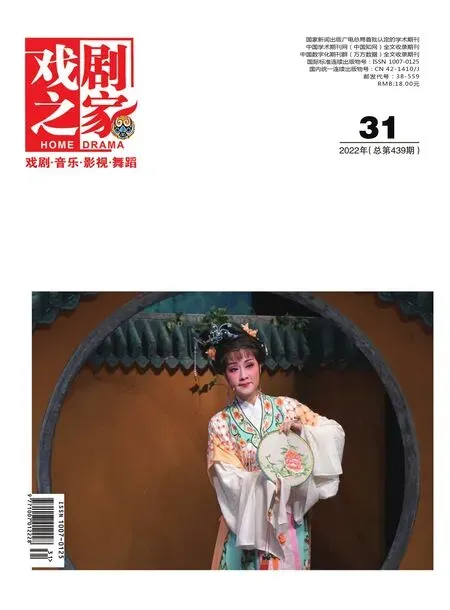“瀟湘夜雨”急千里
——元代“瀟湘夜雨”詩詞的文化內涵與情感特色
陳素萍
(湖南科技學院 文法學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根和魂,地域文化則是特定區域的生態、傳統、民俗的表現,一般都獨具特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雖時光流轉,物是人非,但我們依然可以在古人描寫風景的詩詞當中領略彼時風景的神韻。山水風景常被我國古代文人墨客青睞,以至于很多不知名的風景都是因為他們的吟詠描繪而名滿天下,比如崔顥的《黃鶴樓》,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等。
一、宋元“瀟湘八景”詩詞概述
湖南省的風景名勝除了上述提到的岳陽樓和鄰近的洞庭湖、君山島外,常被大家提起的還有岳麓書院、橘子洲、回雁峰、南岳衡山等,但這與古代的湖南風景定位存在一定差異。古人熟悉的湖南風景主要是“瀟湘八景”。“瀟湘”是湖南的代名詞,“瀟湘八景”一般是指坐落在湖南省境內的八處盛景。具體而言,是指永州城北瀟湘匯合處的萍洲、衡陽回雁峰、衡山城北清涼寺、湘潭與長沙接壤處的昭山、橘子洲、湘陰縣城江邊、洞庭湖以及桃花源對岸的白鱗洲等處風景。“瀟湘八景”的聞名得益于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當中的總結,他分別為這八處風景起了極為雅致的名稱,即瀟湘夜雨、平沙落雁、煙寺晚鐘、山市晴嵐、江天暮雪、遠浦帆歸、洞庭秋月和漁村落照。這些優雅的名字很好地凸顯了每處景觀的風景特點,極具文化氣息。文化與景色相互襯托,相得益彰。自此,“瀟湘八景”受到諸多文人墨客的關注和喜愛。
一般來講,人們在欣賞美景時會產生一系列情緒,古代文人習慣用詩詞的方式來寫景狀物、抒情言志。自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確立“瀟湘八景”的地位之后,諸多文人不吝筆墨,爭相描摹“瀟湘八景”,比如宋代詩人劉克莊的“詠瀟湘八景各一首”,分別對“瀟湘八景”的不同景觀進行了吟詠。類似的還有宋代詩人楊公遠、張經等人的創作,此類作品統稱為“瀟湘八景”詩詞。這些詩詞多姿多彩,各具特色,寄寓了作者不同的情思,蘊含著多樣的文化意蘊。文人對“瀟湘八景”的追捧并不局限于宋代,就算到了元代乃至明清,依然還有大量借“瀟湘八景”以寄情的作品。
二、元代“瀟湘夜雨”詩詞的文化內涵
與唐宋相比,元代詩詞文化已趨于沒落,但元代依然涌現出諸多詩詞作品,只是,在唐宋詩詞的籠罩下,這些作品的光彩偏于黯淡而已。“瀟湘八景”組詩詩題眾多,其中,“瀟湘夜雨”景觀位于瀟湘故里的萍洲島上,領受了瀟湘二水攜來的九嶷靈氣,其風景清麗淡雅;碰上瀟瀟夜雨,變得格外蒼茫幽遠;再融進舜帝、二妃、柳子、宋迪等人的悲傷憂愁,“瀟湘夜雨”在歷史的長河中慢慢發酵,被賦予萬種深情,終成“瀟湘八景”之首。本文以元代“瀟湘夜雨”詩題為例,以點帶面,對元代“瀟湘八景”詩詞的文化內涵進行解析。
(一)四面烘托,身臨其境
當今時代,3D、4D、5D 技術可以讓我們獲得強烈的逼真感。但在古代,就算沒有電子技術,詩詞語言也同樣能夠使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元代學者陳孚曾對“瀟湘八景”進行簡單而又全面的描繪,讓人如同置身其中。下面我們就來感受作者是如何運用簡短的語言彰顯詩詞的魅力的。
瀟湘八景 其四 瀟湘夜雨
昭潭黑云起,橘洲風捲沙。亂雨灑篷急,驚墮檣上鴉。
黿鼉互出沒,暗浪鳴櫓牙。漁燈半明滅,濕光穿蘆花。
此詩僅40 字,卻描述了云、風、沙、雨、篷、墻、鴉、黿、鼉、浪、櫓、漁燈、蘆花等諸多景和物,還分別凸顯了不同景物的特點,并用它們共同呈現瀟湘夜雨的狀貌。起筆寫云、風、沙從“昭潭”和“橘洲”急卷而來,暗示了“八景”之間的聯系;用“黑”和“捲”兩字預示疾風驟雨即將來臨,讓人有窒息之感。接著正面寫雨,用“亂”和“急”凸顯雨勢之大,甚至驚落了桅桿上的烏鴉,也急壞了讀者的心。在風急雨猛的攻勢下,黿鼉不再出沒,湖中暗浪不斷擊打檣櫓。漁燈忽明忽暗,照射出夜晚的濕氣。作者從眼前景象出發寫瀟湘夜雨,讓人分不清哪些是實,哪些是虛,只覺得仿佛這些景物就在自己的眼前,令人感到恍惚迷離,又似身入其境,真實無比。
(二)寓情于景,悲苦離愁
離別自古就是文人喜愛的主題,元代詩詞也對此主題多有延續。“秋思之祖”馬致遠創作了《天凈沙·秋思》,通過描繪一幅凄涼蕭瑟的秋郊夕照圖傳達了游子的羈愁旅思。他還創作了《瀟湘八景》,其中的《瀟湘夜雨》表達了他的離愁之苦。
壽陽曲·瀟湘夜雨
漁燈暗,客夢回,一聲聲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萬里,是離人幾行清淚。
初看此詞,我們可能覺得內容疏于景色描繪,偏離了“瀟湘夜雨”,其實不然。作者雖沒有具體描述景色,卻把握了瀟湘夜雨的核心,即“瀟湘”本身所暗含的離愁別緒——其源頭便是娥皇、女英與舜帝的千古離愁。作者以“漁燈暗”開頭,奠定了全詞的感傷基調,也為后面的“家萬里”和“清淚”埋下伏筆。漁燈夜晚,五更夢回,聽到雨聲滴落,作者心碎落淚。“一聲聲”明指下雨,恰好契合“瀟湘夜雨”詩題,同時,也可與后兩句一起暗指。“孤舟五更家萬里”,深夜的自己孤身寄居于一葉扁舟,感慨離家萬里之遙,生出許多悲傷,故而幾行清淚潸然而下。和著淚再次睡下,也許夢中聽到一聲聲呼喚,或是家人的,或是自己的。作者采用寓情于景的方式,較為隱晦地表達了自己客居他鄉時對家人的思念之情和離別之苦。
(三)借景寫事,抨擊時政
古人寫諷刺題材的詩詞并不少,但將諷刺融合在景物中的詩詞并不多,貝瓊是其中之一。貝瓊生于元,卒于明,曾跟隨楊維楨學詩,但他能獨立思考、取長補短,這使得他的詩詞能獨領風騷。他的《瀟湘夜雨》讓我們感受到作者的抱負,以及對于時政的反思。
題誠道原瀟湘八景 其一 瀟湘夜雨
江空夜如何,急雨千里灑。水生黃陵廟,云暗蒼梧野。
鼓瑟來湘靈,移舟近漁者。重華不可見,竹上淚如寫。
此詩首聯“江空夜如何”以提問開篇,用“急雨千里灑”回答,說明此時正下著瓢潑大雨,同時暗合詩眼“夜雨”。頷聯寫景,遠處的黃陵廟快要被大雨浸沒,整片的荒野幾乎被烏云遮蔽,再次說明雨勢很大,“黃陵廟”“蒼梧野”都位于湖南境內,也暗合了詩眼“瀟湘”。頸聯寫“湘靈鼓瑟”,出自屈原《楚辭·遠游》“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湘靈”即舜帝二妃,“舜帝南巡,崩于蒼梧之野”,二妃追隨而來未能相見,投水自盡,變成了“湘靈”,常在江邊鼓瑟表達哀思。詩中作者也如湘靈追尋舜帝一樣找尋著,甚至劃動船只接近漁舟,只想得償所愿。但尾聯說“重華不可見”,重華就是舜帝,舜姓姚,名重華。此處是借二妃尋舜不遇喻明君難見。“竹上淚如寫”接續前面,二妃尋舜不遇,慟哭遠望,淚灑湘竹,斑痕難滅,遂成“斑竹”,此處借湘靈之淚痕寓詩人之傷痕。“竹”還代指丹青,即史書,“竹上淚”說明此時的史書都是血淚,百姓生活艱難困窮,文人志士報國無門。這首詩表面是在寫景,寫夜空暗云、傾盆急雨,其實是在描述時政,表明當時社會的黑暗和動蕩。這首詩表達了作者對時局的看法、對百姓的關懷、對明君的期待,還表達著自己的失望、無奈與憤懣。
(四)蒼茫大地,終歸平凡
詩詞雖然只是簡短的文字,表達作者的思想認知卻極具穿透力,能讓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人生體味。元代文學家揭奚斯精通經史百家,還擅長作詩,語言簡潔而又恰到好處。下面通過他的《瀟湘夜雨》來分析作者的心路歷程。
瀟湘夜雨
涔涔湘江樹,荒荒楚天路,穩系渡頭船,莫教流下去。
此詩用“涔涔”開頭,“涔涔”指的是汗水、淚水、雨水等往下流。結合語境,湘江路上的“涔涔”表示的是雨水往下流。次句“荒荒楚天路”,此處作者沒有像前述幾位作者一樣重點描述雨勢之大和雨勢之急,而是寫此時的天地仿佛都沉浸在一片細雨之中,將這瀟湘夜雨表述得極具詩意和美感。“穩系渡頭船,莫教流下去”,則是從寫景轉到寫事、寫人,漁者將船穩穩地系在渡邊,避免讓它被水沖走;仿佛說人也要有一種執拗,那就是不能夠隨波逐流、墮落沉淪。簡單的描寫卻意境悠遠,讓人產生一種蒼茫荒涼之感,既慨嘆天地之遼闊,又需要認清現實,回歸平凡。
三、元代“瀟湘夜雨”詩詞的情感特色
王國維《人間詞話》云:“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瀟湘八景詩詞無疑是以“景語”為主,但誠如王國維所言,“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只是在表現方式上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隱或顯,皆不脫一個“情”字。需要強調的是,元代文人借瀟湘八景所表現的“情”,似乎更深沉、急切,甚至危機四伏。
首先,元代文人所描寫的“瀟湘夜雨”,其夜色更深沉,其雨勢更急切而遼闊。從陳孚的“昭潭黑云起,橘洲風捲沙”,到貝瓊的“江空夜如何,急雨千里灑。水生黃陵廟,云暗蒼梧野”,再到揭奚斯的“涔涔湘江樹,荒荒楚天路”,這遼闊江天的疾風驟雨,定然不是詩人眼見的“實景”,而是心底蘊含的“實情”。從“實景”而言,詩人站在瀟湘匯合處的萍洲,怎能看見“昭潭黑云”“橘洲風沙”?更難見黃陵廟的“水生”、蒼梧野的“云暗”。“眼”不能見,但“心”則可望,詩人可以借心底所想的“虛景”來表達心之所愿的“實情”。因此,元代詩人寫夜色的深沉、雨勢的急切,正是在表現他們當時的心境。
要了解元代詩人異樣的心境,陳孚的《詠永州》或許可以作為參照:
燒痕慘淡帶昏鴉,數盡寒梅未見花。回雁峰南三百里,捕蛇說里數千家。
澄江繞郭聞漁唱,怪石堆庭見吏衙。昔日愚溪何自苦,永州猶未見天涯。
元代詩人陳孚曾出使安南(今越南),此詩是他路過永州時所作。《元史》稱他“天才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為詩文,大抵援筆即成,不事雕斫”。他詩風簡淡,不事雕琢,《詠永州》正是這種風格。尤為重要的是,詩中對柳宗元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永州并非地遠天荒之處,甚或還有“澄江繞郭聞漁唱,怪石堆庭見吏衙”的美景,柳宗元在這樣的地方生活,還何必覺得“自苦”呢?!陳孚之所以如此批評柳宗元,一是因為他到過更遠的地方——安南,因而“永州猶未見天涯”;二是因為陳孚遭受了更為不公正的待遇。當時蒙古統治者實行民族歧視政策,他們把自己統治下的人分為四個等級,依次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陳孚是南人,當然不能重用。陳孚的這種待遇,可說是元代詩人的代表,這就是他們所描寫的“瀟湘夜雨”之所以夜色更深沉、雨勢更急切的心理基礎。
其次,元代文人寫“瀟湘夜雨”甚或給人以危機四伏之感。從“亂雨灑篷急,驚墮檣上鴉”,到“孤舟五更家萬里”,再到“穩系渡頭船,莫教流下去”,無不使人感覺到詩人所處的環境已是岌岌可危。試想,“亂雨”之急,連棲息在桅桿上的烏鴉都被打落,棲息在船上的人能不危險?那“渡頭”的一葉“孤舟”,在暴風驟雨中飄搖,船上的人雖然急切地想要“穩系”,但在這天低云暗的“五更”時節,怎能輕易找到“穩系”之處?因此,不管船上之人是如何地叫喊“莫教流下去”,但“急雨千里灑”所形成的激流,似乎正要將這一葉孤舟帶向“荒荒楚天路”,這陣勢是多么危急而又無可奈何,簡直給人一種絕望之感!
元代文人的這種“絕望”因何而起?因“重華不可見,竹上淚如寫”。堯舜是中國文人的希望所在,堯舜之道是中國文化的根脈所在。對中國文人而言,不擔心“亡國”,但最擔心“亡天下”——“亡國”只是改朝換代,一個新王朝的建立沒準還能帶來太平盛世;“亡天下”不僅意味著天下大亂,還意味著堯舜之道的失傳,文化根脈的中斷。有元一代,正是這種“亡天下”的時代,科舉制度被廢,堯舜之道被棄,中國的傳統文化幾近斷絕,僅有少數文人通過雜劇的形式斷斷續續地傳承著文化根脈。因此,“重華不可見,竹上淚如寫”,正是元代“亡天下”真實情況的寫照,那竹上之淚,不僅是娥皇、女英的,更是元代全體文人的。誠如是,元代文人面對“瀟湘夜雨”之景所表現出來的情感,才會那樣地深沉、慘痛乃至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