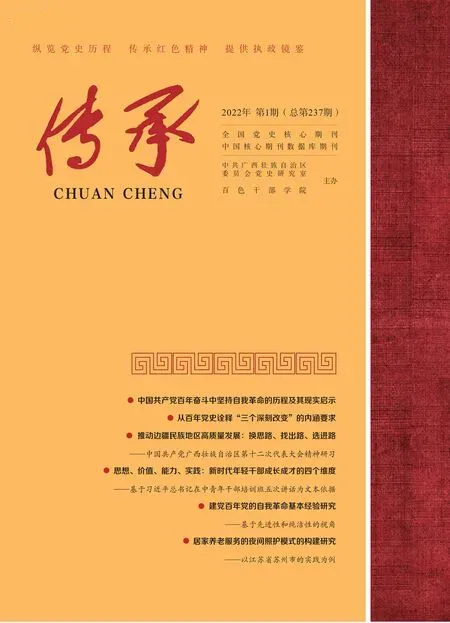中央紅軍在西延山區實現戰略轉向的實證研究
——以社嶺村、蟆嶺村、白竹寨、岔嶺村為中心
□ 藍 珊,楊明智,張玉棟
廣西師范大學,廣西 桂林 541004
湘江戰役距離遵義會議召開一個多月,湘江戰役后黨的軍事路線發生改變,以及一系列會議的召開,使中共中央逐漸從“左”傾教條主義影響下擺脫出來,開始實現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轉變。目前的研究較多關注湘江戰役的突圍狀況、遵義會議的作用,而對湘江戰役后紅軍的路線走向以及轉折過程的研究非常薄弱,現有的軍史史料與著作對紅軍長征在西延山區實現戰略轉向的記載較少,部分記載也存在一些分歧,非常需要深入研究、深化認識。
社嶺村、蟆嶺村、白竹寨、岔嶺村是中央紅軍長征在西延山區實現戰略轉向的必經之地,廣西師范大學“湘江戰役研究”課題組通過重走境內長征路段,對沿途村鎮知情老人、村民等進行調查采訪,親臨紅軍烈士墓地察看等,獲得從未被挖掘的口述、影像、圖片等第一手資料。文章以文獻解讀、田野調查、口述采訪等方式,將紅軍在西延山區進行戰略轉向路線的文獻資料、遺址遺存、親歷者后代口述三者進行相互印證和補充。通過三者互證,證實遺址遺存和口述材料的真實性與有效性。許多親歷者已過世,此次研究訪問了親歷者的后人,及時搶救了口述資料。但由于洪災等自然因素的影響,部分埋葬紅軍的墓冢被沖毀,未能及時搶救,由此也說明現有歷史材料的珍貴。
一、中央紅軍長征在西延山區實現戰略轉向始末
文獻資料調查是研究的基礎。根據文獻資料,首先對中央紅軍經過西延山區的歷史進行簡單回顧。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被迫作出退出中央根據地的決定,計劃沿紅六軍團西進路線向西實行戰略轉移,到湘鄂西同紅三軍和紅六軍團會合[1]。
紅六軍團作為長征先遣隊,在1934年9月4日渡過湘江,5日進入西延山區[2]8。隊伍經油榨坪、大埠頭(今資源縣城)、車田鄉,向西北方向的湖南省城步縣行軍。紅六軍團作為長征先遣隊,在9月4日渡過湘江,5日進入西延山區[2]8。隊伍經油榨坪、大埠頭、車田鄉,向西北方向的湖南省城步縣行軍。同年12月1日中央紅軍主力渡過湘江[2]27,進入西延山區[3]189。形成以紅三軍團、紅八軍團為左翼,形成以紅一軍團、紅九軍團為右翼的部署,多路翻越越城嶺[4]24。
朱德于1934年12月1日17時發電文“我野戰軍于二號早應進到西延地域,整理部隊……一、二縱隊明二日早進到西延(胡嶺)地域,并向大榕江口、城步及新寧方向警戒”[5],紅軍中央軍委縱隊原計劃在西延山區油榨坪休整,再沿紅六軍團路線向西北方向行軍。
在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后,蔣介石絲毫未有放松剿滅中央紅軍的戰略考量。他判斷中央紅軍仍將沿著紅六軍團先遣隊從大埠頭經車田鄉出湖南城步,北出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遂急忙調整部署,企圖圍殲紅軍于北進湘西的途中。1934年12月1日,電文《何鍵關于速向湘桂邊區轉移向劉建緒薛岳發布的命令》明確指出“我軍以繼續截剿之目的,迅速向新寧、城步、綏寧、靖縣方面轉移”[6]468,“追剿總司令”何鍵[7]220令第一、第二兵團15個師,在北面湖南新寧、城步、綏寧、武岡堵截紅軍,配合桂軍完成前堵后追口袋布陣。
而紅軍曾在大帽嶺之戰中,因楊得志指揮的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在大帽嶺與國民黨湘軍發生戰斗,得知國民黨軍正在湘桂邊境修筑大量戰壕、碉堡等工事,據情報,蔣介石已經調動了5倍于紅軍的強大兵力集中在新寧、城步一帶,形成了一個大口袋,如果再堅持北出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無疑就是將紅軍往虎口里送,根據《朱德對三十四師與主力會合路線和發展游擊戰爭的指示》電令表示“桂敵正向西移,興安之南西進之路較少”(4)資源來源于2016年中共桂林市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湘江戰役文集》第65頁。,得知敵人在西南方向兵力較為薄弱這一形勢,加上先前灌陽新圩阻擊戰、光華鋪阻擊戰、覺山阻擊戰中央紅軍損失慘重的教訓,中央軍委對于“中央紅軍繼續走蕭克等率領紅六軍團西征的老路硬闖湘江,還是走別的路”[2]17的爭論逐漸明晰。1934年12月3日,紅軍主力部隊在油榨坪休整之時,中央軍委召開油榨坪會議,據考證,周恩來、博古、李德、朱德、王稼祥等參加[4]25。經綜合分析,中央軍委決定改變沿著紅六軍團向西北即從西延大埠頭經五排車田到湖南城步的原定路線,于當日16時發電文確定紅軍主力在西延山區的行進轉向,原計劃行軍方向為西北,現行軍方向為西南“北經小李、西山嶺、社水、皮水隘向龍勝以北,南經楓木山、廣塘、千家寺、中洞向龍勝及中間由楓木山經塘坊邊、兩渡橋西進的諸道路”[8],由此,中央紅軍在西延山區的戰略轉向路線已確定,這是中央紅軍第一次改變沿著紅六軍團先遣隊路線行進的嘗試。
1934年12月3日16時電報發出后,中央紅軍在西延山區轉向行進。12月4日,軍委一縱隊經蟆嶺村、塘坊,翻越老山界。二縱隊兵分兩路,一路經蔣家山到煙竹坪,另一路經龍獅底到四山田。紅五軍團到達楓木山。紅八軍團在馬嶺村兵分兩路,一路經岔嶺到高寨,另一路經陽鳥江到達陽火坪。12月5—6日,軍委一、二縱隊相繼成功翻越老山界,由塘洞抵達龍勝江底,只有一、九軍團進入城步縣、蓬洞一帶警戒[4]109-110,進行運動防御,滯緩敵軍向南進攻。12月8日,后衛紅五、八軍團到達塘洞后,與桂軍四十三師的一個團發生激戰,以掩護在龍勝江底休息的軍委一縱隊,因山路崎嶇,山高林密,桂軍不敢逼近,當日晚除了紅五軍團三十七團留下警戒,其余全部離開資源抵達龍勝江底[4]111。
12月3日,何鍵致劉建緒、薛岳電文命令中偵查到紅軍方面“匪殘部由咸水、西延、車田、蓬洞,循蕭匪故道,向西急竄。其一部似分向龍勝竄走”,于是派“第一兵團劉總指揮即以一部尾匪追剿,主力經新寧、城步間覓匪”,第二兵團由武岡經竹江州“截擊西竄之匪,兵堵匪北竄,以一部策應第一兵團”[3]199。國民黨軍隊仍將圍剿主力分布在新寧、城步一帶。
根據12月5日《湘軍劉總指揮建緒歌戌電》電文“據報:支日,偽一軍團殘部竄抵車田,有向綏寧、通道西逃之勢。又,偽三、五、八、九軍團未經大埠頭,似向龍勝方向潰走”[6]485,國民黨軍此時發現紅軍軍委縱隊未按照紅六軍團路線行軍,《追剿軍總部微亥電》寫到“匪大部由西南之廣唐、雷霹州、越貓兒山土岡嶺,向龍勝西竄”[3]201,12月6日《何總司令鍵答復桂白道歉微辰電》中表示“承兄迭電囑我向南延伸,亦以時間、兵力而(兩)不許可之故,致留此一線之隙未能彌縫,竟使殘匪竄脫”[3]201。紅軍主力部隊行軍路線的轉向,正是利用國軍和桂軍縫隙行軍,使國民黨軍向南調兵不及。
12月7日,根據《命令十二月七日午后八時于梅口第一路司令部》[6]606“匪一部由車田向綏寧、通道北竄,其主力或由龍勝北竄,或入黔省,企圖不明”,紅軍的突然轉向,成功迷惑了敵軍,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堵截計劃。8日,根據《何鍵關于防堵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向劉建緒、薛岳發布的命令》電文判斷紅軍“似有沿湘、桂邊境西竄貴州之企圖。我桂軍刻正以夏軍由西延繼續追剿,以廖軍經龍勝、古宜進出通道”,國民黨軍隊兵分多路對紅軍進行圍剿,將軍隊主力集結于綏寧附近,向南覓匪截擊,其中一路防止紅軍縱隊北上“第一兵團應以一部位置于城步附近堵剿北竄殘匪”,另外一路“第二兵團著經由洪江迅速進出會同、靖縣,向通道方面覓匪截擊,并督修所任地區內之碉堡線”[6]496。由于紅軍靈活機動的戰略轉向,使得國民黨方面對中央紅軍軍委縱隊主力的行進方向判斷失誤。中央紅軍成功避開敵人主力,搶占時機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西南方向突擊,使得敵人陷入被動追剿的局面。
中央紅軍開辟新的西進路線,機警靈活的戰略布局,使得敵軍無法準確預知紅軍軍委縱隊的行進方向,敵軍既要防止中央紅軍沿著紅六軍團先遣隊路線北上,又要防止紅軍改變路線向貴州方向前進,兵分多路對紅軍進行圍剿。中央紅軍的這一戰略轉向決定,既分散了敵人的兵力,也分散了紅軍對抗敵人的壓力。
中央紅軍部隊在西延山區實現轉向,轉向路線由楓木山,經社嶺村、蟆嶺村,白竹寨、岔嶺村落路段前往華江銳偉、千家寺一帶,進入原始森林中,翻越越城嶺主峰老山界,向龍勝江底方向西進,果斷決定放棄沿著紅六軍團先遣隊路線從西延出湖南城步的打算,擺脫優勢敵軍圍追堵截的被動局面,使中央紅軍奪取戰略轉移的主動權,避免鉆入國民黨軍布好的口袋陣,從而遭受全軍覆滅的厄運。
二、以村寨為中心對戰略轉向過程進行實證研究
廣西師范大學作為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湘江戰役研究”的承擔單位,以資源縣村寨為中心進行調查,收集當年紅軍在西延山區的長征路線的歷史資料。通過對韋斯門(廣西師范大學選派社嶺村駐村書記)、梁基保(救助紅軍親歷者的后人)、梁基發(白竹寨生產隊隊長)、趙清明(社嶺村原黨支書)、趙明昆(岔嶺村原黨支書)進行口述采訪,獲得一些珍貴的口述資料和文物資料。
(一)社嶺村
紅軍進入西延山區后,從楓木山經社嶺村、蟆嶺村、白竹寨,前往華江、千家寺方向。白竹寨村民梁基保根據其父親和爺爺的口述,“紅軍是在一個下雨又下雪的冬天晚上到,當時來了很多人,在山坳里打著火把”。
(二)蟆嶺村
紅軍經過蟆嶺村時,村民楊老檢曾給紅軍帶路,有一條通往白竹寨的鄉路途經楊老檢家門口。楊老檢家原是木房建構,用石頭堆砌出門房地基。目前房子遺留最大的地基大約長0.4米,寬0.3米,高5米。可見,通過丈量地基得知,楊老檢家大概有120平方米,房子下方是一片田地,挖有排水道。后來政府開辟了新的水泥道路通往白竹寨,原鄉路已荒廢。
(三)白竹寨
1934年間白竹寨共有5戶人家,紅軍在白竹寨前進時正好經過梁基保爺爺的家,有一個連隊留宿在此,曾將3匹馬拴在梁基保爺爺家的梨子樹前,1匹紅馬、2匹黃馬。目前,梁基保爺爺家的房子地基上尚存在,但拴馬的梨樹被砍掉了。
據梁基保回憶,“我爺爺帶著我父親在通往華江方向的路上埋葬了3個犧牲了的紅軍”。這一段史實是梁基保聽其父親梁丕遠口述。白竹寨生產隊原隊長梁基發回憶父輩傳下來的故事補充說:“這3個犧牲的紅軍是因為受傷掉隊而犧牲的。紅軍留宿在老百姓家里,在屋堂空地睡稻草,不驚動老百姓。”百姓們自發地埋葬已經犧牲的紅軍烈士,但墓冢已被洪水沖走了。
梁基保的外公彭哲文救助了1名受傷的紅軍,“時間大致是在1934年冬天,受傷的紅軍大概20歲,在我外公家大概住了一年。他把傷養好以后,本來想找部隊會合,結果被人告密,告密者是大莊田村人。國民黨政府知道后,派人把剛養好傷的紅軍推到矮山底下,尸體至今沒有找到。新中國成立后告密者被共產黨槍斃了,還抓了一個土豪(村長)的小老婆,這個人曾經幫國民黨抓了很多壯丁,后也被槍斃了。這個村新中國成立前有70人,現在白竹寨有200人左右。”
(四)岔嶺村
據岔嶺村黨支書趙明昆介紹,岔嶺,土名雙八祖,現在還遺存著紅軍打仗的工事。這是村民原本建造的防御工事,后來成為紅軍阻擊國民黨軍的陣地,工事前方的坳底還埋葬著兩個犧牲的紅軍烈士。
趙明昆介紹,“從這里到老山界,翻越貓兒山,大概有5公里路程。以前有3兄弟從湖南移民到這里發家,逐漸發展到現在有50人。湘江戰役期間,這個村有十幾戶人家。住在這個地方的紅軍有二三十人。紅軍來打仗之前,叫老百姓帶著小孩去山里躲,紅軍在寨子里住,房屋未受到破壞”。
在調研的路途中調研組成員體驗到紅軍在西延山區行軍過程經歷的山勢險峻,道路崎嶇,其中途徑幾近90度的陡壁,陡壁下方是山谷深淵,可知紅軍長征過西延山區的艱難與艱險。
本次一共調研了8處紅軍長征經過的有關遺址,即社嶺村山坳小道、楊老檢家地基、蟆嶺河木橋石基、梁基保爺爺家的地基、金雞嶺埋葬紅軍地、梁基保外公彭哲文家的山頭、岔嶺村防御工事和趙明昆家。證實紅軍經過瑤區的5戶人家,即梁基保外公彭哲文家、梁基保爺爺家、趙明昆家、趙明昆哥哥家、趙明昆奶奶家。紅軍過西延山區的歷史,是通過父輩與子輩有直系血緣關系的人口口相傳下來,受訪者記憶集中在特定的村莊和人,通過歷史記憶還原歷史現場,通過歷史現場實證歷史記憶。
從歷史的邏輯判斷,且經過人證、物證調查,這條紅軍在西延山區實現戰略轉向的路線是真實存在的,符合湘江戰役后的突圍情況,是長征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內容。但因這些地方偏僻、封閉等原因,這段歷史一直未被外界知曉,使得這段重要且特殊的歷史記憶被封存。
三、紅軍長征在西延山區實現戰略轉向的意義和影響
綜合文獻調查和實地考察,可以發現:
(一)戰略轉向是紅軍長征歷史上首次改變沿著紅六軍團先遣隊路線行進的成功實踐
從地圖上來看,紅軍長征途中在資源縣油榨坪突然轉向,走了一個很大的曲線。從楓木山折返,經社嶺村、蟆嶺村、白竹寨、岔嶺村等,向老山界方向前進。這是中央紅軍長征歷史上改變沿著紅六軍團先遣隊行軍路線的首次嘗試,是紅軍重大戰略決策與命運轉折,是對“左”傾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斗爭,是從敵我情況出發,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歷史事實,雖然油榨坪會議決議之后只是從行軍路線上做了變通,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實行戰略轉兵,目的是為了便于北上湘西,與紅二、紅六方面軍會合,要從根本上實現戰略轉兵,必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周恩來于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也證實了這一點。“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為激烈。”[9]爭論的焦點是關于紅軍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及路線問題。紅軍在西延山區實現路線轉向的成功實踐,是最早放棄沿著紅六軍團先遣隊路線行軍的戰略決定。油榨坪會議的正確決策,戰略轉向路線的正確部署,毛澤東軍事主張的正確實踐,為后來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戰略決策作了成功示范,油榨坪會議成了遵義會議的最早孕育階段,深刻反映了湘江戰役與中國革命發展道路轉折過程的關系,以及湘江戰役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影響。
(二)戰略轉向利用了西延山區的復雜地形
湘江戰役主戰場雖然不在西延山區,但紅軍長征過西延山區卻是湘江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利用復雜地形避實就虛地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時任國民黨第四集團軍第七軍第二十四師第七十團團附黃炳細回憶:“第三日,紅軍已向大埠頭前進。第七十團跟追到楓木坪時,我方三架飛機,在上空盤旋,企圖轟炸紅軍,但飛行人員技術低劣,認識不清,反使第七十團停滯不前。后在楓樹坪山谷中的梯田地帶,發現我方飛機一架,栽倒在地,只剩飛機殘骸,飛行員殘尸兩具。”[10]當時西延山區尚未通公路,到處是原始森林,西延地界的復雜地形使得敵軍無法發揮空軍優勢,敵人的追趕速度放慢,飛機無法準確轟炸紅軍目標,起到了避實就虛的作用,保存了革命的火種,因此,紅軍長征過西延山區處于湘江戰役大收官的重要地位。
(三)戰略轉向使得紅軍變被動為主動
國民黨軍集中兵力在城步、綏寧方向布下口袋陣,如果一味按照紅六軍團先遣隊行軍路線行軍,敵軍根據紅軍先遣隊的行軍路線,準確掌握中央紅軍的西進路線,長征先遣隊的探路就變成了打草驚蛇,使中央紅軍處于被動局面。據分析,紅軍于1934年12月3日決定轉向,國民黨軍方面直到12月5日才后知后覺分兵追擊,因對中央紅軍軍委縱隊主力的行進方向判斷失誤,直到中央紅軍主力從西南方向出了龍勝江底,國民黨軍仍將追剿主力安排在西北城步、綏寧一帶,紅軍改變行軍路線向敵軍釋放“煙霧彈”,滯緩敵軍追剿速度,變被動為主動牽制敵軍。國民黨軍雖然相當于紅軍的5倍,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但由于蔣介石與湘、桂以及西南的矛盾極深,白崇禧名為配合行動剿滅紅軍,實則要把紅軍盡快驅離桂,且不愿越境追擊,加上紅軍及時迅速地戰略轉向,靈活而敏捷地利用國軍與桂軍行軍縫隙,國民黨軍的追擊部隊不但摸不著頭腦,反而處處陷入被動,事實上還為紅軍的西進“送行”。
(四)戰略轉向使得紅軍縱隊行軍布局由單一到復雜
紅軍前進路線根據作戰地形和敵情需要,制定了向西延山區前進過程中紅軍的前進縱隊由單一變復雜的軍事路線。由從瑞金出發的3個縱隊,右翼為三軍團,紅八軍團跟后;左翼為紅一軍團,紅九軍團跟后,紅五軍團做總后衛,拱衛著1萬多人的中央縱隊成甬道式前進[4]22;到向湘江前進的4個縱隊,第一縱隊(紅一軍團之主力)沿道縣、蔣家嶺、文市向全州以南前進;第二縱隊(紅一軍團一個師、軍委第一縱隊及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經雷口關及文市南面前進;第三縱隊(紅三軍團、軍委第二縱隊及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經小坪、鄧家源向灌陽山道前進,相繼占領灌陽,以后向興安前進;第四縱隊(紅八、九軍團)經永明(或繞過永明縣城)從三峰山向灌陽、興安前進(5)資源來源于2016年中共桂林市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湘江戰役文集》第18頁。。
紅軍進入西延山區為5~7個縱隊。1934年12月1—8日,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及軍委縱隊(即紅星縱隊)中央縱隊(即紅章縱隊)在長征途中突圍湘江后,除了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其余紅軍主力都進入了桂北西延山區,根據復雜地形和敵情需要,在行軍過程中由5條路線再分支為7條路線(6)資源來源于2019年中共資源縣委黨史辦公室編著的《資源縣關于湘江戰役歷史和革命精神研究課題匯編》第44頁。。本文提到的社嶺村、蟆嶺村、白竹寨、岔嶺村為紅軍經過西延山區戰略轉向的其中一條。
在紅軍主力全部離開廣西桂北地區之后,在黎平會議上撤銷紅八軍團、教導師(7)中央教導師在1934年10月至12月編為軍委第二縱隊第一梯隊參加長征。師長張經武,政委何長工,參謀長孫毅,政治部主任李熙。、保衛團的建制,將原中央縱隊的第一、二縱隊合編為一個縱隊,紅軍縱隊經過整編,再回歸單一布局(8)資源來源于2016年中共桂林市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湘江戰役文集》第217頁。。
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體現了當時紅軍長征的處境異常險惡,紅軍縱隊由單一變化到復雜,以應對地形、敵情等自然和人為的極端復雜環境,是毛澤東正確軍事戰略的偉大實踐,為后面紅軍長征過山區的作戰方略提供了參考。
(五)進行了長征途中比較早的民族工作實踐
紅軍長征進入越城嶺山區所經過的地域,大都是瑤族、苗族等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山區,人煙稀少。由于長期遭受國民黨政府的歧視壓迫和封建軍閥的燒殺掠奪,這里的人們飽受兵災之苦。且國民黨地方政府極力在群眾中作污蔑紅軍的宣傳,大部分瑤族、苗族群眾在紅軍到來之前,都帶著糧食和用具躲到深山老林,給紅軍經過當地造成了很大困難。紅軍能否順利通過桂北少數民族地區,關系到紅軍的生死存亡。
在進入西延山區前夕,紅軍政治部于11月29日針對紅軍過少數民族地區下達了《關于苗瑤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9)資源來源于2016年中共桂林市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湘江戰役文集》第51頁。以及《關于對苗瑤民的口號》(10)資源來源于2016年中共桂林市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湘江戰役文集》第53頁。的命令,將黨的民族工作思想和方針以標語口號的形式呈現出來,提出的民族政策使各族同胞認識到紅軍是老百姓自己的隊伍。進入西延山區成了紅軍長征途中比較早的民族工作實踐。
歷史上,桂北地區有著自己的鄉規民約和行為規范。1933年初,為反抗國民黨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和歧視,桂北地區也爆發了一些起義[11],但并未上升到階級斗爭層面。而黨的群眾路線,是啟發和強化這些少數民族群眾的階級意識,使黨的組織、黨的綱領、革命目標進入鄉村社會,特別是農民中間。
紅軍把民族工作當作紅軍整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了在長征途中比較早的民族工作實踐,為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紅軍長征在西延山區成功實現戰略轉向,是紅軍長征歷史上首次改變沿著紅六軍團先遣隊行軍路線的戰略創新,有效利用了西延山區的復雜地形避實就虛地牽制敵軍。戰略轉向使得紅軍變被動為主動,避免落入敵人的口袋陣遭受覆滅的艱難境地。紅軍縱隊在西延山區行軍布局由單一到復雜,體現了紅軍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靈活戰略布局,是毛澤東軍事主張的正確實踐,戰略轉向的成功實踐為后來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遵義會議等一系列會議的召開和戰略決策作了成功示范。紅軍在西延山區落實的民族政策,成了長征途中的比較早的民族工作實踐。中央紅軍在西延山區的戰略轉向過程,體現了湘江戰役對中國共產黨軍事路線、組織路線、思想路線、群眾路線和民族政策的深刻影響,這些對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轉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