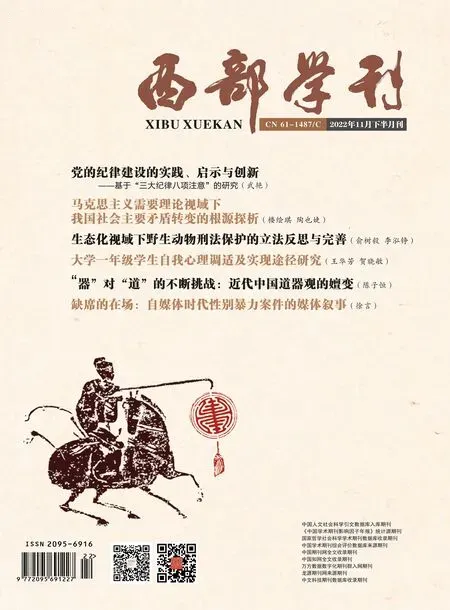西夏地方勢力政治變遷
張 禎
引言
西夏是以黨項拓跋部為首建立起來的少數民族政權,繼承了游牧民族部落制的特點,在黨項族內部雖然共尊拓跋氏為首領,但仍然存在諸多實力強勁的其他部落。“西夏政權是以拓跋氏為首的黨項強宗大姓的聯合專政,這個統治集團的成員和眾多宗族的家長及軍事首領們構成西夏國家的統治階級”[1]。可以說西夏政權是以拓跋氏為核心,聯合其他黨項部落共同建立的,也難怪李繼遷準備反抗宋朝時“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2]586“復連娶豪族”[3]13986,以爭取黨項各個部落的支持。這些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部落演變成為地方勢力的代表——番姓大族,成為西夏政治勢力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學界對于西夏的地方政治研究由來已久,依托于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門》的解讀,西夏地方政區劃分“并非嚴格地遵循中原政區中的層級關系”[4],地方軍政體系“除了經略司體系之外,西夏還有轉運司體系和刺史體系”[5]。然而,目前學界對于西夏地方政治勢力的變遷卻鮮有提及。
一、西夏的地方番姓大族勢力
關于黨項的番姓大族,隋唐時期記載有八大姓氏:“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余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最為強族。”[6]

此外,地方番姓大族通過與皇族聯姻的形式得以干預朝政,甚至還能左右西夏國主的擁立。元昊去世后,遺命“立從弟委哥寧令”[2]3902,卻遭到以沒藏訛龐為首的番姓大族勢力的反對。“其大酋悮移賞都、埋移香、熱嵬浪布、野也浪啰與沒藏訛厖(龐)議所立”[2]3902,在沒藏訛龐的支持下,眾人擁立年幼的諒祚為西夏國主,以悮移賞都為首的“三大將分治其國”[3]9676。秉常時期后族梁氏長期把持朝政,“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乙)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10]番姓大族長期把持朝政后果是引起西夏政權動蕩,人心思變:“夏國變故……諸梁擅兵,大酋數輩各懷去就,上下洶亂,興州左右新舊行邪造逆之臣與秉常故時親黨,各擁兵自固,斬絕河津,南北阻隔”[2]7566。
除去沒藏氏、梁氏外,對西夏影響較大的后族勢力還有破丑氏、衛慕氏、罔氏等。歷代西夏統治者一直都有與地方番姓大族通婚的風俗,這一做法無疑增強了黨項各部族之間的凝聚力,但也維持了地方豪酋大族的勢力,不利于西夏王朝的政治穩定。
二、迅速發展的漢姓大族以及鎮守邊疆的西夏皇族
西夏王朝在建立發展過程之中注重吸收任用漢族優秀的人才。諸如李繼遷時期的張浦、何憲,元昊時期的張元、李文貴,諒祚時期的學士蘇立、景詢等人。他們都是從中原地區叛逃到西夏的漢人謀士,最終被西夏統治者授予官職,得以重用。這些漢族士子憑借才識得以參與西夏王朝的治理,迅速成為西夏社會之中的地主階級,從而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漢姓大族作為西夏的新興的地主階級政治勢力,在西夏中后期政治斗爭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就是仁孝時期的權臣任得敬。他從地方軍官開始一步步發展,進爵成為西夏的異姓王,到最后竟然演變成了公然分裂國家、請求金朝冊封的鬧劇,極大破壞了西夏王朝的統治。任得敬本是宋朝的西安州判,在夏兵來犯后,率領全城軍民投降于西夏,乾順令其“權知州事”[9]402。任得敬女兒任氏被乾順納為妃子后,“擢任得敬為靜州防御使”[9]402,后升任為靜州都統軍。任得敬憑借靜州的軍隊多次討伐西夏境內的叛亂,素有威望,在仁孝時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勢力,“兵威震河南”[9]408。地方政治勢力的代表任得敬入朝當政后,先是被任命為尚書令,后擔任相國一職,由西平公進爵楚王,又進爵為秦晉國王,“出入儀從,幾與國主等”[9]424。任得敬位極人臣后仍不滿足,“以弟任德聰為殿前太尉、仁得恭為興慶尹”[9]423,安插親信來控制朝政,意圖篡位。雖然在金世宗的支持下,仁孝最終剿滅了任得敬及其黨羽,但西夏的地方政治勢力仍然有威脅到中央統治的力量。任得敬伏誅后,仁孝曾數次西巡,意圖安撫各大地方政治勢力,維護王朝穩定,防止分裂國家的政變再次發生。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仁孝西巡至甘州,為安撫人心,下令刊刻《黑河建橋敕碑》。碑文提及,“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祐我邦家”,希望西夏得到神靈庇護,風調雨順,國家興旺。
元昊建立西夏王朝之后,為了掩蓋黨項民族曾經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歷史,毅然決定更改姓氏,“屬族悉改‘嵬名’,蕃部尊榮之,疏族不與焉”[9]131。拓跋皇族憑借血緣宗親關系,成為西夏的貴族階層,他們往往被委以重任,皇子、宗親還有封王的傳統,是維護王朝統治的重要力量。然而隨著西夏社會的發展,西夏皇族也逐漸從政治中心興慶府向地方流動,打破了番姓大族勢力壟斷地方軍政的政治格局。“在西夏立國初期,皇族大都世居京城,但隨著西夏享國日久,皇族逐漸由京城流向地方,如沙洲、西涼府及黑水鎮燕軍司,地域元素逐漸影響到了皇族的宗族結構”[11]。
西夏皇族有的是在政治斗爭中被貶黜在外,如齊國忠武王嵬名彥忠,“任得敬害其能,中以蜚語,貶守涼州”[9]461。嵬名仁友為仁孝族弟,因功被封為越王,其子安全“上表誦先世功,冀嗣爵;純佑不許,封鎮夷郡王,安全由是生怨”[9]457。鎮夷郡王安全受封地治所為甘州,“所居甘州東據黃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生存環境和經濟條件十分優越……成為鎮撫西陲的軍事重鎮和河西走廊一帶的政治中心”[12]321。也有一部分嵬名宗室是因才能出眾被委派到地方以鎮守此地。舒王仁禮“通蕃、漢文字,有才思”[9]381,先是擔任秘書監一職,后擢拔為河南轉運使。西夏所指“河南”即河套地區的興靈平原。據《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門》記載,位于靈州的“大都督府”設有轉運司,四正、六承旨。仁禮后奉命“監軍韋州”[9]418,負責管理西夏地方軍政事務。遵頊襲承齊王爵、廷試進士后,“未幾擢大都督府主”[9]461。曲也怯律鎮守于甘州,“歲戊戌,太祖之征回鶻也,夏人不能以兵從,既克回鶻,益日疑懼,紫金(屈野怯律)守甘州以備焉”[13]。夏獻宗嵬名德旺之弟被封為清平郡王,越王仁友也曾“初封郡王”[9]457。
三、西夏后期地方政治勢力的演進
西夏從仁宗仁孝開始,地方政治勢力愈發膨脹,漸漸有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之勢。隨著西夏社會的發展,地方政治勢力逐漸發展成為三股政治力量,即地方番姓大族勢力、迅速膨脹的漢族地主階級和鎮守地方的皇族。這些地方政治勢力迫切想要在西夏政權之中攫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勢必會與中央政權之間產生沖突矛盾。
元昊雖然仿照中原地區的政治制度建立了西夏政權,但西夏依舊帶有濃重的游牧民族部落制度殘余,歷代西夏國主與各番姓大族諸如衛慕氏、罔氏和野利氏等進行政治聯姻便是一大例證。前期西夏王朝政治動蕩持續不斷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各番姓大族與嵬名皇族的矛盾。發展到西夏中后期,各大后族勢力集團在政治斗爭中因失敗而逐漸消靡,但地方番姓大族仍然牢牢把持著地方軍政大權。仁孝時期的“任得敬分國”,可以看作是漢族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臺、把持西夏朝政的一次嘗試。西夏王朝吸取前期后族頻繁專政、禍亂朝綱的教訓,對于地方政治勢力入朝主政的警惕性很高。夏大慶元年(1140年),任得敬收復夏州,撲滅蕭合達叛亂,立有大功,仁孝本想擢拔內職被濮王仁忠勸阻,受封西平公、翔慶軍都統軍。七年后的夏人慶四年(1147年),任得敬奉表請求參與國政,再次被御史中丞熱辣公濟勸阻。夏天盛元年(1149年),任得敬聽聞濮王仁忠去世,以金珠賄賂晉王,才得以入朝被任命為尚書令。由此可見,西夏地方政治勢力想要入朝干政十分困難。這也是自乾順剿滅后族梁氏以后,一直到仁孝時期,這段時間內再無后族勢力禍亂朝綱的原因之一。《金史·西夏傳》記載任得敬得以入朝干政后,“遂相夏國二十馀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14]2869。
任得敬沒有聯合其他地方政治勢力的支持,在與皇族的政治斗爭中勢單力孤,加上金朝的反對,最終失敗。而在西夏后期卻先后發生了兩次宗室篡奪皇權的政變。第一次是在桓宗純佑時期,宗室鎮夷郡王安全廢純佑自立。襄宗安全本是越王仁友之子,“天資暴狠,心術險鷙”[9]464,想要襲承越王爵位卻被純佑拒絕,改封為鎮夷郡王。安全由此懷恨在心,在其封地聯合地方大族,“利用甘州豐饒的資源,厲兵秣馬,培養羽翼”[12]321。夏天慶十三年(1206年),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死于廢所”[14]2871。安全篡位以后,蒙古又多次來犯,西夏在與蒙古的斗爭中屢次受挫,迫于蒙古威勢,被迫采取附蒙攻金的政策,金夏關系迅速惡化。夏皇建二年(1211年),西夏再次發生篡權奪位的政變。與嵬名安全降爵、貶黜在外不同,嵬名遵頊是深受器重、在地方委以重任的西夏皇族。其父齊國忠武王彥忠被任得敬貶守涼州后,“在郡有政績,蕃、漢畏懷”[9]461;遵頊“重明粹,少力學,長博通群書,工隸篆”[9]461,襲承齊王爵位,“以宗室策試及第,為大都督府主”[3]14027。
種種跡象表明,遵頊的這場宮廷政變是得到了絕大部分政治勢力的支持的。從西夏國內政治形式來說,安全即位帶給西夏的并不是興旺強盛,“其統治能力受到懷疑,再加上其本身為篡位登基,所以統治基礎并不穩固”[15]。安全與遵頊的政治背景也截然不同,安全被純佑降爵為郡王,而遵頊及其父彥忠在西夏都有著良好的口碑,狀元及第后襲爵齊王鎮守大都督府。結合以上兩點,我們可以合理推測:襄宗安全篡奪國主之位后,對內不能安撫百姓,對外四處樹敵,蒙古軍隊甚至兵圍中興府,安全不得已納女請和,一時間西夏國內民怨四起。而時任大都督府主的齊王遵頊卻有著良好的品行,是西夏宗室之中較為優秀的人才,于是在各方政治勢力的支持下,即位西夏國主。
總之,襄宗安全即位后排除異己,打壓擁護純佑的政治力量,客觀上也削弱了中央勢力,此消彼長之下,地方勢力愈發強大。神宗遵頊的繼位表明地方勢力最終登上了西夏的政治舞臺,中央政權與地方勢力的政治斗爭以地方勢力的獲勝而告終。
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歷來都是封建王朝所要面臨的問題。同一時期的宋朝吸取了唐末以來藩鎮林立的教訓,在地方上采取“以文制武”的政策,著力加強中央集權。而西夏王朝作為黨項族建立的民族政權,部落制度的傳統對其影響深遠,各番姓大族勢力的阻撓也使得政治改革舉步維艱。西夏既無法根除盤踞在地方的世家大族,也沒有完全倒向中原王朝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政治治理模式,這就導致了政治動蕩伴隨了王朝的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