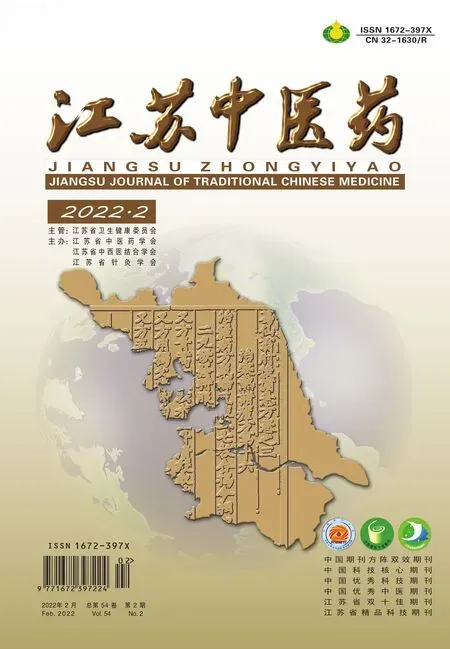肝脾同調法分期辨治胰腺癌思路擷要
阮 帥 舒 鵬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南京210029)
胰腺癌是消化道惡性腫瘤之一。2018年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癌癥數據顯示:中國659 732例惡性腫瘤患者中,胰腺癌患者有17 823例,發病率在所有惡性腫瘤中排第10位,死亡率在所有惡性腫瘤中位列第5,且呈逐年惡化的趨勢[1]。由于胰腺生理的特殊性,胰腺癌病位深,早期診斷難度高,臨床以晚期較為多見。患者在手術及放化療后,5年生存率低,復發轉移率高,且預后差[2],因此是臨床亟待解決的棘手病癥。中醫認為,肝主疏泄,調暢氣機,疏利膽汁、胰液于腸,以助飲食消化,化生氣血,供給后天之本。若肝失疏泄,膽汁及胰液不能正常分泌和排泄,則會影響脾胃運化功能,即木克土,謂之相乘,也稱之為“肝郁乘脾”。同樣,脾失健運,水谷精微無法濡養肝膽,也會導致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土反克木,即土侮木,也稱之為“土壅木郁”。由此可見,肝脾失調可能影響胰腺正常生理功能,給癌毒以可乘之機,當以肝脾同調為法治之,以健脾為本,疏肝為要,標本兼顧,扶正祛邪,試分析如下。
1 胰腺癌病名溯源
胰腺癌可歸屬于中醫學“脾積”“心積”范疇[3]。《難經·五十六難》[4]曰:“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為肌膚。”《素問·腹中論》[5]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病名曰伏梁……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難經》所述之“伏梁”與胰腺解剖學部位大致相符,且胰腺癌患者臨床多見腹脹、胸脅疼痛、黃疸、鼓脹等,屬中醫肝膽疾病;《素問》指出了此類病癥的嚴重程度。
2 病機責之脾虛肝郁
2.1 脾虛寒熱不調為本 “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正氣是機體抵御外來邪氣的能力,由先后天之本化生而來。《脾胃論》言:“內傷脾胃,百病由生。”脾氣虧虛則后天之本難以維系,久之臟腑功能衰退,氣血陰陽失衡導致癌毒內侵,肝膽郁滯,發為胰腺癌。胰腺癌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其病機無不體現脾虛的特點。胰腺癌最多見的癥狀為食欲不振,其次有惡心、嘔吐,亦見腹瀉甚至黑便。平素脾胃虛弱或病后中氣不足,以致脾失健運、胃失受納,故見胃脘痞悶、食欲不振、惡心、嘔吐等癥。臨證見寒熱不調的患者,多以虛證為主,脾虛故水谷難以運化,后天失養,繼生虛寒,見食欲不振、口淡、腹中冷痛、大便稀薄瀉下不消化食物;或繼生虛熱,見口干舌燥、潮熱盜汗、心煩不寐。總之,脾虛寒熱不調是胰腺癌發生、發展的根本,貫穿疾病發展始終。
2.2 肝郁膽腑毒侵為標 胰腺癌常見黃疸、持續性腹痛等邪實癥狀,這與肝郁膽腑毒侵密切相關。當癌毒侵襲機體,往往氣機郁結,導致肝失疏泄,膽汁、胰液無法正常分泌排泄,因此口苦、黃疸、厭食油膩、腹脹、腹痛等癥通常伴隨疾病進展不斷加重。國醫大師周仲瑛教授認為癌毒屬毒邪之一,是在內外多種因素作用下,在人體臟腑功能失調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對人體有明顯傷害性的特異性致病因子。它具有顯著區別于一般邪氣的致病特點,即猛烈性、頑固性、流竄性、隱匿性、損正性等[6]。因此癌毒侵襲是胰腺癌發病的病理基礎,由此導致的肝氣郁滯、肝膽失于疏泄又是胰腺癌發生、發展的重要病機。
3 肝脾同調,分期論治
3.1 健脾疏肝,標本兼顧
3.1.1 健脾為本,助生氣血 全國名中醫劉沈林教授曾提出消化道腫瘤的治則應以健脾為要。胰腺癌病機以脾虛為本,健脾則為治療的根本大法[7]。脾氣充盛則氣血化生充足,臨證可以《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益氣健脾的代表方參苓白術散為基本方。此方在四君子湯的基礎上加味,由人參、茯苓、白術、白扁豆、陳皮、山藥、蓮子肉、砂仁、薏苡仁、桔梗、大棗、甘草12味藥組成,具有健脾益氣、和胃滲濕的功效。原書記載其主治:“脾胃虛弱,飲食不進,多困少力,中滿痞噎,心忪氣喘,嘔吐泄瀉及傷寒咳噫。”方中人參、白術、茯苓健脾助運、扶助正氣,共為君藥;山藥、蓮子肉補脾,共為臣藥,蓮子肉兼能收澀,對于胰腺癌患者因脾虛所導致的腹瀉癥狀可以起到改善作用;白扁豆、薏苡仁為佐,加強君藥、臣藥和中祛濕之功,現代藥理學研究發現薏苡仁具有提高機體免疫功能、抑制血管生成及胰腺癌細胞增殖等多種功效[8];砂仁醒脾和胃、行氣通滯,與桔梗共用,亦為佐藥,可緩解胰腺癌患者食欲不振、腹脹不舒癥狀;“國老”炙甘草與大棗共奏健脾和中、調和諸藥之效,為使藥。全方平調寒熱。若患者中焦虛寒,癥見腹部隱痛綿綿不休,喜溫喜按,受涼以后疼痛加重,納食不香,神疲乏力,手足不溫,大便溏薄等,可加用干姜、肉桂、附子以溫煦脾土;若陰虛火旺,癥見口干唇燥、腹中嘈雜、干嘔、飲食減少或吞咽不利、大便干結,舌紅、少苔,或舌光、干絳,脈細數等可加用百合、知母、麥冬、鱉甲滋陰清虛熱。此外,由于胰腺癌惡性程度高,遣方用藥時針對其侵襲性強的特點可選擇添加三棱、莪術、山慈菇、半枝蓮等抗癌中藥,在全方健脾益氣的基礎上增強行氣化瘀解毒、抗復發轉移的效果。
3.1.2 疏肝為要,利膽通腑 結合胰腺癌脾虛肝郁的根本病機,肝郁膽腑毒侵為胰腺癌發病之標,健脾的同時應疏肝行氣、利膽通腑。臨證時,辨明膽腑濕毒、熱毒偏重,可予清熱化濕、開郁解毒。若膽腑濕毒偏盛,癥見周身乏力困重、渴喜熱飲、胸悶脘痞、腹脹便溏,舌胖、苔厚膩,脈濡緩,可以茵陳五苓散為基本方利濕清熱;若膽腑熱毒偏盛,癥見身熱口苦、汗出黏膩、心煩不寐、便溏不爽,舌紅、苔黃膩,脈濡數,可以大柴胡湯打底,內瀉熱結、解毒祛濕。還可加抗癌解毒藥白花蛇舌草、石見穿、八月札等祛除癌毒,配以紅花、川芎、乳香、郁金、佛手等行氣化瘀之品以祛除沉積體內的瘀毒,輔以海藻、浙貝母、夏枯草、地龍、僵蠶等軟堅散結、化痰通絡以抑制胰腺癌進展。
3.2 分期辨治,精準立法 國醫大師周仲瑛教授認為胰腺癌證屬虛實夾雜,不同疾病階段病機亦不同,故當分期辨證施治,同時強調胰腺癌患者多伴虛證,用藥不宜峻猛,祛邪不可傷正。
3.2.1 邪盛勢急當緩急通降、解毒祛邪 胰腺癌初期,邪毒較盛,病癥特異性雖不強,但病情進展迅速,膽腑內濕、熱、痰、毒相互搏結,發為實證,多見腹痛、黃疸等消化系統癥狀。患者此時正氣不虛,病起通常勢急,治療以抗癌解毒、軟堅散結、通腑祛邪為主。若見面色鮮黃、發熱、口干口苦、心煩、二便秘結,舌紅、苔黃膩,脈弦數者,此為濕熱熏灼,困遏膽腑,膽汁不循膽道而外溢,治療當用制大黃、茵陳、黃芩、金錢草、海金沙利膽退黃解毒,豬苓、車前子清熱利水滲濕。在此基礎上,可靈活使用蟲類藥,如守宮破結通絡治風、蜈蚣清熱解毒開瘀、土鱉蟲消癥破堅定痛,取其針對頑疾有加強解毒祛邪之功。
3.2.2 正虛邪戀當攻補兼施、行氣活血 胰腺癌中期,部分患者此時已明確診斷,或行手術,或行放化療等攻邪措施,患者臟腑功能失調,邪正交爭,虛實夾雜,病情較重。臨證常見脅肋部疼痛不舒、胃納差、大便稀溏或排便習慣改變、腹中如有結塊或脹或痛等臨床癥狀,舌淡苔膩,邊有齒痕,脈弦。此為肝郁脾虛、氣滯血瘀,導致體內形成癥瘕,當治以健脾養肝、和胃利膽、行氣活血之法,攻補兼施,調理臟腑。藥用生黃芪、黨參、茯苓、炒白術、淮山藥健脾益氣、運化水濕;柴胡、白芍、香附疏肝解郁、柔肝緩急;紫蘇梗、枳殼、陳皮、木香行氣導滯、理氣寬中;丹參、延胡索、生蒲黃、五靈脂活血散瘀止痛;三棱、莪術、石見穿化瘀消積。
3.2.3 虛羸少氣當補益氣血、調和陰陽 胰腺癌終末期,癌毒走注,正氣耗傷,證見氣血不足、陰陽兩虛。患者通常體形消瘦,面色萎黃,精神不振,情緒低落,自覺乏力納差,脘腹痞脹,上腹疼痛陣作或持續不解,心悸少寐,或伴眩暈耳鳴,畏寒,易出虛汗,手足心發熱,二便不調,舌淡、苔少,脈濡細緩。此時患者氣虛血少、寒熱不調、陰陽失衡,治當益氣補血、平調寒熱、調和陰陽。藥用生黃芪、防風益氣固表;黨參、白術、茯苓、炙甘草健脾助運;當歸、熟地黃、白芍、川芎補血養血;黃芩清上退熱、干姜和胃溫中,寒熱并用,辛開苦降;半夏乃調和陰陽之要藥,鄒潤安先生在《本經疏證》中言:“半夏可使人身正氣由陽入陰,是治陰邪竊踞陽位之要藥”,因此方中必不可少;加以冬蟲夏草、補骨脂、杜仲溫陽,黃精、枸杞子、鱉甲滋陰,以扶正補虛、調和陰陽。周仲瑛教授治療此期胰腺癌以益氣養陰、健脾開胃之品為主[9]。
3.3 活用蟲藥,祛除頑邪 蟲類藥乃血肉有情之品,在惡性腫瘤的診療中常可發揮獨特功效。現代藥理學研究發現,蟲類藥可以通過誘導胰腺癌細胞凋亡、抑制胰腺癌細胞增殖、抗新生血管生成、提高機體免疫力等途徑達到抗癌、防止復發轉移的目的[10]。溫病大家葉天士認為蟲類藥“飛者升,走者降,有血者入血,無血者行氣,靈動迅速,以搜剔絡中混處之邪”[11]。近代醫家朱良春在其所著《蟲類藥的應用》一書中言:“蟲類藥有特殊的破積化瘀作用。”臨床治療胰腺癌常用僵蠶、守宮、地龍、蜈蚣、全蝎等辨證配伍[12]。蜈蚣、全蝎搜風攻毒、通絡散結,地龍活血祛瘀消積,僵蠶化痰散結止痛,療效相對普通草藥更佳,對于胰腺癌膽腑毒侵、癌腫結塊可起到解毒疏泄、消積緩急的良好效果。此外,蛤蚧補腎益肺,鱉甲膠滋養腎陰,阿膠充盛氣血,常用于扶助正氣,適用于晚期陰陽失調的患者。但也應當注意,蟲類藥毒副作用較草藥猛烈,臨證時需要根據藥典規定及患者病情慎重使用,應從小劑量開始用起,依據患者服藥后的反應進行加減,最多不宜超過5 g,且蟲類藥藥味不宜過多,一般選用二三味[13]。
4 驗案舉隅
程某,男,51歲。2017年3月9日初診。
主訴:腹瀉持續2個月,加重1周。患者因“腹脹伴大便不成形4月余”于2016年3月至江蘇省人民醫院就診,行PET-CT檢查后確診胰腺體部癌,于2016年7月18日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術后病理示:胰腺(與膽總管相連處)中分化腺癌(1.6 cm×1.0 cm×0.7 cm),部分為黏液腺癌,癌組織浸潤至周圍脂肪組織,見神經累及,膽總管切緣、胰腺切緣、胃切緣、十二指腸切緣、十二指腸乳頭未見癌浸潤。術后予吉西他濱+替吉奧化療6個周期,后因明顯消化功能紊亂停止化療。近2個月來患者自覺口苦,胃納差,噯氣頻,腹脹便溏于午后晚間較甚,情志不暢。刻下:不欲飲食,噯氣頻頻,腹脹腹痛,便后緩解,大便日行3~4次,不成形,畏寒,無惡心嘔吐、噯腐吞酸,望之面白、形體消瘦。舌質紫、欠潤、苔少,邊有齒痕,脈弦細。西醫診斷:胰腺惡性腫瘤術后、化療后;中醫診斷:胰腺癌(脾腎虛寒,肝郁毒侵)。治以溫補脾腎、疏肝祛邪。予參苓白術散化裁。處方:
生黃芪30 g,白芍15 g,黨參15 g,茯苓15 g,炒白術20 g,淮山藥15 g,白扁豆10 g,防風10 g,陳皮6 g,半夏10 g,枳殼10 g,浙貝母10 g,海螵蛸20 g(先煎),醋柴胡6 g,守宮3 g,三棱20 g,莪術20 g,土鱉蟲5 g,五靈脂10 g(包),生蒲黃10 g(包),炮姜5 g,肉桂3 g,雞內金10 g,炒麥芽15 g,炒谷芽15 g,焦山楂12 g,焦六神曲12 g,炙甘草5 g。14劑。每日1劑,水煎后沖入三七粉3 g,偏熱送服,早晚飯后半小時溫服。
2017年3月23日二診:自訴腹瀉好轉,大便日行1~2次,較前成形。胃納增多,噯氣緩解,但仍覺乏力,手足不溫,左上腹脹氣明顯。舌質淡、苔薄白,脈細。原方去炮姜,加紫蘇梗10 g、制附片10 g、干姜10 g、仙鶴草30 g、當歸10 g,14劑,水煎后沖入三七粉3 g,服法同前。
2017年4月13日三診:患者諸癥好轉,精神體力好,食欲佳,自覺無明顯不適,二便調,偶見噯氣、泛酸。舌質淡紅、苔薄白,脈弦。予二診方加紫丹參10 g、淡吳茱萸3 g,14劑,水煎后沖入三七粉3 g,服法同前,同時加用中成藥貞芪扶正膠囊以提高機體免疫力。
后患者定期隨診,調治2年余,諸癥平穩,生活質量高,無明顯不適,可自主活動。
按:該患者初次就診時已行手術并接受多次化療。我們認為患者處于疾病中期,整體屬虛實夾雜,證屬癌毒內侵、肝氣郁結、脾氣不足、腎陽虧虛,當以健脾為本,兼以溫補腎陽,輔以疏肝行氣、解毒祛邪。方中生黃芪、防風、白術、黨參、茯苓、山藥、白扁豆可健脾益氣、滲濕止瀉,增強脾胃運化水谷精微的能力;黃芪、防風、白術組成玉屏風散可益氣固表,提高機體免疫力以抵抗外邪;炮姜、肉桂溫中散寒、溫補腎陽;白芍、醋柴胡柔肝緩急、疏肝解郁;土鱉蟲、守宮為蟲類藥,配合三棱、莪術可攻堅破瘀、解毒抗癌,增強祛邪之效;陳皮、半夏、枳殼、浙貝母行氣寬中、化痰消痞散結;生蒲黃、五靈脂、三七粉活血散瘀定痛;海螵蛸收濕斂瘡止瀉;炒谷芽、炒麥芽、焦山楂、焦六神曲開胃和胃、消食助運。諸藥相合,共奏疏肝行氣活血、補氣溫養肝腎、解毒抗癌、扶正祛邪之功。二診時,患者腹瀉較前有所好轉,便次減少,大便成形,中焦虛寒較前緩解,但手足不溫,故改原方中炮姜為干姜,添加制附片,繼續溫補脾腎;左上腹脹氣明顯,予紫蘇梗增強行氣寬中之效,緩解腹脹,幫助消化;感乏力則予仙鶴草、當歸補虛養血,助生氣力。三診時,患者精神體力好轉明顯,偶見噯氣泛酸,予二診方加淡吳茱萸,此藥性熱祛寒,功能制酸止痛,兼有疏肝解郁、降逆止嘔之效,可改善患者脾陽虧虛、肝胃不和之證。
5 結語
胰腺癌隱匿性強、惡性程度高,早期難以被發現,臨床確診時通常以中晚期居多,死亡率也偏高。目前西醫治療主要以手術、化療為主,其中根治性(R0)切除是治療胰腺癌最有效的方法。無法手術的患者,根據個體差異,通常進行吉西他濱、氟尿嘧啶類以及白蛋白紫杉醇等單藥或二藥、三藥聯合化療。近年來,靶向及免疫治療研究成果頗豐,PARP抑制劑[14]及帕博利珠單抗[15]也被應用于符合相應條件的胰腺癌治療中。
中醫藥配合治療胰腺癌可以改善患者癥狀,減少化療或其他治療的毒副反應,達到縮瘤減毒、降低復發轉移率的目的。胰腺癌治療雖然棘手,但是病性總屬虛實夾雜,基本病機為脾虛肝郁,治療可以肝脾同調為法,健脾平調寒熱以扶正,疏肝利膽通腑以祛邪,輔以行氣化瘀、軟堅散結之品,化痰通絡、解毒消癥,臨證還可靈活選用蟲類藥以加強祛邪之功。中醫藥個體化診療,病證結合,分期論治,平和用藥,祛邪不傷正,臨床療效顯著。在手術、化療、放療、靶向及免疫藥物治療的基礎上加用中醫藥治療胰腺癌,能夠有效減輕腫瘤負荷,抑制病情進展,甚至控制病情逐漸轉佳,是未來胰腺癌診療的重要研究方向,值得深入思考,不斷討論、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