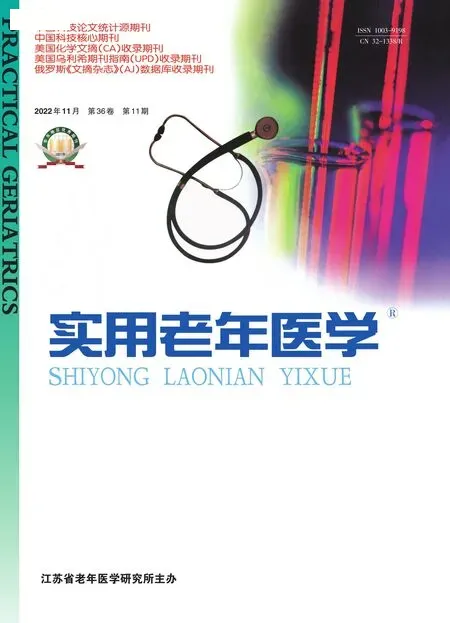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病人膈肌形態改變及相關因素分析
李艷 王肖瀟 孫莉 南淑良 霍樹芬 任小平 王水利 溫紅俠
COPD是一種以進行性、不可逆性的氣道阻塞為特征的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1]。呼吸肌疲勞是COPD病人呼吸困難進行性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導致呼吸衰竭的主要病理機制之一[2]。膈肌作為最重要的呼吸肌,占所有呼吸肌功能的60%~80%,因此膈肌功能將嚴重影響疾病預后及病人的生活質量。膈肌功能評估需要通過壓力學指標和膈肌肌電圖等來評價,但考慮到操作的侵入性、舒適度、復雜耗時及經濟等因素,臨床應用較少。近年來膈肌影像學檢查被廣泛應用在COPD病人膈肌功能檢查,可直接觀察病人膈肌形態學變化,尤其是超聲檢查,是目前臨床最常用來評價膈肌形態和功能的手段[3]。COPD急性加重期(AECOPD)為病人在COPD病史基礎上伴有呼吸系統癥狀的急性惡化。文獻回顧發現,目前研究中針對老年AECOPD病人的膈肌形態改變及相關危險因素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應用超聲觀察老年AECOPD病人膈肌結構改變,為疾病狀態的評估和后續康復治療提供客觀診療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0年6月至2021年2月就診于陜西省人民醫院的老年AECOPD病人58例作為AECOPD組,年齡61~92歲,平均(73.12±10.20)歲,其中男50例,女8例,平均BMI為23.49±3.71。根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議(GOLD)2020年指南,按照FEV1%pred=50%為界分為輕-中度亞組及重度-極重度亞組。同時選取本院同時期49例健康體檢老年人作為對照組,年齡63~81歲,平均(73.53±8.10)歲,其中男39例,女10例,平均BMI為23.25±3.41。2組間年齡、性別、體質量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已通過陜西省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同意(審批文號20200213)并所有受試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COPD組納入標準:年齡≥60歲,且臨床診斷符合GOLD2020急性加重期診斷標準。排除標準:(1)合并其他呼吸系統疾病,如腫瘤、氣液胸、活動性結核等;(2)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3)合并其他疾病: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惡性腫瘤、糖尿病、肝腎功能衰竭、神經或肌肉疾病(重癥肌無力、格林巴利綜合征等)以及嚴重精神類疾病無法配合等;(4)有既往手術史:3個月內手術史,既往胸部、上腹部手術史;(5)BMI>30.0;(6)長期服用鎮靜、興奮劑等藥物影響膈肌運動。對照組納入標準:(1)既往無慢性呼吸系統疾病、惡性腫瘤、糖尿病、嚴重的精神系統疾病、神經或肌肉疾病、肝腎功能衰竭、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病史;(2)無長期吸煙史、粉塵和化學物質接觸史;(3)肺功能檢查FEV1/FVC>70%且FEV1%pred>80%;(4)未長期服用影響膈肌活動類藥品。
1.2 研究內容
1.2.1 基線資料:測量所有受試者的身高、體質量,計算BMI,記錄COPD病程時間、近1年內急性加重次數。
1.2.2 肺功能測定:AECOPD組均在入院前3 d完成,健康對照組在體檢當天完成。肺功能儀統一選用美國CareFusion公司生產。記錄受試者的FVC、FEV1/FVC、FEV1% pred。
1.2.3 動脈血氣分析:AECOPD組受試者在安靜狀態下,平靜呼吸自然空氣,積極消除其緊張情緒。采用ABL90 Series血氣分析儀測定動脈血pH、PaO2、PaCO2。呼吸衰竭的診斷標準為PaO2<60 mmHg伴或不伴PaCO2>50 mmHg。
1.2.4 血清白蛋白(ALB)測定:采集AECOPD組受試者空腹靜脈血約2 mL,通過化學發光法分析測定血清ALB的含量。
1.2.5 COPD病人健康狀態損害評估:采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評估量表(COPD assessment test, CAT)對AECOPD病人健康狀態損害程度進行評估。
1.2.6 超聲測量膈肌形態學:半臥位式,使用高頻探頭置于受試者右鎖骨中線與腋前線之間的第8~9肋間胸壁上,獲得高回聲的胸膜層和腹膜層之間的距離即為膈肌厚度(thickness of diaphragm, TD)。分別測量平靜呼氣末膈肌厚度(diaphragm thickness at function residual capacity, TdiFRC),盡力吸氣末膈肌厚度(diaphragm thickness at forced vital capacity, TdiFVC)和盡力呼氣末膈肌厚度(diaphragm thickness at residual volume, TdiRV),上述數據分別測量3次后取平均值。計算膈肌增厚分數(thickening fraction, TF)=(TdiFVC-TdiFRC)/TdiFRC[4]。使用低頻探頭置于受試者右鎖骨中線平行于第7~8肋間的位置,在B型超聲下獲取呼吸周期中膈肌動度最大處,使取樣線垂直于此處后調整為M型超聲獲得吸氣和呼氣末基線至最高點間垂直距離的差值。按照上述方法囑受試者平靜呼吸測量3次后取平均值即為平靜呼吸時膈肌移動度(degree of diaphragm, DD),然后囑其用力呼吸,相同操作測量3次后取最大值即為用力呼吸時膈肌移動度(DDmax)。
2 結果
2.1 基線資料及肺功能指標比較 3組間性別、年齡、BMI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重-極重度組FVC、FEV1/FVC、FEV1%pred顯著低于輕-中度組和對照組(P<0.05),輕-中度組FEV1%pred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3組基線資料及肺功能比較
2.2 膈肌形態學改變 老年重-極重度組TdiFRC、TdiRV、DD、DDmax、TF與輕-中度組、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輕-中度組與對照組比較,TdiFVC、DDmax及TF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3組間膈肌形態學指標比較
2.3 輕-中度組和重-極重度組病情比較 2組病程、合并呼吸衰竭比例、ALB水平、近1年內急性加重次數、CAT評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輕-中度組及重-極重度組間臨床指標比較
2.4 AECOPD病人TF及DD相關因素分析 以TF、DD為因變量,FEV1%pred、病程時間、是否合并呼吸衰竭、ALB水平、近1年內急性加重次數、CAT評分為自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結果顯示TF與FEV1%pred呈正相關(β=0.547,P<0.05),與病程時間、近1年內急性加重次數呈負相關(β=-0.959、-5.978,P<0.05),見表4。DD與病程時間、近1年內急性加重次數呈負相關(β=-0.027、-0.150,P<0.05),見表5。

表4 多重線性回歸分析TF的相關因素

表5 多重線性回歸分析DD的相關因素
3 討論
在呼吸周期中,膈肌的形態學改變可反映膈肌收縮功能。COPD病人由于肺內長期處于過度充氣狀態,導致膈肌收縮區面積減小、肌纖維縮短,膈結構改變、收縮能力降低,出現肌肉疲勞和功能障礙,進一步加重病人氣流受限的程度,二者進入惡性循壞。膈肌影像學檢查有動態胸部數字化X線攝影、CT、MRI及超聲檢查等手段。胸部CT檢查可以清晰地觀察膈肌形態、位置異常等,并且能夠掌握肺氣腫情況,但輻射劑量相對高,不作為常規評價膈肌功能的手段[5]。雖然MRI能夠測量直立位時膈肌的運動[6],但相對復雜,成本較高,對操作的要求也較高。因此,超聲檢查是目前臨床評價膈肌形態和功能最常用的手段,其操作簡單且無電離輻射,可用于重癥病人床旁檢測[3,7-9],具有良好的準確性和可重復性等優勢[10]。
本研究發現,在平靜呼氣末及用力呼氣末膈肌厚度方面,老年輕-中度AECOPD病人較對照組沒有顯著差異,重-極重度組病人較對照組顯著增厚;在TdiFVC方面,不論輕-中度還是重-極重度AECOPD病人均較對照組出現下降趨勢。Okura等[11]納入38例COPD穩定期男性病人,也發現其TdiFVC較年輕健康對照組和老年健康對照組均有顯著降低(P<0.001),但TdiFRC及TdiFVC較對照組無明顯差異。但Yal?n等[12]的研究支持COPD穩定期病人TdiRV較健康人下降。可能原因在于:本研究COPD病人均處于急性加重期時測量膈肌形態,之前有研究也證實了膈肌功能障礙與AECOPD有關[8],由于急性期炎癥反應,氣流受限程度加重等因素,導致膈肌舒張困難。
很多研究已經證實TF也可作為間接評價膈肌收縮能力的指標。而且因膈肌厚度受個體差異的影響較大,因此TF可更準確、敏感地反映膈肌收縮功能[11,13]。本研究中,COPD病人TF顯著降低,并隨著肺功能氣流阻塞程度的增加呈現進行性下降。在呼吸運動中,膈肌的上下移動可以引起膈肌長度的變化,位置處于低平時將導致膈肌長度縮短從而影響收縮性能[14],使COPD病人DD較健康人群呈下降趨勢[11]。本研究結果顯示,輕-中度COPD病人與健康對照組間DD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是重-極重度病人的膈肌活動度明顯下降。另有研究也證實,盡力呼吸時COPD病人膈肌移動度顯著降低[15],而且重-極重度COPD病人的DDmax明顯低于輕-中度病人(P<0.05)[16],結果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本研究發現,TF與FEV1%pred、病程時間、近1年內急性加重次數呈負相關,DD與病程時間、近1年內急性加重次數呈負相關,說明COPD疾病程度對膈肌的結構和功能均有顯著影響。一項關于COPD病人膈肌尸檢結果發現、病程越長、膈肌受損越嚴重,這可能與病人體內持續存在的炎癥因子、氧化應激等引起肌肉蛋白分解代謝增加、合成減少有關[17]。
COPD病人的吸氣末膈肌厚度與橫膈移動度均下降,TF和橫膈移動度可以間接反映病人肺功能氣流受限程度和生活狀態。目前臨床中存在部分人群因呼吸困難、聽力理解力下降等因素導致無法配合完成肺功能檢查以明確診斷,因此基于目前研究結果,后期如果在無法獲取肺功能的情況下,DD和TF或許可以作為替代指標更好地應用于臨床。當然,后續可繼續開展大樣本研究,尋求最佳的膈肌超聲指標作為對肺功能的補充。此外,今后可開展吸氣肌訓練等干預措施,進一步研究膈肌形態及功能的變化,進而指導臨床疾病康復治療,為延長病人的生存時間和提高生活質量帶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