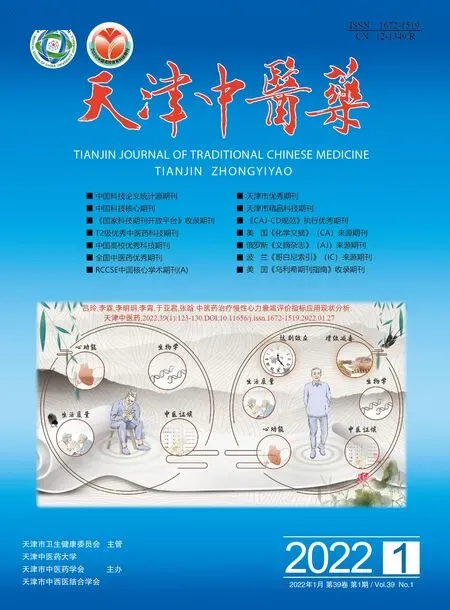基于《黃帝內經》“壯火食氣”思想探討糖尿病火熱傷氣病機*
蔣里,張耀夫,孟繁章,周婧雅,趙進喜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北京 100700)
糖尿病是一種以高血糖為特征的內分泌代謝疾病,其特點為胰島素的絕對或相對不足和靶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性降低,引起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電解質和水代謝紊亂。根據2013年中國國家疾病控制中心和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調查,中國目前2型糖尿病患病率為10.4%,已成為世界上糖尿病患病人數最多的國家[1]。中醫藥防治糖尿病及其并發癥的臨床療效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與重視。有學者認為,火熱傷氣,糖濁內生是糖尿病發生進展的關鍵因素[2],靈活運用清熱益氣治法既符合本病中醫基本認識,又可明確改善臨床患者當前癥狀和長期預后。文章基于《黃帝內經》“壯火食氣”理論探討糖尿病的中醫病因病機特點,以期為今后臨床治療提供思路。
1 《黃帝內經》“壯火食氣”思想初探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云:“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對于“壯火”及“少火”的理解,后世醫家分歧較大,大致有兩種觀點。第一,生理角度,如《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將“壯火”看作氣味純厚的藥物,將“少火”為氣味溫和的藥物,藥物峻烈則損傷正氣,溫和則養人臟腑;王冰注《黃帝內經素問》則將“壯火”理解為人體精氣滋養的身體功能。第二,病理角度,將“壯火”看作體內過亢之火,病理邪火,燔灼正氣,如《類經·陰陽類》云:“火太過則氣反衰,火和平則氣乃壯。”《黃帝內經集注》亦云:“火壯于外則散氣,火平于外則生氣。”此說似更符合臨床。
《黃帝內經》中有關消渴病的論述暗合“壯火食氣”的學術思想。《素問·陰陽別論》曰:“二陽結謂之消”,王冰注云“胃熱則消谷”,《靈樞·邪氣臟腑病形》又曰:“心脈微小為消癉,滑甚為善渴......滑者陽氣勝”,均強調消渴內熱的病機。《素問·奇病論》所謂“五氣之溢也,名為脾癉......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結合《靈樞·五變》所謂:“怒則氣上逆,胸中蓄積,血氣逆流,臗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可知消渴以內熱為先,從口甘之脾癉,可一步步演變為消谷善饑之“消渴”及血脈不行之“消癉”,《靈樞·五變》進一步補充:“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癉。”可見消癉者五臟柔弱氣虛。
綜合來看,多食甘美,形體肥胖,遂成脾癉;臟腑內熱久積,漸生消渴;又因飲食肥甘,邪熱不去,“壯火食氣”,五臟六腑失養,故轉為消癉。《靈樞·本臟》云:“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肺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腎脆,則善病消癉易傷。”指出心肺脾肝腎諸臟脆弱,體質偏頗,則消渴病“壯熱食氣”,會進一步損傷相應內臟,導致“消癉易傷”。
呂仁和教授認為:“脾癉”“消渴”“消癉”分別與現代醫學的糖尿病前期、臨床糖尿病期與并發癥期相對應[3]。癉者,熱也,機體由于外感邪毒,或飲食失調,或情志內傷之后,人體陰陽失調,陽氣偏亢而化火,此即“壯火”“壯火食氣”,耗傷人體正氣。糖尿病患者的“內熱”就是邪火,不僅可以傷陰,又可耗氣,所以臨床常見消谷善饑、乏力消瘦、大便秘結等熱傷氣陰的癥狀。糖尿病臨床常見的氣陰兩虛證,包括晚期常見的陰陽俱虛證,實際上都是火熱傷氣的結果。
2 歷代醫家對消渴病火熱傷氣病機認識
歷代醫家從不同病位、病因及表現論述“壯火食氣”的具體內涵。朱丹溪將病理之壯火分為君火過旺之“心火亢盛”和相火過旺之“相火妄動”,認為壯火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的貪欲耗傷肝腎真陰,強調君火引動相火而致病。李東垣詳細闡發了“壯火”產生的機制,衍化創立了“陰火”學說,認為病理之壯火源于脾胃,又包括五臟六腑的病理邪火,如《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曰:“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脾胃氣虛,則下流于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陰火過亢則為壯火,常常表現為濕熱、痰火、郁熱、熱毒以及病理君相之邪火[4]。
火熱傷氣與消渴病關系密切。張仲景上承內經“壯火食氣”說,論述消渴病火熱傷氣的病機演化。其一,論厥陰消渴。《傷寒論》326條曰:“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下之不肯之。”胃熱陰虛,擾及厥陰肝木,肝氣攜胃火克伐脾氣,火熱傷氣,故見口渴、氣逆、嘔吐。強調厥陰消渴之火熱在肝胃,氣虛在脾。其二,論雜病消渴。《金匱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篇曰:“趺陽脈浮而數,浮即為氣,數即消谷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又云:“趺陽脈數,胃中有熱,即消谷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即數。”浮為胃氣有余,數為胃熱亢盛,胃熱傷及脾氣,脾不為胃行其津液,以致精微下注,滲入膀胱,腸道失潤,故見身體消瘦,小便數,大便堅。火熱傷氣,氣虛不能化津,津虧無以上承,所以消渴多見口干舌燥而渴,《金匱要略》所謂“渴欲飲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即是此證。強調胃熱脾虛在雜病消渴發病中的重要作用。
金代名醫劉完素強調燥熱傷氣,如《河間六書·三消論》云:“雖有五臟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遇各異,其歸燥熱一也......熱氣怫郁,玄府閉塞,而致津液、血脈、營衛、清氣不能升降出入故也。”認為燥熱過盛,會影響氣機的正常運行,制方用咸寒以勝火,甘緩以散結,辛散以抑燥,常用清熱益氣之三黃丸、人參白術散及人參散。李東垣主張脾胃伏火,即胃熱基礎的脾虛證,如《脾胃論·脾胃勝衰論》云:“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氣分則能食,脾虛則肌肉削,即食亦也。”《蘭室秘藏·消渴門》進一步論述:“足陽明胃主血,熱則消谷善饑,血中伏火,津液不足,結而不潤,皆燥熱為病也。”認為元氣下陷,陽伏陰中化火,“陰火”日盛,耗氣傷津,引發消渴。治療強調“扶正必先補脾土”,反對濫用苦寒折火之品。因此,綜合歷代醫家對消渴病病因病機的理解,無論胃熱、濕熱、燥熱、伏熱,火熱傷氣都是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
3 糖尿病火熱傷氣病機的現代臨床意義
3.1 2型糖尿病“壯火食氣”的含義 2型糖尿病屬中醫“消渴病”范疇,火熱傷氣在2型糖尿病發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在當代較大的心理壓力及高油脂、高能量飲食的背景下,內生火熱,氣機受阻更成為糖尿病發病不可忽視的病機。火熱為病機之要,消耗人體正氣,氣不化津,陰虧津損,是謂“渴”;火熱內燔,形消善食,是謂“消”,故2型糖尿病多有消渴之癥。陰虛血少,日久絡瘀,變生“微型癥瘕”,導致痹痿脫疽、視瞻昏渺、腎風勞淋等多種慢性并發癥。
趙進喜教授認為,糖尿病的壯火實際上有3層含義:其一,從病位著眼,糖尿病之熱常以一臟一腑為本,散及三焦,呈廣泛存在的慢性低度炎癥及全身散發的并發癥。火熱還根據患者的不同體質累及相應的臟腑病位[5]。陽明體質者易發陽明熱盛,而厥陰肝旺體質者易發肝火,太陽陽氣過亢體質者常累及肺系。橫斷面調查顯示,南方初發糖尿病患者多為厥陰體質[6],而北方糖尿病患者多為太陽、陽明體質[7]。其二,從病性入手,有濕熱、痰熱、瘀熱、郁熱、毒熱和結熱之別[8]。正因熱邪常與痰、濕、積滯、瘀血等有形之邪膠結,才使其熱難清,病程遷延難愈。根據現代人的飲食生活習慣,火熱尤以脾胃肝膽的濕熱、郁熱、毒熱為主。如金建寧等[9]觀察發現糖尿病患者尤以脾胃濕熱、肝膽郁熱、肺胃燥熱及熱毒最為多見。其三,微觀角度下,壯火可看作糖尿病發展中的糖脂代謝紊亂[10]。脾癉期“數食甘美”,過度攝入高脂肪膳食,導致體內代謝產物堆積,炎癥因子表達上調,糖脂代謝紊亂,繼而血糖升高。“食氣”也有3層含義:其一,氣虛證及氣陰兩虛證的出現。明確診斷的糖尿病患者,血糖升高,常常出現形體肥胖、倦怠乏力、少氣懶言、腹脹納呆等氣虛癥狀[11]。火熱毒邪耗氣傷陰,臨床上也常見氣陰兩虛證。有學者對2型糖尿病中醫證候進行聚類分析研究,證明糖尿病本虛證中以氣虛證最為多見[12],氣陰兩虛證型是本病數量最多的一種中醫證型[13]。其二,正氣不足,抵抗力降低。糖尿病患者內火亢盛,正氣虧損,常引動外邪,表現為感冒、淋證、瘙癢等癥狀。糖尿病患者合并呼吸道、消化道及泌尿生殖道感染的風險較普通人更大。其三,胰島功能下降。以糖脂代謝紊亂為病理實質的“壯火”邪熱,通過糖脂毒性、炎癥損傷等途徑,導致胰島細胞功能損傷調亡,引發胰島素抵抗,加速疾病進展。
總的來說,2型糖尿病作為一類胰島素相對分泌不足的代謝性疾病,其主要病理過程為胰島素抵抗—高胰島素血癥—糖脂代謝紊亂—糖脂毒性損害—糖尿病[14]。“壯火”不僅體現了中醫視角下,以脾胃肝膽的濕熱、郁熱、毒熱為核心的邪熱特征,還暗含了特有飲食習慣及社會背景下,因糖脂代謝紊亂產生的高胰島素血癥、高血糖、游離脂肪酸等代謝產物[15]。這些代謝產物參與復雜的炎性機制,最終使患者產生消谷善饑、口渴引飲、乏力納差等內熱氣虛的表現,此時胰島的正常生理功能已經漸進性減退,“壯火食氣”是這一過程的高度概述。
3.2 基于火熱傷氣的2型糖尿病臨床研究 2型糖尿病患者臨床常見的陰虛、氣陰兩虛甚至陰陽俱虛,實際都是火熱傷氣的結果,治應標本兼顧,虛實同調,重視苦寒清熱及甘溫益氣的協同運用[16]。以黃連、黃芩、黃芪等清熱益氣藥為主,標本兼顧,輔以養陰、活血、解毒等治法,對2型糖尿病具有較好療效。袁卉屏[17]觀察清熱益氣法治療糖尿病的療效,治療組以人參、黃連為主進行干預,而對照組單用黃連素進行治療,觀察3個月后,治療組的胰島素敏感指數等指標均優于對照組。勞汝明[18]以清熱益氣湯配伍治療2型糖尿病,治療組在西藥治療基礎上另外加服中藥清熱益氣湯,結果表明清熱益氣湯能夠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提高胰島素敏感性。王松等[19]研究發現,清熱益氣中藥(黃連、人參等)相比格列美脲更能降低炎性因子C-反應蛋白、腫瘤壞死因子和白細胞介素-6含量,且呈劑量依賴性。
4 小結
2型糖尿病病機從火熱傷氣出發,內熱傷陰,氣虛血瘀,導致各種并發癥,火熱傷氣貫穿病程始終,故治療2型糖尿病時需引起足夠重視。治療上當緊扣火熱傷氣,標本兼顧,虛實同調,靈活運用清熱益氣治法,并隨癥加減。中醫現代臨床當抓住火熱傷氣病機,同時注意飲食、住行等調適,發揚“治未病”觀念,從根源上保護胰島,防治2型糖尿病及其并發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