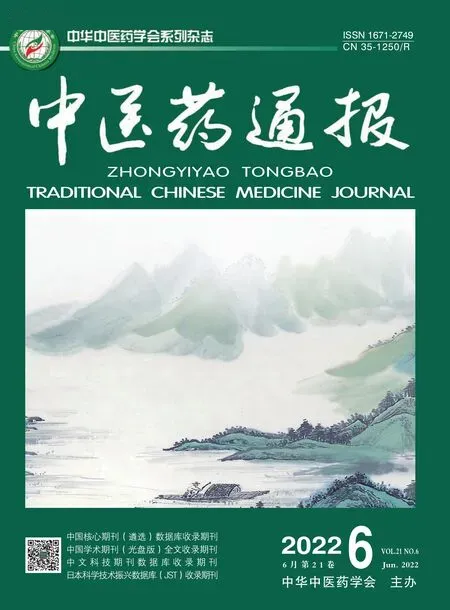論張子和“飲當去水,溫補轉劇”之治飲思想
陳 榆 莫迪麟
張從正,字子和,號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蘭考)人,五十歲左右作為隨軍軍醫經歷軍旅生活,后曾短暫入召太醫院,晚年在友人麻知幾及門人協助下完成《儒門事親》一書。《儒門事親》成書于金大正年間(1224—1232年),共十五卷。從《儒門事親·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十三》得見,張子和認為“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1],當有邪氣時,應速去邪氣,使氣血恢復通暢。攻邪可根據病邪位置,靈活運用汗、吐、下三法。若需補益,則應確保病邪已祛除,才可考慮以補劑助其元氣恢復。同篇末段又曰:“使用藥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補,止有三法。”[1]指出攻邪與補益等法雖然名目各異,但“邪去正安”之核心思想始終一致。從《儒門事親?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十七》一篇中,可見張子和提倡補益選用平和之品或日常飲食,反對盲目溫補。張子和擅長醫治各種疾病,對痰飲病尤有心得,故于《儒門事親·卷三》中立《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一篇以抒己見。
1 張子和對“飲”的認識
在《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的開首,張子和已開宗明義,指出“留飲,止證也,不過蓄水而已”[1]。從此句可知,“留飲”是儲蓄在體內的不正常水液,其特點在于不隨氣化、停止于一處,亦因其靜止的特性,會阻礙正常的氣機運動。張子和亦引述“王氏《脈經》中派之為四:痰飲、懸飲、支飲、溢飲”及“《千金方》又派之為五飲。皆觀病之形狀而定名也”,指出不論是“痰飲、懸飲、支飲、溢飲”或是其他名字,總歸是飲。此篇所討論的“飲”為廣義的“飲”,即不當有而有之水,下文統稱為“留飲”。
班固的《白虎通德論》提及:“故水者,陰也,卑,故下。”張子和亦引用此概念,指出水的本質屬陰,本應為人體一部分,但因各種原因而成為邪氣。《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提到“入腎則為涌水,濯濯如囊漿,上下無所之”,指出水無屬于自己的居所,會因哪里有空隙而流溢至該處,故水在不同人身上停留,就會衍生不同名稱之飲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化氣,陰成形。”張子和把水在身體滯留日久的影響總結為兩大方面,正如《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所言之“在陽不去者,久則化氣,在陰不去者,久則成形”,留飲一方面會耗損陽氣,另一方面會成為有形之實邪。
2 反對“飲為寒積”的理解
張子和認為:“今之用方者,例言飲為寒積,皆用溫熱之劑以補之燥之。”[1]本句之“例言”一詞可見認為“飲為寒積”的醫者極多,而張子和卻不同意此觀點。其提及水飲其來有五,“有憤郁而得之者,有困乏而得之者,有思慮而得之者,有痛飲而得之者,有熱時傷冷而得之者,飲證雖多,無出于此”[1]。張子和根據以上病因,解釋留飲形成的五個機理,曰:“夫憤郁而不得伸,則肝氣乘脾,脾氣不化,故為留飲。肝主慮,久慮而不決,則飲氣不行。脾主思,久思而不已,則脾結,故亦為留飲。人因勞役遠來,乘困飲水,脾胃力衰,因而嗜臥,不能布散于脈,亦為留飲。人飲酒過多,腸胃已滿,又復增之,脬經不及滲泄,久久如斯,亦為留飲。因隆暑津液焦涸,喜飲寒水,本欲止渴,乘快過多,逸而不動,亦為留飲。”[1]由此可見,水飲不單純是寒引起的問題,也可因五行生克、情志、起居、臟腑特性等不同因素而誘發。即使是最接近“寒積”的“原因五”,亦有“隆暑津液焦涸”的先決條件,亦即暑熱邪氣傷津耗氣后,過飲生冷成留飲,陰液本因暑氣受損,假如溫補豈不是更傷陰氣?總括而言,張子和認為眾醫所持有的“飲為寒積”的觀點流于表面,既未追溯水飲病的由來,亦未能全面反映水飲病的病機,并為下文作鋪墊。
3 指出“溫補轉劇”的機理
《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中的一個主要觀點,是抨擊當時之醫家以“溫補治飲”作為主要治飲之法的做法。上述已說明留飲不一定皆為寒積,此段張子和更提出,即使真的是有“寒飲在中”,亦不應投溫熱藥。張子和指出當寒飲在中焦,“以熱藥從上投之”雖看似合理,但反而會“為寒所拒”。這是因為病邪所在和藥力所到之間存有差異,故出現“水濕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其上焦枯,其下焦寒栗”[1]之弊。病痰飲者,陽氣受寒邪壓抑不利行散,怫結于內,本有病熱的傾向,當溫熱藥的藥氣欲經上焦到中焦時,便難免引動上焦心火,舊病未去之余造成新病。同時,因水“上下無所”,自然會流向低處、虛處,故上部有實火時水邪則下注,造成上熱下寒的情況。張子和在下文中甚至提出“留飲下無補法”,因為留飲為有形實邪,氣已經受隔塞,再補氣則令氣壅塞的情況加劇。而張子和所謂的“補”亦不限于藥補,而是包括“燔針艾火”在內的一切溫熱之法。
4 張子和處理水飲的方法
4.1 治病核心在于氣機治水飲當首先確保氣機通暢。張子和在文中引用《素問·六微旨大論》“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之說,強調氣的出入升降如常最為重要。雖然說人之氣向來貴在通暢,任何疾病均與氣機息息相關,但治水飲時氣機通暢尤其關鍵。因為《素問·經脈別論》有言:“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水作為有形之物,蕩漾于六腑中,化則為津液,不化不通則為留飲,其害更甚于氣滯。又《難經?三十一難》曰:“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當留飲堵塞于胃腸時,其實也阻礙了三焦在全身氣血的流動。《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曰:“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藏府肌肉之紋理也。”《靈樞?本藏》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因為三焦和腠理的聯系,留飲的影響亦不限于里,而往往影響肌表。換言之,留飲雖只在一處,其害卻遠播。但治療上因留飲有形,相較于無形的氣,更可以被明確地攻逐出人體。而攻逐留飲后,要評價氣機通暢與否,可從飲食得知,因脾胃為氣機升降的樞紐,《儒門事親》多處皆以“思食”“食進”為邪去正安的證明。
4.2 “留者攻之”及用藥的時機、位置與藥性正如上文所述,張子和并不認為留飲是單純的寒積,水固為寒,但留飲的側重點在于其留結于內,故并不能以溫補陽氣之法祛除。《素問·至真要大論》曰:“留者攻之。”指出當病邪留滯不去,應以瀉下、滌飲、攻瘀等法“攻之”。張子和在《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中曰:“況乎留飲下無補法。氣方隔塞,補則轉增。豈知《內經》所謂留者攻之,何后人不師古之什也!”[1]值得注意的是,“留者攻之”并不只限于攻逐留飲,而能推廣至祛除一切有礙氣血通流的因素,繼而協助五臟六腑氣機恢復正常升降。《儒門事親?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曾提到:“《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去而腸胃潔,瘕盡而榮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者存焉。”[1]可見,在攻的過程中,其實亦有補益之意。假如醫者成功攻逐留飲,卻因此敗壞脾胃,這便有違“留者攻之”之意。因此,張子和從時機與藥性兩方面考慮,舉例說明醫者該如何“留者攻之”,具體如下。
治療留飲時機方面,張子和認為邪未祛除時不宜補,新病宜峻藥速攻,久病宜緩攻。《儒門事親·汗吐下三法該盡治病詮十三》曰:“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鶩而不可制矣。”[1]可見,張子和認為有邪氣積聚時不能急于補益,否則正氣未曾得助,邪氣便已受補藥刺激而“橫鶩而不可制”,并指出“惟脈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中張子和以劉河間三花神佑丸為例,指出“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丸”能使“氣流飲去”。同篇又引河內某人病飲一案為例,說明即使藥不變,隨時日而改變服法,亦有“補瀉不同”。散較峻而丸較緩,散丸交替使用,先以前者滌蕩腸胃水飲,十余劑后,丸劑則可在前者的基礎上健脾化濕,如此重復交替,直到“腸胃寬潤,惟思粥食少許,日漸愈”。《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續曰:“夫黃連、黃柏,可以清上、燥濕,黃芪、茯苓,可以補下、滲濕。二者可以收后,不可以先驅。”[1]可以看出,張子和并未完全反對治飲時運用溫補藥物,但要認清先后次序,邪去則可補。若尚有留飲未盡去,則需重復運用“苦葶藶、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藥”,待“伏水皆去”,則可溫補。
藥性方面,張子和非常重視寒熱。即使同為攻下藥,性不同則功效有別。《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曰:“前人處五飲丸三十余味,其間有礬石、巴豆、附子、烏頭,雖是下攻,終同燥熱,雖亦有寒藥相參,力孤無援。”[1]批評了當時之人攻下之方過于雜亂,寒熱同用,最終使攻下之力大減。因此張子和主張攻下之方需藥性專一,方能中病,故在《儒門事親·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一篇則提到,“水腫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不利”可以“澤瀉、羊蹄苗根、牛膽、蘭葉汁、苦瓠子”[1]等一派苦寒藥分利水濕。可見,張子和認為即使藥物的功效和發揮作用的位置恰當,寒熱仍然非常關鍵,寒熱錯配,則攻邪之力大減,或失治病之最佳時機。
4.3 從病案看“留者攻之”的具體應用上文已提及張子和對“留者攻之”的理解和運用此法時該考慮的因素,接下來則會透過討論《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所載的醫案,來理解該如何把握“寓補于攻”的尺度。
《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載:“昔有病此者,數十年不愈,予診之,左手脈,三部皆微而小;右手脈,三部皆滑而大。微小為寒,滑大為燥。”[1]病人病數十年不愈,張子和認為左脈三部俱寒而右脈三部俱燥可見病人病勢遍及上、中、下焦,水飲積聚而津液未能布散,更有可能是先前曾用溫補,加劇病情。因而此病為久病留飲,形氣俱傷。
張子和認為第一階段的治療應先涌寒痰數升,攻逐在臟腑的水邪,大汗出能外泄在皮毛、腠理的水,再引導水液到腑中潤其燥垢而使之能從下出,曰“余以瓜蒂散,涌其寒痰數升,汗出如沃,次以導水禹功,去腸胃中燥垢亦數升,其人半愈”[1]。就如河水泛濫,一方面可先把多余的河水直接抽走,另一方面,可以導引河水,借用水本身的特性,滋潤堵塞于河道中的干泥,從而使水得以抵達下游,而中上游的水亦不再泛濫。因為水之成邪不僅僅是水液過多的問題,同時也是分布不均的問題。
張子和認為第二階段的治療可以用淡滲之品。經過先前大刀闊斧地攻逐水飲和處理燥熱,氣機已經大致恢復通暢,“然后以淡劑,流其余蘊,以降火之劑,開其胃口,不逾月而痊”[1]。因為想要淡滲利濕的話,首先要確保水有可以離開的通道,如若仍像一開始般邪實寒熱壅塞三焦,則用再多的利水藥也是徒勞,反而有機會更傷其枯燥之陰。連、柏降火,使胃陰得復而胃口開。上文提到氣機通暢的證明視乎脾胃,因為脾胃位處中焦,是一身氣機升降的樞紐,胃口復可見氣機已通暢。
最后一個治療階段,若邪未盡去,仍可攻邪,但強調中病即止,不要攻邪太過,曰:“復未盡者,可以苦葶藶、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藥,伏水皆去矣。”[1]。因伏水深伏,有時飲邪未能盡祛,但攻邪之法終能傷及正氣,故攻逐時必須留意中病即止,以防傷害脾胃之氣。
總結以上三個治療階段可知,張子和的攻邪和補益并非互不相干。第一階段祛邪同時透過輸布津液而補益陰津;第二階段透過清熱利水藥補脾胃,恢復脾胃受納運化而驗明全身氣機通暢;第三階段則提醒攻邪方法應該靈活,時刻注意藥力,以免過猶不及。由此病案可知張子和如何攻中帶補、寓補于攻,闡析了“留者攻之”的深度。
5 與仲景“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之治飲法的聯系
張仲景(150—219年),名機,南陽郡涅陽縣(今河南鄧州)人。曾為長沙太守,被后人尊為“醫圣”,著有《傷寒雜病論》和《金匱要略》。古往今來,學醫之人皆奉《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為經典,其中《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第十二》就曾詳細討論了痰飲病的證治,并提出“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的治法。
人飲水入胃,但脾胃陽虛運化無力,水液不布而為痰飲。痰飲屬陰邪,能阻礙氣機,繼而再傷陽。仲景所說的“痰飲”,即張子和所說的“留飲”。此病從病性看,當屬正虛邪實。正氣虛,故應用溫藥以溫運脾胃;邪氣盛,故應用溫藥以溫散寒飲。用藥的目的在于調和虛實,損有余而補不足。
5.1 “溫藥和之”不同于“溫藥補之”溫藥,一般指藥性溫,助陽氣之品。和,指調和緩解。魏荔彤在《金匱要略方論本義》中說:“言和之,則不專事溫補,即有行消之品,亦概其例義于溫藥之中,方謂之和之,而不可謂之補之益之也。”[2]魏荔彤指出,溫藥的含意并非溫性藥物之意,只要以和之方法祛除水邪亦可視之為溫藥,本句更注重“和”一字。而又從《傷寒論》中“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后,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一條,可看出“和之”不一定要用溫藥。況且“熱則寒之”,仲景治療飲熱互結之證,亦會用到寒藥,《金匱要略》就載有“腹滿,口舌干燥,此腸間有水氣,己椒藶黃丸主之”的條文,方中防己、葶藶子、大黃皆為寒藥。
由以上可見,張仲景“溫藥和之”不同于一般醫者“溫藥補之”,雖然一般醫者醫治痰飲病時亦多用白術、桂枝等溫性藥物,但背后運用之理法有異。換言之,仲景和張子和的觀點并非相互對立。
5.2 時代不同故所關心的亦不同上一部分已厘清了“溫藥和之”和“溫補”的差別,仲景和張子和二人,實際上都以使氣機通暢為目的,但這樣并不代表兩人治痰飲的方法一樣。
張仲景“溫藥和之”的代表方為苓桂術甘湯,方能溫陽化飲,健脾利水。方能使水邪從小便去,亦符合張子和對“攻邪”的理解,如直接引用仲景此方來論述“飲當去水”的觀點原是更直接。只是,自宋以來醫師普遍喜用辛溫香燥之品,同時又潛移默化地受仲景“溫藥和之”思想的影響,以為飲就是寒,只能用溫藥以治之,而沒有其他方法。故此,張子和反而引用“今代劉河間依仲景十棗湯,制三花神佑丸,而加大黃、牽牛。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丸,氣流飲去”的例子去闡述“去水”之法。從《儒門事親》書中多次引用仲景條文可知張子和熟讀仲景醫書,其明知苓桂術甘湯為治痰飲的第一方,卻不用以此方解釋此病,可能別有深意。三花神佑丸加了大黃、牽牛,瀉下逐水之力更強,可以推斷張子和更加重視邪氣對氣機壅室損傷的一方面。
上文提到,飲為陰邪。仲景的時代,死于傷寒者不計其數,而傷寒病是以傷陽氣為主要發病傾向的,或而令仲景更關心的是陰邪阻礙氣機,會進一步損傷虛弱的陽氣。反之,張子和的年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盛行,人們濫用香燥之藥,傷于熱的人很多,故其更擔心陰邪阻礙氣機,會使氣郁化火,進一步傷害陰氣。張仲景重視飲為寒邪,易傷陽氣,陽氣傷則陽虛氣機不通;張子和則重視留飲為停留之邪,留而化熱成實,阻礙氣機。兩者雖重點不同,但最終都以氣機通暢為治病依歸。張子和雖然不同意“飲為寒積”,卻從未反對“飲為陰邪”,而“溫補轉劇”之劇更有可能是針對“氣機阻塞”轉劇,是針對留飲成實而言,而非寒邪直接惡化。對張子和來說,溫藥本身便離不開溫運、溫散之品,按“溫補轉劇”的機理來看,即使用溫熱藥的目的不在補,亦有“水濕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之風險。故張子和更希望以神佑丸為例子,說明甘遂、大戟、大黃、牽牛等寒涼之藥亦能逐水助氣機恢復運化,非定要以溫運、溫散之品,才能幫助脾胃。神佑丸又來自十棗湯,繼承仲景逐水不忘顧護脾胃之意,又比十棗湯更為寒涼,以針對時弊,更能體現張子和能融會前人之言,而變通于今日之病。
6 小結
《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論述了張子和對留飲的認識。首先,從何謂“飲”討論張子和為何反對“飲為寒積”的觀點,再說明“溫補轉劇”的機理。然后,提出張子和處理水飲最在乎氣機通暢,“留者攻之”是恢復氣機暢通的方法,并以病案說明“留者攻之”有不同階段和層次,恰當使用能寓補于攻。透過比較張子和之“溫補轉劇”與張仲景之“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的治痰飲思想,可知張子和提出之治法不但沒有與仲景相違,而且繼承了“溫藥和之”的治法,對飲邪久留這一方面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