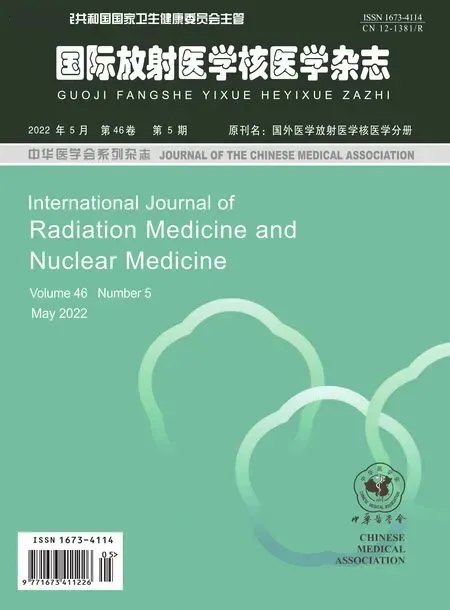早期檢測蒽環類藥物心臟毒性的影像學研究進展
王璐霞 郝新忠 王若楠 李思進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核醫學科,太原 030001
腫瘤治療技術的進步使患者生存期延長,但伴隨的不良反應也增加了其病死率[1]。其中腫瘤治療相關心功能不全(cancer therapy-related cardiac dysfunction,CTRCD)是最嚴重的不良反應,可能會使治療中斷從而影響治療效果;降低患者的生存質量甚至導致患者過早死亡[2-3]。蒽環類藥物(anthracyclines,ANTs)自20 世紀60 年代問世以來,因其抗腫瘤作用強、抗腫瘤譜廣而聞名,已作為淋巴瘤的一線治療藥物。多數淋巴瘤患者通過規范治療,生存時間可顯著延長,甚至終身治愈[4]。但ANTs 造成的不可逆的心臟損傷會影響預后[5]。有研究結果表明,在給予ANTs 多年后,超過50%的患者可發生左心室亞臨床變化[6]。若能及早發現心肌損傷并予以干預治療,患者通常恢復良好[7]。目前,CTRCD 主要根據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進行診斷[3,8-10],但尚無統一的診斷標準。歐洲腫瘤醫學會提出,當超聲心動圖測量的LVEF>50%,但與治療前相比LVEF 下降>15%時,仍可診斷為CTRCD[8]。但是有研究結果表明,LVEF 并不是一個靈敏指標,當心內膜活體組織病理學檢查已經觀察到心肌損傷時,LVEF 并未下降[11]。因此,需要選擇更加靈敏準確的技術方法對CTRCD 進行早期檢測,如超聲心動圖心肌應變成像、心臟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心肌應變成像和心肌組織定量成像以及PET/CT 顯像。本文就可能有助于早期檢測ANTs 心臟毒性的影像學新方法進行綜述。
1 超聲心動圖心肌應變成像
超聲心動圖心肌應變成像是通過二維和三維斑點追蹤(speckle tracking derived,STE)技術對心肌進行評估,其主要反映心肌力學的改變。左心室心肌應變參數包括整體縱向應變(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周向應變和徑向應變,其中GLS 是腫瘤治療期間評估心臟毒性研究最廣泛的參數[3]。多項國際共識認為,對于CTRCD 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的評估,GLS 較 LVEF 更靈敏[3,8-10]。美國超聲協會和歐洲心血管影像協會聯合發布的共識中提出,當GLS 較治療前下降>15%時,可診斷為亞臨床CTRCD[9]。一項納入1 783 例惡性腫瘤患者的薈萃分析結果顯示,與基線相比,ANTs(部分患者聯合曲妥珠單抗)化療期間GLS 受損越嚴重,患CTRCD 的風險越高[12]。
目前,GLS 并未在臨床中得到廣泛應用。其原因為通過二維STE 評估心肌應變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如斑點脫離平面運動的脫靶追蹤、長時間多點圖像采集等,這導致檢查時間過長、圖像質量參差不齊[13]。而三維STE 的技術克服了二維STE 的缺點,可同時獲得整體及局部的心肌應變參數[14]。但是三維STE 儀器供應商之間的差異和斑點追蹤軟件的頻繁升級導致無法獲得統一的參考值且無法進行多次對比,從而導致三維STE 難以被臨床廣泛接受[13,15]。盡管如此,超聲心動圖心肌應變成像仍是多項國際共識公認的早期檢測CTRCD的方法。
2 CMR 心肌應變成像和心肌組織定量成像
CMR 是評估心肌質量、心室容積及心臟收縮和舒張功能的“金標準”[16]。Tahir 等[17]的研究結果表明,CMR 的多個參數(如心肌應變參數、心肌組織定量參數等)是檢測化療患者亞臨床左心室機械變化及間質纖維化的新方法。
2.1 CMR 心肌應變成像
CMR 心肌應變技術多種多樣,其中以心臟磁共振特征追蹤(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feature tracking,CMR-FT)技術為代表。CMR-FT可以通過常規CMR 電影成像評估心肌應變,無需進行額外掃描[18]。CMR-FT 與STE 相似,都可以評價心肌力學的改變,但CMR-FT 結合了心內膜和心外膜的邊界追蹤、心肌組織內體素運動的模式追蹤,減少了對觀察者的依賴性[19]。Wang 等[20]通過CMR-FT 技術對ANTs 心臟毒性比格犬模型進行研究,結果表明,GLS 可能是早期檢測ANTs心肌損傷的標志物。Harries 等[21]的研究結果表明,與健康對照組相比,接受ANTs 治療且 LVEF正常的腫瘤幸存者的心肌GLS 明顯受損。但是該研究觀察到的變化是亞臨床的,未對受試者是否發生CTRCD 進行隨訪,因此,其臨床意義需要進一步評估。
2.2 CMR 心肌組織定量成像
ANTs 心肌病早期以心肌水腫、炎癥和空泡化為特征表現,后期以彌漫性心肌纖維化為主要表現[22]。CMR 具有獨特的無創性評估心肌組織的能力。平掃T1 值和T2 值是通過縱向弛豫時間定量成像(T1 mapping)和橫向弛豫時間定量成像(T2 mapping)獲得的心肌組織定量參數,可以反映心肌細胞微觀結構的變化,而且通過T1 mapping 還可獲得細胞外容積 (extracellular volume,ECV)值,即細胞外間質容積占整個心肌容積的百分比[23]。平掃T1 值和ECV 值可以評估心肌彌漫性纖維化,平掃 T2 值可以評估心肌細胞水腫[23]。Galán-Arriola 等[22]的動物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平掃 T2 值升高是大白豬ANTs 心臟毒性的早期表現。研究者發現,給予大白豬阿霉素6 周后平掃 T2 值顯著升高,這與心肌細胞水腫相關,而且早于LVEF 的降低;此外,當檢測到平掃 T2 值升高后停止化療可以阻止左心室功能障礙的進一步發展。Park 等[24]發現,阿霉素治療組大鼠在第6 周時出現平掃T1 值、平掃T2 值和ECV 明顯升高,而LVEF在第12 周時才顯著下降。Tahir 等[17]的前瞻性研究結果表明,39 例乳腺癌患者在表阿霉素化療結束時平掃 T1 值、平掃T2 值升高,而且平掃T1 值與LVEF≤60%聯合使用可以對后續發生的CTRCD 進行早期預測,靈敏度和特異度均達到75%以上。這些研究結果均表明,CMR 心肌組織定量成像在早期檢測ANTs 心臟毒性方面具有臨床應用潛力。
CMR 的T1 mapping 和T2 mapping 是一種有價值的非侵入性方法,可反映ANTs 心臟毒性的亞臨床組織病理學變化,但這些發現對接受ANTs 治療的腫瘤幸存者的臨床和預后價值仍需被充分證實。
3 PET/CT 顯像
3.1 18F-FDG PET/CT 顯像
ANTs 心臟毒性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主要機制是氧化應激和能量代謝損傷,可表現為心肌線粒體的損傷和心肌能量底物的改變,即脂肪酸代謝減少、葡萄糖代謝增加[25]。18F-FDG PET/CT 代謝顯像可評估各組織臟器的葡萄糖代謝活性,在臨床應用中具有獨特的優勢。18F-FDG PET/CT 腫瘤顯像時,患者需要禁食4~6 h 以抑制心肌對葡萄糖的生理性攝取,從而通過18F-FDG 攝取情況評估心臟是否出現異常糖代謝增高。因此,18F-FDG PET/CT 在評估患者病情及療效的同時也能識別心臟能量代謝的損傷。Bauckneht等[26]對69 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連續行4 次18F-FDG PET/CT顯像(化療前、化療中、化療后及隨訪期)中左心室的SUV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隨著阿霉素劑量的增加,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會增高;同時他們還進行了動物實驗,同樣發現阿霉素化療后小鼠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顯著增高,并指出這種代謝效應的劑量依賴性十分明顯,而且實驗具有可重復性。Seiffert 等[27]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在阿霉素化療前、化療中及化療后,淋巴瘤患者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總體呈上升趨勢。這2 項研究結果均表明,左心室18F-FDG的攝取隨著ANTs 劑量的增加而增高,因此,左心室18F-FDG攝取增高可能是ANTs 心臟毒性的早期跡象,而且與ANTs心臟毒性的劑量依賴性有良好的一致性。Sarocchi 等[28]發現,阿霉素化療會導致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左心室心肌18F-FDG攝取增高并與LVEF 下降有關。這進一步證明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增高與ANTs 心臟毒性有關。衛毛毛等[29]發現,18F-FDG PET/CT 能早期診斷ANTs 的心臟毒性,且以治療后心臟與本底的SUVmax比值=7.0 為閾值時,特異度可達到80%。但SUV 受禁食時間、血糖濃度、顯像時間和顯像設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且應用18F-FDG PET/CT 評價ANTs 心臟毒性需要對比分析,因此SUV 在臨床應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0]。Bauckneht 等[31]通過評分法分析36 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18F-FDG PET/CT 顯像,結果顯示,相對于SUV 的評價方法,評分法或許能改善患者和顯像設備間的可變性,使18F-FDG PET/CT 顯像成為多中心環境下預測阿霉素心臟毒性的工具。評分法可能在18F-FDG PET/CT評價ANTs 心臟毒性中更具臨床實用性,但相關研究較少,而且缺乏統一的評分標準。
此外,Borde 等[32]回顧性分析18 例淋巴瘤患者阿霉素化療前后的18F-FDG PET/CT 顯像,結果顯示,部分患者化療后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增高,并提出這可能與ANTs心臟毒性的個體易感性有關。Gorla 等[33]報道了一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男性,30 歲)接受低劑量阿霉素(320 mg)化療后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較化療前顯著增高且隨后被診斷為急性心肌損傷的病例,而2 次檢查在飲食、禁食時間(6 h)和血糖水平(分別為73 mg/dl 和82 mg/dl)等方面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因此,他們認為阿霉素化療后在18F-FDG PET/CT 顯像中,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顯著增高可能是早期發現急性心肌損傷的影像學表現。該病例報道排除了影響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的混雜因素,證明了左心室心肌18F-FDG 攝取增高與ANTs 心臟毒性相關,并驗證了ANTs心臟毒性顯著的個體差異性。
臨床中常用的評估ANTs 心臟毒性的方法都需要額外的、甚至是高昂的費用。18F-FDG PET/CT 作為腫瘤患者(尤其是淋巴瘤患者)的常用檢查方法,不僅能監測病情變化、評估治療效果,也有可能在不產生額外的檢查費用及輻射的情況下早期評價ANTs 的心臟毒性。但由于心肌代謝的復雜性[34],心肌18F-FDG 攝取的變異較大,即使在禁食4~6 h的情況下,心肌18F-FDG 攝取仍然是可變的、不一致的,這往往給臨床診斷帶來困難。有研究結果表明,延長禁食時間及低碳水化合物、高脂、高蛋白飲食等可以更好地抑制心肌18F-FDG 的生理性攝取[35],但其臨床實施的可行性仍需評估。此外,臨床中存在多重混雜因素(如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使CTRCD 對心肌代謝的影響并不是十分明確。
目前關于18F-FDG PET/CT 評價ANTs 心臟毒性的研究多為回顧性且數量較少,而且患者檢查前并沒有進行特殊準備來進一步抑制心肌18F-FDG 的生理性攝取。今后仍需大規模的前瞻性研究進一步證明其臨床意義。
3.2 其他顯像劑的PET/CT 顯像
線粒體是ANTs 心臟毒性的主要靶點[36-37],約占心肌細胞體積的35%,并且是產生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主要來源[36]。新型線粒體和ROS 的PET 分子特異性探針可以在亞細胞水平檢測心臟損傷,從而可對ANTs的心臟毒性進行早期無創性評估[38]。18F-Mitophos(一種對線粒體膜電位敏感的親脂性陽離子)和68Ga-Galmydar(一種疏水性鎵離子絡合物)是常用的線粒體靶向示蹤劑,18F-6-(4-((1-(2-fluoroethyl)-1H-1,2,3-triazol-4-yl)methoxy)phenyl)-5-methyl-5,6-dihydrophenanthridine-3,8-diamine (DHMT)是ROS靶向示蹤劑[38-39]。Sivapackiam 等[40]的動物實驗結果顯示,阿霉素治療組大鼠心臟68Ga-Galmydar 的攝取量(SUV=0.92)較對照組(SUV=1.76)低。McCluskey 等[41]的研究結果也表明,阿霉素化療組大鼠心臟18F-Mitophos 的攝取量低于對照組,而且當阿霉素劑量增加時,這一現象更加明顯。Boutagy等[39]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給予阿霉素化療的大鼠的LVEF下降之前,18F-DHMT PET/CT 顯像可檢測到心臟ROS 生成明顯增加。同時有研究結果表明,18F-DHMT PET/CT 顯像也能對大型動物模型(比格犬)心肌ROS 的產生進行絕對定量分析[42]。這些實驗研究結果均表明,PET/CT 分子顯像可在早期對ANTs 心臟毒性的代謝變化進行無創性評估。誘導心肌細胞凋亡是ANTs 心臟毒性的機制之一[37]。PET 凋亡分子顯像可在活體內觀察細胞凋亡,是一種有效的、無創性檢測方法。Su 等[43]在ANTs 心臟毒性小鼠模型中發現小鼠心肌細胞凋亡增加,18F-caspase18 攝取增高。石琴等[44]的動物研究結果表明,與阿霉素化療前及對照組相比,小鼠心臟18F-2-(5-氟-戊基)-2-甲基丙二酸(18F-ML-10)的攝取量在給藥后的第2(4 mg/kg)、9(8 mg/kg)和16 天(12 mg/kg)持續增高,而CMR 檢測獲得的LVEF 在第16 天明顯降低。前述研究結果初步表明,PET 凋亡分子顯像可用于早期評估ANTs 的心臟毒性。
在動物實驗中,PET 分子特異性探針有助于早期檢測ANTs 的心臟毒性,而且與18F-FDG 相比,干擾因素較少,具有更大的臨床轉化優勢。但是這需要在臨床受試者的前瞻性研究中進行檢驗,以確認其在人體中的顯像效果。
4 總結與展望
CTRCD 是影響腫瘤患者長期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ANTs 的心臟毒性,早期發現有助于更好地治療與恢復。超聲心動圖心肌應變、CMR 心肌應變及心肌組織定量成像、PET/CT 等先進成像方法或許能改變以往依靠LVEF來確定患者發生ANTs 心臟毒性的風險,并可能在不可逆損傷發生之前對ANTs 的心臟毒性進行早期檢測,從而改善腫瘤幸存者的臨床結局。但是這些影像學新方法的臨床和預后評估效用仍需進一步充分證實,而且在臨床工作中的實際應用仍面臨著挑戰。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無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王璐霞負責命題的提出、文獻的查閱、綜述的撰寫;郝新忠、王若楠負責綜述的審閱;李思進負責綜述的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