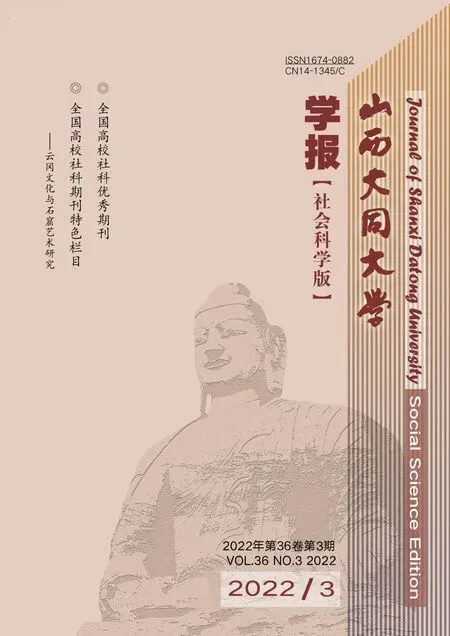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我國適用之否定
扈曉芹,樊劉佳
(太原科技大學法學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每當有低齡犯罪,特別是低齡嚴重犯罪、惡性犯罪、暴力犯罪出現的時候,社會都會重新討論我國刑事責任年齡的制定是否合理,是否應該存在一條年齡界線,以及這條界線應該劃在什么年齡才合適。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因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廣泛認可,被一些專家學者提及并倡議進行“本土化”移植,以打破我國刑事責任年齡的“僵化”規定。如秦濤教授提出,當前我國采取一種機械式的推定責任年齡制度,即未達規定年齡的兒童,即使證明其在惡劣行為時具有法規意識,也不能視同其已具備達到法定年齡的責任能力,從而被追訴。[1]而英美法系國家運用“惡意補足年齡規則”解決這一類低齡但惡性案件的責任承擔推定上就具有一定彈性,靈活許多,值得我們借鑒。[2]同時,高艷東教授也表示,在極少比例的極端惡性案件中,可以對涉案的未成年犯采取“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來遏制其產生的與年齡不相符合的社會危害性。[3]
2021年3月1日,備受關注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刑事責任年齡下調至十二周歲,年滿十二周歲的未成年人犯情節特別惡劣的故意殺人或傷害罪有望被追訴,接受刑事處罰,承擔刑事責任。這就對專家學者提出在我國適用“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觀點造成新的挑戰。那么“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真的適合我們的國情和法治環境嗎?
一、惡意補足年齡規則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Malicious supplement age),是英美法系國家刑事領域中一項預防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獨具特色的制度,極具參考價值。這一規則最初由英國律師布萊克斯通提出,他認為:未及刑事責任歸屬年齡的未成年行為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推定并不是絕對的,如若控方能提交完整閉合的“證據鏈”,以證明其在犯罪行為時確切的主觀惡意,那么其將被視為已達到可以被追訴的刑事責任年齡。[4]《布萊克法律詞典》對這一規則也作出相關說明:低于法定年齡的兒童除非有足夠佐證證明其有明確的犯罪意圖,否則將被推定為不足以承擔刑事責任。[5]
簡單來說,“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就是指不達法定刑事責任年齡起點的低齡未成年人,如若被充分且具體的“證據鏈”證明其在犯罪時主觀上持有犯罪意圖,本身具備區分對錯是非的辨別能力,客觀上又著手實行了觸犯法律的行為,“惡意”程度足以彌補年齡因素,進而使其在形式上視同達到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推定其應當被追訴承擔刑事責任。
(一)世界各國應用情況 1987年,美國國會在一項議案中提出,青少年本性善良,國家應該竭力救助感化未成年犯,不應動用刑罰手段懲罰他們,并主張重新啟用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提出建立“年齡最低區間保留”機制。[6](P230)而由美國法學會公布的《美國模范刑法典》中就列明具體條文:“7至14周歲的未成年人被推定免于追究刑事責任,除非檢方有完整有力的證據證明其的確具備犯罪能力。”[6](P231-232)加利福尼亞州、阿肯色州、華盛頓州、內華達州等在地區法中也明確保留了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且未成年案件通常都交由檢察官和法官視個案情況具體判斷,確保懲罰犯罪和保護相應的法益。[7]
馬來西亞刑法典第八十三條規定:年齡滿10周歲但不達12周歲的兒童,可以適用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如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擁有足夠成熟的理解力,足以辨認和控制自己的行為,則免除他們因刑事責任年齡而被賦予的特權,應當被定罪處罰。[8]
馬來西亞刑法典是以1860年印度刑法典為藍本的,[9]故在印度的刑法第八十三條同樣存在相似條文:“7至12周歲的低齡少年被推定不具備辨別是非的能力,擁有免除刑事責任的特權”。即,印度刑法同樣采用惡意補足年齡規則。[9]
我國香港地區現行法律體系參照的是英美法系,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同樣在其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方面占據一個較為重要的地位。根據香港《少年犯條例》規定,10歲至14歲的未成年人不絕對承擔刑事責任,只有被證明實施行為時具有犯意,并明確知曉自己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且行為本身具備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如有預謀的殺害或傷害他人等行為,該少年才可被司法機關追訴刑事責任。[9]
但是,英國作為“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發源地,卻在2009年上議院審理未成年人案件時明確10至14周歲的未成年人無刑事責任能力可推翻的推定規則不再被適用,即廢除了“惡意補足年齡規則”。[10]而英國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也進行了重新規整,由14周歲大調至10周歲。然而,有專家學者經過研究認為,“惡意補足年齡規則”被英國淘汰并非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而是其將刑事責任年齡降至10周歲,致使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失去了發揮作用的年齡空間,低齡未成年人不能再將辨認能力缺失作為借口以逃避法律制裁。[11]
那么,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與“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適用到底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呢?
(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本質 比照各國對“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適用,不難發現,這一“彈性”規則,同樣被“剛性”要求束縛,其被限定在相對負刑事責任的年齡階段中運用。同時,基本上所有國家都沒有限定犯罪類型。
每個國家,包括英美法系的國家,都規定了一個絕對不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底線,這一底線之下的兒童推定為善意且不能明辨自己的行為,并且不被任何事實證據所撼動。同樣,也存在一個負完全刑事責任的界線,界線之上的行為人按照正常程序被追訴,再無年齡“保護傘”。只有介于這兩個絕對年齡之間,被推定享有不被追究刑事責任“特權”的未成年人,惡意補足年齡制度才具備發揮價值的空間。
所以,從本質上來看,“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針對的范圍有限,僅適用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涉及的所有犯罪。因為這一年齡段中未成年人的智力、心理、識別力發展差異較大,必須采用一些規則平衡差異,以達到預防和懲治犯罪的目的,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三)與我國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關系 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分段式劃分制度與“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間存在互斥性,并行適用會產生沖突。
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重新對我國刑事責任年齡進行劃分,降低最低限度,意味著我國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具體到五段劃分模式:12周歲以下年齡段絕對免除刑事責任;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僅對情節特別惡劣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犯罪承擔嚴格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相對承擔特定的八種嚴重犯罪的刑事責任;已滿16周歲為完全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最后一點,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均處于從輕或者減輕刑事責任階段。
我國當前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為12周歲,意味著即使引用“惡意補足刑事責任年齡”,也不能對12歲以下孩子的惡性犯罪作出處罰,引入毫無意義。實現12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被追究刑責的可能只能通過再次調整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下限。因此,面對我國現有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體系,忽略降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一味地強調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來應對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缺乏司法適用價值。
我國現行的刑事責任年齡體系包含兩段相對刑事責任年齡,即12至14周歲,14至16周歲。法條中又分別對這兩個年齡段的少年行為人限定了犯罪類型,惡劣、嚴重、故意犯罪才有可能被追訴。換句話說,我們其實已經將“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內涵融合進來,就是所謂按照“惡意”懲罰未成年犯,但是“惡意”認定被大范圍限制。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針對所有犯罪,引入這一規則反而擴大了懲罰犯罪的范圍,與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從教育和保護理念相違背。
雖然“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同樣將保護未成年人作為關鍵要領,但相較于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其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更加顯著。[12]
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不可適用于我國刑事司法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英美法系國家已沿用多年,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至于是否能將其引入并適用于中國,學界也存在較大爭議。筆者認為,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英美法系國家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中固然是可行之舉,但將其引入并適用于中國刑事司法一說,還缺乏相應的環境背景與理論支撐。
(一)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差異決定了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我國適用的不可行性 眾所周知,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之間最本質的區別在于前者屬于判例法國家而后者屬于成文法國家。英美法系的法官總是從功利主義原則出發,主張在疑難個案中考量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平衡,熱衷于尋找與當前案例相似的判例,再進行具體的案例比對、區分和歸納,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生命力的重要來源在于經驗,而非邏輯。”[13]而大陸法系的法官面對案件的時候則采取從抽象到一般再到具體的三段論演繹模式,傾向于比對大前提中的法律規定和小前提中的客觀事實來得出最終的法律結論。[14]
可以看出,英美法系中的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在個案的審理中具有較強的自由裁量權和主觀臆斷性,這也是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英美法系中得以長期適用的重要因素;而大陸法系基于成文法的歷史傳統,重視實體法,強調“刑法明文規定”以及刑法典的統帥和決定性意義,從而約束刑事司法。[15]
由此可見,大陸法系總伴隨著法律條文的拘束,司法人員也僅能在法律的許可和限定之下進行司法活動。所以,未成年人在何種情況下構成犯罪、何種情況下不構成犯罪、需要承擔怎樣的刑事責任,均由刑法明文規定,司法人員在其中只是法律的踐行者而非審判者,也再次強調了惡意補足年齡規則與大陸法系的不相匹配與不相融合性。
(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與我國法律適用基本原則相矛盾 經歷了數年的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我國已形成較為完備的法律原則適用體系、適用環境,若貿然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則將面臨以下問題:
1.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沖突
眾所周知,大陸法系刑法主張罪刑法定,而我國更是遵循嚴格罪刑法定的國家,未成年人犯罪中包括刑事責任年齡、犯罪行為、損害后果及觸犯的罪名等問題均已通過刑法予以明文規定,這恰是符合罪刑法定理念的要求;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恰恰相反,其注重通過利益衡量和經驗運用對“惡意”進行認定,進而推翻“法定”的年齡限制。可見,若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將與罪刑法定產生矛盾,不利于兩者的共存與發展。
2.不符合刑法的謙抑性要求
在古代社會,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往往需采用重刑對不法行為進行壓制,因此刑法的作用集中體現在懲罰機能上。行至日益文明、日益平安的今日,刑法更應該通過發揮謙抑性來實現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平衡。我國現行刑事立法對未成年人犯罪作了詳細的規定,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人只有在相對具體的條件下才可構成犯罪進而予以處罰,已綜合考量了包括刑法謙抑性的多方面因素,而非片面的“一刀切”。同時,我國也有著較為完備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機制,如法治教育的對象正進一步擴大至未成年人家長、遺棄流浪兒童收容點、公辦工讀學校等,制定全方位預防治理方案,營造“防護無死角”社會環境,進一步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16]因此,面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若通過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來增強刑法的威懾性,則刑法本身的預防性與謙抑性也將被忽視。
3.違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
該原則是刑事訴訟中的主要基本原則之一,主張在案件存疑時應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決,雖然這里的“存疑”主要在于證據證明方面,但其中也反映了我國刑事司法對于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權利保障的重視,強調無罪推定。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強調的是有罪推定,“惡意”認定結果可以直接彌補年齡的缺失,形式上將未成年人視同已達刑事責任年齡,追訴其實施的嚴重不法行為的刑事責任。可見,從刑事訴訟的角度分析亦不足以支撐將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引入并適用。
4.“惡意”的認定缺乏縝密性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核心要義和關鍵立足點在于對“惡意”的把控。[17]現實中,對“惡意”的推定,一般以行為人實施行為時意識到“錯誤性且故意為之”為標準,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縝密性。
認識到“錯誤并故意為之”并不意味著絕對或者等于具備了違法性。拿違背道德與違反法律來分析,行為人故意實施明知是違背道德的錯誤行為也并不代表該行為人明知違背了法律的規定。
對于未成年人而言,所接受的教育有限,父母和老師只教授了“什么事情不能做”“做這些事情是不好的”,而并沒有從啟蒙教育就傳授孩子說“某某行為屬于違法行為,如果實施了某某行為將受到法律的制裁”等等。現有的對“惡意”的認定和判斷的經驗和標準過于片面,所以不能過高期望未成年人具備邏輯清晰的違法性認識。
5.與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國情不相適應
立足于當前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態勢,未成年人心智教育、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手段、未成年人成長環境均存在顯著差別。2013年我國未成年犯抽樣調查分析報告中顯示,不同的成長環境下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存在很大差異,鄉村和“城中村”為67%,而機關與學校僅是2.3%。[18]
在這一背景下,綜合多方面因素重新審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顯得格外重要。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率顯著高于我國兒童犯罪率的平均水平,而生活環境以及社會、家庭的關愛等方面又是導致犯罪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間幾乎呈現正相關依附關系。且,低齡未成年人并非屬于高犯罪率群體,其實施犯罪行為的情況仍屬特別案例,占總犯罪率的小份額比例,所以,也就沒有必要揮舞著刑罰的“大棒”對其嚴加規制。[19]雖然我國已基本消除貧困,國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留守兒童、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民生問題依然存在,而作為法律底線的刑罰不應涉足過多。農村留守兒童是未成年犯罪的高發人群,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可能會造成城鄉歧視,破壞刑法的謙抑性。
綜上所述,無論從法系層面、法律原則或是國情方面對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可行性進行分析,都難以得出相對牢固的理論依據,因此,筆者認為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上并不適用。
三、我國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是解決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行之舉
面對近年頻發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我國刑事立法作出了迅速的反應,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重新規整刑事責任年齡的劃分范圍,將最低法定年齡門檻調整至12周歲,并增補了12周歲至14周歲未成年人犯罪的具體情形。相較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我國對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以及調整顯得更符合我國實際情況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解決路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調整體現了刑法的適應性與靈活性 近年來,未成年人惡性行為事件屢屢出現在網絡熱搜中,如2019年10月大連的13歲男童強奸未遂、殺害10歲女孩小琪(化名),拋尸花壇,因加害人尚且不足14周歲,屬于受絕對保護的未成年人,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20]又如2018年湖南的12歲男孩不服母親嚴厲管教,持刀弒母,因不達年齡被釋放,由家長接回監管。[21]這一系列惡性事件被廣泛關注,民眾秉持“有罪必罰”的樸素正義觀,廣泛聚集討論,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社會輿論呼聲愈演愈烈。
與1979年相比,當下的中國無論是經濟背景還是教育條件都發生了覆天翻地的變化,青少年較之40余年前的同齡人而言,其生理、認知和辨認能力都得到了極大地提升,現下部分12歲的未成年人對事物的分析辨別、法條的理解與責任的承擔能力甚至遠超于過去14歲的未成年人,所以我國刑事責任年齡下限一直維持在14周歲。[22]對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重新規整,充分體現了刑法的發展必須適應社會的進步這一靈活性。
(二)刑事責任年齡的具體規定反映出我國在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上規言矩步的態度 我國現行刑事責任年齡體系比較嚴格,劃分為五個階段,但無論是哪一階段,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規定都是較為詳細具體的。
目前最為引人注意的就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亮點,即情節惡劣,呈現極大惡意的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可以被追訴,承擔相對應的刑事責任,這其中包含了兩個要件:一是實體要件,即涉及的犯罪僅限于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罪,且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要求致人死亡、重傷、嚴重殘疾;二是程序要件,即需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也就是說,需要同時滿足上述的實體要件和程序要件才可以追訴“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可見,對年齡越低的未成年人犯罪,我國刑法的規定就越謹慎,態度越嚴謹,規言矩步,決不允許超乎法度。
結語
法律對于很多的群體是有特別規則的,尤其是未成年人,因為他們是一個國家生命力的體現,他們代表著希望,幫助他們走上光明的前途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初衷。懲罰從來都不是最優手段,“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并不適用于我國,本土化移植會沖擊目前穩定的少年刑事司法體系,引發“水土不服”。況且,我國當前刑事年齡制度事實上已經將“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最優內容納入其中并加以具體限制,即,嚴重“惡意”足以被處罰。降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的最優措施,立足于我國國情,足以應對當前以及未來很長時間內出現的未成年人犯罪矯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