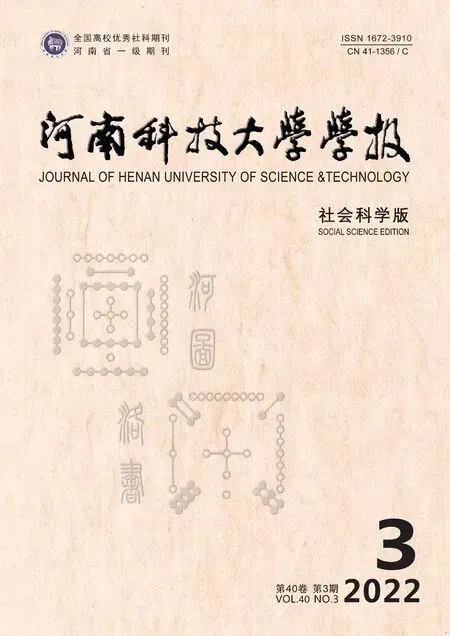文化資本視角下黃河文化傳承與發(fā)展路徑探析
張文博,劉禹堯
(1.河南省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 產業(yè)研究所,鄭州 450003;2.吉林大學 商學院,長春 130012)
在中華上下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黃河流域占據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區(qū)域長達3000多年[1],并且孕育了輝煌的古人類文明。地處黃河流域的河南地處中原,歷史底蘊深厚,鄭州、開封、洛陽和安陽均屬于中國八大古都之列,集聚了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本。但作為其中重要部分的黃河文化卻出現了傳承斷層,青年一代追逐流行文化,社會注重經濟發(fā)展,忽略了對于黃河文化的傳承和保護。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黃河文化保護、傳承和弘揚將成為黃河流域各省市各項工作的重點之一。黃河文化的概念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理解。宏觀上的黃河文化包括黃河流域勞動人民在生產生活實踐活動中創(chuàng)造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內容和范圍很廣;微觀的黃河文化是指黃河流域生存和工作的人民所具有的精神訴求、價值取向、基本理論以及行為方式的綜合[2],主要與意識形態(tài)有關,內容單一、范圍較窄。不僅包括“民為邦本”“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思想,還包括自強不息、敢于拼搏、勤勞務實、開拓進取等民族精神。黃河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fā)揚需要從多方位出發(fā),創(chuàng)新方法,在黃河文化保護、傳承和發(fā)揚中以廣義黃河文化為基礎,從社會、教育和經濟等文化資本三個角度探討黃河文化的作用機制以及傳承和發(fā)展方法。
一、理論基礎
對于文化資本的概念,學術界還沒有達成共識。文化資本不僅指文化與文化生產、傳播、發(fā)展等活動中的無形資產,也包括相關的有形資產。隨著文化資本的概念在不同學科領域廣泛應用,概念內涵也呈現多元化傾向。文化資本并不是一個實體性概念,而是功能性概念[3]。黃河文化資本不是指其本身,而是指黃河文化所能發(fā)揮的作用。社會學、教育學、經濟學分別從階層、教育和經濟發(fā)展角度對文化資本進行定義。
(一)社會學文化資本
社會學領域文化資本(以下簡稱社會文化資本)通過改變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階層等方式來影響社會發(fā)展。布爾迪厄在《區(qū)隔》中提出文化資本具有傳統(tǒng)資本的功能,可以用于投資,但與傳統(tǒng)資本不同的是,文化資本投資的結果是產生權力。隨著知識滲入經濟和社會,文化與經濟、文化與社會的聯(lián)動發(fā)展提高了文化資本的價值,文化資本日益成為一種統(tǒng)治階級的資本。郭桂周、易娜伊和趙忠平認為文化資本具有強大的再生產能力,同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一樣可以完成社會現有秩序和不平等的再生產,還可以通過隱蔽的方式實現現有秩序合法化[3]。文化資本投資形成的權力可以改變社會秩序,統(tǒng)治階層可以通過文化輸出加深社會大眾對現有社會秩序的認知,進而促進現有社會秩序的合法化或者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實現文化資本增值。
不同階層獲得文化資本的數量和質量也存在差異。喬納森·特納認為文化資本是特定群體在交往過程中表現出的行為習慣、語言風格、生活方式和價值信仰等[4]。通過特定場域、資本與習性之間的交集所產生的文化趣味體現了階層屬性,在這種階層屬性文化培養(yǎng)下所形成的習慣、語言等也體現了階層屬性,加劇了由物質資本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國內目前還沒有固化的階層文化,因此通過文化資本增強社會各階層的共通感,調節(jié)文化資本“二次分配”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黃河文化歷經具有嚴格階級差距的封建社會,但隨著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黃河文化也隨之不斷發(fā)展變化,其所具有的階級屬性被削弱。當下所傳承的黃河文化是人民的文化,不以物質基礎、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出現顯著差異,而以黃河文化為基礎培養(yǎng)的行為、習慣等體現人民的意識。
(二)教育學文化資本
教育學領域中的文化資本(以下簡稱教育文化資本)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通過教育積累文化資本,培養(yǎng)受教育群體的慣習和認知性,以達到文化資本增值的目的。文化資本對于教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兩方面。從社會教育角度來講,詹姆斯·費雪強調了文化資本的價值增值屬性,認為文化資本實際上是個人為了既定目標而不斷完善自身并對自身增加教育投資所獲得的文化能力,突出了教育是文化資本積累的重要方式。胡安寧認為“階層地位—文化資本—學校環(huán)境—學業(yè)成就”正向單向遞進,是教育文化資本增值的邏輯,缺少任何一環(huán),文化資本增值都會受到影響[5]。但是黃河文化資本的增值作用不只在于學業(yè)成就,更在于個人品性、思維和意識等,因此其受此邏輯的影響較小。這也意味著社會黃河文化教育既不受階層限制,又可以形式多樣,促進發(fā)展“普惠”文化資本。
布爾迪厄最早從社會學和教育學視角提出,文化資本是能夠通過時間和代際傳遞而在社會場域中積累、轉換和傳承的資本形式[6],并最終以教育資質的形式制度化。徐望認為通過家庭教育所積累的文化資本可以作為隱性非物質財富不斷傳承[7],這種特有的文化資本有助于自身發(fā)展和晉升。郭桂周、易娜伊和趙忠平則認為這種家庭教育可以是家庭生活中有意識、無意識的言傳身教,通過潛移默化的影響實現文化資本的再生產[3]。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文化水平、教育背景、生活水平等都會影響文化資本代際積累。不同于社會教育,家庭教育有顯著的差異和壁壘,當下許多家庭對黃河文化的重視程度不足,家庭教育對于黃河文化資本的積累還需不斷提高。
(三)經濟學文化資本
從經濟學角度講,文化資本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密不可分。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戴維·思羅斯比認為文化資本實際上是文化價值的積累,這種積累外在表現為財富并可能會引起物品或服務的不斷流動,與此同時會形成本身具有文化和經濟雙重價值的商品[8]。思羅斯比強調了文化資本財富的形式以及價值增值。李沛新較早將文化資本的概念具體化,將其分為建筑和文物、文化產品以及文化資源三個部分[9]。
文化資本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封福育和李娟利用中國2010—2017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fā)現,文化資本積累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10]。進一步分析表明,文化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階段不同,經濟增長受文化資本影響的程度也不同,受社會發(fā)展狀況、政治制度、經濟發(fā)展水平、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與金融資本一樣,文化資本也存在差別,這種差別不僅表現在數量方面,也表現在質量方面[10]。在當今信息化時代,加強傳統(tǒng)文化與信息技術的結合,才能使傳統(tǒng)文化保持競爭力。文化資本作為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內容,能顯著提高經濟增長數量,但市場文化資本卻導致了較低的經濟增長質量[11]。白濤和李萍分別從文化資本的構成內容以及其在新型城鎮(zhèn)化中的作用闡釋了文化資本對經濟發(fā)展的作用[12-13]。為進一步提高中國經濟增長效率,李娟偉認為不僅要提高文化資本水平,還要促進不同文化理念之間的融合[14]。黃河文化也可以作為經濟財富參與經濟發(fā)展,但是黃河文化資本要實現持續(xù)升值就必須與時代和社會發(fā)展相融合。
社會文化資本、教育文化資本與經濟學領域文化資本(以下簡稱經濟文化資本)可以相互促進發(fā)展。教育可以作為社會和經濟文化資本積累的重要方式,社會和經濟文化資本可以為教育文化資本積累提供平臺和資源。
二、黃河文化資本的作用機制
(一)社會學領域黃河文化資本
社會對于黃河文化的需求源于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隨著信息科技發(fā)展,網絡自媒體技術逐漸成熟,由此涌現出一系列社交媒體,擴大了價值觀念的影響,思想意識領域成為政府維護社會秩序的重點領域。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借助網絡媒體逐步滲入,影響社會價值觀,加劇“網絡暴力”“社會威脅”等,擾亂社會秩序。
對于社會秩序的研究,康德提出社會秩序就是符合常規(guī)的觀念。我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秩序一直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必然要素,“禮”作為封建社會不斷發(fā)展積累的文化資本,就像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為人們理出合乎道德的經濟秩序[15]。它不僅僅是一種個體行為規(guī)范,也是一種社會秩序,黃河文化也包括很多禮的部分。雖然很多禮制已經不符合當下的社會發(fā)展要求,但是禮制的理念對維護社會秩序依然很重要,愛國、重孝、親友等依然是當下社會必須遵循的秩序。在新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信息化和工業(yè)化打破了原來的小農經濟體制,城鎮(zhèn)化也打破了原來傳統(tǒng)鄉(xiāng)土為主的社會格局。黃河文化經過千年傳承和積淀形成了豐厚的黃河文化資本,這種資本與社會相融合并影響社會運行,黃河文化資本可以通過隱蔽的方式實現現有秩序的合法化。黃河文化源于勞動人民的社會實踐,蘊含勞動人民精耕細作的思維和意識。同時,黃河文化歷經多次王朝更替,也蘊含了統(tǒng)治階層民為邦本、天人合一、仁政、禮法并舉等國家治理思想。它與新的社會文化相結合形成新的文化資本,這種文化資本既符合社會工薪階層的利益,也符合政府等社會治理者的利益。經過代際傳遞和不斷創(chuàng)新融合,黃河文化資本可以貫通政府的統(tǒng)籌思維與群眾的慣性思維,既能讓政府把握社會問題下群眾的思想,也能讓群眾理解政策背后政府的思想。黃河文化資本化為潛在的社會秩序,表現為主流的意識和行為,政府考慮到打破現有秩序的機會成本,在制定政策時勢必會考慮社會潛在秩序,促進現有秩序合法化。黃河文化由于是一種公有的文化財富,因此社會領域黃河文化資本的作用還在于拉近由經濟資本所劃分的社會潛在階層,在精神層面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互聯(lián)網的普及,使得網絡社會在傳統(tǒng)社會基礎上逐漸發(fā)展壯大,影響范圍和速度不斷提高,建立和完善網絡社會秩序成為社會治理的重點。網絡社會雖然在社會結構、人員構成、運行方式等方面與傳統(tǒng)社會有很大差距,但是參與網絡社會的人具有共通的思想意識。針對網絡社會中出現的去中心化、身體缺場、貨幣崇拜等一系列問題[16],社會領域黃河文化資本同樣可以滲入網絡社會,依靠資本力量建立以大眾社會道德和公德為基礎的潛在秩序,強化國家倡導性價值規(guī)范和主導性信仰體系,增強網絡社會道德控制系統(tǒng),維護網絡社會秩序。黃河文化資本既要引導網絡主流文化思維,又要積極融入互聯(lián)網,運用互聯(lián)網發(fā)展新的黃河文化資本。
社會學文化資本還體現在城市發(fā)展方面,城市之間也會因為經濟發(fā)展差異出現潛在“階層”。城市之間的模仿會導致不同城市建設和發(fā)展模式趨于統(tǒng)一,中西部城市過度模仿沿海城市,大規(guī)模拆舊建新,忽略了地域文化差異。經濟高質量發(fā)展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然是社會發(fā)展的重點,但是城市發(fā)展不能忽略文化因素,脫離文化底蘊的城市發(fā)展模式很難建立有地方特色的發(fā)展道路。黃河流域內不同城市的黃河文化地域差異顯著,這些差異化的黃河文化會形成差異化的文化資本。獨特的黃河文化資本融入城市發(fā)展中,通過打造獨特的城市品牌,形成鮮明的城市特色,維護城市發(fā)展多樣性,緩解由于城市經濟發(fā)展造成的潛在“階層”差異,實現文化資本價值增值。
(二)教育學領域黃河文化資本
黃河文化通過培養(yǎng)青年良好的品質、健康的思維和意識,可以彌補國內外流行文化的缺失。相較于傳統(tǒng)文化,流行文化對新一代青年的影響更深,這種影響可能源于流行文化為自我意識強烈、渴望自我表現的青年學生提供更多展示個性、表達情感的機會,也與當下學校注重培養(yǎng)青年個性化的性格有重要聯(lián)系[17]。流行文化還進一步打破了社會文化之間隱性的“階層”差異,極大地滿足了青年群體迫于社會壓力而產生的斗爭和反抗心理。流行文化的“標新立異”傾向在迎合青年追求個性與自我實現的同時[18],也使得部分青年更加浮躁、膚淺。同時,過度追求個性化還削弱了集體意識。在國內流行文化逐步加大對青少年的影響時,外來流行文化也開始扎根,青少年是受外來文化影響最深的群體,西方文化依托各種消費品借助發(fā)達的國內國際物流體系以及網絡自媒體滲入青年的生活,影響他們的思維和價值判斷。
黃河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代表,經過千年的沉淀和積累,凝結了無數勞動人民的智慧,具有豐厚的文化底蘊。青年在學習黃河文化的過程中,應通過黃河文化教育把握黃河文化脈絡、了解黃河知識、感受黃河文化精神,將黃河文化內化于自身意識和精神領域,培養(yǎng)青年沉穩(wěn)、耐心、自信等優(yōu)良品質,逐步形成自身獨特的慣習和認知,這種獨特的慣習和認知就是通過黃河文化教育積累的文化資本。在實踐中個人獨特的慣習和認知通過在特定時刻發(fā)揮作用,實現文化資本價值增值。黃河文化資本蘊含的勤勞務實、團結統(tǒng)一、自強不息等民族精神,通過增強集體意識、削弱享受心理、培養(yǎng)民族文化理念等方式完善青年品質來發(fā)揮其資本效益,健全的精神品質為工作、社交、生活等提供精神動力并推動實現文化資本價值增值。
同時,當今社會中出現的“網抑云”“無效內卷”等社會病態(tài)現象以及社會公眾人物“道德無底線”現象,都體現了在物質資本極大豐富的背景下,文化資本較為嚴重的缺失。教育是個人文化資本積累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之一,義務教育階段家庭和學校的影響讓個人開始具有自身獨特的慣習和認知,此時黃河文化更多以知識積累為主,家庭教育也可逐步滲透,家庭教育所積累的文化資本會影響其生活的基本判斷;高中和大學階段個人的認知和慣習初步形成,在黃河文化知識積累的過程中,可以體會和學習黃河文化精神,使個人黃河文化資本積累達到一定高度。黃河文化教育形成文化資本并不只發(fā)生在義務教育、高中、大學等學校教育階段,還會發(fā)生在其他社會教育階段。社會和家庭教育所積累的文化資本,可以改善物質資本所誘發(fā)的精神亞健康,防止跌入物欲陷阱,培養(yǎng)積極向上的心態(tài),建立基本道德底線,提高自我約束和控制力。黃河文化中也不乏杜甫、王維、李商隱等愛國詩人,也有王安石、房玄齡等仕途艱辛但忠貞愛國的丞相,還有晉商、豫商等物質資本豐厚的誠信商幫等,這些文化資本可以通過類似“保險機制”發(fā)揮作用,通過提前積累文化資本,在面對潛在問題時發(fā)揮作用,降低因個人價值觀偏差而造成不可挽救的風險。
(三)經濟學領域黃河文化資本
從經濟學角度講,文化資本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參考李沛新對經濟學領域文化資本的分類[9],根據文化資本的物理形態(tài)將其分為三類,一是完全物質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主要指賦予文化意義的并用于文化商品生產的自然風光、古代建筑、文化遺址等固態(tài)的文化資本;二是具有雙重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這類文化資本既有物質形態(tài)也有非物質形態(tài),包括繪畫、戲曲、民謠、雕刻等文化資源;三是完全意識領域的文化資本,主要指融通并蘊藏于個體精神或身體的各種思想、方法、理論、故事等文化資源。
黃河文化包含龍門石窟、仰韶文化遺址、少林寺、殷墟遺址、兵馬俑等固體文化資本,這些文化資本以載體形式承載歷史,以載體內蘊藏的歷史文化,通過社會群體對于歷史的好奇和探索以及歷史文化內在的牽引力吸引游客,帶動文化旅游產業(yè)發(fā)展,同時帶動餐飲、服務等相關產業(yè)發(fā)展,實現文化資本價值增值。但是隨著歷史被不斷發(fā)掘,歷史文化的神秘感持續(xù)減弱,特別是文化旅游模式過度商業(yè)化和同質化,沖淡了文化氛圍,極大削弱了文化資本的增值能力。各個地方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迎合社會流量,過度開發(fā)黃河文化,強行賦予歷史背景,造成黃河文化資本不良發(fā)展,甚至出現劣質資本驅逐優(yōu)質資本的現象,不利于主流黃河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另外,還有一些地區(qū)對于黃河文化資本保護力度不夠,出現兩個極端,一是沒有充分認識到這類文化資本的價值,導致文化遺址無人保護,受到人為和外在因素破壞;二是過于追求文化資本所產生的經濟收益,導致過度開發(fā),不利于文化資本的可持續(xù)增值。
黃河文化中流傳下來的圖書、繪畫、戲劇等文化資源,既有物質形態(tài)的作品也有非物質形態(tài)的傳統(tǒng)技藝,集中展示了黃河流域人民的精神風貌、民風民俗等,具有高度的文化價值。這類文化資本部分可以作為商品直接進行交易,并且憑借其文化內涵以及稀缺性,實現價值增值;部分則被收藏入各地博物館或紀念館等,作為文物收藏、展示和宣傳,通過與文化旅游相結合實現文化資本增值;還可以作為生產方式,用于經濟投資,與實體經濟相結合實現價值增值。黃河流域各朝代流傳下來的官窯瓷器、名家書畫等用于交易或收藏,因其獨特的歷史內涵和供給側的稀缺,帶動了拍賣行業(yè)的發(fā)展;清明上河圖、唐宮仕女圖、后母戊鼎等國寶級文物被博物館收藏用于展覽,提升了國家形象、展示文化魅力、帶動了文化旅游業(yè)等實現文化資本增值,也推動了文化博覽業(yè)。年畫、燒瓷、剪紙等傳統(tǒng)工藝通過與實體產業(yè)相結合,以其成熟的、市場稀缺的生產方式作為文化資本投資于實體經濟,并通過獲得經濟收益或削減生產成本實現文化資本升值。
完全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可以通過打造文化品牌促進經濟發(fā)展。文化資本作為要素投入社會生產,與特定產品相結合形成具有獨特文化底蘊的品牌來實現文化資本增值。促進文化資本與文化產業(yè)、工業(yè)、服務業(yè)等融合,創(chuàng)新發(fā)展模式,打造新的文化品牌,是文化資本增值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傳統(tǒng)產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方式。特別是以青年為主要群體的青年流行文化更注重人的個體意識[19],在這種文化影響下,青年群體對商品的品牌及其文化需要更為敏感[20],更注重時尚元素。當下比較成功的模式是將歷史文化故事融入經濟生產之中,充分利用文化資本對產品進行包裝,利用文化之間的共通,吸引消費群體注意,促進消費。當下市場同類產品較多,部分產品質量提升空間較小,如何在市場競爭中擴大自身優(yōu)勢、提高競爭力是促進發(fā)展必須思考的問題。黃河文化資本包含商、三國、唐、宋等朝代無數先進的文化思想、文化故事、民族精神,黃河文化資本雄厚。黃河流域特色農業(yè)、釀酒業(yè)、餐飲業(yè)等產業(yè)眾多,但是這些產業(yè)分布較為分散,缺乏特色和影響力,再加上疫情沖擊,無法形成規(guī)模效益。充分發(fā)揮黃河文化作用,探索產業(yè)和文化資本的結合路徑,將文化要素投入產品生產,塑造獨特品牌文化,在實現傳統(tǒng)產業(yè)升級的同時實現文化資本增值。
(四)黃河文化資本相互促進發(fā)展
三個領域的文化資本可以相互促進以推動黃河文化的傳承和保護。社會和教育文化資本聯(lián)系緊密,教育文化資本積累和增值是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方式,通過教育積累的文化資本在達到質變時會促進物質資本積累,以消耗教育文化資本為基礎物質資本的提升可以提高社會地位,從提升精神層次向提高社會層次轉變。通過教育積累的文化資本形成獨立的思維和意識并實現增值后,這種文化資本會被不斷傳承,經過不斷的傳承和積累形成特定的社會文化資本。同時,社會文化資本可以通過改善學習環(huán)境、增加文化教育資源、提高學習效率等加速教育文化資本積累。
社會文化資本、教育文化資本與經濟文化資本可以相互促進發(fā)展。社會黃河文化資本和教育黃河文化資本通過加強黃河文化消費,以黃河文化消費帶動黃河文化生產和投資,促進經濟文化資本發(fā)展,經濟黃河文化資本通過增強文化產業(yè)、引導文化市場走向、增強文化品牌影響力等引導社會文化學習氛圍,提高文化隱性地位,促進社會文化資本和教育文化資本積累和增值。
三、黃河文化傳承與發(fā)揚
(一)加強黃河文化教育
不同于依靠勞動力數量的傳統(tǒng)密集型勞動資本,經濟高質量發(fā)展離不開勞動者的知識儲備和綜合素質。大力發(fā)展黃河文化教育不僅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綜合素質,緩解社會勞動力供需不平衡的問題,提高社會就業(yè)率,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9],還有利于黃河文化資本積累,促進黃河文化傳承和發(fā)揚。
從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兩個方面加強黃河文化教育。社會教育既包括義務教育階段、高中以及大學等,還包括主要依靠日常工作生活的學習、實踐和沉淀。家庭教育則是家庭內代際之間黃河文化的傳承。對于黃河文化的學習主要在于領悟黃河文化精神、學習黃河文化知識,兩者缺一不可。脫離黃河文化精神僅憑黃河知識累積所形成的文化資本很難實現價值增值,缺乏黃河文化知識的黃河文化精神很難持續(xù)和應用。
黃河文化教育要打破傳統(tǒng)形式,從傳道解惑到實踐體驗,除了增加黃河文化相關課程外,還可以采取辯論、演講、討論等多樣化的形式,增加社會實踐,引導青少年重視黃河文化、正確看待黃河文化和流行文化,營造學習黃河文化的良好氛圍。家庭教育則更多的是在耳濡目染之中傳承黃河文化精神,可通過旅游、電影等方式促進青少年學習和了解黃河文化,父母參與黃河文化教育,傳遞社會資本是影響黃河文化代際傳承的重要因素。
(二)加大黃河文化投資
加強黃河文化投資可以促進黃河經濟文化資本積累。部分黃河文化缺乏載體,文化開發(fā)程度不足,再加上傳承斷層,很多優(yōu)秀黃河文化已經消失。通過增加文化投資建設文化載體、維護和修繕文化遺產、建設黃河文化傳承和發(fā)展平臺等,發(fā)展文化產業(yè),以產業(yè)為基礎更好地傳承和發(fā)揚黃河文化。黃河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也會進一步促進文化產業(yè)發(fā)展,從而有效促進文化資本積累。
文化投資離不開文化市場,并以具體的文化產業(yè)為載體,文化投資、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yè)相互協(xié)調才能促進文化經濟高質量發(fā)展。文化市場是刺激黃河文化發(fā)展的內生動力,文化市場可以引導社會資本投向黃河文化產業(yè),促進社會發(fā)展黃河文化消費品、影視、旅游、文化服務等,加速經濟文化資本積累。經濟文化資本的利益導向,吸引社會研究和發(fā)展黃河文化,在社會營造學習黃河文化的良好氛圍,促進黃河文化的傳承和發(fā)揚。文化市場可以分為兩部分[21],一部分是以產品為主的文化產品市場,另一部分是潛在的文化要素市場。兩個市場相互促進,文化要素市場為文化產品市場提供多元要素促進其多樣發(fā)展,文化產品市場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也有利于文化要素市場的有序流動與拓展,黃河文化投資會促進文化要素市場中資本要素的積累和流動,為黃河文化產品市場的發(fā)展提供資本支撐,同時黃河文化要素市場的積累和流動以及黃河文化產品市場的發(fā)展也會源源不斷的吸引投資,在外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huán),促進黃河文化發(fā)展。
黃河文化具有獨特性、稀缺性以及影響力廣等特點,在發(fā)展過程中社會主體不能僅關注黃河文化的經濟價值,還需關注其社會價值。為了促進黃河文化更好地傳承和發(fā)揚,保持其影響力,黃河文化投資不能完全由市場決定,還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導。政府意向也是促進黃河文化傳承和發(fā)揚的重要方式。從國內市場來看,經濟投資者會充分考慮政府發(fā)展導向,利用政府政策優(yōu)勢降低投資成本和投資風險,保障利潤最大化。政府對于黃河文化的定位、重要性認知以及發(fā)展愿景等都會影響黃河文化投資的政策走向,進而影響黃河文化投資。黃河流域各地市政府在城市建設、空間布局、產業(yè)定位等方面融入黃河文化,加大對黃河文化的投資,同時引領社會投資者投資黃河文化,從而促進黃河文化發(fā)展。
(三)促進黃河文化與科技融合
數字信息產業(yè)、互聯(lián)網科技產業(yè)等規(guī)模不斷擴張、貢獻不斷增強,已成為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增長極,文化與科技的融合與利用已成為當前我國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新趨向[22]。傳統(tǒng)的文化產業(yè)已經不能滿足人民的多樣文化需求,在有限的文化資源條件下只有通過運用高新科技手段促進文化生產方式變革,才能更大程度上服務不同的群體,為青少年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的文化學習環(huán)境,促進文化的傳承和發(fā)揚。利用數字科技還可以挖掘文化產業(yè)潛在的價值,實現文化資本積累,促進文化資本溢出。
黃河文化與科技融合可以增加黃河文化展現形式,豐富黃河文化載體,更新黃河文化保護機制,加速黃河文化傳播等。綜合利用各種數字化工具、互聯(lián)網、5D等科技將現有黃河文化遺產以視頻、聲頻、文字、圖片等多種形式加以展示,創(chuàng)新黃河文化體驗方式。各地政府從理論、機制與平臺三個角度構建黃河文化保護機制,充分利用數字化手段完善黃河文化保護機制,加強保護的數字化與信息化,保障黃河文化遺產充分保護和高效利用。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等一系列新型媒介推進黃河文化傳播,借鑒《我在故宮修文物》《國家寶藏》等優(yōu)質紀錄片和綜藝,更多以青少年的視角講解黃河文化、再現黃河文化、品味黃河文化,利用大眾演員、體育明星等拉近黃河文化與大眾的距離,促進黃河文化傳承和發(fā)揚。
黃河文化與科技融合,可以充分發(fā)揮黃河文化資本的作用,將新經濟發(fā)展與地方文化特色相融合,不僅有利于構建地方特色經濟,打造黃河流域各具特色的經濟文化名城,還有利于新經濟與地方經濟融合,利用黃河文化的群眾基礎為新經濟發(fā)展開拓市場。建立由數字技術研發(fā)、歷史文化探索和解讀、大眾媒體傳播等多方聯(lián)合的文化協(xié)同創(chuàng)新平臺,支撐黃河文化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