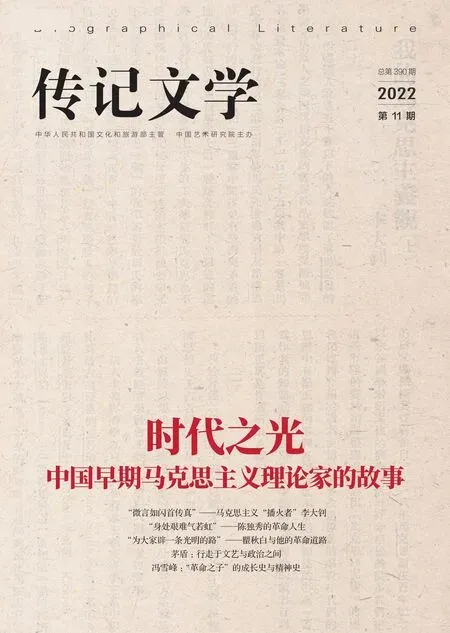國家古籍事業的傳薪者們
劉仝保
2022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加強文物古籍保護利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這是中央政府在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及“古籍保護利用”,古籍保護正迎來春天。實施古籍保護利用,版本知識尤為重要。版本目錄是指著錄圖書的篇目和主要內容,包括圖書作者或編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況,以便考辨其源流,版本目錄學作為我國的一項傳統學問,對學術研究、整理古籍都有著重要參考價值。在學習、工作中,我結識了古籍版本學家郭紀森、馬春懷,古籍文獻鑒定學家吳希賢、張宗序,還有外文版本學家種金明等,他們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國家古籍事業。
與這些老先生們的交往,源于我在家鄉河北省冀縣讀中學階段喜好搜集民俗與地方名人史料。我請方志辦的常來樹老師引薦,結識了郭紀森先生,郭先生為我撰寫了一些琉璃廠衡水籍人士的傳略信息,此后便保持通信多年。隨后,我又陸續認識了其他幾位先生。他們共同的特點是,都從十五六歲的販夫走卒成長為享譽時代的版本學家,甚至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重要成員。
第一次見到郭紀森先生是在他返鄉省親的女兒家,那時我也就十五六歲,他卻已是耄耋高齡。魁梧的身材絲毫不見彎腰駝背的老態,只是花白寸發和臉上的皺紋彰顯著經歷的滄桑,濃密的長壽眉下雙目炯炯傳神,一口冀縣話透出絲絲京腔的味道,慢聲細語,但渾厚響亮,說話必是以“您”開頭,且身體微微前傾,一副和顏悅色的儒雅形象。
同是在十五六歲的年紀,郭先生卻因家境貧寒離開了老家郭家莊的私塾,由叔父郭恒利引薦到北京隆福寺的古舊書店稽古堂當了學徒工,三年后出師做伙計。1939 年,他被琉璃廠書鋪勤有堂聘為副經理。1943 年,他在西琉璃廠從孟慶德手中接過開通書社,自任經理主營大部頭古書和考古類圖書。1956年“公私合營”后,開通書社并入中國書店,他出任琉璃廠古籍書店副經理。1981 年10 月退休后,他被中國書店聘為首批業務顧問,1992年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郭先生畢生從事古舊書事業80 多年,從未改過行,憑借著一身過硬的“過眼學”,經手流通的古籍圖書難以數計,如今全國各大圖書館和教授們的書齋中,很多都有他所提供的古籍圖書資料。
眾所周知,琉璃廠作為文化意義上的特色街區,是明末清初因官員和京外趕考的舉人流連在此逛書肆而起。在中國沒有公共圖書館概念之前,書肆就扮演了其功能。
郭先生一生都奉獻在琉璃廠這座開放的“大圖書館”上,并創造了諸多佳話,整個古舊書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尤其是他在與學者交往中表現出的深明大義更是傳為美談。
郭先生曾親口跟我講過,很多學者都委托他尋購過稀世版本。如金石考古家容庚編纂《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歷史學家顧頡剛編纂《禹貢》刊,考古學家胡厚宣編《甲骨文合集》,民族史學家翁獨健標點《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古典文學專家顧學頡編注《白香山詩集注》,等等,都有他提供的珍貴古書資料。另外,郭先生和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洪煨蓮長達30 余年的書緣往事,更令學術界和古舊書行擊節嘆賞。
2009 年11 月22 日,洪煨蓮先生的學生、我國歷史地理學開創者侯仁之先生的女兒侯馥興,在一篇回憶錄中詳實披露了這件事。
20 世紀30 年代,郭紀森在琉璃廠稽古堂書攤上結識了洪煨蓮,知道他是研究中外歷史的知名學者,時任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主任。“凡是他所需求的,我都盡力去辦,便取得了他的賞識和信任。”據郭先生回憶,根據洪煨蓮的需求,自己為他提供了《四部叢刊》初、二、三編,《靜嘉堂秘籍志》明初蜀藩刻本,萬歷張之象刻本《史通》等大量典籍史料。由于得到郭先生及時、專業的幫助,洪煨蓮編撰我國古籍經、史、子、集的各種“引得”才得以順利進行,后來共出版64 種、81 冊,至今仍為國內外學術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書。
1941 年,燕京大學被日寇占領封鎖,洪煨蓮遭日本憲兵逮捕入獄,郭先生主動幫助洪家整理存書并搬至城內。洪煨蓮出獄后仍被日軍監視,郭先生不避危險,受其委托給洪煨蓮的學生侯仁之捎去口信,要他寧死不替日本人做事。1945 年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學復校,洪煨蓮回校工作,郭先生又幫他從城里把藏書搬回燕南園洪宅。1946 年,洪煨蓮應聘赴哈佛大學講學,行前托郭先生購買了一批圖書,孰料一去幾十年未回國。郭先生保存這些圖書直到中美建交后,才遵洪囑交其親屬捐獻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1980 年3 月29 日,洪煨蓮又托侯仁之的夫人張瑋瑛從美國帶來委托書,把他在北京琉璃廠的一處房產贈送給郭先生,但郭先生堅持把房子上交國家。他說自己只是個賣書的,房子非本分所得,情意領了就是了。
退休后,郭先生經常深入民間挖掘收購古籍圖書,收集到元刻本《靜修先生集》、明藍格抄本《冊府元龜》《四庫珍本》等善本古籍圖書數百種,并找到了《敬錄堂叢書》《晨風閣叢書》《紀元通考》等多種古籍圖書的版片,由中國書店重新印刷發行,使這些珍貴的古籍能夠流傳后世。
談及古書流通的秘訣,郭先生說收購是至關重要的起點。他認為,收購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是否能夠很好地保護和發揮古書的價值,而收購的關鍵就是要了解書,能夠掌握一定的版本知識,能大體判斷用途大小,比較熟悉各種古舊書刊的出版情況,包括前后版次,流傳多少,以及叢書本、單刻本、原刻本、翻刻本的差別,等等。
我曾問郭先生:“搶救中,哪部古書最讓您震撼?”郭先生回答說是清雍正年間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這部大書算是我國類書之冠,十分珍貴,印刷僅65 部,全書10040 卷、5020 冊,現在很少能見到。”1948 年,天津的國民黨官員倉惶逃竄時曾準備把這部書當作“還魂紙”送往造紙廠,郭先生得知消息后,三下天津,伙同同行全部買下,使其免遭厄運。
學者們向郭先生求書,而我作為文史小愛好者向他也有一“求”,那就是求證為啥說是“河北人發祥北京琉璃廠”?
1999 年夏,尚在讀中學的我借暑假去北京探親時,到位于南新華街與騾馬市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中國書店收購科拜訪了郭先生。談話中,郭先生無意的一句話讓我興奮不已。
“小劉也是咱衡水的!都是老鄉。”郭先生把我介紹給辦公室里的老先生們后,他繼續說:“是咱們河北人奠定了北京琉璃廠的基礎,或說是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廠,并延續了琉璃廠文化,河北人當中以咱衡水人為主,衡水人中以咱冀縣人為多。”我瞪大眼睛,竟不怎么禮貌地插嘴道:“什么?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廠?您再說一遍!”郭先生一愣,以為說錯了什么話,我忙解釋:“這么爆的料兒,您老繼續講講。”這么一說,逗得郭先生和其他老先生們呵呵直樂,我就像小孩聽“古兒”一樣那么陶醉,拖著腮幫子,邊聽邊記。
“由于河北靠近北京,來往比較便利,明萬歷年間就有衡水人在琉璃廠經營古玩字畫和古書店鋪,到了清朝科舉廢除后,就取代了江西幫而享盛名,親戚帶親戚、同鄉帶同鄉,我就是這么到的北京,先到隆福寺,后到琉璃廠。”郭先生說,這種傳承關系使得不少河北人來京以買賣書為生。
郭先生看我聽得入迷,又翻箱倒柜找來一本孫殿起(冀縣人,著名版本目錄學家,14 歲進琉璃廠,著有《販書偶記》《叢書目錄拾遺》《清代禁書知見錄》《記廠肆坊刊書籍》等)于1962 年出版的《琉璃廠小志》送我。

1999 年,尚在讀中學的本文作者于暑假期間到中國書店拜訪郭紀森先生(右)
《琉璃廠小志》是一部研究琉璃廠史志及古籍版本和古籍市場的重要文獻。其中,第三章“書肆變遷記”記載:“上溯道光咸豐年間,下至20世紀40 年代,在琉璃廠開設書業店鋪的共三○五處,而由冀縣、衡水、深縣、棗強、阜城、景縣等衡水籍人士開辦的共一百六十四處”;第四章“販書傳薪記”中又稱:“當時琉璃廠以經營古玩字畫為主的店鋪共一百四十六處,衡水籍開設的有六十處,以書畫裝裱業為主的店鋪共十九處,衡水籍開設的有十一處……”除了《琉璃廠小志》外,明萬歷年間李誠誥的《海甸行》與清乾隆年間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也均有“衡水人在琉璃廠”的活動記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因生活的暫時困難,有些人回鄉務農。“公私合營”后,又有不少人返京重操舊業,繼續壯大琉璃廠的衡水隊伍。百余年來,琉璃廠從業人員中衡水籍人士仍占相當大的比例。郭先生還給我引薦了古籍版本學家張宗序(深縣人,16 歲進入琉璃廠)、馬春懷(冀縣人,16 歲進入琉璃廠),古籍文獻鑒定學家吳希賢(冀縣人,16 歲進入琉璃廠),外文版本學家種金明(衡水市人,15 歲進入琉璃廠)等先生,當時他們在中國書店及北京市文物局從事古籍版本鑒定,也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時刻。

孫殿起:《琉璃廠小志》
期間,我又結識了另外一些成名成家于琉璃廠的衡水籍人士,如碑帖文物鑒定學家馬寶山(衡水市人,16 歲進入琉璃廠)、裝裱藝術大家劉金濤(棗強縣人,12 歲進入琉璃廠)、一得閣老廠長第二代傳人張英勤(深縣人,14 歲進入琉璃廠)等。拜訪中,我也一一懇求老先生們對郭先生首提“河北人發祥北京琉璃廠”一說的意見,大家紛紛表示贊成,因為他們都是琉璃廠的活資料庫。
離京前,張英勤先生還將一份簽名加蓋手章的《一得閣創始人、傳人史記》贈與我,更為難得的是郭先生給我送來他近年手寫的《回憶古舊書業概況》《在舊書店學徒期間學習業務的經歷》《古舊書行業興衰變遷》《書業文昌會館》等16 頁近萬字的影印稿,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這些資料都彌足珍貴。郭先生在《書業文昌會館》中寫道:“琉璃廠書業乾隆嘉慶年間以前多系江西人經營……后以同鄉關系頗有仿此行者,遂成一集團,直至清末科舉廢除后,此種集團始無形取消,待江西幫繼起者多系河北人,彼此引薦同鄉親族子侄由鄉間入城謀生,后來如河北冀縣、南宮、棗強、衡水、深縣、束鹿等縣的人逐漸多起來。”

本文作者采訪郭紀森先生的若干新聞報道
我發現,琉璃廠的衡水籍人士大都出生在20 世紀一二十年代,那時衡水境內的滏陽河、滹沱河泛濫,冀縣、衡水、棗強、深縣等地大水成災,不少人因饑逃荒,孩子到了十五六歲的年齡,要么成為家里的壯勞力,要么外出謀生。找關系去北京琉璃廠成為一些孩子的“好”選擇。其實,他們年齡小、文化程度尚低,卻要從事如此艱深難懂的古書業,其歷程的艱難可想而知。但這些為了糊口的毛孩子們很是爭氣,慢慢從這條街上的販夫走卒,通過往來于各地的大小書肆,出入于巨賈名流的書齋,逐漸熟悉書的版本、源流、內容,在搜集、整理、修復、翻印各種古舊書籍中終成大器,成為了響當當的“師”或“家”,在中國版本事業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回到衡水后,我即撰寫了一則新聞稿《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并征得郭先生及上述幾位老先生的同意,將其刊登在當時河北發行量最大的《燕趙都市報》上。盡管稿子發出后,也有不少外地學者對這其中的淵源與衍變有些微詞,但的確是衡水人撐起了琉璃廠的繁華,使之薪火傳承至今,符合歷史事實,絕非杜撰。現在琉璃廠的槐陰山房、雅文齋、博古齋、一得閣、金濤齋等20 多家老字號仍由衡水人經營著,還有不少老先生的后人依然工作在琉璃廠的古舊書店與古董行,活躍在父輩祖輩們打下的文化江山之中。
自此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政協報》、《中國文化報》、《藏書報》、《北京晚報》、《生活早報》等都在引用郭先生的這句“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其觀點越來越被學術界認可,諸多學者開始撰寫相關文章,逐漸形成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
從城市品牌的角度來看,這是郭先生對區域文化及家鄉的一大貢獻。從此,衡水、冀州兩級政府及文化部門紛紛舉起“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這面文化大旗,舉辦了“北京琉璃廠——追尋冀人的足跡”文化研討會、“中國古舊書文化傳薪者——琉璃廠之冀州人”座談會等。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前館長鄒愛蓮曾說過:“琉璃廠是北京歷史文化的一塊金字招牌,它不僅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世界的驕傲;早年支撐著琉璃廠的是河北人,他們為琉璃廠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功不可沒。”2019 年4 月,衡水市政府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文華衡水”大展的官方前言中強調:“晚清以降,衡水儒商走京闖衛,促進了北京琉璃廠的文化興盛,培育了眾多行業泰斗與文化耆宿。”琉璃廠作為具有歷史底蘊的文化空間,我總覺得不能單一地從地理概念上描述成是文化商品的交易場所,它更多的應是近現代以來文化學者與書商、書商與古董商、文人學者之間往來的一個故事策源地。在這條街上,我穿梭過無數次,拜訪了多位老先生及他們的后人,更能深深地感知到郭先生的性情恬淡,他助人為樂卻不事張揚,之功之德,已成典范。
1994 年10 月,古籍版本學家雷夢水先生(冀縣人,著有《琉璃廠書肆四記》《書林瑣記》《古書經眼錄》等)去世后,尚有大量遺稿未出版,郭先生唯恐家屬管理不善,便從中協調,聯絡中國書店予以出版,這其中就包括珍貴的《販書偶記再續》一書。此外,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吳希賢先生,曾編撰全國珍善本書籍目錄1200 多種,他在古書文物清理小組工作期間,耗時十數年,從親手整理的230 多萬冊古籍中精心挑選出世所罕見的歷代珍稀版本,將其中特點突出、有代表性的書頁加以編輯而成《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但尚未等到出版,吳先生就在2001 年11 月去世。郭先生做了大量善后工作,使得其作得以在2003 年8 月由中國書店出版。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丁瑜先生在寫于2002 年9 月的序言中稱:“老友郭紀森先生持書稿囑余為序,拜讀之,頗受啟迪,故略述葑菲之見,并志景仰。”郭先生終生都未出版過自己的專著,卻能樂此不疲為同行甘做嫁衣,這是何等的高尚情懷。
我最后一次見郭先生是在2007年冬,那時我已到北京工作,之前每年都會和郭先生見見面、聊聊天。這次,盡管郭先生耳已失聰,但思維清晰,仍堅持用紙和筆與我交流,并把一本自己影印制作的線裝《名賢集》加蓋印章后贈予我,最后又拿起毛筆顫顫抖抖地寫下四個規規矩矩的大字“崇德尊學”,這四個字一直勉勵著后生,更是他一生做事的原則。在郭先生家,我們談起剛剛去世的史樹青先生,郭先生有些惋惜。他說:“啟功、張岱年、史樹青都是我的至交,他們在圈子里被尊為稀有的‘朱砂’,而我只是塊‘紅土’。常言:‘朱砂’最為珍貴,如今‘朱砂’沒了,我們這些‘紅土’也倍顯價值了!”

吳希賢:《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
史樹青先生也是郭先生介紹我認識的,后來每次與史先生見面,他總會說:“我們都要向郭先生學習,他的‘書皮學’‘人名學’很好,他能記住5000 部書名、5000 個人名,了不起。”
2007 年11 月7 日,被郭先生譽為“朱砂”的史樹青先生在京病逝,享年86 歲。我以小文《先生,我們會好好讀書》追憶,后被收錄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斗室的回憶——史樹青先生紀念文集》中。
2009 年4 月29 日,“紅土”也隨“朱砂”而去!郭紀森先生與世長辭。郭先生一生低調謙和,他的長孫郭學鵬說:“爺爺去世時快95歲了。他特別低姿態,誰也不讓通知。”據我所知,張宗序、馬春懷、種金明等優秀的中國書店人也都已先后離世。
張宗序先生作為中國書店開店元勛之一,從事古舊書鑒定和收購工作70 余年,對搶救、保護祖國文化遺產,尤其是培養版本鑒定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早在20 世紀80年代,他就已經掌握了比較深厚的古籍版本目錄學知識,有熟悉具體業務的方法和經驗,成為古舊書業博覽橫通的專家之一。1981 年,在有關部門的組織下,他與馬鍵齋等專家為古籍善本書編目,撰寫了近百萬字的《我國古籍簡介》《古籍要籍介紹》《古籍版本源流》《古籍常用工具及使用》等古籍業務教材。1983 年后,按照國務院關于普查和編制全國善本古書目決定,以及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新華書店總店、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古舊書工作委員會的委托,他參與培訓班教學工作,為全國各地的古舊書從業者及圖書館、博物館工作者、大學文獻專業和圖書館專業師生傳授古書版本學等知識,可謂“桃李滿天下”。
種金明先生,同樣是一位古籍版本學家,尤為熟悉外文舊書版本,曾收購過大批珍貴外文期刊。如德文原版《新時代》分裝35 冊的全套合訂本,1883 年創刊至1922 年停刊,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恩格斯曾在該刊發表過許多重要論著,當時國內還沒有一套該刊,只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最后三卷(1919—1922)。中央編譯局向國外匯款訂購該刊影印本,但兩年多沒有音信,中國書店以低價提供該套原版舊刊,解決了編譯局的用書急需,也填補了我國收藏國際共運史資料的一個空白。他一生過手了大量的珍貴原版外文舊書,滿足了國內不少研究單位和圖書館的需求。
術業有專攻,琉璃廠的古舊書人各有各的獨門絕技。如馬春懷先生是孫殿起先生的再傳弟子,也是雷夢水先生的得意門生,他除了精通版本,還擅書法懂佛學經典,所經手的金泥書寫的佛經曾被趙樸初先生譽為“鎮觀之寶”,而周紹良先生更是就稱為“幾百年不世出的國寶”……
每當我走進圖書館時,腦海中總會蹦出這幾位老人的名字,包括他們的形象、他們的言談舉止,還有他們的版本故事,感覺每位先生的腦子里都裝著一個古籍版本圖書館,對各種版本的圖書如數家珍。2021 年,我把和老先生們交往的故事一一整理,變成筆下的黃金,融進了我的書里,由此把拙作的名字定為《文化的力量——與智者對話的思考》,以此致敬這些中國古籍人,永續傳承他們的書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