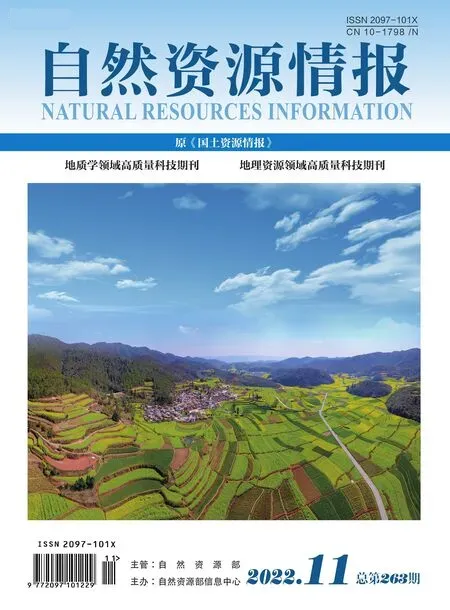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影響機制的多視角探析
——基于山東省212份農戶問卷調查的實證
羅 梓,翟騰騰,2,劉 碩,孫宸寧
(1.曲阜師范大學 地理與旅游學院,山東 日照 276826; 2.日照市國土空間規劃與生態建設重點實驗室,山東 日照 276826)
當前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由于宅基地流轉困難、戶籍制度限制、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不完善等[1],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不減反增。相關學者主要聚焦于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影響的多因素的分析[2-5],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對意愿影響因素的差異分析[6-7],農戶分化及異質性[8-9]、家庭生命周期[10]、城鎮化[11]對整理意愿的影響,整理意愿的互動影響[12],農村居民點整理現實潛力測算[13]等方面。已有研究多從農戶客觀條件或農戶對客觀因素評價的單一視角構建決策模型,而主客觀結合視角下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影響機制的研究相對不足。本文基于山東省212份典型村莊的農戶調研數據,從農戶主觀視角和客觀條件兩方面構建農村居民點整理決策模型,揭示農戶意愿影響機制。
1 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
1.1 基于農戶主觀心理感受視角的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
1.1.1 基于TPB的農戶決策理論分析
計劃行為理論(TPB)從心理學視角詮釋行為意愿是影響個體決策的關鍵因素,且同時受到主觀規范、行為態度、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2,14-15]。行為態度是指個體所做出的一種相對穩定的評價性反映,農戶對農村居民點整理越滿意,參與整理的意愿就越強烈。主觀規范是指個體在意愿選擇上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主觀規范越趨于正面,農戶參與整理的意愿就越高。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體感知對參與活動的控制程度,農戶預期風險阻礙越大,參與整理的意愿就越低。
1.1.2 基于TAM的農戶決策理論分析
技術接受模型(TAM)中的感知有用性對行為態度和意愿均產生影響,行為態度和感知有用性同時受到感知易用性的影響[16]。感知有用性是指個體認為使用系統時為自己帶來紅利的多寡,農戶感知有用性越高,越傾向于整理。感知易用性是指個體認為使用系統的容易程度,農戶感知易用性越高,態度就越積極,同時也會提升感知有用性。
1.1.3 基于TAM-TPB的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
TPB和TAM都源自理性行為理論,并通過行為態度因素建立關聯。本文將TAM與TPB模型相結合,借鑒有關成果[2,6]構建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決策模型(圖1)。

圖1 基于TAM-TPB的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決策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行為態度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的行為意愿;
H2 :知覺行為控制顯著負向影響農戶的行為意愿 ;
H3:主觀規范顯著正向影響農戶意愿;
H4:感知有用性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的行為態度;
H5 :感知有用性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的行為意愿 ;
H6:感知易用性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的感知有用性;
H7:感知易用性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的行為態度。
1.2 基于農戶客觀條件的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
農村居民點因區位狀況、個人及家庭特征、宅基地及房屋特征的差異,因而農戶的整理意愿不同。借鑒相關研究成果[9,15]結合研究區農戶特點,提出如下假設(圖2)。

圖2 農戶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的客觀影響因素
區位狀況:村莊所處地形條件、宅基地區位的交通條件越差,農戶參與整理的意愿越高;村莊到城鎮的距離越遠,農戶戀土情節更濃厚,農戶參與整理的意愿越低。
個人特征:男女受教育程度差異逐漸縮小,性別對參與意愿的影響不大;農戶年齡越大,思想越保守,參與的意愿越低;農戶對政策理解越透徹,參與的意愿越強;從事非農職業的農戶,對宅基地的依賴低,參與的意愿較強。
家庭特征:家庭勞動力人數越多,需贍養的老人越少,家庭經濟負擔輕,參與整理的意愿越高;有養老保險的農戶生活保障水平更高,對宅基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依賴越低,參與整理的意愿強;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以非農務工為主,家庭年總收入較高的農戶,住房需求和購買力較高,參與整理的意愿較強;農戶承包地面積越大,更依賴于傳統農村生活,參與整理的意愿越弱。
宅基地及房屋特征:宅基地面積越大,閑置宅基地參與整理,農戶預期得到更多經濟補償,參與整理的意愿較高;所住房屋越新的農戶,參與整理的意愿越低。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結構方程
結構方程模型(SEM)由基于因子分析的測量模型與基于路徑分析的結構模型組成。測量模型測量潛變量與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構模型用于分析外生潛變量與內生潛變量之間的關系。
測量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結構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式中:X表示外生指標構成的關系方程,ξ為外生潛變量構成的列向量,ΛX表示X在ξ上的因子載荷矩陣。Y表示內生指標構成的關系方程,η為內生潛變量構成的列向量,ΛY表示Y在η上的因子載荷矩陣。δ、ε為測量模型的誤差項。B為內生潛變量間的關系矩陣,Γ為外生潛變量對內生潛變量的關系矩陣,ζ為η方程的殘差項。
2.1.2 二元Logistic分析
農戶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意愿為因變量P,分為“愿意”和“不愿意”兩類,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關系。具體模型如下:

式中:P為農戶參與整理意愿的概率,愿意時,P為1;不愿意時,P為0。β0是常數值;Xm是意愿影響因素;βm是偏回歸系數,表示Xm對P的作用強度。
2.2 數據來源
為增強樣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樣本農戶的選擇上盡量涵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地形條件、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經濟活動類型的區域。本文選擇典型農業區山東省菏澤市曹縣、淄博市高青縣,以及城郊區淄博市淄川區、泰安市泰山區作為調研區域。本文數據來源于2021年8月的問卷調查,調查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調研的每個村莊問卷數不少于3份,共發放問卷216份,有效問卷212份,有效問卷率為98.15%,覆蓋36個鄉鎮中未實施農村居民點整理的63個自然村。
2.3 樣本特征描述
男性戶主占53.77%;農戶年齡在50歲及以上占51.89%;農戶個人文化程度以小學、初中為主,分別占28.30%和39.62%,表明農戶整體文化程度不高;21.70%的農戶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務農,74.06%的農戶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非農務工;對村莊基礎設施條件的滿意程度為一般及以下的農戶占63.68%,具備農村居民點整理的需求。總體上,本文樣本選擇較為廣泛,農戶基本特征符合研究需要,樣本具有典型性。
愿意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農戶占47.17%,不愿意的占52.83%,整理意愿偏低。其中,生產、生活不便,拆遷補償低為不愿意參與整理的主要原因(圖3)。

圖3 農戶不愿意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原因分布
3 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意愿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3.1 基于農戶主觀心理感受視角的意愿分析
3.1.1 量表設計與說明
量表設計為6個潛變量,共30個觀測變量。內生潛變量采用二分類變量,1表示“同意”,0表示“不同意”;外生潛變量下的觀測變量采用“1~5”級量表測量,變量解釋與編號見表1。

表1 變量解釋與編號

續表
3.1.2 數據信度與效度檢驗
首先,運用SPSS 26對數據進行信度檢驗,Cronbachα=0.791,高于0.7的可接受標準,表明數據具有良好的信度。然后,使用KMO統計量和Bartlett球形檢驗進行數據效度檢驗,KMO=0.801,大于0.5,Bartlett球形檢驗值為0.000,小于0.001,說明數據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可進行因子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剔除任意因子負荷小于0.5的因子后,剩余25個因子,累計解釋總方差為65.23%。
3.1.3 模型修正與假設驗證
采用AMOS 24軟件繪制初始模型,利用模型擴展和模型限制對模型進行修正,最終模型擬合度指標良好(表2),可用來分析影響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的生成路徑。

表2 模型擬合度指標
運用SEM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標準化路徑系數如圖4所示。行為態度與主觀規范均對行為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1和H3驗證通過;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顯著正向影響行為態度,假設H7和H4驗證通過;感知易用性對感知有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6得到驗證;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愿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假設H2得到驗證;假設H5在模型中未通過顯著性檢驗(P>0.05),不予支持。

圖4 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農戶意愿模型觀測變量影響路徑
3.1.4 結果分析
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與行為態度對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意愿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經統計,其影響效應如表3所示。

表3 潛變量對行為意愿的影響效應
(1)感知易用性分析
感知易用性顯著正向影響行為態度,即農戶越感到農村居民點整理易于執行,整理態度就越積極。感知易用性對感知有用性的影響為正,表明農戶認為農村居民點整理越容易進行,則行為結果越趨近于自身期望。感知易用性的觀測變量中,政策宣傳力度的標準化載荷系數為0.857(圖4),遠高于其他觀測變量,說明政策宣傳力度越大,農戶對政策理解越透徹,其參與整理的意愿就越高。感知易用性對行為意愿的總效應為0.146(表3),中介效應為0.146,表明感知易用性通過路徑H7-H1對農戶意愿產生間接的正向影響。
(2)感知有用性分析
感知有用性對行為態度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說明農戶對參與整理的感知有用性越大,其參與整理的態度就越積極。感知有用性的觀測變量中生活垃圾處理情況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改善、居住環境改善的標準化載荷系數分別為0.865、0.791和0.791(圖4),均遠高于其他變量,說明農戶認為農村居民點整理可以促進村容整潔和提升人居環境。從表3可知,感知有用性對行為意愿的中介效應為0.083,表明感知有用性通過路徑H4-H1間接影響農戶的參與意愿。
(3)行為態度分析
行為態度顯著正向影響農戶的參與意愿,說明農戶參與整理的態度越積極,參與整理的意愿就越強烈。行為態度的觀測變量中農戶對農村居民點整理相關政策的評價標準化載荷系數遠高于其他觀測變量,農戶對政策的評價正向越強,其參與整理的意愿越高。
(4)知覺行為控制分析
知覺行為控制對意愿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農戶對各項阻礙因素的認同程度越高,農戶參與的意愿就越低。知覺行為控制的觀測變量中日常消費增加、生活習慣發生改變的標準化載荷系數較高,農戶集中居住后,水、電、燃氣等費用明顯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戶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成本,會阻礙其參與整理;耕作距離增加、鄰里關系等生活方式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整理后的風險,農戶參與整理意愿隨之減弱。
(5)主觀規范分析
主觀規范對農戶意愿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農戶受到的社會群體壓力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參與整理意愿。主觀規范的觀測變量中,周邊鄰居贊成和親戚朋友支持的標準化載荷系數分別為0.907、0.886,遠高于其他觀測變量,反映出農戶對農村居民點整理具有一定的從眾心理。
3.2 基于農戶客觀條件的意愿分析
3.2.1 數據處理及變量說明
基于農戶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的理論分析,選取17個可能會影響農戶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的自變量(表4),用SPSS 26中的共線性診斷對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得出容忍度>0.1且方差膨脹因子<5,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

表4 變量解釋說明
3.2.2 結果分析
估計結果顯示,模型p值為0.000,小于0.05,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的值分別為0.290和0.387,均大于0.15,說明模型解釋能力較強;Hosmer和Lemeshow檢驗的卡方值為16.947, sig為0.136,大于0.05水平,說明模型擬合度較好,模型通過檢驗。農戶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影響因素的參數估計結果(表5)。

表5 模型估計結果
(1)區位狀況
村莊所處地形條件對農戶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丘陵及山地地區相比于平原地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后,因此,農戶想改變現狀,整理意愿較高。村莊到城鎮距離對農戶意愿有顯著負向影響,在10%的水平上顯著,村莊距城鎮越遠,受到城鎮經濟的輻射越小。農戶的思想越偏于保守,參與整理的意愿越低。
(2)個人特征
文化程度對農戶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農戶對政策、風險的認知越清楚,參與整理的意愿越高。
(3)家庭特征
家庭贍養老人的人數顯著負向影響農戶意愿,在10%的水平上顯著。家庭贍養老人的人數越多,經濟負擔越重,農戶預期參與整理后的經濟補償不能有效減輕家庭經濟負擔,農戶參與整理的意愿 就低。
(4)宅基地及房屋特征
房屋新舊情況對農戶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在5%的水平上顯著。房屋狀況越破舊的農戶,越傾向于通過整理改善房屋條件,參與整理的意愿越高。
4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農戶主觀心理感受和客觀條件兩方面構建了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決策模型,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從研究區樣本整體來看,愿意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農戶占47.17%,不愿意的占52.83%,參與整理的農戶意愿偏低。
(2)從農戶主觀心理感受視角,行為態度、主觀規范、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對農戶參與整理的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知覺行為控制對參與整理的意愿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其中,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是影響農戶參與整理意愿的直接因素,感知有用性通過行為態度為中介變量對參與意愿整理產生顯著間接影響,感知易用性分別以行為態度和感知有用性為中介變量對農戶參與整理意愿產生顯著間接影響。
(3)從農戶客觀條件視角,文化程度、村莊所處地形條件、房屋新舊情況對農戶參與整理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家庭贍養老人的人數、村莊到城鎮的距離對參與整理意愿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建議。一是充分尊重農戶意愿,引導農戶自愿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二是展示農村居民點整理的成功案例,使農戶了解進行居民點整理后對村莊發展和個人家庭生活帶來的增益,消除農戶心理上對整理結果的不確定性。三是加大政策宣傳力度,使農戶充分了解農村居民點整理相關政策的含義,發揮行為態度在決策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四是因地制宜綜合分析村莊的內外部環境,從單一的整村推進模式向整村推進與零拆整建相結合的模式轉變,降低整理的阻力。五是完善農戶長期安置保障和補償政策,為參與農村居民點整理的農戶提供就業崗位。六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應適應地方經濟的發展,多措并舉,避免農村“二次空心化”。
由于受實證研究數據的限制,對不同整理模式下農戶的整理意愿及影響機制的研究還有待后續研究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