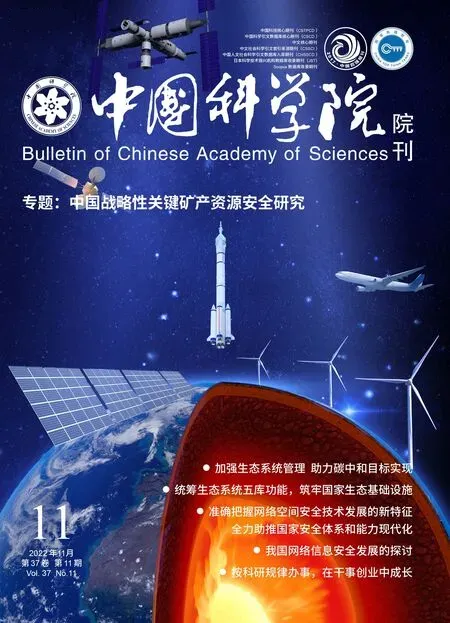綠色低碳轉型背景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戰略與對策
劉 剛 劉立濤 歐陽鋅 劉仟策 李 想 閆 強
1 北京大學 城市與環境學院 北京 100871
2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丹麥南丹麥大學 綠色技術系 歐登塞 5230
4 中國地質科學院礦產資源研究所 北京 100037
近年來,隨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壓力和政策力度的加大,以風電、光伏、電動汽車、高效儲能、永磁電機等為代表的綠色低碳轉型成為全球共識[1]。例如,國際能源署《2050 年凈零排放:全球能源行業路線圖》預測,到 2030 年電動汽車在全球汽車銷量中的占比將從 5% 左右上升至 60% 以上,到 2050 年全球 90% 的電力生產來自可再生能源,其中風能和光伏發電占 70%。同樣,清潔能源和低碳技術的發展是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基礎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將拉動關鍵金屬消費大幅增長,如電動汽車發展依賴鋰、鈷、鎳等電池材料,海上風機需要稀土永磁,燃料電池和氫能發展離不開鉑族元素。國際能源署 2050 年凈零排放情景下,僅 2020——2030 年鋰、鈷、鎳、銅、錳和稀土等關鍵金屬的市場規模就將增加近 6 倍以上[2,3]。
然而,與傳統化石能源面臨的供需錯位和產地集中[4]等挑戰類似,支撐清潔能源和低碳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關鍵金屬礦產如鋰、鈷、鎳、稀土、鉑等,儲量高度集中于智利、剛果、印尼、澳大利亞、中國和南非等國家[5],而消費卻主要在美國、歐盟和中國。與此同時,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俄烏沖突等引發地緣沖突加劇,國際局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保障關鍵能源、資源和供應鏈安全挑戰愈加凸顯[6]。面對綠色低碳轉型的緊迫性和關鍵金屬安全挑戰的嚴峻性,通過多種途徑保障清潔能源供應鏈和關鍵金屬安全已成為美國[7,8]、歐盟[9]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國家安全層面的戰略共識。
從傳統碳基化石能源向新型金屬基清潔能源轉型,其本質優勢之一在于,清潔能源系統所消耗的金屬在理論上可以無限循環利用。因此,確保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金屬安全,既需要開源、節流和進口多元化等與傳統化石能源安全相似的戰略舉措,也需要將循環利用提升到確保關鍵金屬供應韌性的戰略高度。當前,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戰略上高度重視關鍵金屬循環利用。例如,2021 年 2 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第 14017 號行政令《美國的供應鏈》(America’s Supply Chain),要求在 100 天內對關鍵礦產和材料供應鏈的脆弱性進行評估,評估報告中循環利用(recycling)一詞出現了 193 次[10]。
有鑒于此,本文通過梳理關鍵金屬循環利用的潛力、挑戰及主要發達國家的應對戰略,為我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戰略和對策制定提供借鑒,以期助力我國實現廣泛而深刻社會變革基礎上的“雙碳”目標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的綠色低碳轉型。文中討論適用于所有廣義上與綠色低碳轉型相關的關鍵金屬,既包括目前探討較多的清潔能源技術關鍵金屬[11],也包括如醫療器械、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新興產業技術中所涉及的關鍵金屬。
1 歷史經驗和未來需求表明,關鍵金屬循環利用潛力巨大
1.1 循環利用已成為保障金屬供應安全、減少采礦影響的重要補充和必要手段
金屬具有循環利用的典型特征。從鐵、鋁、銅等大宗金屬和金、鉑、鈀等稀貴金屬生產消費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循環利用已經成為保障金屬供應安全的重要補充和必要手段。當前,全球每年從新廢(生產、鍛造和制造等消費前環節)和舊廢(消費后報廢產品)金屬廢料中回收約 6.3 億噸鋼鐵[12]、2 057 萬噸鋁[13]、870 萬噸銅[14]。目前,全球 18 種金屬的廢棄階段回收率(再生金屬占產生金屬廢料總量的比重[15])可超過 50%,包括鋼鐵、鋁、銅、鈷、鉻、金、鉛、錳、鈮、鎳、鈀、鉑、錸、銠、銀、錫、鈦、鋅,其中鈮、鉛、釕的二次資源供應占比(再生金屬占金屬總供應量的比重)超過 50%,其余 13 種金屬的二次資源供應占比為 25%——50%[16]。從總量來看,我國金屬回收(包括回收進口廢料)占全球較大比例,2019 年回收約 2.4 億噸鋼鐵、607 萬噸鋁、215 萬噸銅、237 萬噸鉛和 140 萬噸鋅[17]。
國家經濟的發展通常會同時增加金屬循環利用的潛力。以銅為例(圖 1 和 2),隨著一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長,人均銅報廢量從低于 2.5 千克/人(如南非、印度、巴西)穩步增長到 10——15 千克/人左右(大多數發達國家)。當前,全球銅廢棄階段回收率約為 40%,二次資源供應占比約為 32%。其中,德國、奧地利、瑞典等發達國家具有技術優勢,新廢銅廢棄階段回收率(>90%)明顯高于其他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舊廢銅廢棄階段回收率(<10%)較低;相反,中國由于較高的社會回收率及進口消納部分發達國家廢料[18],日本、德國等國由于較嚴格的資源環境政策,舊廢料廢棄階段回收率(20%——80%)較高。綜合來看,奧地利、中國、日本、德國等具有較高的二次資源供應占比,近年來已經上升到 50% 左右。

圖1 1976——2020年典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人均銅報廢量與人均GDP的關系Figure 1 Historical per capita copper scrap generation versus per capita GDP for selected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1976 to 2020

圖2 1976——2020年典型國家廢銅料產生量、統計回收量與二次供應占比變化(a)中國;(b)美國;(c)日本;(d)德國;(e)巴西;(f)加拿大;(g)澳大利亞;(h)南非;(i)印度;(j)瑞典Figure 1 Historical scrap generation by simulation, scrap recycling by statistics, and share of recycled copper in total supply for selected countries from 1976 to 2020(a) China, (b) US, (c) Japan, (d) Germany, (e) Brazil, (f) Canada, (g) Australia, (h) South Africa, (i) India, and (j) Sweden
金屬循環利用對于降低金屬采礦和原生生產的能耗和碳排放至關重要。例如,通過礦石轉爐煉制是通過廢鋼電爐生產鋼單位能耗的 2.5 倍[19],因此每回收 1 噸廢鋼可節約 1.5 噸二氧化碳、1.4 噸鐵礦石和 740 千克煤炭,每年回收的 6.3 億噸廢鋼相當于減少 9.45 億噸碳排放[11]。廢鋁循環利用相比原鋁生產減少 95% 的能源消耗,因此每回收 1 噸廢鋁可節約 16 噸二氧化碳,每年回收的 2 057 萬噸廢鋁相當于減少 4 億噸碳排放[13]。金屬循環利用的這種巨大環境優勢,進一步促使各國將循環利用作為同時保障金屬供應安全與減少環境影響的戰略手段。
1.2 綠色低碳轉型驅動關鍵金屬消費大幅上升,循環利用潛力巨大
雖然當前全球鋰、稀土等關鍵金屬回收利用率仍較低,但從中長期來看,綠色低碳轉型將驅動關鍵金屬消費長期大幅上升,循環利用潛力不斷釋放,二次資源供應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綜合多種預測[15,20-23],2010——2050 年,全球大宗金屬鐵、鋁的年需求量將增長 2——5 倍,分別達到 22 億——52 億噸與 0.75 億——2.15 億噸;銅的年需求量將增長 2——8 倍,達到 0.27 億——1.20 億噸(圖 3)。其中,銅是綠色低碳技術中應用最廣、需求增長最快的金屬;預計到 2040 年,全球太陽能光伏、風力發電新增產能對銅的需求量都將增長 2——3 倍,分別達到約 80 萬——100 萬噸、40——60 萬噸。動力電池關鍵金屬中,鋰的增速最快,年需求量將增長 7——58 倍,達到 20 萬——163 萬噸;鈷的年需求量將增長 5——14 倍,達到 42 萬——126 萬噸;鎳的年需求量將增長 3——6 倍,達到 450 萬——1 000 萬噸。風能永磁電機關鍵金屬中,釹的年需求量將增長 2——7 倍,達到 6 萬——24 萬噸;鏑的年需求量將增長 2——25 倍,達到 0.3 萬——5.0 萬噸。光伏技術關鍵金屬中,絕對消費量雖不大,但因其極高的產品附加值和極大的增幅,鍺、碲、銦的年需求量將分別增長 70 倍、13——138 倍、2——11 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大宗金屬與關鍵金屬的主要消費者。據預測[23],到 2030 年,中國大宗金屬鐵、鋁、銅的需求量將達到 7.7 億噸、4 500 萬噸、1 350 萬噸,占全球總需求量的 20%——40%;關鍵金屬鋰、鈷、鎳、鉑的需求量將達到 60 萬噸、270 萬噸、190 萬噸,占全球總需求量的 40%——80%。

圖3 2010——2050年典型關鍵金屬全球需求量預測[15,20-23]Figure 3 Global demand forecast of selected critical metals, 2010-2050[15, 20-23]
未來20——30 年,隨著關鍵金屬消費逐漸趨穩,社會在用存量中的金屬資源逐漸作為二次資源釋放出來,關鍵金屬再生供應潛力將大幅上升。據預測,2050——2060 年,全球再生鋼鐵產量將超過原生鋼鐵產量,人類可能邁入廢鋼循環利用時代[24]。同樣地,全球鋰報廢量將在 2030 年達到 11 萬噸,在 2050 年達到 40 萬噸,鋰的二次資源供應占比將在 2050 年達到 23%[25];2020——2050 年,鈷的累積二次資源供應占比將達到 66%,到 2050 年,僅電動汽車電池回收就可以滿足當年 26%——44% 的鈷需求[26]。
2 循環利用已成為主要發達國家保障關鍵金屬供應安全的戰略共識
早在20世紀中期,以美國、歐盟、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即開始關注關鍵金屬的循環利用,并在近年來逐漸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例如,美國在 2021 年發布行政令《美國的供應鏈》(America’s Supply Chain),2022 年宣布向兩大項目——開展從電池中回收鋰、鈷、鎳和石墨,開展從煤灰和礦山廢料中回收稀土等關鍵礦物分別投入 1.4 億美元和 30 億美元[7]。2022 年 5 月,歐盟發布的《清潔能源金屬:解決歐洲原材料挑戰的途徑》(Metal for Clean Energy:Pathways to Solving Europe’s Raw Materials Challenge)指出,循環利用是實現歐洲清潔能源關鍵金屬戰略自主的關鍵所在,到 2050 年,循環利用可以滿足歐洲 45%——65% 的基本金屬需求、77% 的電池金屬需求及 200% 的稀土需求[27]。日本于 2020 年出臺的《日本全球資源新戰略》也明確指出促進關鍵金屬循環再生的戰略意義[28],并包括提高冶煉技術效率、重點促進稀土循環再生、提高項目經濟效益等具體舉措。
從科技和研發投入角度看,循環利用已成為發達國家針對關鍵金屬科研投入中最多的生命周期階段,超過探-采-選礦、加工制造等階段。以歐盟為例,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歐盟大力投入關鍵金屬循環利用研發,累計經費投入已超過 1.1 億歐元[29],項目涉及稀土、銦、鈷、銀、鎵、硅等超過 15 種關鍵金屬的循環再生技術與管理(圖 4)。例如,作為歐盟近年資助的關鍵金屬循環利用的代表項目之一,SUSMAGPRO 于 2019 年立項,以德國高校牽頭,多國企業、高校、科研單位共同參與,資助金額達 1 400 萬歐元,旨在促進以歐洲回收的釹磁鐵為基礎建立稀土二次資源供應鏈。此外,依托 ProSUM 兩期項目,歐盟還建立了包括含關鍵金屬產品的城市礦山數據平臺(Urban Mine Platform),形成了“產-學-研”一體化的知識傳播及轉化體系。

圖4 2015年以來歐盟涉及關鍵金屬循環利用主要研發項目及其在全生命周期階段資助投入中的占比Figure 4 Major project funded by European Union on critical metals recycling since 2015 and its proportion in to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by critical metal life cycle stage
從技術專利角度看,在長期研發投入下,西方發達國家在關鍵金屬循環利用專利方面形成了較大歷史優勢。過去 20 年,全球關鍵金屬循環利用相關專利家族數公開總量已超過 15 萬件,其中美國、日本、歐洲、韓國長期占據主導地位。2013 年以后,中國的關鍵金屬循環利用專利迅速增加,至今已占到 80% 以上(圖 5)。然而,盡管在專利授權及公開數量上中國開始占據主導優勢,但技術轉化仍存在不足。以稀土釹元素為例,中國在釹元素的全生命周期各個階段(包括永磁及永磁零件的生產、加工制造、循環再生)仍需要大量的技術進口。

圖5 1990——2020年部分國家和地區稀土釹循環利用相關專利家族公開數量Figure 5 Number of disclosed neodymium recycling related patent families by country/region, 1990-2020
3 全球及我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挑戰
金屬循環利用受報廢產品的社會回收率和回收后的分離處理提取率兩方面影響。報廢產品社會回收率與社會經濟和管理政策等多種因素相關,而分離提取率則主要受技術經濟條件限制[30]。總體來講,目前關鍵金屬全球社會回收率仍不高,拆解處理難度較大,分離處理和提取的精度和深度不足,循環再利用品質與成本難以滿足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材料要求。隨著關鍵金屬應用產品多樣性、技術復雜性進一步增加,全球產業鏈愈發復雜,全球尤其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關鍵金屬循環利用面臨的技術、經濟和管理挑戰仍然巨大。
3.1 關鍵金屬應用量小面廣、產品多樣、技術復雜,回收技術經濟成本高成為最大共性挑戰
隨著科技高速發展和消費持續升級,關鍵金屬被廣泛應用于各種綠色低碳產品如風電、光伏、電動汽車等,以及新興產業技術如醫療器械、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雖然通常用量較小,但是在各部件中分布廣泛、功能關鍵。越發多樣化的產品(如更新換代的電子產品和不同類型的充電樁)不但縮短了產品使用周期,也加大了報廢產品的社會回收難度,增加了產品回收和循環過程中的分類和物流成本。同時,隨著產品技術復雜性增加,報廢產品中各類金屬的分離處理難度越來越大[16],關鍵金屬回收和循環利用的技術成本也隨之上升。
在此背景下,我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面臨的挑戰突出。能夠平衡關鍵金屬回收成本的大型企業會受物流成本和生產能力限制而不能覆蓋全部區域,本地的中小企業又會因技術落后等問題而面臨高昂的處理成本。以磷酸鋰動力電池的回收為例,目前很多中小企業在回收環節中會忽視其中鋰的價值,將其作為普通廢鐵處理,不但降低了循環利用的經濟價值,還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
3.2 全球金屬產業鏈復雜交錯,循環利用發展水平不均衡,加大循環利用產業發展風險
從全生命周期看,金屬可以沿區域內產業鏈上、下游和區域間貿易 2 個維度流動[31]。隨著全球貿易網絡深刻變化,各國關鍵金屬相關產業從生產、加工、使用到回收等多環節常呈現錯位發展。以銅為例[18],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銅生產國,中國是最大的銅消費國,而在銅的回收階段,德國、奧地利、瑞典等發達國家擁有更高的二次資源回收率。同時,關鍵金屬產業鏈上各主體利益復雜交錯,產業鏈任何一環出現的問題都可能沿整個產業鏈傳導,影響下游金屬循環產業發展。例如,關鍵能源金屬中不少是伴生金屬,其聯合生產機制決定了大宗金屬(如鋁)去產能或加大循環利用力度,可能會削弱所關聯關鍵金屬(如鎵)循環利用的潛力[32,33]。
面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關鍵金屬循環利用上的技術代差和發展中國家逐漸執行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如中國的“禁廢令”)[18],傳統金屬回收所依靠的“出口轉移”和發展中國家消納模式面臨很大挑戰。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地緣沖突、貿易政策變動等因素影響,產業鏈上、下游公司面臨的經濟、環境和社會風險持續增加,原材料與產品價格震蕩波動,加重了我國金屬循環產業發展風險。
3.3 我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相關管理政策仍待完善,動態性和配套性不強
與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7,27,28],中國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還沒有系統完整的關鍵金屬循環利用管理政策。同時,未來需求、循環利用潛力和技術的動態變化,加大了配套管理政策并最大程度促進循環利用、保障供應安全的難度。例如,引入延長使用壽命、梯級利用、再制造等循環經濟策略,將在減少資源需求量的同時,延長關鍵金屬在社會在用存量中的服役時間,推遲循環再生潛力釋放和市場發展[26]。如何應對這個窗口期需求激增與循環再生滯后效應的雙重脅迫,將對我國循環利用管理政策制定帶來嚴峻挑戰。
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金屬循環再生產業,但目前銅、鋁、鉛等大宗金屬的再生利用仍以中低端為主,分選精度和深度不足,回收對象主要局限在易收集且分選處理技術相對成熟的電子產品。而對回收難度高且收集過程中物流、管理挑戰大的產品,例如風電、光伏、氫能、儲能等高技術附加值和清潔能源技術產品與基礎設施[34],關注度較低。同時,現有循環產業示范區主要密集分布在長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等較發達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的循環再生產業布局密度仍較低,如何適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和關鍵金屬回收物流與產業布局優化仍需探討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于2021年園區循環化改造示范試點和“城市礦產”示范基地驗收結果的公示. (2021-10-09)[2022-08-20]. https://www.ndrc.gov.cn/hdjl/wsgsjdc/202110/t20211019_1300043.html?code=&state=123.。
4 對策與建議
未來 20——30 年,綠色低碳轉型將既是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公約數,又是大國技術和產業競爭的新高地。在這一背景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已被主要發達國家提升到保障清潔能源轉型和產業鏈安全的戰略高度。中國作為最大的清潔能源和低碳技術(如光伏、風能、電動汽車等)投資國、生產國和應用市場,已經并將繼續成為全球最大的關鍵金屬消費國。面對需求的快速增長,部分關鍵金屬國內供給不足,國際爭奪加劇,短期內無法替代,如何從戰略和戰術層面確保社會蓄積的關鍵金屬高效、清潔和永續循環利用,是我們進入金屬基能源時代急需回答的時代之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4 點對策和建議。
(1)加大頂層設計和系統考慮,立足大國競爭和國家安全高度構建我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戰略。深刻把握關鍵金屬物質循環本質規律,考慮開采、生產、加工、制造、使用、廢物管理和回收的全生命周期過程,系統全面構建我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戰略;探索高層級協調和跨部門保障機制,借鑒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關于全面加強資源節約工作的意見》等,制定上下游一體、產業鏈系統聯動的關鍵金屬循環利用促進政策;加強關鍵金屬循環利用戰略與綠色低碳轉型戰略等既有國家戰略的深度融合與協調,實現以“雙碳”目標驅動循環利用產業發展;面向百年變局背景下的大國競合,打造完善包括減量、提效、替代、多樣化和循環利用在內的關鍵金屬安全保障全維度戰略工具箱。
(2)基于我國不同關鍵金屬供需安全態勢,區別制定有針對性的循環利用對策。對于我國的短缺關鍵金屬(如鈷、鉑等),要從外交、經濟等多維度綜合發力,充分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既加快國內循環利用產能布局,又鼓勵企業走出去,不斷拓展海外循環利用產能合作,同時確保資源安全和產業競爭優勢。對于我國的優勢關鍵金屬(如稀土、鎢等),一方面要綜合考慮原生、再生成本和產能布局,保障國際市場穩定和我國的主體供應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綢繆,從環境挑戰、技術競爭和國家產業鏈安全出發,穩健促進國內循環利用產能發展。
(3)探索“政用產學研”多主體協同創新合作體系,培育關鍵金屬循環利用合作平臺和競爭優勢。構建循環利用產學研協同創新和合作平臺,落實完善生產責任延伸制度、產品生態設計和產業鏈閉環管理;探索成本補貼、稅收優惠等激勵政策,支持關鍵金屬產品高效收集、分類和運輸,提高關鍵金屬循環利用技術經濟可行性;通過全生命周期過程標準化設計和技術研發聯動,開發高效、經濟和標準化的回收流程,創新“互聯網+回收”等多渠道回收模式;為消費者購買賦權,標注產品壽命、更換和維修服務、能耗和循環材料含量等,通過多渠道促進循環利用產品購買、使用和公眾循環利用習慣。
(4)加大科技研發,建立關鍵金屬循環利用重點技術目錄和重點產品監管追蹤體系。加大循環利用科技研發投入,實現循環利用關鍵技術突破,打牢提升關鍵金屬循環利用率和競爭優勢的關鍵科學和技術基礎;運用區塊鏈等技術為光伏、風能、動力電池等重點產品的關鍵部件建立“護照”,以在全生命周期內識別和跟蹤其化學成分、來源和廢舊產品健康狀況,加強信息公開、數據共享,以點帶面促進提高關鍵金屬循環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