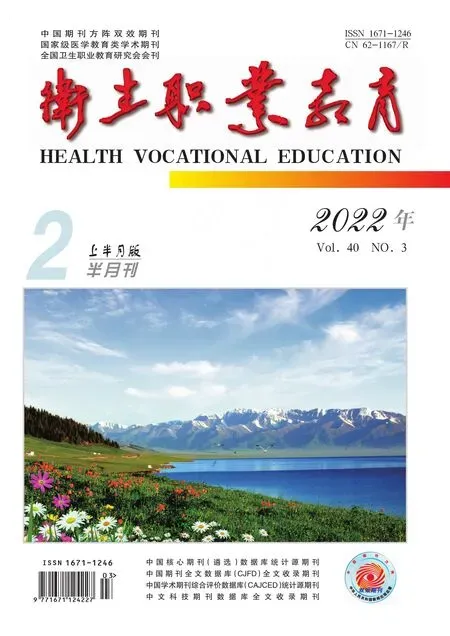新時期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建設發展探析
李曉宇,黃振宇,呂家俊,孫宏亮
(1.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遼寧 大連 116044;2.大連醫科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遼寧 大連 116044)
醫學志愿服務組織是指依法成立的以開展與醫療活動相關的志愿服務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組織,通常以醫務人員、醫學專業大學生志愿者為主體。根據組織部門的不同可將其大致分為醫學院校組織、醫院組織、社會自發組織和社區組織等,主要從事醫學科普、健康宣教、醫療保健、幫扶義診、衛生調研和科學防疫等工作。
1 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建設發展現狀
1.1 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宣傳力度不夠
目前,醫學志愿服務組織主要通過官網、官方公眾號等發布信息,輔以志愿者個人微博、微信朋友圈等途徑達到宣傳目的,但是無論在廣大群眾熟知的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媒體還是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體平臺,關于醫學志愿服務的信息極少,且存在信息更新不及時、消息滯后等現象,部分醫學志愿服務組織甚至沒有自己的信息平臺。群眾對于醫學志愿服務的了解更多是因為身邊有志愿者從而滾雪球式接收相關信息,部分想加入醫學志愿服務組織的人由于信息匱乏及渠道受限不能如愿。另外,大部分不具有醫學背景的人對于醫學志愿服務的認知不全面,認為其具有較高的風險和門檻,并與自己的日常生活距離較遠,對其望而卻步。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發展,衛生事業已關系到每個人的生活,許多疾病的傳播與發生發展也是在人群中進行的,維護健康不應只是醫學專業人員的責任,而應得到不同階層人群的廣泛關注。
1.2 志愿者素質良莠不齊,專業培訓不足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志愿服務的需求日益專業化、多元化,醫學志愿服務組織與群眾之間的供需對接失衡愈發突出。醫學志愿服務組織中的志愿者常常來自社會各個層面,具有不同的特質且缺乏必要的專業培訓,志愿服務水平低下。研究發現,受調查者對醫院志愿者培訓工作滿意率僅為80.6%,10%左右的志愿者和被幫助對象認為志愿服務效果一般[1]。另一研究發現,參與過醫院志愿服務的醫務人員中接受過相關培訓的僅占35.51%[2],可見志愿者培訓率低已成為各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廣泛存在的問題。一方面志愿服務缺乏指南類文件,急需志愿服務培訓方面的實踐指導,現有規范的制定多依據志愿者主觀感受,無法進行客觀的標準化的考核。另一方面團隊成員構成不盡相同,有的可能由于醫院高強度、高精密度的工作經歷,參與志愿服務時容易出現輕視、懈怠現象;有的因為尚不熟悉某項操作技能,從而容易出現不可避免的錯誤;有的出于強迫并非自愿參加志愿服務,極易出現抵觸情緒;更有甚者本身思想道德水平有限,把參與醫學志愿服務當作是實現自身利益的跳板,以精致利己主義玷污志愿服務動機。
1.3 資源分配不均,醫學志愿者權益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在組織層面,大部分醫學志愿服務組織缺乏科學化管理機制,存在人力、物力資源分配不均問題,難以因地制宜發揮作用。以上海市兒童醫院陽光愛心志愿者服務隊為例,由于自薦產生的組長對小組管理力不從心,組織設想的由總負責人通過各個組長對各組組員進行相關服務安排與培訓的兩級管理模式最終演變成總負責人需要同時與組長以及眾多組員保持聯系的三級管理模式,從而造成志愿組織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3]。同時,志愿者權益保障主要有法律與保險兩部分。一方面,法律保障有待完善。目前我國缺乏關于突發事件中志愿者權益保障的立法,在現行有效法規中,僅《志愿者服務條例》對此做出了說明,缺乏高位階統一立法[4],無法妥善全面保障志愿者權益。另一方面,保險制度相對欠缺。目前我國志愿服務基本保險僅針對注冊志愿者開展,缺乏對民間自發形成的志愿者團體的保護。除基本的人際交流問題、惡劣的自然環境問題等外,醫學志愿者還會面臨較高的傳染病感染風險以及護理危重癥患者死亡后所帶來的心理創傷等問題。2020年3月志愿者何輝在抗疫前線中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引發熱議。參考《工傷保險條例》,只有建立勞動關系的在職或在職請假期間獲批的員工受傷方可認定為工傷。若出現這種在道德之內而在法理之外的情況,其保障體系仍有待完善。在部分暴露風險大、強度負荷重、工作條件艱苦的醫學志愿服務中,醫學志愿者身份認定更加模糊,使得志愿者沒有安全感,影響了其參與積極性。
1.4 行業規范缺乏,突發事件下的應急能力有待提高
醫學志愿服務相較于其他志愿服務,應具有更高的行業規范和行為準則,然而目前對其界定較為籠統,不同地區間存在較大差距,急需明確的專業指引。志愿服務組織通常能從其靈活性發力形成局部社區自救、互救系統,為政府公共服務系統的暫時失靈應急。但現今我國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的應急能力不足,難以簡化多余低效環節,不能制定普適性規范指南,服務水平低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醫學志愿服務組織普遍存在響應速度較慢、相對無序化的問題,延長了突發事件下志愿服務組織應急周期。同時,應急志愿服務的開展缺乏整體性,難以形成志愿服務組織內部與社區社會組織的聯動。以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中心點武漢為例,存在社區與多方力量協同不足、應急配置志愿者與常態化城市志愿服務供需對接滯后等問題[5]。
2 新時期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建設發展路徑探析
2.1 產生機制的轉型——由專業領銜向全民共建轉變
衛生事業的本質是“人人需要、共同受益”的社會公益事業,醫學志愿服務組織依賴于醫學專業人員的力量是有限的,衛生工作必須由封閉轉為開放,提升社會參與性。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也揭示,單純依賴醫學手段難以有效解決產生健康問題的社會根源,需要衛生系統內外、政府各部門的協調行動和全社會的共同參與[6]。“互聯網+”背景下可鼓勵醫學志愿服務組織打造特色自媒體平臺,發揮流量優勢,通過短、平、快的微視頻等易于被公眾接受的形式,擴大自身影響力,拓展志愿者招募渠道。只有真正調動起人們的主觀能動性,讓參與醫學志愿服務活動成為廣大群眾的自發行動,使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打造共建共享、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盡責的社會治理生態共同體,才能在新時期為我國衛生事業發展帶來新的活力與生機。
2.2 組織方式的轉型——由外生型向生活化轉變
志愿服務組織需完善組織管理體系,真正搭建有效平臺,摒棄空泛化的形式和目標化的導向。首先,優化志愿者培訓機制,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創新培訓手段,如開展線上微課和模擬訓練,進行系統化醫學培訓,提升公共衛生知識水平,提高突發事件下的應急能力。特別需要加強志愿者隊伍的心理建設,定期組織心理疏導,開展團隊拓展訓練,培育集體精神。其次,引入市場管理、監管激勵等科學管理機制[7],提倡醫學志愿服務組織高效利用有限的資源充分提高自身可信度、擴大社會影響力,合理引入外部資源,形成資源整合的正反饋機制。再次,完善志愿者權益保障制度,加強對志愿者的人文關懷。最后,由政府干預轉變為政府參與,強化醫學志愿服務組織自主自治,使志愿風尚成為生活日常。
2.3 激勵機制的轉型——由道德外束向價值內驅轉變
目前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對于志愿者的激勵多局限于榮譽授予,這種外在激勵是暫時的,缺乏長效依托。首先,應強化志愿認知與信仰教育,實現德行再塑,使志愿實踐成為行動自覺。醫學志愿服務不能停留于外界道德準則和價值標準的他律,需直擊志愿者內心,與個體內在因素整合,形成主體內在核心道德態度的認同,主動趨同于志愿團體及其規范,將其有機融入個體道德態度系統,最終表現為志愿自律。其次,科學樹立志愿服務榜樣,推出多元化榜樣形象來契合大眾的心理認同和價值需求,增強志愿者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促進心流效應的形成,強化志愿服務與自我實現的聯系。最后,建立對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的深度宣傳機制,在傳統框架下加強敘事醫學教育,以事明理,以情動人,積極促進志愿文化交流,在全社會營造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和諧氛圍,在滿足社會尊重需求的基礎上促成價值內驅轉變。
2.4 聯動形式的轉型——由小圈子的微生態向集成化的共同體轉變
醫學志愿服務組織的整體發展終究要回歸基層,應促成其結構和功能的交聯互通,在中心“供血”的基礎上實現末梢“活血”至關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突發事件中,已有學者提議建設網絡救災志愿服務體系,搭建知識共享平臺[8],強調志愿服務組織間的協作,尤其是突發事件下的應急驅動。后疫情時代應鼓勵知名醫學志愿服務組織發揮引領作用,打造特色化志愿服務文化品牌,帶動周邊組織發展。不同類別的志愿服務組織可以加強協作,實現優勢互補,深化與社區的合作,拓展志愿服務覆蓋面和宣傳范圍。醫學志愿服務組織間可實現資源的合作共享,建立志愿服務專業聯盟。不同地區的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可以彼此借鑒發展經驗,共同開展活動。應健全醫學志愿服務組織統籌協調機制,建立醫學志愿服務組織有效評估監督機制,并加強社工與志愿者的合作,營造眾志守望的和諧氛圍。最終在多元化的協同發展布局下,構建醫學志愿服務組織規范化、專業化、整體化、特色化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形成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共同體,提升志愿服務效能。
2.5 發展模式的轉型——由本土化向國際化轉變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中國政府合作各種經濟社會發展項目時,聯合國志愿人員組織就已經參與合作,帶來了國際志愿服務的理念和規范[9]。據《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介紹[10],2015—2019年,中國共派出202批次3 588名援外醫療隊員,累計診治1 100萬名患者,并對當地醫務人員進行帶教培訓,開展巡回義診、藥械捐贈等,1 500余人獲得有關國家頒發的總統勛章等榮譽。截至2020年10月,中國向33國派出35個援外醫療專家組協助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浪潮中,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持續推進,我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擴大,醫學志愿服務事業也逐漸與國際接軌。當前,我國醫學志愿服務組織已成為推進全球化進程的重要紐帶,是對外傳播中國聲音、宣揚中華文化的有力平臺,向世界呈現出文明、和諧、自信、友善的中國形象,背后透露出的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是國際視野下的軟實力擔當。醫學志愿服務組織應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拓展志愿形式,豐富志愿文化內涵,加強國際交流,與國際志愿服務事業接軌,深化區域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走向世界,面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