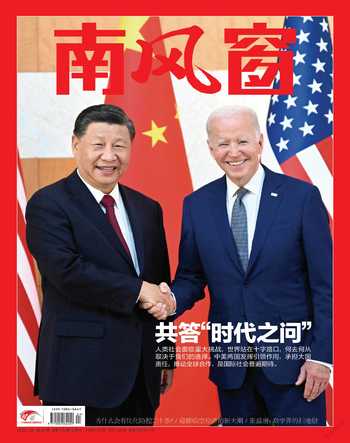區域差異與中國城市化的未來
賀雪峰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本文節選自《北京工業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

中國沿海城市經濟帶未來的人口和經濟占比還會持續提高。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從出口導向轉向依靠內循環,“雙循環”發展使中西部地區經濟就有了更大增長空間。值得強調和注意的是,中西部將共同持續發展,但在發展中一定要防止市縣惡性競爭。
目前,中國沿海地區發展是全域工業化和城市化模式,即除生態紅線以外的土地均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那么,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發展策略,還可能再按東部沿海地區的模式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嗎?
筆者認為,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國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人口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流動幾乎是必然的。人往高處走,越是規模巨大,社會具有聚集效應,只要國家相關部門按市場規律,沒有人為政策限制,特大城市和沿海地區將仍然是人口流入地區,中西部地區則是人口流出地區。
在整個區域人口流出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區內部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其中省會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已經具有相對于區域內其他地區發展的更大優勢,則必然是人口流入的地區。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源顯示,中國區域人口增長雖然緩慢或凈減少,但是省會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人口卻幾無例外得到快速增長,并且中西部地區縣域人口幾無例外地出現凈減少。
目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不再可能復制東部沿海地區20世紀的鄉村工業模式,且鄉村工業化已無可能。從縣域經濟來看,中國百強縣幾乎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尤其集中在江蘇、浙江和山東等。廣東百強縣少,并非廣東經濟不發達,而是珠三角縣改為市轄區,體制上已經城市化。若以區作為縣級單位,2021年,深圳南山區GDP超過6000億元,比百強縣之首的江蘇昆山還高1/3以上。相對來講,中西部地區百強縣排名靠后,往往是依靠資源或就在省會城市周邊。因而,我國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成長空間在未來一定時期還是很有限的。
當前,中西部地區已普遍出現的市縣競爭項目。一個地級市下面有10多個縣相互競爭,地級市往往也很難形成適度規模,從而很難形成對現代制造業的最低容納能力。中西部地區普遍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恰恰是,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建設現代制造業的基地,雖點多面廣、基礎設施投入大,但卻非常分散,無法產生規模效益,致使已經進駐的制造業企業很難存活下來。
劉勝枝 北京郵電大學數字傳播學教授 施丙容 北京郵電大學研究生
本文系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重點課題“青年文化新現象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盡管虛擬偶像包含著人類突破肉身限制的技術想象,但是粉絲看重的仍然是其提供的情緒價值,而粉絲和虛擬偶像之間這種以情感的需求和滿足為核心的關系形成了類似真實親密關系的一種準社會關系。準社會關系一詞是美國媒介學者霍頓(Donald Horton)和沃爾(Richard Wohl)在研究電視觀眾時提出來的,他們發現觀眾對其了解喜愛的媒介人物產生了情感依賴,形成了類似現實中朋友或戀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又是單向地建立在想象基礎上的社會關系,所以他們稱之為準社會關系。后來,準社會關系被應用到動漫、偶像崇拜、直播等新的文化消費研究領域,其內在機理和特點也被重新審視,比如其單向性就受到較多質疑。虛擬偶像是一種新的媒介,如英尼斯所言,不同的媒介有著不同的技術“偏向”和文化“偏向”,必然會形成新的媒介體驗和接受方式,也會重塑人與媒介的新關系。

粉絲和虛擬偶像之間的關系和真人偶像相比具有更為親密的屬性,這與虛擬偶像的媒介屬性及粉絲們的媒介使用密切相關。從媒介屬性來看,偶像的虛擬性打破了粉絲與真人接觸可能產生的距離感,而虛擬偶像的二次元形象及純真可愛的軟妹人設也容易吸引粉絲,粉絲面對虛擬偶像往往具有更強的主體性,相對于真人偶像占有更具優勢性的地位。從媒介使用場景來看,粉絲觀看虛擬偶像主要通過手機或電腦屏幕進行,這種交流具有一對一的私人性和近距離性,比較容易拉近粉絲和虛擬偶像的情感距離。研究表明,具有卷入性的粉絲參與行為會增加其黏性和情感能量,從而形成柯林斯提出的“互動儀式鏈”,使單次接觸中的短暫情感在不斷互動中積累醞釀進而轉化為長期穩定的親密關系。
粉絲們對虛擬偶像的文化消費成了一場理想主義的文化烏托邦試驗,在其身上建構了自己對親密關系的認知和想象。正如詹金斯在其《文本盜獵者》中所說,“粉絲圈的核心點,即其烏托邦社群的身份。粉絲圈的認同感與其說是逃離現實,不如說是另類現實,比起俗世社會來說,這里的價值觀更加人性也更加民主”。毋庸置疑,粉絲們的認同在想象的、文化的層面上彌補了其現實生活中親密關系的匱乏。
章永樂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本文節選自《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8期
要理解被殖民者長期稱為“西印度”的拉丁美洲的處境,不妨將其與殖民者眼中的“東印度”即東南亞地區做一個對比。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紀就在這兩個區域建立起穩固的殖民統治,后來又有荷蘭、英國、法國等殖民者加入。在兩個區域的不少地方,發展出了類似的社會經濟特征,如大莊園、大地主和天主教的強大影響力。拉丁美洲的民族獨立運動比東南亞要早一個世紀,但兩者的歷史境遇大大不同。
19世紀以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獨立后經濟上先依附于英國,后依附于美國。二戰后,隨著美國霸權的進一步鞏固,拉美各國受其影響程度也逐漸加深。如巴西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一度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實行貿易保護,吸引外資在國內建立工廠,然后補貼中產階層購買國產工業制成品,以期建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至1990年代,巴西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還處于保護期的許多本國工業企業在進口商品的沖擊下紛紛垮掉,大量國有工業企業被私有化,公共服務大幅削減,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由于拉美政權無法避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與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巨大影響,一旦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外資撤離,財政收入暴跌,政治動蕩也就接踵而至。而政黨輪替通常意味著經濟政策的大幅震蕩。最近拉美的政治鐘擺再次向左偏移,但只要經濟基礎沒有改變,恐怕拉美就很難擺脫這種充滿動蕩的政治周期。
這些歷史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當代中國主體性的構成。中國有著非常完整和系統的、從未中斷過的古代文明,在近代是少數未完全淪為殖民地的非西方國家之一。中國通過深刻的社會革命,重新獲得獨立自主,走出了一條“自主性開放”的道路。而拉美的前西方文明已經基本上被毀滅了,現存的拉美文明主要是殖民地文明,但西方性一直存在于拉美的血脈里,其主要語言與主導性宗教都來自西方。無須期待拉美擺脫這種“西方性”,真正重要的是,拉美能否在政治經濟上擺脫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支配和壓迫,為自身多元因素混合而成的傳統獲取自由舒展和生長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