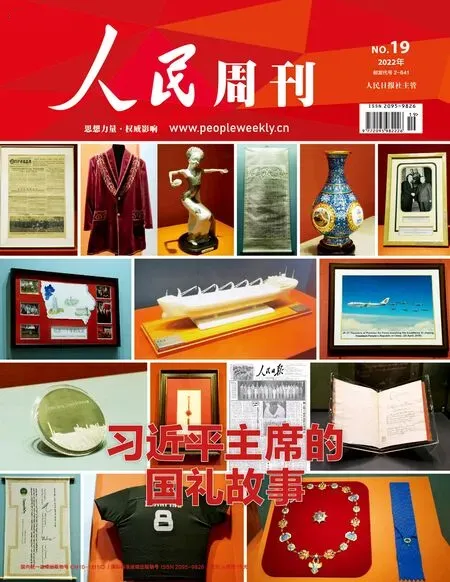探尋載人航天精神樹起一座“特別”的太空豐碑
劉巖 劉淮宇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中,“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和新時代北斗精神都與航天事業有關。這些精神是航天人在航天實踐活動中孕育出的精神法寶。
2022年恰逢黨的二十大召開,讓我們跨越時空,走進那些航天人曾經奮斗、戰斗過的地方,追尋紅色印記,追憶鮮為人知的往事,一起探尋航天人不斷挑戰自我、實現跨越的寶貴精神財富。
2022年是航天大年,除了中國宇航發射次數將再創新高外,最令人關注的莫過于中國空間站即將完成在軌建造——中國人將真正擁有一個鐫刻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烙印的太空家園。
2022年也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實施30周年。30年來,中國載人航天事業從無到有、由弱變強,不僅帶動了一大批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更是樹立起一座“特別”的豐碑,有力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
“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隨著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實施而逐漸形成。中國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團五院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曾說,載人航天精神的特別之處就在于“特別”二字,“特別”是載人航天精神的核心。
特別能吃苦
中國載人航天事業的起步之艱苦,用“白手起家”來形容,再貼切不過。
落后美俄幾十年,中國載人航天事業想要從“追跑”到“并跑”甚至到“領跑”,必然要用最短的時間找到最優解——苦,是吃定了。
盛夏時節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綠樹成蔭,柏油馬路筆直地延伸至各個廠房,身穿各色工裝的航天人在廠房間穿梭,一派忙而不亂的景象。時間倒退30年,那時的條件沒有現在這樣優渥。
現年83歲的陳灼華是五院最早一批參與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載人航天發射場選址的人員之一,后來,他還受邀參加了海南新建發射場選址論證評審工作。
2022年7月,在我國最年輕的現代化航天發射場——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來這里觀看中國空間站問天實驗艙發射的陳灼華回憶起自己參與載人航天工程的點點滴滴。
“‘921’工程立項之初,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條件和如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想打個電話都要請基地機關的同志幫忙,不像現在手機人人都有。”陳灼華回憶,1993年,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開始選點建設為載人航天服務的發射塔架。在進行大量勘測后,載人航天發射場最終選取了既離生活區不遠又相對安全的區域。隨后,各大系統配套建筑開始在此施工,經年累月,才變成了今天的模樣。
載人航天事業的成就是全國各方面大力協同取得的。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載人航天發射工位、廠房等的建設方面,時間進度要求很緊。工程建設指揮部帶著建設施工單位的人員采取“三班倒”“人停機不停”的方式,克服重重困難推進工程進度。施工人員困了,就裹著大衣打個盹兒;餓了,就泡包方便面;連續奮戰十幾個晝夜也是家常便飯。
被授予“時代楷模”榮譽稱號的航天員群體同樣是胸懷航天報國之志、矢志獻身航天事業的杰出代表。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王亞平在出征太空之前,不敢直視送行人群中的女兒。她婆娑的淚眼,感動了所有人。“媽媽會給你摘一顆天上的星星。”王亞平這樣安慰女兒。
王亞平從太空回來后,女兒收到了媽媽摘回來的“星星”。“媽媽摘的‘星星’本來就是假的……我得將來自己去天空偵查一下,去太空上給媽媽摘一顆巨大的星星!”在王亞平的親身示范下,夢想的種子開始在女兒的心中發芽。
在載人航天隊伍中,大家說得最多的詞是“團隊”“我們”,只要有“團隊”和“我們”,再多的苦也吃得下。正如八院神舟飛船副總師張崇峰講的那樣:“我們天天如履薄冰,我們非常明白,從事載人航天這份事業,要耐得住寂寞,要遠離浮躁。”
特別能戰斗
“特別能戰斗”,是載人航天隊伍始終如一的堅毅恪守。
“載人航天,人命關天”,成敗系于毫發,質量高于一切。在打造第一個神舟飛船返回艙時,技術人員一起將每一道工序、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機件、每一個時間進度節點,都逐一排列出來,制定出的計劃流程打印在紙上長度超過5米。這種精細化的工作極大地提高了效率,加快了飛船的研制進度。
與此同時,僅用4年的時間,載人航天工程的基礎建設就獲得了重大進展,一座具有21世紀國際先進水平的航天城在北京唐家嶺拔地而起。
2011年,我國先后成功發射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神舟八號飛船,實施中國首次空間交會對接任務。這在中國載人航天“三步走”規劃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任務實施前,2010年11月的一天,八院負責對接機構研發設計的副主任設計師靳宗向等人在上海做試驗時,發現神舟九號對接機構上的一個傳感器捕獲信號沒出現。他們當時就想,作為同型號的神舟八號會不會也有同樣的問題?
那時,神舟八號已經運抵北京,處于總裝待命狀態,但由于當時無法判斷傳感器兩個觸點的相對位置是否完全符合標準,他們當機立斷,將對接機構運回上海重新拆卸檢查。經過幾個晝夜的奮戰,解決了可能存在的隱患。
現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空間站系統總設計師楊宏,在工程立項之初就加入了這支隊伍,親身參與并見證了載人航天“三步走”的非凡歷程。
擔任神舟六號飛船副總設計師時,楊宏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無論是在AIT,還是在實驗室,他都身兼數職,主持著各項工作。憑借著務實、穩健、細致的工作作風,他將神舟飛船的技術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13個分系統、643臺設備、40萬條語句、82個軟件、10萬多只元器件無一差錯。
即便現在已經擔任了空間站系統總設計師,楊宏也從未停止過學習、創新的步伐。他積極引入先進信息技術,大膽應用“以太網”“WIFI”等技術,大幅度提升了中國空間站智能化水平和平臺綜合性能。
從飛船研制之初,到如今中國空間站即將建造完成,載人航天的每一點進步,無不體現著載人航天隊伍追求一流產品質量、一流科學管理、一流技術水平的境界和不停戰斗的情懷。
特別能攻關
載人航天是系統最復雜、科技最密集、創新最活躍的科技活動。這項工程不僅綜合性強、協作面廣、技術難度高、風險大,而且總工程研制周期長,任務十分艱巨。
專為載人航天工程研制的長二F火箭是“長二捆”火箭的改進加強型,它因肩負載人使命而與“長二捆”火箭有很大差別,必須先確定安全性、可靠性指標,再根據這些目標來進行火箭設計。
當時,長征系列火箭才發射二十幾次,技術積累和經驗積累還遠遠不夠。加之經費投入有限,研制載人火箭過程中哪些是必須要做的試驗、哪些可以省去不做,上人前需要試驗飛行幾次等,這些都是需要反復研究論證的問題。
在時任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等領導專家的帶領下,結合當時的國情和經費情況,火箭研制隊伍明確了火箭載人需解決的三大技術問題——提高可靠性指標、確保航天員安全和發射載人飛船的適應性。
“載人航天任務要出成果是10年、8年以后的事,工程立項初期選擇了載人航天,可以說就是選擇了寂寞,去發射場執行任務的機會、出國的機會可能就會很少。”一院原黨委書記梁小虹直言。
從載人火箭研制任務下達的那一刻起,一院一部35號樓辦公室的燈光就沒有在正常下班時間熄滅過。研讀資料、討論問題甚至大聲辯論,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在載人航天這個富有挑戰性的高技術領域蹚出中國人的一條路。
現任一院長二F運載火箭總指揮荊木春,那時是負責火箭故障檢測處理系統研制的牽頭人。彼時,該領域在國內是一片空白,涉及多項難題,荊木春和同事可參考的技術資料非常有限,具體方案的實現完全要靠自己在探索中研究解決。
為此,在方案論證階段,荊木春幾乎天天加班熬夜,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可行性報告的準備工作。隨后,荊木春和同事結合外國的先進技術和實際情況,一次次修正、復核、改進,最終形成了故障診斷和逃逸途徑的雛形,為中國載人航天運載火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神舟飛船方面,很多最初參與研制的老專家甚至連飛船是什么樣子都沒見過,但奮力攻關之下,硬是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飛天之路。
自1992年載人航天工程立項實施以來,一代代航天人自力更生、接續奮斗——從無人飛行到載人飛行,從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從艙內實驗到出艙活動,從單船飛行到組合體穩定運行,先后掌握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跨越了發達國家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跡。
可以說,載人航天隊伍篤守“成功才是硬道理”的奮斗信條,用不懈攻關的行動踐行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承諾。航天科技集團原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張宏顯說:“我真切地感受到,載人航天精神是對航天人堅守不渝和科學求實的精神特質的集中反映,實實在在地推動著載人航天事業的發展。”
特別能奉獻
載人航天工程立項后,航天系統開始組建技術班子,任命戚發軔為飛船總設計師。任命剛一周,張宏顯突然接到戚發軔打來的電話:“接到五院人事部門電話通知,今年年齡到了,準備退休。我這個總師還怎么當?”
“當時擔任著型號總師、副總師、分系統主任設計師的同志幾乎全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1995年左右,載人航天正處于初樣研制的關鍵時刻,這批技術骨干都要退休,根本解決不了老帶新的接班問題。”張宏顯回憶說。
怎么辦?航天總部機關提出建議,只要技術骨干滿足“工作需要、本人愿意、身體健康”3個要求,就一律工作到把航天員送上天以后再退休。與此同時,為骨干們增加多個副手,以便選拔接班人,實行“傳幫帶”。
收到這個消息的老同志們頓覺眼前一片明朗——他們非常愿意將畢生的精力奉獻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上。
這樣一來,載人航天技術骨干隊伍更加穩定,同時還完成了新老交替和過渡,45歲以下擔任工程各系統主任設計師以上職務的各級技術骨干所占比例超過80%。一個更加富有朝氣、富有戰斗力的新梯隊形成了。
這群執著奉獻的航天人也一直經受著“中國人沒有技術和能力承擔載人航天工程”的質疑。他們將這些質疑化作前進的動力,為了民族的渴望和國家的重托,傾心盡力地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打造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中國“神箭”“神舟”。
然而,2003年,正當作為國家“天字第一號”任務的神舟五號飛船全力以赴準備下半年發射時,非典來襲。為不拖進度,所有人吃住在工作單位,全身心奉獻在緊張的工作當中。
那時的網絡還不像現在這樣發達,大家忍住思念不回家、不與家人見面,全然不顧安危,最終換來神舟五號發射任務圓滿成功。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近些年。2020年初,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發射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發,研制人員再次傳承發揚抗擊非典時期的奉獻精神,在發射場堅守100多天,圓滿完成了任務。
一直講奉獻,難道沒有外界的誘惑嗎?當然,誘惑一直存在。
“獵頭”們擅長用車子、房子、票子等豐厚條件誘惑航天人,但是他們抵擋住了這些誘惑,自覺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個人選擇與事業需要、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用實際行動堅定地傳承著祖國至上的基因底色。
如果留心觀察,你就能發現,在航天系統之外,還有很多人喜歡將4個“特別”的載人航天精神寫在墻上、掛在嘴邊、記在心里,并不只是因為它簡單、順口,而是它那看似簡潔卻十分深刻的內涵時時刻刻提醒著大家,要向著個人期待、向著美好未來,行走出“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的足跡。
(原載于《中國航天報》,本刊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