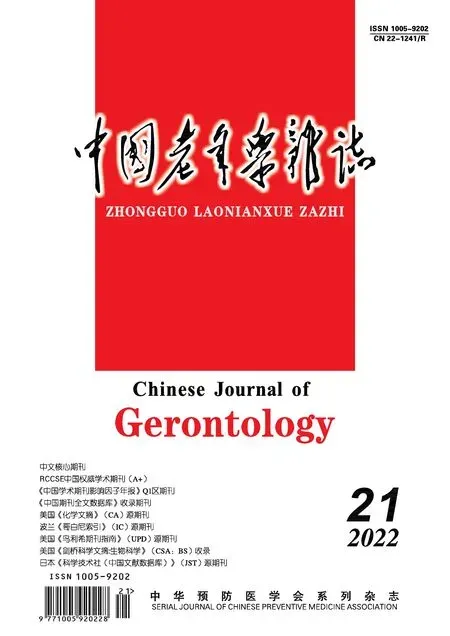腫瘤標志物與結締組織病相關間質性肺病的相關性
楊劉敏 馬天罡 呂雪嬌 任錦
(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吉林 長春 130041)
間質性肺病(ILD)是一組主要累及肺泡及周圍組織和肺間質,以慢性炎癥及間質纖維化為主,具有相似的影像學、病理學和臨床表現特點的肺臟薄壁組織炎癥性疾病。目前ILD的分類采用2002年美國胸科學會(ATS)和歐洲呼吸學會(ERS)推薦的分類方法〔1〕。其中,結締組織病(CTD)是繼發性ILD的首要基礎疾病。CTD相關的ILD(CTD-ILD)患者多為老年人,有報道證實年齡較大、吸煙暴露等是CTD患者并發ILD的已知危險因素〔2〕。由于老年患者的機體免疫力低下、易并發感染及治療藥物副作用等因素,導致隨著年齡增加,CTD-ILD患者的急性加重次數、疾病嚴重程度、住院率和死亡率等也明顯升高〔3,4〕。同時,有研究表明CTD-ILD患者的直接醫療保健,老年護理和間接成本明顯高于CTD不伴ILD患者,嚴重增加了醫療資源消耗、個人及社會經濟負擔〔5,6〕。目前CTD-ILD的發病率及死亡率較高,且治療措施有限,因此早期診斷、盡早干預對改善患者預后、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減輕家庭及社會負擔意義重大。CTD-ILD具有發病隱匿、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發病率高等特點,診治難度大,僅根據臨床征象很難診斷,需結合多種相關輔助檢查。目前臨床上診斷CTD-ILD主要依靠高分辨率(HR)CT、肺活檢和肺功能檢測等。
近年來,隨著免疫學和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新發現的一類與細胞生長和增殖有關,且能客觀反映疾病發生、發展狀況的生化指標被稱為生物標志物。對于幫助臨床醫生早期診斷疾病具有明顯的優勢。腫瘤細胞本身合成和釋放的某些生物性物質,或機體對腫瘤細胞反應而產生的物質,根據它們的生物化學或免疫特征,體液中具有定性或定量變化的物質(不包括來自腫瘤患者的物質和組織)被稱為腫瘤生物標志物〔7〕。然而,現實中并不存在絕對理想的腫瘤標志物。目前常見的腫瘤標志物中,它們不僅存在于惡性腫瘤中,而且在良性腫瘤、炎癥、甚至正常組織中也存在。
目前,多數研究發現在特發性肺間質纖維化(IPF)〔8~11〕中也存在血清腫瘤標志物升高現象,并且這些患者不存在惡性腫瘤病史依據。也有文獻證實腫瘤標志物水平與疾病嚴重程度(比如肺功能指標、肺纖維化程度等)及預后相關〔8,10〕。IPF患者的病理特點是肺泡上皮細胞凋亡、成纖維細胞的增殖和細胞外基質蛋白的沉積〔12,13〕。腫瘤患者的病理特點是腫瘤細胞的持續惡性增殖。這說明在IPF和腫瘤的病理特征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雖然大多數ILD的病因仍不明確,但不論是何種原因所致的ILD,其病理特征均是肺成纖維細胞的異常或惡性增殖。而且CTD所致的ILD與特發性ILD的組織病理學和放射學特征也是相同的〔1,14,15〕。另外,在臨床工作中,尼達尼布常作為IPF患者的一線用藥,實際上,它目前不僅被批準用于抗腫瘤治療〔16〕,還被用于治療系統性硬化癥(SSc)-ILD患者〔17〕。這些說明CTD-ILD與腫瘤的病理特征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進而造成CTD-ILD患者腫瘤標志物水平的異常升高。本文就CTD-ILD與血清腫瘤標志物水平的相關性研究進行論述。
1 CTD-ILD與腫瘤標志物
CTD是一組被定義為以自身免疫介導的器官損傷和循環自身抗體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多系統疾病〔15〕,侵犯全身結締組織,可累及多種臟器。常見的CTD包括系統性紅斑狼瘡(SLE)、SSc、特發性炎性肌病(IIM)、干燥綜合征(SS)和類風濕關節炎(RA)等。這些彌漫性CTD都可累及肺間質,導致彌漫性肺泡及其毛細血管功能單位的喪失,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及生存。目前CTD-ILD的發病機制還不完全清楚,有研究認為與遺傳和環境因素引發的免疫失調/炎癥及隨后的纖維化關系密切〔18〕。CTD-ILD患者與腫瘤患者的病理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臨床工作及研究〔19〕中,我們發現CTD-ILD患者中出現多種腫瘤標志物水平升高,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現象,如癌胚抗原(CEA)、CA125、CA15-3、CA19-9、細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等。腫瘤標志物水平的升高與CTD-ILD發生、嚴重程度及預后密切相關。以下將分別詳述各腫瘤標志物在CTD-ILD的表達情況及意義。
2 CA15-3
CA15-3 又稱為多肽性上皮黏蛋白(PEM),是巨大黏液素樣糖蛋白上的一個抗原決定簇,該糖蛋白為MUC1黏蛋白的產物。MUC1黏蛋白可以抑制上皮細胞之間的細胞黏附,具有降低惡性細胞對細胞毒性T細胞的敏感性的免疫調節作用,與成纖維細胞因子產生作用,促進成纖維細胞增殖〔20〕。CA15-3一般不出現在血液循環中,而血清CA15-3水平升高可能與上皮細胞產物病理性泄漏到血液循環中有關〔21〕。在臨床工作中,我們觀察到CTD患者并發ILD時血清CA15-3水平升高,這可能與肺間質損傷、肺纖維化程度有關。研究發現當RA〔22,23〕、原發性SS(pSS)〔24〕、SSc〔25~27〕、皮膚炎(DM)/多發性肌炎(PM)〔28~30〕患者并發ILD時,其CA15-3水平明顯高于不伴ILD的患者,這說明在CTD患者中,具有高水平CA15-3的患者發生ILD的風險增加。Shi等〔24〕發現高水平的CA15-3不僅是pSS患者并發ILD的危險因素之一,還發現單獨使用CA15-3對pSS-ILD患者的診斷價值并不比單獨或組合的其他腫瘤標志物弱,甚至更高。這充分體現了高水平的CA15-3對pSS患者并發ILD具有較高的診斷價值。相關研究〔25~27〕發現,在SSc患者中血清CA15-3水平與患者的肺部損害程度密切相關。并且De Luca等〔27〕也發現SSc-ILD患者的血清CA15-3水平與用力肺活量(FVC)呈負相關,與肺泡和間質評分直接相關。這些研究表明CA15-3水平對評估SSc患者并發ILD嚴重程度具有重要意義。總之,CA15-3水平在pSS患者并發ILD的診斷、評估SSc患者并發ILD的疾病嚴重程度方面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綜上所述,血清CA15-3水平升高提示pSS患者并發ILD的可能性大;并且其與FVC指標聯合可評估SSc并發ILD患者的疾病嚴重程度。
3 CEA
CEA是一種富含多糖的蛋白復合物,分子量較大,是1965年由Gold和Freedman首次從人類結直腸癌(CRC)組織中分離出來〔31〕。CEA是免疫球蛋白大家庭中的一員,有參與調節細胞進展、細胞識別和細胞黏附的糖蛋白的作用〔32〕。CEA是一種廣譜性腫瘤標志物,可在多種腫瘤中表達,臟器特異性低,可存在于胎兒和成人的結腸黏膜、肺及乳腺中。CEA在終末肺泡腔中存在鱗狀化生、上皮分層及不典型增生這些區域的上皮細胞有著高表達現象〔10〕。近年來,研究發現在pSS〔24〕、SSc〔27〕、DM/PM〔28,33〕患者中,并發ILD患者的CEA水平明顯高于無ILD患者。Shi等〔24〕發現pSS-ILD患者血清中的CEA水平明顯高于不伴ILD的pSS患者,并且與pSS患者是否為疾病活動期無關。結合上文可總結出高水平的CA15-3和CEA可增加pSS患者發生ILD的風險,對pSS患者伴發ILD的診斷具有重要意義。De Luca等〔27〕研究發現CEA水平與SSc-ILD患者的FVC負相關,并且與肺泡和間質評分直接相關。這說明當CA15-3和CEA水平共同升高時,對于評價SSc-ILD疾病的嚴重程度表現出良好的靈敏度。另外,在DM-ILD患者中,Wang等〔28〕發現CEA與CA15-3可評估患者的疾病嚴重程度,并且血清CEA水平高的患者,其死亡率更高。這些說明高水平的CEA和CA15-3對CTD-ILD的疾病診斷和評估嚴重程度有重要作用,但卻缺乏特異性。另外也證明了DM-ILD患者的CEA水平越高,其死亡風險越大。
4 CA125
CA125為一種高度糖基化的蛋白質,于1981年首次被鑒定為卵巢癌抗原〔34〕,存在于上皮性卵巢癌組織及病人的血清中。CA125具有影響細胞間相互識別、黏著的作用,在胎兒體腔上皮分泌物及羊水中及成人的輸卵管、子宮和宮頸內膜也可發現CA125。CA125在卵巢癌診斷方面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差,其他生理或病理疾病(如月經、妊娠、子宮內膜異位癥和腹膜炎癥性疾病)也可致CA125水平升高〔35〕。另外,CA125在氣管、支氣管上皮及腺體和胸膜間皮細胞受到炎癥刺激時明顯升高。研究發現,當RA〔22,23,36〕、pSS〔24〕、DM/PM〔28,29〕患者并發ILD時,血清CA125的水平明顯高于不伴ILD患者。另外,Wang等〔22〕還通過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較高水平的CA125是RA患者發生ILD危險因素。Wang等〔28〕和楊源等〔29〕研究發現在DM/PM患者并發ILD時,均存在血清CA125、CA15-3水平升高的征象。說明當血清CA125、CA15-3水平同時升高時,提示DM/PM患者發生ILD的可能性大,具有較高的靈敏度。
5 CA19-9
CA19-9是一種含有在糖蛋白和糖脂中發現的聚糖抗原的唾液酸,屬于唾液酸化Lewis血型抗原,使用單克隆抗體測量的血清CA199水平升高已被用作胰腺癌的診斷或預后生物標志物〔37,38〕。在正常人唾液腺、前列腺、胰腺、乳腺、胃、膽管、膽囊、支氣管的上皮細胞存在微量CA19-9。有研究結果表明,血清CA19-9水平不僅在胰腺和其他癌癥患者中升高,而且在非癌癥疾病中如肺纖維化等疾病也明顯升高〔39〕。在臨床工作中,我們也發現CTD患者出現肺部受累時,CA19-9水平升高。有文獻證實,在RA〔22,23,36〕、DM/PM〔28〕、SSc〔27〕患者出現ILD時其CA19-9水平升高。Zheng等〔36〕發現,RA患者并發ILD時CA19-9水平不僅明顯升高,且其水平在無ILD的RA患者和健康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當CA15-3、CA125、CA19-9同時升高時,RA患者發生ILD的可能性大,對RA患者并發ILD的診斷具有重要意義。
6 CYFRA21-1
CYFRA21-1是角蛋白CK19的可溶性片段,是一類構成細胞骨架的中間絲狀物,可在腫瘤細胞壞死溶解時大量釋放入血,進而被檢測到。但CYFRA21-1是非器官特異性腫瘤標志物,其主要分布于富含上皮細胞的組織或器官,如肺、乳腺、膀胱、腸道、子宮等,當這些組織發生惡變時,血液中的CYFRA21-1水平可見升高。近年來,發現在非惡性腫瘤疾病中也有CYFRA21-1升高的情況。研究〔29,40,41〕發現,在DM/PM患者并發ILD時,CYFRA21-1水平明顯高于不伴ILD患者。這說明,CYFRA21-1在CTD-ILD的診斷方面具有一定作用。
綜上所述,血清腫瘤標志物檢測可能對CTD所致ILD的早期診斷,評估疾病嚴重程度及預測疾病預后有指導作用。在評估病情時,往往需要綜合多種腫瘤標志物的水平進行評估,如在DM/PM患者發生ILD時,患者多數出現CA125、CA15-3水平共同升高,另外其CEA和CA15-3水平與疾病嚴重程度密切相關,并且CEA水平越高,患者死亡率也隨之升高。SSc-ILD患者的血清CEA和CA15-3水平明顯升高,并且與FVC指標聯合時對評估疾病嚴重程度有重要意義。當pSS患者的血清CA15-3和CEA水平明顯升高時,提示其并發ILD的風險升高;在RA-ILD患者中可發現血清CA15-3、CA125、CA19-9三者水平同時升高。除此之外,還可結合肺功能、風濕免疫特異性抗體指標等共同判定病情的預后及進展情況,從而指導臨床治療。
在臨床工作中,理想的生物標志物應具有高度的特異性,敏感性和預測性。盡管這些研究報道了血清腫瘤標志物對CTD-ILD的診斷、評估嚴重程度等方面具有潛在價值,但仍存在與腫瘤標志物研究相關的問題尚未解決:①這些腫瘤標志物在CTD-ILD中產生的具體機制仍不清楚。ILD的主要發病機制可能與持續損傷,過度修復,上皮細胞凋亡和成纖維細胞病灶的形成有關。ILD的病理特征以成纖維細胞的異常增殖為主,與腫瘤的病理具有相似性。另外,據報道,CA125、CA153和CEA等反映了上皮細胞的增殖和分泌,這可能為解釋ILD患者腫瘤標志物水平升高的原因提供新證據〔42〕。②目前還沒有專門定義的生物標志物來預測CTD患者ILD疾病的發生、發展。單項或多項腫瘤標志物聯合時對不同類型CTD并發ILD的診斷、評估嚴重程度等方面顯現出較高的靈敏度,但其特異性較差,因此,在診斷不同類型CTD-ILD時仍需結合患者的癥狀、體征、其余檢查和檢驗結果。對于CTD-ILD患者的生物標志物研究仍需繼續。③相關研究樣本量小,單中心,缺乏大規模,多中心的樣本數據支持,并且未對臨床驗證進行有效的隨訪。因此,未來關注點仍需進行更多的研究和實驗來進一步客觀地評估腫瘤標志物的臨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