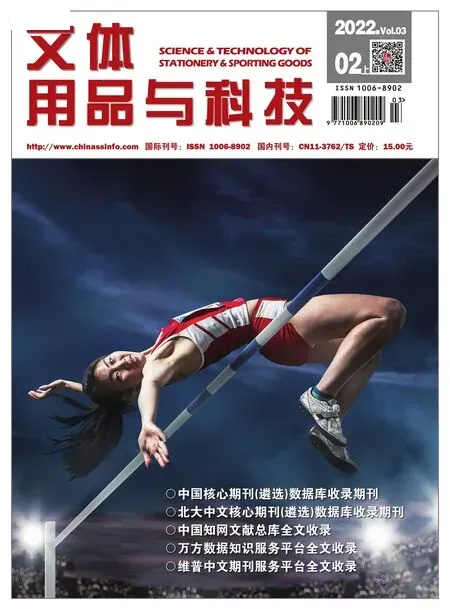漢代蹴鞠比賽模式研究
宋萬政
(南昌大學 江西 南昌 330031)
自2004年國際足聯宣布 “中國古代的蹴鞠是足球的起源”以來,蹴鞠一直都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漢代是蹴鞠發展的重要時期,活動群體廣泛,形式多樣,并初步形成了競技規則,漢代蹴鞠比賽對印證我國競技足球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是縱觀這些研究,許多學者對漢代蹴鞠比賽的概括表達尚未明確。在蹴鞠比賽人數的研究中仝晰綱等(2008)指出:在競賽中,效法歷法中每年12個月的規定,雙方各6人,共12人進行對陣互相抗衡,是謂“法月衡對,二六相當”。但程旭冒 (2011)指出:“二六”在古時以乘法計算,“二六”故指12人,“相當”表示雙方人數相等,即指參賽雙方各有12人。此外,一些學者對蹴鞠比賽的場地抱有不一樣的看法,仝晰綱等(2008)指出:“鞠”是圓形的,球場四周圍著方墻,似有天圓地方的寓意。”但宋秀平等(2010)指出:“文獻中的“墻”,是球門的意思,“圓鞠方墻”則指的是圓形的足球,方形的球門。”
綜上所述,目前對于漢代足球比賽在場地以及組織形式上學者仍存在質疑,這與缺少專門性的、綜述性的關于漢代足球比賽的研究有關。作者以權威史書、權威學術期刊論文等研究為依據,對漢代蹴鞠比賽的歷史地位、競賽場地、參與人員、競賽形式進行概括,以期能對各學者帶來啟發。
1、研究方法
本文在中國知網利用關鍵詞 ,“漢代”、“蹴鞠”為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檢索相關文獻共52篇。作者選取其中核心期刊14篇以及3部專著為本章研究資料。
2、現代競技足球的雛形
通過整理篩選的文獻可知,劉秉果(2002)在《中國蹴鞠與現代足球》一文中指出:“漢代是中國歷史上蹴鞠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時期,這說明足球運動不是一蹴而就,其比賽的模式是在古人的智慧上一點一滴的形成的。”張孟杰(2015)指出:“蹴鞠的形式及制度到了漢代,也有了創新締造,制定了相關的競賽規則,蹴鞠運動競賽規則的健全性、完整性都已見雛形。”崔樂泉(2016)在《中國古代球類活動演進與捶丸起源研究——兼具考古學資料分析》一文中認同了漢代蹴鞠是歷史上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期的觀點。并通過對考古資料的分析,得出漢代蹴鞠運動已經發展的非常專業化。證實此概述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出現了中國最早的蹴鞠專業書籍,其二是,出現了專業的競賽規則。
綜上所述,作者認為該運動從起源至漢代期間可能出現過蹴鞠比賽,但其組織形式以及規則制度并無相關記載。從漢代開始蹴鞠比賽建立了規范化的制度和專業的競賽規則,所以作者認為漢代蹴鞠比賽是現代競技足球的雛形。
3、漢代蹴鞠比賽模式
關于各學者對漢代蹴鞠比賽的基本情況的研究大多數依據東漢李尤的《鞠城銘》為主要參考材料而進行考證,因李尤在東漢和帝、安帝、順帝執政時擔任朝中官員,這篇《蹴鞠銘》的寫作,應是根據他親眼所見而寫成的,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作者將通過查閱相關書籍資料,力求展現出符合歷史的漢代蹴鞠比賽模式。
3.1、競賽場地
對于漢代蹴鞠比賽場地,各學者的觀點存在較大差異,許斌等(2002)指出:“圓鞠方墻,仿象陰陽”意思是:圓圓的鞠像天,屬陽,有圍墻的球場是方的像地,屬陰;場地兩端各有兩個月狀球門,彼此相對。但據何晏《景福殿賦》的“注”得知,每個鞠域有一個守門員,因此場地兩端各有兩個月狀球門與人數不相符合。夏思永(2003)再次指出:“《景福殿賦》記載“其西側有左戚右平,講肆之場,二六對陣,殿翼相當”。李善注釋: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仝晰綱等(2008)指出:在《鞠城銘》中,李尤筆下的蹴鞠場是“圓鞠方墻,仿像陰陽”。即“鞠”是圓形的,球場四周圍著方墻,和“陰陽相對”連起來看,似有天圓地方的寓意。古人有天圓地方之說,認為天屬陽,地屬陰。而鞠是圓的,球場是方的,可比之天地陰陽。而宋秀萍等(2010)指出:“根據《辭源》中的解釋“墻”的意思就是門。故為用圓鞠攻方門,即以圓陽而攻方陰,這就是“仿像陰陽”的真諦。”但作者通過查找古文得知,墻在古文中多翻譯“圍墻”“土墻”“墻闕”從此可看出該學者略顯片面,且陰陽相對在空間上發生了改變,故作者認為墻為門表述不當。程旭冒(2011)指出:“根據漢朝時期建筑習俗,鞠城在場地外還會圍城一堵圍墻,所謂“方墻”,是指“鞠城”的圍墻。書中記載的“法月”,是指法定的半月形門口的“鞠室”。“衡對”是指兩個大小均衡的“鞠室”,分別東西對置。”但帥培業(2011)指出:“在漢代球門設置方面,有學者對“二六相當”理解為一邊六個門洞。”但目前關于“二六”一詞的研究,多指雙方的上場球員,不是指球門數量,因此對于一邊六個球門的設置的假設也被排除。
綜上所述作者認為漢代時期蹴鞠比賽場地為方形用土墻圍起,場地兩邊各擺放一個球門進行比賽。
3.2、參賽人員
關于蹴鞠比賽參賽人員,古文中記載是為練兵而設立的。趙紅衛 (2012)指出:“漢代許多文獻亦把蹴鞠最初的功用定為軍事訓練,借蹴鞠游戲來進行軍事訓練是漢代蹴鞠的一項重要功用。”黃金葵等(2013)指出:“漢代時期,在軍事練兵的常規項目中,蹴鞠是代表性項目,當時所有符合兵役條件的男子都要接受相應訓練。”在裁判員方面,學者間已經形成統一觀點,張樹軍(2009)指出:“比賽有裁判,裁判要秉公執法,糾正誤差,不循私情;雙方都要遵守裁判的裁決;如雙方不服裁決,則由本地執事來最終判決。”程旭冒(2011)指出:“所謂“建長”的意思是蹴鞠項目設立裁判長,存在的意義與當今足球運動裁判相同,“平”是裁判的標準要公平公正,不可徇私舞弊。“其例有常”是指裁判對比賽現場發生的事例,應按常規處理。”張孟杰(2015)指出:“建長立平,其列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可見早在漢代的蹴鞠也已經建立了足球裁判員執法比賽的制度和紀律。
綜上所述,漢朝蹴鞠比賽參賽人員由裁判員和比賽人員構成,比賽人員為士兵。作者認為漢代時期蹴鞠比賽是為了操練士兵,增強身體素質以及團隊協作能力而設立的。
3.3、比賽人數
關于蹴鞠比賽參賽人數的研究,各學者間存在兩種看法,雙方各6人參賽和各12人參賽的觀點。劉秉果(1994)指出:“漢代蹴鞠發展的主流是蹴鞠比賽,兩隊直接對抗比賽,一隊六人由裁判組織比賽。”仝晰綱等(2008)指出:“在競賽中,效法歷法中每年12個月的規定,雙方各6人,共12人進行對陣互相抗衡,是謂“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崔樂泉(2016)指出:“參考古書記錄,當時的球場為方形,競賽隊員為雙方各6人,共12人進行對陣抗衡。”但劉秉果(2003)推翻了之前的看法指出:“上場踢球的隊員是二十人,“法月衡對,二六相當。這里的二六便是乘積,“十二人也。”張樹軍(2009)指出:“十二人制法”來源于東漢李尤在《鞠城銘》中的記載:比賽雙方共有兩隊參加,每隊只允許12人上場;比賽有裁判,裁判要秉公執法,糾正誤差,不循私情。”
綜上所述,各學者均傾向于,雙方比賽人數各6人,參賽隊員一共12人進行比賽,至于守門員存在與否,通過文獻的查閱未能詳細解釋。作者根據《鞠城銘》中仿像陰陽推斷,蹴鞠場地是根據陰陽五行,天圓地方所建立,那么關于競賽人數也應參考其中,雙方各6人對抗,12個人仿像12個月,6陰6陽,陰陽互動,兩儀生四象符合《易經》思想,所以作者認為漢代蹴鞠比賽應是雙方各六人進行比賽。
3.4、競賽規則
關于競賽規則,各學者對其內容研究相對較少。翁士勛(2005)指出:“漢代蹴鞠在練兵過程中主要目的是為了練習士兵團結協作的意識以及隨機應變的反映能力,項目特點即便捷靈活,瞬息多變,快速運球、傳球并通過激烈的身體對抗取得比賽的勝利。”程旭冒(2011)關于蹴鞠比賽的雙方攻防活動,激烈的對抗必不可少。雙方士兵的最終目的則是通過對鞠球的爭搶、傳帶,待機沖破對方的防線,將球攻入對方球門,最后以攻入的球的數量進行勝負的判定。由此可見,蹴鞠運動在漢代作為練兵的項目,既能增強士兵體魄又可提高團結意識。練兵中有著激烈的對抗,其激烈緊張程度,不亞于當今的足球對抗賽”綜上所述,作者認為,漢代蹴鞠比賽同當今競技足球比賽規則相似,通過隊員之間配合將鞠攻入鞠室中即為勝利,外加多參賽人員的分析,漢代設立蹴鞠比賽目的為操練士兵,可見比賽對抗性極強。
4、結論
漢代蹴鞠比賽是當今競技足球的雛形。該比賽模式為:參賽士兵雙方各六人,在場地用土墻圍成的方形場地中進行,場地兩側各設立球門一個,比賽時設立裁判員,雙方球員通過配合將球攻入鞠室為勝利,漢代蹴鞠比賽以增進士兵間配合,提高士兵身體素質而設立,有著激烈的對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