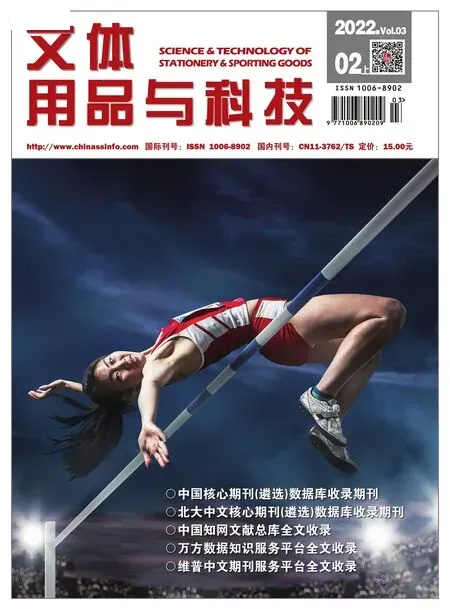論“哥老會”對巴渝武術發展的影響
孫傳娜 黃毅 楊詩夢
(上海體育學院武術學院 上海 200438)
1、巴渝武術的源流與特點
巴渝大地,山高水長;巴渝武術,歷史悠久。兩千多年前,重慶為巴子國都城,《呂氏春秋》里論及“賨人尚武”,這里的賨人即現在重慶嘉陵江沿岸早先的一個民族。據古籍《漢書·西域傳》嚴師古注:“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俞州也。”此處的俞州,曾作為古代巴族人的政治中心,現指重慶城;這也就是現在重慶人自稱“巴渝”的由來。
巴渝武術通指產生或傳播于重慶地區的武術,其作為一種地域武術文化,巴渝武術(指東峨眉派)與巴蜀武術(指西峨眉派)合稱為峨眉派,其中巴渝武術形成和發展與重慶高山大川的地域特點是不可分割的。重慶地區因高山大川、險山惡水的地域特點塑造了重慶人彪悍、頑強、尚武的特點。明清時期,四川人口因戰亂大幅銳減,當時隸屬于四川的重慶影響并不是很大,追其緣由不僅得益于重慶高山大川易守難攻的地形,還因作為“湖廣填四川”的必經之地,大批外省移民停留在巴渝地區結社組織,其中,“哥老會”的會眾在此地活動頻繁。也正是受“湖廣填四川”的影響,逐漸形成了不同于巴蜀武術表現出的內外兼修、巧柔制勝的特點,巴渝武術凸顯出大開大合、剛勁猛烈的特點,如作為重慶代表拳種的 “余家拳”,于1918年由余發齋引入重慶,而余發齋不僅是“哥老會”成員,還被稱為“大爺”(公口帶頭),先是通過藥幫傳授武藝廣收門徒,后又被任命為“揚武國技社總教習”。
2、“哥老會”的源流與特點
“哥老會”最初出現在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并在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得到較大規模的發展。“哥老會”由咽嚕演變而來,至清末民國時期成為盛行于四川、重慶地區的一種秘密結社組織,其成員身份由不同階層組成,俗稱“袍哥人家”,又稱“哥弟會”。其成員在巴渝地區被稱為“袍哥”,也叫“漢留”。“袍哥”的來源大致有兩種,一種是《詩經·無衣》所講:與子同“袍”之義,表示身穿同一袍色的兄弟;另一說是“袍”同“胞”發音相近,寓意袍哥之間好比同胞之兄弟。而“漢留”的說法是取自《三國演義》中關羽棄曹追漢留舊袍的故事,喻意要將其從漢朝遺留下來的精神氣節傳承保留下去。清代文武兼備的秀才何崇政在《拳論》一書上寫一詩:一樹開五花,五花八葉扶;皎皎峨嵋月,風義滿江湖。受此詩影響,人們對“五花八葉”的歷史歸納略有不同,其中趙斌與代凌江在《關于峨眉武術分類中的五花八葉的歷史淵源考證》文獻中認為,何崇政曾投身太平天國,因精湛武藝,善于峨眉槍術與棍術,文墨不俗,被石達開任命為“記室”(類似于秘書),后因清軍追殺,停留在川西、川東等地,通過秘密結社組織“哥老會”來結交豪杰志士,并借傳習武術掩蔽其宣傳教義、社旨試圖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因太平天國面臨分崩離析之節,何崇政甚是絕望,便削發為僧,義憤的撰寫出《峨眉拳譜》一書,而書的開篇詩句中“一樹”指的就是反清復明的秘密結社組織“哥老會”,“五花”指的便是提供組織習練武術的場所,即青牛、青城、鐵佛、黃陵、點易等五個活動據點。
“哥老會”形成初期,主要成員由破產的農民,失業的手工業者、裁撤閑散的軍人、從外省遷入巴渝的移民等組成。而以游民中豪俠善斗者充當領導,煙幫、鹽幫、船幫、馬幫則是該會的組成部分。可見“哥老會”的成員十分復雜,巴渝俗話說:“袍哥能結萬人緣”,“上齊紅頂子(指當官的),下齊討口子(指乞丐)”。按“哥老會”的規定,各執其責,包括江湖上的驚、培、飄、猜、風、火、爵、耀、僧、道、隸、卒、戲、解、幻、聽各色人等,“如身家清,己事明,具有入漢留資格。”其中“解”指的是“跑馬賣解”,耍馬戲和習武的會眾,民間又稱“操扁卦”。在“哥老會”中常常會看到職業不同、身份各異的人稱“兄道弟”,借此來相互扶持。其實質是傳統家族式人身依附的社會組織,此乃中國長期自然經濟形成的封建家族的社會化。
3、“哥老會”對巴渝武術發展的促進作用
3.1、營造了良好的習武氛圍
“哥老會”會眾廣泛,為巴渝武術奠定了龐大的習武人群。單以重慶一地而論,三教九流,簡直無所不有。據1949年《四川幫會調查》和1950年《重慶幫會調查》,重慶袍哥有“五百余社”,袍哥人數“占全市人口70%-80%,而以袍哥為職的人數將近十萬人”。而“哥老會”主要以“仁、義、禮、智、信”為堂口命名,各堂口下的組成人員也不盡相同。新編《宜賓縣志》中有記載:“宜賓俗語說:‘仁字旗買田置莊,義字旗買賣客商,禮字旗弄刀耍槍,方字旗開條想方’”;而巴渝地區“禮字旗堂口”的開設為練武者提供了切磋武技的場所,營造了較為良好的習武氛圍。
在清朝武舉制度的推廣下,巴渝不少道、府、州設有專門習練武術的場所。如,巴渝不少地主豪紳為謀取私利,廣設“武棚”、“箭道”、“馬道”(江北縣復興鄉的“馬道子”便是當時騎射的跑道,至今遺址尚存)。然而對于廣泛的民間喜愛武術者來說,由于身處下層,無法進入專門的場地習武,所以大多無業游民和下層民眾等紛紛加入“哥老會”,在空閑時常練拳習棒、舞刀弄槍、舉石鎖、石擔等,以求強身健體與抗強自衛。這為平日的互助互救和抵抗外來反動入侵時,利用武技與敵人對抗奠定了基礎。如,在1860年前后的李(永和)蘭(大順)反清武裝起義和1863年酉陽、巴州、江北、涪陵、大足等縣先后進行的反帝武裝斗爭中,都充分發揮了練拳、使棍等武術技藝。鴉片戰爭后,巴渝地區習武之人不乏其人,如酷愛武術,喜歡求教切磋,將武術生活化的璧山縣(現璧山區)的鄧顯楊,人稱“鄧四教師”、“國技家”。又如江北魚嘴鄉土地沖的宋宗法海的徒弟周玉峰,因武藝精湛、武德高尚與其次子周應雄等八人合稱“八大金剛”。
3.2、強化了習武者的禮儀教化
未曾學藝先識禮,由此可見,“禮”對習武者而言,它是超越技術層面而存在的。“三道門”是武術拜師禮儀的核心部分,分別是“中間人引進、多方考察、拜師儀式”。而開山分儀式作為“哥老會”尤為重要的儀式,凡入會新人需要由四大盟兄“恩、承、引、保”進行推薦考察,其中“引兄”負責向公口引薦新人,“保兄”負責擔保,“承兄”負責身份查驗,確認新人品行端正后,再有“恩兄”批準加入;待多方考察之后,再需邀請各個碼頭與堂口的人參與祝賀,籌備莊重的開山儀式。據有關重慶袍哥的描述:“會場的布置也是嚴格和壯觀的,門為轅門,堂為‘忠義堂’,正中安置龍頭寶座,兩邊設虎豹皮交椅,大哥、客位坐交椅,可見其布置的嚴謹。”據劉師亮《漢留史》中的開山令,“此為過客適逢該地正作方手,欲出上覆,碼頭上無人,是以實行開山,故用開山令,此事不常有,然有此一令。”
據資料記載,袍哥在相互見面之時必行“作揖禮”以表問候。這與武術的“抱拳禮”雖略有差異,但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巴渝武者尚禮的品行。武術中的“抱拳禮是并步站立,左手四指伸直并攏向后伸張,大拇指內扣為掌;右手五指卷緊,拇指壓于食指、中指第二指關節上為拳,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兩臂撐圓,拳、掌與胸間距離為20-30cm。而袍哥的“作揖禮”則是右手四指卷緊,右手拇指挺直,左手四指自然包裹于右拳的拳背處,左手拇指挺直,右手于內,左手于外;兩大拇指永不倒樁,表示袍哥人家絕不拉稀擺帶(掉鏈子),“哥老會”中的“作揖禮”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袍哥們乃至巴渝武者不能追求私欲,不顧他人,要學會“克己”,即克制不合理的或過分的欲望和要求,使自己的言談舉止時時處處符合“禮”的要求.所謂“克己復禮”,實際上就是講“以禮克己”。而“哥老會”中“作揖禮”歸屬于道德理性范疇,是對“哥老會”中尤其是武者之間、武者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種規范性要求,體現了“哥老會”中練武人之間的群體性的價值關系.
3.3、塑造了習武者的道德品格
未曾習武先明德,這要求武者在習武過程中追求高尚德行。從開山令就可以看出,“哥老會”儀式的嚴格與程序性,每逢開山都要完善準備,進行嚴格的儀式后,由擔保人帶領新人進入會場,紅旗管事負責宣讀新人與“恩、承、引、保”四大拜兄名單;而入會者具備武藝精湛與武德高尚可以作為優先入會的條件。如,在1990年李子峰編寫的《海底》一書中所講“入會者要有忠義之心,還要有武藝方可入會;而道德敗壞、作風不好、門風不正的習武者拒絕入會。”這潛移默化的推動了巴渝習武者對武德的較高追求。
“哥老會”十分注重會眾人員“講江湖規矩”,這和“哥老會”所推崇的精神及道德準則緊密相關,“尚義”是其主導內容,所以說袍哥倡導的“講規矩”最主要的目的是倡導袍哥之間講義氣。“哥老會”倡導“義氣結合、豪俠仗義、團結互助、平等對待”,借以在專制社會里維護自身的生存權利。它要求會眾對艱苦成員實行無條件幫助。另外,“哥老會”為美化“仁、義”,倡導認盜不認偷的觀念,即允許劫富濟貧、搶劫攔道之類的行為,但不容許偷雞摸狗的行為,對盜匪和竊賊持不同的態度。這也充分體現了習武之人的團結與忠義。而這與武德中“仁、義、禮、志、勇”等方面的仁義情懷又不謀而合,無疑是熏陶了大量的巴渝習武練習者,提升了自身的道德修養。
3.4、弘揚了習武者的俠義情懷
“哥老會”在發展過程中倡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較大程度上激發了巴渝武者的俠義情懷。袍哥推崇“桃園聚義”、“瓦崗威風”、“梁山根本”,可以歸結為一個“俠”字。如武藝高強的張達三因“救民若渴、赴義若饑”被人稱為“川西袍哥三巨子”,《漢書》稱之為“大俠”。溫力教授在《中國武術概論》中也明確提到,哥老會、大刀會等結社組織蘊含“俠”(鋤強扶弱、見義勇為等方式)的特征。隨著秘密結社之風的盛行,個體的豪俠演變成了集體的結社組織。這一變化也弘揚了巴渝習武者的”舍生取義”的俠義氣度。
從清代至民國的長期時間里,“哥老會”曾廣泛地活動于川渝的大街小巷,這段時期“哥老會”對巴渝人民影響深遠,現仍然能在巴渝社會中找到“袍哥人家”的影子;常聽到一句口頭禪是:“袍哥人家,義字當先,決不拉稀擺帶!”。“拉稀擺帶”一詞在四川話里指的是那些在關鍵時候掉鏈子,做事情不可靠的人,不講信用,在關鍵時候不能迎難而上,反而顯示出懦弱,退縮的一些特質。而“袍哥人家”則從來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因此在這句話中,一定表達出來的是對“袍哥人家”俠義氣度的一種肯定,乃至贊賞。如出生于重慶市北碚區的一個自耕中農家庭的劉子均,自幼習武,敢于仗義執言、鋤強扶弱,深得街坊鄰居一致好評。可見“哥老會”中倡導的俠義情懷與巴渝武者的生活相交融。
3.5、激發了習武者的愛國熱情
民國初年“哥老會”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無不激發著巴渝武者的愛國熱情。伴隨清王朝腐敗加劇,社會動蕩不安,官逼民反日益嚴重,出現了“要生存,就要斗爭,就要習武”的狀況。為擺脫困境越來越無業游民和下層民眾等加入“哥老會”,常練拳習棒、舞刀弄槍、舉石鎖、石擔等,健體強身、抗強自衛、互救互助,以便遇到外來反動入侵時,挺身而出,利用武技與敵人對抗。咸豐十一年,張弟才等人聯合當地“哥老會”,攻占涪州鶴游坪(今重慶墊江縣坪山鎮),發布檄文,彰顯了李藍起義軍討伐清政府的決心。在此期間越來越多的習武人士相繼加入“哥老會”,響應李藍起義軍號召,至此重慶袍哥們的反清運動達到了高峰。而在重慶光復過程中,同盟會與袍哥會開展合作,如,武藝高強的石青陽、夏之時等同盟會員便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哥老會”,取得了袍哥們的支持,為即將到來的起義拉攏人手。不管是1860年前后的李(永和)藍(大順)反清武裝起義還是1863年酉陽、巴州、江北、涪陵、大足等縣先后進行反帝武裝斗爭中,都充分發揮了練拳實使棍等各種武術技藝,推動了巴渝武術的發展。又如聞名重慶的袍哥仁字號大爺張樹三,是重慶有名的拳師。相傳他一掌能擊碎20匹磚,從學門徒甚眾,好交朋友,任俠好義,武藝高強。曾在辛亥年重慶反正之時,號召大批武藝高強的袍哥弟子和門徒參加起義。
巴渝“哥老會”作為辛亥革命時期同盟會的重要合作方,袍哥在當地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最終因其封建性逐漸淡出了巴渝人民的視野,然而在當時出現的“要生存,就要斗爭,就要習武”的習武氛圍下較大程度上推動了巴渝武術的發展,這是毋庸置疑。
4、結論
在清末民初的動蕩年代,“哥老會”作為一大互救互助社會秘密組織,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雖然“哥老會”中的由官僚士紳們組成的“清水袍哥”會欺壓百姓,同時“哥老會”對會眾處罰嚴苛、封建落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哥老會”會眾廣泛,較大程度上為巴渝武術的發展奠定了龐大的習武群眾基礎,營造了“要生存,就要斗爭,就得練武”習武氛圍;而其嚴密的規范儀式,強化了“哥老會”成員和巴渝習武者的禮儀教化;也因為“哥老會”講江湖規矩,塑造了“哥老會”中的巴渝習武者的道德品格;而“哥老會”在發展過程中倡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較大程度上激發了哥老會會眾“忠、義”的俠義情懷;而后在民國初年“哥老會”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無不激發著“袍哥”乃至巴渝武者的愛國熱情。“哥老會”在亂世中較長時間的立足并且逐漸發展壯大,可以說“哥老會”在巴渝武術的發展中有較為著緊密聯系。“哥老會”不僅繼承和發展了部分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而且在重慶近現代歷史上扮演過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研究 “哥老會”有助于我們今天正確認識和理解近代巴渝武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