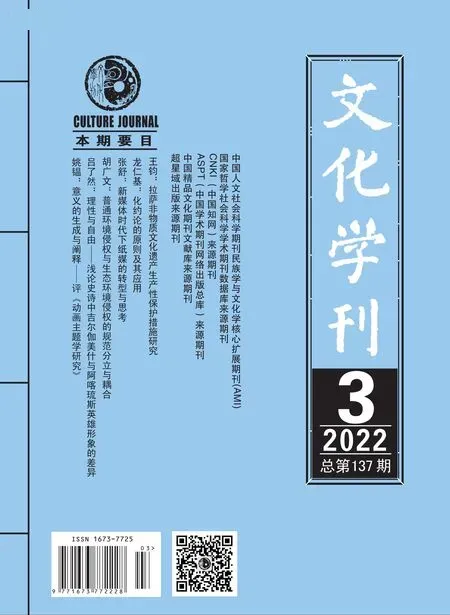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理性主義國家觀解讀
代 博 代建鵬
馬克思早期政治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在這一時期,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開始接近于啟蒙主義,而后逐漸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的政論實踐進一步增強了他的政治觀念,他開始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馬克思基本是站在理性主義的立場上,表達他對國家、法和社會現實關系問題的認識發展。
一、馬克思理性主義國家觀的理論來源
(一)國家的理性基礎——契約
社會契約思想起源于古希臘時期,以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為代表的思想中都帶有社會契約的思想萌芽。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論述了伊壁鳩魯和德謨克利特對于原子運動的不同看法,進而從排斥運動引申到近代契約論,批判契約論建構的現實基礎的“自然狀態”,把契約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之上,將政治國家的理論研究和人類現實社會相結合,完成了對傳統社會契約論的超越。
1.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和國家的起源
霍布斯認為國家是由人們的意志和契約構成的。他認為,人是一種“自然物體”,人的自然權利,來源于國家同時又受到國家的約束,人們在自然狀態中生活必須依靠“自然法”才能維護生存權利。“自然法”只是在道德的基礎上,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幫助人們擺脫困境,為了達到自我保存的目的,人們訂立契約轉讓自然權利,以契約說為基礎的國家學說揭開了籠罩在統治權力之下的“君權神授”的神秘面紗。人類在訂立契約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從自在世界進一步轉向人化世界,最終產生國家。霍布斯第一次用人的自然屬性和自然理性闡述國家的起源和本質,對后期的社會政治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洛克的社會契約論
洛克根據人性論、自然法理論系統地制定和完善了有關國家起源、本質及形式等理想政治理論制度。洛克認為自然狀態是和平與自由的狀態,人們平等的享有自然權利,在平等的基礎之上,由于沒有自由限制,人們難免產生爭奪財產權的沖突,訂立社會契約建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財產糾紛,保護人們自由、財產等自然權利,人們所放棄的只是維護自然法、懲罰犯罪者的判決和執行權力。契約對任何人都具有約束力,統治者是參加契約的一方,是從訂立契約的人們中選出來的,因此,也受到契約的限制,人民有權推翻暴君。
3.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盧梭認為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借助自我完善化的能力,思維變得更加活躍,伴隨著社會生活和人類語言、智力等方面的發展,逐漸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人們開始結成了家庭,導致人類不平等的根源及私有制的產生。盧梭認為人們之間建立的約定是社會公共秩序的基礎,公意是社會契約的基礎,是人民共同意志與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現,指導人們在不平等的社會狀態下公意保障個人自由,在具體的社會政治實踐中表現為法律,法律保障個人的權利平等。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建構起了民主政治思想,即“人民主權的民主共和國”。
《萊茵報》時期以前,馬克思在哲學范圍內的政治思想意識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比較了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思想,馬克思認為,排斥是自我意識的最初形式,標志著原子概念的最終實現。原子在感性的狀態下依靠排斥具有了物質的屬性,原子在與他物的相互運動中,由于其物質性即物質關系的影響,原子始終受到外部力量的約束和形式規定從而缺乏獨立性和自由,而在原子的排斥運動中,其特殊意志與普遍意志相結合,特殊意志受到普遍意志的約束和規定,但在二者的對立統一中,原子固有的獨立性和自由并沒有被去除,這也正與盧梭倡導的公意相符合。因此,馬克思對排斥運動的意義引申到社會政治領域:實現了原子排斥的諸形式在政治領域表現為契約,在社會領域則表現為友誼。馬克思認為,契約是政治國家的理性前提,本身來自于“市民社會”而不是人類自然狀態中。“政治社會依賴于一種契約和協議”[1],馬克思站在人與社會關系的角度上批判了契約的理論前提“個人主義”以及資產階級虛假的自由民主理論,引申出取消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博士論文中的政治國家意識既是對近代契約論的繼承,也是對它的超越和發展。
(二)黑格爾的國家觀
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最關注的政治問題是國家問題,這一時期,國家的作用貫穿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馬克思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方法受到黑格爾國家觀的影響,然而,黑格爾的國家觀在面臨“物質利益”難題、國家理性和社會現實的沖突等困境時束手無策,馬克思開始反思和懷疑黑格爾國家觀,由此開始新的探索。
首先,黑格爾是客觀唯心主義者,他對國家的理解是從自身觀念出發,認為國家是自在自為的觀念的理念。黑格爾認為真理是一個過程,遵循著“正題-反題-合題”的邏輯形式,是絕對精神的外在表現。他把人類精神視為絕對精神實現自己的手段[2],現實世界、國家是從屬于絕對精神的,因此,他的理性國家觀也帶有客觀唯心主義色彩,具有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
其次,黑格爾強調“整體主義”,國家是一個整體性的機構。市民社會的特殊利益是普遍之外的利益,他認為國家意識包含在和它不相適應的官僚政治中,公眾意識是多數人觀點的融合,官僚機構能夠暫時緩和利益矛盾,正是由于國家的存在這種矛盾才能解決,國家作為有機的整體,國家是個人的客觀化和現實化,使個人融入到整體中。
二、馬克思理性主義國家觀的體現
《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的國家觀念仍然受到黑格爾的國家觀的影響,但同時,馬克思意識到黑格爾哲學在處理現實利益問題時的局限性,由此在社會現實問題中進行新的探索。
(一)反對書報檢查令
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馬克思批判書報檢查令用法律的形式來管制人的思想,限制報刊出版者獨立行使對官員和國家機構批評和監督權利,這種“虛偽的自由主義”剝奪了報刊出版者本人的批評和監督權利,批評反而成為書報檢查官的職責,這種相互關系就本末倒置了。馬克思批判書報檢查令拒絕人民公開發表意見,批評和監督的客觀標準已經消失了,官員的批評只是在表面上代表國家普遍利益,然而實際權利的支柱往往是特殊利益代表,這樣的國家是他律的基督教國家。
在《關于出版自由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中,馬克思闡述了各代表為自我等級辯論的不同意見:諸侯等級代表認為報刊是上流社會的出版物,他們斥責人民“不謙遜”而反對出版自由;貴族等級歪曲普遍權利的概念,認為應該把省議會“真實”的事情“全部公布”;騎士等級代表從人們思想不成熟出發反對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本身是思想的體現,用“人的不完善”來混淆檢查制度和出版法之間的本質區別;城市等級的辯護人把出版自由歸結為行業自由,然而把出版物和行業混為一談,相當于只討論出版商和書商這類的工商業謀利領域,把出版物作為一種物質手段;最后,馬克思贊成農民等級的辯護。新聞出版應該擺脫特殊利益等級的約束和限制,按照自身的規律自由、獨立地發展,充分體現人民意志。
書報檢查制度在形式和本質上的客觀標準都是建立在檢察官員的虛幻概念之上,因此,廢除書報檢查令,設立自由報刊才能獲得更多的真正的自由。自由報刊是社會輿論的產物,同時又反作用于社會輿論,它化私人利益為普遍利益。自由的出版物是聯系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的有聲紐帶,它體現人民公開表達自由意識的權利,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因此,“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3]。”
(二)對歷史法學派自然法和實證法的批判
18世紀末的德國人在同法國文化的對抗中感受到傷痛和自卑,開始反對把自然科學所包含的一切傾向性,以此為背景,德國漸漸出現了以浪漫主義反對理性主義的思想傾向,認為民族的發展需要民族精神的實現,這種思想促成德意志法律思想新出路——歷史法學派。
1.對自然法的批判
馬克思指出歷史法學派的自然法思想以“原始狀態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為基礎,我們可以借助胡果的自然法來追溯歷史法學派的發展,但胡果還沒有接觸到浪漫主義的自然狀態的人,胡果的自然法思想可以上溯到海德,胡果作為歷史法學派的自然人,他認為每一個時代都可以依靠自己獨有的特點產生出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自然人,自然狀態的人沒有固定的模樣。胡果編造虛構出他的自然法理論,企圖將現實社會投射進他虛構的自然之中,“為力圖證明他的歷史資料是如何符合現代社會埋下根基,為他的實證主義理論創造歷史證據”[4]。
2.對實證法的批判
馬克思批判胡果認為存在即權威,他的論據是實證的、非批判的,并不能分辨出差別。歷史學派將各種各樣的“實際”當作武器,不斷否定他們自己認為不正確的原則,德國的制度中的腐敗形式和專制制度同樣實際,然而歷史法學派不會去打碎德國舊制度權威束縛人們的鎖鏈,相反,實證主義是對現實的無條件承認,胡果顛覆的是將虛幻的、空想的東西當作實際,否認存在事物合乎理性。在他的懷疑主義中,不合乎理性的事物成了實證事物,去除實證事物中的理性假象,而承認失去理性假象的實證的現實。馬克思從理性出發,批判胡果用這種荒誕的庸俗的懷疑主義扼殺了實證事物的精神。馬克思通過從歷史法學派批判轉向批判現實,試圖喚醒普通民眾的革命意識,體現了馬克思向唯物主義轉變的過程,“一切從‘現有’出發,從現實社會的客觀存在物出發”[5]。
(三)私人利益、等級制和國家理性的矛盾
在萊茵省,隨著資產階級和物質利益矛盾問題的發展,社會階級貧富對立日益嚴重,造成“貧民階級”的產生。馬克思指出省等級議會將撿拾枯樹枝和活樹枝混為一談,站在林木所有者的立場上給撿拾枯樹的貧民定罪。馬克思批判等級代表使用的“習慣法”是一種“特權者的習慣和法相抵觸的習慣”,然而立法只是在處理私權方面把權力提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把偶然的讓步變為必然的讓步。法律本應體現人民的普遍利益,體現事物的法的本質的真實表達,但是法律把未必違反森林條例的行為強行貼上盜竊林木的違法行為的標簽,使“貧民階級”成為法的犧牲品,只保護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把民眾的懲罰本末倒置了。馬克思用自由的理性國家觀批判等級議會的辯論,他們的基本原則只是為了確保林木所有者的利益。
馬克思認為人民理性的國家觀的實現在世俗生活中遭遇到私人利益的阻擾。私人利益的數字只是披上了理性的外衣,它是隨機編造的。“利益就其本性來說是盲目的、無止境的、片面的,它具有不法的本能”[3],立法并沒有取消國家對等級所有權的特權,利益試圖掌控法的規則,私人利益是與等級制度聯系在一起的,等級的代表力圖歪曲私人利益所有權的概念,使國家成為私人利益的工具。馬克思批判說,立法者的最高本質是非人道的、異己的,私人利益作為一種拜物教,它抹殺了不同事物之間的區別,“人們的拜物教就是動物崇拜”[3],與國家理性相對立。
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批判省等級議會只代表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它把對行政機構等特殊等級的懲罰降低到私人利益物質手段的水平,法律效力只是一種多余的形式,只剩下一副“空洞的假面具”。因此,解決法律規定的各項原則和保護林木利益之間沖突的最佳途徑是取消等級制,建立人民代表制,萊茵省的公民應該戰勝等級代表,擺脫“下流的唯物主義”,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各級人民的普遍利益,體現出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的統一。
(四)現實和管理原則之間的矛盾
在《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中,馬克思基于官僚政府發言人關于富有的土地擁有者和貧窮的葡萄酒釀造者矛盾沖突的辯論,抨擊摩賽爾河沿岸的貧困是由于官僚機構的治理貧困導致的。辯護只是形式上的公開坦率的討論,政府機構并沒有采取實際有效的措施來解決貧困問題,相反,他們認為貧困者的消亡這是一種自然現象,貧困者的求助也不過是“無恥叫囂”。
管理機構僅僅在改革治理的對象上勤懇的努力,并不關注改革治理的方法,官僚等級制度的法律把公民分為積極覺悟和消極不覺悟兩類,積極覺悟的公民沿著管理機構的原則“升官發財”,消極不覺悟的公民卻需要忍受物質和權利上的雙重貧困,這種現實和管理機構的矛盾沖突體現了行政當局的“官僚本質”。官方發言人認為摩賽爾河地區沿岸的貧困原因是由于貧困者自身,而不是行政當局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而馬克思認為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官僚機構的不作為和逃避責任。葡萄酒釀造者在遭遇貧困的威脅時想要揭露官僚世界的虛假景象和利益矛盾沖突,然而,官員們出于自私自利的本性驅使,“想用官僚的理智去對抗市民的理性”,把大部分過錯推卸給私人,指摘私人把私人利益夸大成國家利益,以此來力圖保持自己“權威的官僚的現實”。官僚機構下的行政當局并不能維護人民的合法利益,傾聽人民的現實生活需求的真切呼聲,把治理內容和治理形式本末倒置,因此,解決貧困的問題就需要廢除官僚機構和官僚等級制度,并且設立理性的、代表人們獨立意志的“自由報刊”。
馬克思《萊茵報》時期是其思想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其政治哲學思想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通過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推動了他對黑格爾國家觀的反思和超越,進而形成自己的理性主義國家觀,也促使他從政治轉向政治經濟并朝著哲學社會主義方向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