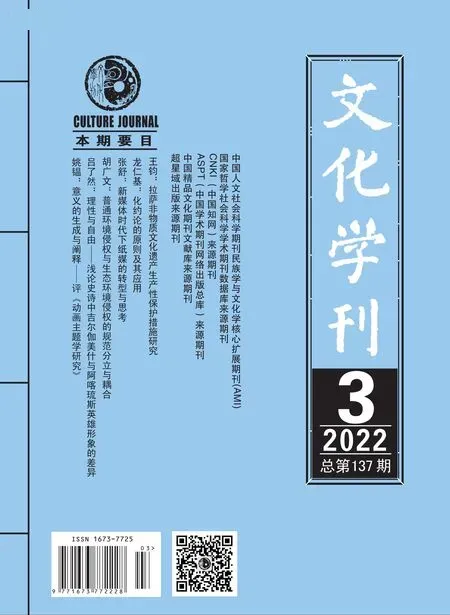略論中國古代哲學的知行觀
邢在陽 魏 姍
方立天先生在《中國古代哲學》中討論了關于中國古代哲學“知”的三種含義:知覺、知識、道德意識。知覺即一種認識事物的能力;知識則是對于事理法則的理解與掌握;道德意識即人對于是非善惡的認識及標準。三者具有明確的差別。相對于“知”的概念,“行”的概念比較簡單,“多指個人的行為、活動,尤其是道德行為,個別的哲學家也用以指生產活動。‘行’也稱‘為’‘習’‘實踐’等含義”[1]50。由此來看知行關系問題,就是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問題。這樣的關系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知”從哪里來?二是“知”對“行”有什么樣的作用?一直以來我們對于知行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于知行是否有先后,如果有先后,孰先孰后?于是就產生兩種主張:一種是贊成“知行合一”,即“知行無先后”;另一種主張“知先行后”或“行先知后”。知行的先后問題是認識的來源問題。由于這兩種觀點的分歧,又衍生出知行孰難孰易和孰輕孰重的問題。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知行的難易只是在相對意義上的難易之分。而知行兩者的輕重問題,則涉及認識中的地位問題[1]21。
一、思想淵源
知行觀是中國哲學特有的話題,在西方哲就沒有這樣的說法[2]。“知”涉及“認識”領域,而“行”涉及“實踐”領域,這在西方哲學是兩方面內容,分別對應“知識論”與“實踐論”。而中國傳統哲學中,哲學家們不認同世界二分化,所以知行觀通常作為一對范疇出現。這對范疇最早出現在《左傳·昭公十年》:“非知之實難,難在行之。”《古文尚書·說命中》也有相近觀點的記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通過這兩則記錄,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出當時古人已經有意識地將知與行并列起來,并且認識到知易而行難,強調了知行合一的觀點[3]。對后世影響意義重大,甚至成為儒家知行學說的重要傳統觀點。
二、發展階段
關于認識的來源問題,春秋末期孔子區別了“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他對“學而知之者”給予了肯定,并且總結了兩點學習方法:第一,“多聞”即“多見”,多看、多觀察是獲得知識和提高道德修養的重要途徑;第二,“思”即“思索”,“學”“思”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 “學”在一定程度上屬于“行”的范疇。據此可知,孔子比較強調“行”的意義與價值。孔子也提出“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觀點。
孟子繼承了孔子“生而知之”的思想,發揮了“良知”說,認為“良知”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而獲得“良知”的途徑就是“盡心”。充分發揮四端之心,就可以認識到自己的本性。認識到自己的本性也就是認識了“天”,達到了最高的修養境界。他繼而提出了:“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這里“求其放心”就是“求學之道”,也是衡量認識的標準。“盡心”就是“知”,“放心”就是行,這具有鮮明的知行合一的傾向。
荀子發展了孔子“學而知之”的思想。他認為,人具有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并且世界也是可知的。認識都是由五官而來并經過心的辨別作用形成的。在知行關系上,荀子強調行比知更重要,他認為去做合乎義的事情叫作“行”,人的認識能力叫作“知”。同時,人的日常活動都屬于行的范圍。他認為知道而力行,這是體認道德,所以荀子強調言行一致,并且行高于言。
春秋時期道家的創始人老子倡導“無為”,向往自由、無拘無束的生活狀態,“他認為‘知’是促使人們脫離這種生活狀態的重要原因,所以在認識論上又強調‘無知’[1]51”,“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老子·第四十八章》)在老子看來,修道的過程中,會因其他事情而產生紛擾,所以他反對接觸外界,排斥感性認識。因此,知行關系在老子這里是不去作為也可以有成就,圣人足不出戶便能知曉天下事。道家著作《莊子》中認為知識以及一切相對的事物都是達到理想境界的障礙,認為如果從萬物本質上看,萬物是無差別的,也就是“齊”的觀點。《莊子》看到了事物的統一性和差異性,但是更側重于強調事物的相對性,并且對于認識主體的能力也持懷疑的態度,認為認識者究竟是不是在認識,能不能認識,也是很難斷定的,莊子的思想對后來的郭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除了儒家和道家,墨家對于知行觀也有一定的表述。墨家的創始人墨子,在認識論上強調“知”來源于“耳目之實”,認為知識來源于對外物的感覺。“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非命上》中,墨子十分重視知對于行的作用,同時又十分強調知后要行,不能只知不行。墨子強調“言必信,行必果。”重視道德上的言行合一。后期墨家繼承和發展了墨子的認識論,對于人的認識能力、認識來源和過程,以及知識的分類和真理的標準等問題,都做出比較正確的論述。首先,后期墨家認為,人們的知識來源于感官和經驗。其次,后期墨家認為不能停留在感官所得的感性認識,人還能對客觀事物進行思慮、探求、比較、推究。這種從“接物”到“論物”就是比較全面地看到了感覺與思維的作用。最后,后期墨家根據知識的來源,把知識分為三類:“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墨子·經上》)后期墨家重視“親知”,強調直接經驗是“說知”的基礎,同時又不停留在直接經驗上,肯定“說知”即推論認識的重要性,這是比較全面的認識觀點。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韓非,繼承墨子和荀子的認識觀點,并且吸收和改造老子的道論,提出了“緣道理”的認識學說。“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托于天智以思慮。”(《韓非子·解老》)人們的認識活動,就是依靠這些感覺器官和思維器官去實現的。韓非認為只有正確的知才有正確的行,知對行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為了取得正確的知,韓非還著重強調“虛靜”的重要性。這是對老、莊的虛靜和荀子的“虛壹而靜”觀點的繼承。
三、主要類型
在先秦時期,經過哲學家們的不斷研討,知行關系向知行一致且重行的方向發展。中國哲學中的知行關系大致可分為三種:重知,并且強調知對于行的指導作用;知行一致;“知出于不知”的不可知論。
(一)重知
西漢時期的董仲舒,從他的“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出發,繼承了儒家的觀點的同時,將天神化,主張人們認識的根本任務就在于體認“天意”,按“天意”行動。“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董仲舒認為“知”能洞察未來禍福利害,預見事物的變化和終結。但是,董仲舒所講的“知”是體察“天意”而后行,把“知”放在起點,夸大了“知”的能動作用,否定“行”是“知”的基礎。
在《淮南子》中,我們也能看到重知的思想。它首先指出,感覺是通過感官獲取的,并且不同的感官各有其感覺作用。“視而行之,莫明于目;聽而精之,莫聰于耳。”(《淮南子·汜論訓》)《淮南子》十分重視“知”,強調“知天”“知人”,認識的任務是要懂得宇宙的自然規律和人間的行為準則,缺少任何一方面或不能與世俗相交,或不能與天道共游。知之重要,在于對行有指導作用。
《淮南子》認為,人的行為是以一定的認識為指導,而人的認識并不都是正確的。所以人們在做事情以前,都要進行謀劃,而謀劃也有是非利害之不同。《淮南子》認為圣人在確定計劃時,先權衡事情的輕重緩急,看清局勢的變化。它強調人的知與行要隨客觀事物的變化而相應變化,它的知行觀的內容是比較豐富的。
(二)知行一致
知行一致的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東漢時期的王充,他著《量知》《實知》《知實》等文,反對漢代流行的“圣人生而知之”說,強調只有接觸實際事物才能取得感性知識。并且對于知的重要性,取得知的途徑,以及知與行的關系都作了明確的闡述。
首先,王充吸取和改造了先秦孟子思想中“勞力者”和“勞心者”的觀點,把人的能力、力量分為兩類:體力和知力。“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論衡·效力》)儒生的能力是有知識,壯士的能力是有力氣,兩者的“知”不同,前者的“知”為博覽群書,而后者的“知”則是舉重拔堅。王充贊揚前者,他認為,知識越豐富,能力越強,力量越大。這里的“知”,主要是指社會政治道德知識,即社會科學知識,然而,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比王充提出的“知為力”的觀念晚約一千五百年,由此可見王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其次,王充反對“生而知之者”的存在。在王充看來,知的來源有四:“聞見”,即感知;“思慮”,即思知,用心思索,進行推論和類比,以求得對難知問題的認識;“學問”,好學多問,既向廣見博識的人學習,也向有實際經驗的人學習;“日為”,經常實踐,培養技能,豐富知識。王充看到了獲得知識的多種途徑,看到了知識技能來源于生產實踐,堅決批判“生而知之”說。對于“不可知之事”也有兩類:一類是通過學和問能夠認識的“難知之事”;另一類是通過學和問也不能曉得的“不可知之事”。這里王充提出“不可知之事”是為了論證“圣人生而知之”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4]。
最后,王充重視知識的廣博,主張博學多問,以避免孤陋寡聞。同時,他還強調要能通,即對廣博知識要加以融會貫通。他重視學以致用,強調學用結合,認為知識最重要的就是能用。
(三)不可知
西晉哲學家郭象通過注釋《莊子》,構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他的“以不知為宗”的認識論與獨化論密切相關。
首先,郭象把認識對象分為兩個方面:事物的現象是可以認識的,而事物的本質、根源和規律是不可認識的。“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莊子·天運注》)也就是說,萬物獨化自生,無本可溯,是不可認識的。
其次,郭象認為人的認識能力和認識范圍也都是有限的,所知、所為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知應該只局限于自己的本分,就是性分之內,不應該在性分之外追求。他發揮了莊子的思想,如果人要以有限的性分追求無限的知識必定是疲憊的。在郭象這里,“知”的含義又有了變化,知是人的自然本能、本能活動,是“性分之知”。郭象舉例說:腳走路,眼看物,只是一種自然生理本能。由此郭象主張取消主觀的認識活動。知是自知,自知就是認識到自己不知,所以知是出于不知,應以不知為宗旨。
最后,郭象認為事物的本質不可能被認識,人的認識能力也有限,因此,他主張人們應當順其自然地使主觀與客觀相冥合。這樣冥合自然的境界就是物我俱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即忘其跡,又忘其所以跡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后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莊子·天地注》)“坐忘”是要消除事物內外的差別,消除主觀和客觀的對立,然后與萬物合為一體,,這就是“玄冥”之境。所以說郭象是繼承了《莊子》又發展了《莊子》,宣揚神秘主義“知出于不知”的不可知論。
四、結語
我國古代哲學的知行觀蘊含在個人的學說和思想中,從先秦開始,逐漸形成中國哲學重行的傳統。“認識來源于實踐”這一觀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并且承認人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哲學家們對于知的內容論述更加具體化,體現在知的概念、知的來源、知的能力等方面。并且知與行的關系也不斷地理論化,對于后世的影響較為深遠。這些理論對于我們今天的生活仍具有一定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