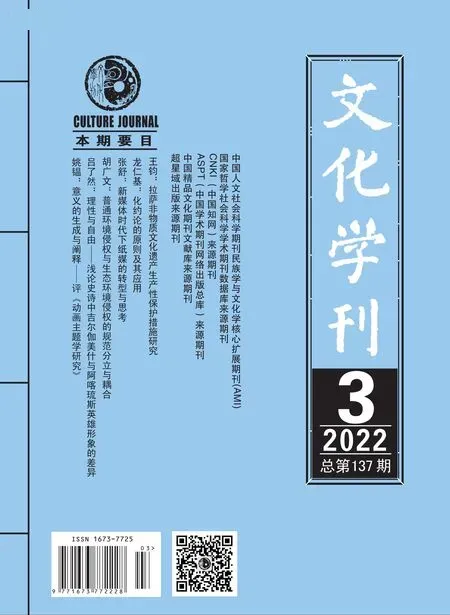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理論探析
彭美琳
一、馬爾庫塞單向度理論的主要思想來源
(一)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
馬爾庫塞認為,馬克思所提出的勞動異化理論是一種提倡人類解放,注重自由、本質及主張人本主義的理論,伴隨著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的形成,受到啟發(fā)的馬爾庫塞推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馬爾庫塞肯定了《手稿》的存在價值,認為“《手稿》中圍繞歷史唯物主義的緣由及其含義做出了探討,找到了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探討何為科學社會主義。”[1]此處所講的全新方向,是指關于人的理論,是人道主義。馬克思的理論不僅描述了異化勞動而且描述了人的異化狀態(tài)以及人性的扭曲。馬爾庫塞基于馬克思提出的異化勞動理論,結合異化社會的特點,將存在其中的人視為是“單向度的人”。向度在界定方向或維度時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單向度的人是不再具有否定性,且喪失了批判性的人。他將這兩項能力定義為人與生俱來的能力,且具有雙向度特性。然而伴隨著工業(yè)技術的持續(xù)發(fā)展,勞動異化普遍化,越來越多的人因此成了單向度人,人的本性也因此而變得日漸扭曲。不同于馬克思,面對勞動異化成因,馬爾庫塞認為與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關聯(lián)有限,他認為是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科技是造成該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在科學技術的持續(xù)發(fā)展中,資本主義成為了各個對立面的控制者,伴隨著資本的控制,面對難以改變的客觀事實,人們逐漸依附于現(xiàn)實,喪失了反抗能力。從該層面而言,馬爾庫塞是參考馬克思的理論,針對異化社會及異化個體進行分析,對其理論的形成打下基礎。
(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
除了基于馬克思的理論以外,馬爾庫塞適當吸取了弗洛伊德的觀點,這一點能夠通過《愛欲和文明》得到參考。《愛欲與文明》是其思想發(fā)展中的代表性作品。書中他參考了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觀點,并以人的無意識領域作為切入點,總結出資本主義社會由于技術的發(fā)展、人的異化,使人的愛欲受到抑制,是異化的社會。處于研究階段的馬爾庫塞突破性地將勞動異化理論和精神分析學融為一體,從分析個體行為及意識逐漸向著無意識領域進行拓展。在他看來,人從出生伊始就有愛欲,但在科技發(fā)達的工業(yè)社會中,人的天性無法被釋放甚至備受壓抑,而解放異化勞動的本質便是讓人們釋放自身的愛欲。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代表先進生產(chǎn)力的技術逐漸成為新的統(tǒng)治工具,迫使人們成為各種物質的追求者亦或是“被奴役者”。個體的反抗意識和否定能力逐漸喪失。弗洛伊德曾通過分析個人及屬系的發(fā)生層次為突破口,圍繞壓抑性心理機制進行深層次分析,他也將愛欲解釋為人類的本質,而這一本質的最終目標是無止境的快樂及個人欲望的滿足,人受快樂原則支配做出種種無意識的行為,是無意識的表現(xiàn)。弗洛依德認為文明的持續(xù)發(fā)展并不會讓人獲得越來越多的快樂,甚至會導致更多痛苦產(chǎn)生。弗洛伊德基于性本能和死本能將其視為以攻擊為主要表現(xiàn)的個體行為,但無論是這兩種沖動中的哪一種,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后都會被抑制或受到約束,這種約束或限制會給人帶來壓抑的情緒,從這一點看文明社會甚至不如野蠻時代。從某種角度來看,人類的文明也是被壓抑的文明。馬爾庫塞認為,伴隨著時代發(fā)展,社會生命本能所存在的實踐意義被弱化,人無法提出對事物批判或否定的意義,逐漸成為只能接受現(xiàn)實的單向度人。他認為這是社會發(fā)展所帶來的創(chuàng)傷,只有更新文明才能撫平創(chuàng)傷。
(三)法蘭克福學派對馬爾庫塞的影響
自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家被更多關注之后,很多學派都受此影響,其中影響最大、影響時間周期最長的是形成于1923年,由霍克海默創(chuàng)辦的法蘭克福學派,該學派最活躍的時間段為20世紀50年代左右,他們的研究是圍繞人的異化、社會的異化等展開的批判。社會批判理論是以否定或批判當時的社會現(xiàn)狀為主要目的,以消滅社會異化為終極目標,從而建立更加健全的社會。在法蘭克福學派創(chuàng)建初期,馬爾庫塞作為領軍人物之一,他同樣也是支持社會批判理論的,在20世紀初,歐洲由于部分國家發(fā)起武裝起義之后并未成功而導致歐洲的工人運動逐漸走向低潮,這和馬克思最初的預言完全不符,無產(chǎn)階級并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贏得勝利,雖然俄國的革命取得成功,但工人運動也并沒有就此走向勝利,而是逐漸沒落,工人運動的失敗使人們反思并逐漸積累經(jīng)驗,再次尋找理論的突破。此時,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表達了個人對于工人運動無法在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的見解,并對馬克思主義的內(nèi)容作出重新的理解,后人將其稱之為新的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特征是以人為中心,而異化理論是重要觀點,強調個體意識去改變歷史的決定性因素,法蘭克福學派便是在該主義的影響下成立的。該學派繼承了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并基于各個層面分析并批判主張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對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革新,是對現(xiàn)實生活中失去實踐力量的社會生活的批判。從這個意義說,法蘭克福學派是對人們生活在現(xiàn)實世界的遮蔽的去除。在馬爾庫塞、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法蘭克福學派蓬勃發(fā)展,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領域中,其影響力長久不衰。與此同時,馬爾庫塞基于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從否定和批判視角出發(fā),促進了社會批判理論形成。其中,《單向度的人》就是他的代表作。
二、馬爾庫塞單向度理論的內(nèi)容
(一)單向度的成因
在《單向度的人》中,馬爾庫塞率先提出“單向度”這一概念。在他看來,單向度是指個體面對客觀事實喪失批判和否定能力,是僅僅具有肯定性思想的人,其否定和批判意識也受到現(xiàn)實的壓抑。受物質的奴役,人們成為接受現(xiàn)實的肯定性的人,社會中的思想也逐漸被統(tǒng)一,最終演變成單向度社會。存在于該社會中的人無法作出否定的決定。單向度的人無法脫離現(xiàn)有的生活,更不能改變當下的狀況。馬爾庫塞表示導致該現(xiàn)象發(fā)生的核心原因是科學技術的持續(xù)發(fā)展使得技術成為控制人們的主導力量,雖然科技的發(fā)展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物質財富,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推動了經(jīng)濟、政治、文化的發(fā)展,但對現(xiàn)實世界的物質滿足使得人們才成為肯定性力量,而不再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性力量。在現(xiàn)代化工業(yè)社會中,人逐漸成為失去否定性和批判性的人。
(二)單向度的表現(xiàn)
第一,是政治方面的單向度。
隨著科學技術的創(chuàng)新,發(fā)達的工業(yè)社會似乎已意識到為何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主張人類的解放與自由。雖然在工業(yè)社會,工人階級于社會中的地位及其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看似過上幸福生活,然而這并非真正意義的解放或自由,科技的發(fā)展和革新使經(jīng)濟蓬勃發(fā)展,雖然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人也逐漸成為技術理性制造下的“物質”奴隸。誠如馬爾庫塞所言:“各類制度存在的本質導致人們無法基于個人意愿選擇心儀的生活方法,人們只能以此選擇各種不同的操控和控制技術。”[2]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創(chuàng)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但工人階級的力量卻日漸減弱,失去了對資本的控制,逐步淪為機械的奴隸。在工業(yè)時代到來以后,如雨后春筍般涌出的科技,令人們的生活及生產(chǎn)模式發(fā)生了改變。雖然人們?nèi)硇牡赝度氲缴鐣a(chǎn)當中,但工人階級依然有很大概率會失業(yè),更無法打破目前的政治分歧。“以科技為核心的社會,導致工人階級的否定地位越來越弱,他們無力和既定社會產(chǎn)生沖突或矛盾。”縱觀整個工業(yè)社會不難看出,在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從中能夠影射出生產(chǎn)資料私有化與生產(chǎn)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工人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其最終所有權卻歸資本家所有。但在單向度社會,各種階級矛盾就會被日漸緩和。物質生活的極大富足使人們的需求得到滿足,工人階級無法感受到資產(chǎn)階級的隱性壓迫,只為了滿足個人需求而努力,這種看似合理的情況,其本質卻極不合理,工人只滿足了資產(chǎn)階級所創(chuàng)造的虛假需求,其實際需求并未被滿足。而從本質上講,工人仍是被資本社會所剝削的,資產(chǎn)階級以虛假需求隱藏了對工人階級的種種剝削。從而緩解了階級矛盾,使得這個單向度社會看似穩(wěn)定地發(fā)展。
第二,是文化方面的單向度。
馬爾庫塞認為,通過分析高層文化統(tǒng)一性,能夠得知文化單向度特點,此處所講的高層文化其實質就是最初的資本主義文化(即封建文化),因為高層次文化所闡述的是理想世界中的文化,是批判現(xiàn)實且高于現(xiàn)實的文化,但在進入工業(yè)社會之后,高層文化與現(xiàn)實融為一體。合理性技術的存在讓商品發(fā)展成文化載體,傳統(tǒng)的文化成果轉變?yōu)槲幕唐罚幕纬傻倪^程則逐漸演變成文化生產(chǎn)。在大眾文化生產(chǎn)過程中,雇主擁有了驅使藝術家的權利,創(chuàng)造藝術也變成了生產(chǎn)消費的過程。文化工業(yè)讓藝術價值越來越低,甚至低于交換價值。起初,文化的真諦是源自日常生活經(jīng)驗和維護日常生活秩序之間的裂隙,但如今文化已經(jīng)不具備超越性。正如馬爾庫塞所言,在文化工業(yè)之后,人們逐漸成為文化機械生產(chǎn)中用于改變個人觀念的齒輪。在經(jīng)濟發(fā)達的工業(yè)社會,人們不再樹立理想追求,行為被資本主義所創(chuàng)造的虛假需求所統(tǒng)一。那些喪失否定意識和批判能力的個體,又會在技術合理性的影響下,擁有更多肯定性思維,與此同時,理性所具有的否定、批判和價值判斷,逐漸被技術理性所取代。而技術理性強調的是中立及客觀,中立以毫無人性情感的傾向為目標,只想要獲得最終與實際目標相契合的結果,不注重是否有價值。在技術理性的影響下,任何事物事件都能被計算、測量甚至可以被控制,即便是人的思想也是如此,最終人們會逐漸失去價值理性,走向理性異化。
第三,是思維方面的單向度。
相較于武力,借助技術控制人的發(fā)展,魅惑性更大,馬爾庫塞表示看似合理的工業(yè)化發(fā)展,其實是在持續(xù)侵略自然讓人擁有越來越大活動范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會由于日漸發(fā)達的科技而越來越渴望控制并征服世界,這一切都和馬克思所追求的共產(chǎn)主義幸福有極大差別。但我們可以承認的是在工業(yè)社會中,個體的物質需求能夠得到充分滿足,但其精神卻貧瘠不堪,人也成為只具有單向度思維的人,單向度思維首先表現(xiàn)在革命性的喪失,資本借助科技研發(fā)出來的多元化商品,使人們沉浸在商品所提供的虛假滿足里,充沛的物質“現(xiàn)實”,使人們失去自由。“如果工人與其雇主能夠看相同的電視,前往同一個地方游玩;公司的普通職員與其雇主的女兒在衣著打扮方面極為相似;黑人與白人乘坐的交通工具一樣、閱讀的刊物相同,但這些相似并不意味著二者間已經(jīng)沒有階級差別,而是表明在當下的制度當中,大多數(shù)人都能于一定程度上享用著維持該制度的滿足及需求。”而原本的階級差異卻因此而被隱藏,機械化大生產(chǎn)的現(xiàn)實,導致人對追求向往自由的想法受到抑制;喪失批判性思維,人們的精神世界逐漸異化,越來越多的人將豪宅、轎車及各種貴重產(chǎn)品視為人生的重要價值,加上資本家大肆宣傳符號文化,使很多百姓深陷消費主義而無法自拔,看似灑脫的生活背后卻被各種提前消費模式透支,很多無產(chǎn)階級在未來的幾年或數(shù)十年勞動力被透支,他們只能以盲目的態(tài)度對待當下的生活,甚至無法自行決定個人的喜愛與厭惡,只能一味地遵從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以支持、歸順的態(tài)度對待資本主義,因為目前所擁有的好與壞都不受個體的評判而被影響,只有肯定并維持當前狀況,才能維持自己的“奴隸”地位,享受看似自由的生活,這一切使工人們逐步成為指揮機械化運動的工具,為整個被技術商品生產(chǎn)的社會奉獻自己的自由和靈魂。無產(chǎn)階級過去被資源分配而被壓制,現(xiàn)在受機械分工限制,成為了機械的“工具”、技術的載體。盧梭曾經(jīng)說過,人是向往自由的,但窮盡一生都被困在枷鎖當中,物質和精神層面的枷鎖掩蓋了仍在激化的階級矛盾,馬爾庫塞認為,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屬于是典型的單向度社會。
三、超越“單向度”的出路及啟示意義
對于單向度社會的出路,馬爾庫塞提出通過革命及非革命兩種方式脫離這個病態(tài)社會,前者是基于美國當時的學生運動所提出的,并且認為只有在社會中的底層流浪者及局外人,種族當中受剝削迫害的群體及失業(yè)的人才會選擇反抗。在他看來,無論是哪個階段的社會歷史,以上幾類人群皆處于主體地位。“所謂其歷史主體,就是那些參與革命,對不自由的統(tǒng)治進行抵制防御甚至是反抗對立的那些人們,而他們就是歷史的主體,革命的力量。”在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歷史主體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同時歷史主體應該是革命的參與者或不認可非自由統(tǒng)治的個體,他們是革命的力量。只有通過革命的方式才能反抗單向度社會,擺脫當前的生活模式,但革命最終并沒有成功。這也是馬爾庫塞后面提出烏托邦思想的重要原因,他把美學及藝術作為出路,解釋為剝離現(xiàn)實且不會被現(xiàn)實社會所影響的,而烏托邦本身就屬于否定性思維,能夠打破當前單向度的思維模式。但他的這一思想只是設想,并未制定詳細路徑,實現(xiàn)概率渺茫。
馬爾庫塞認為發(fā)達的工業(yè)社會之所以會變成單向度社會,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使人異化,單向度的社會并不是暴力的執(zhí)行,而是反抗性思想的消失,人失去了否定性思維,把社會建設成只有肯定性思維的單向度社會。人無法意識到這是一個物質過于富裕的異化社會,意識到在如此的社會環(huán)境中人性無法得到釋放。而如今我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存在著許多資本主義經(jīng)濟成分,所以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經(jīng)營及生產(chǎn)模式仍在某個范圍內(nèi)產(chǎn)生作用,很難在短時間內(nèi)消除異化。在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過程中,我們要對技術發(fā)展保持主動性,成為技術產(chǎn)品的主人,而不是奴隸,并注重人文關懷,重視人及人自身的生存情況與發(fā)展,讓人們在不斷提高物質水平的同時豐富精神世界,如此方可保留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