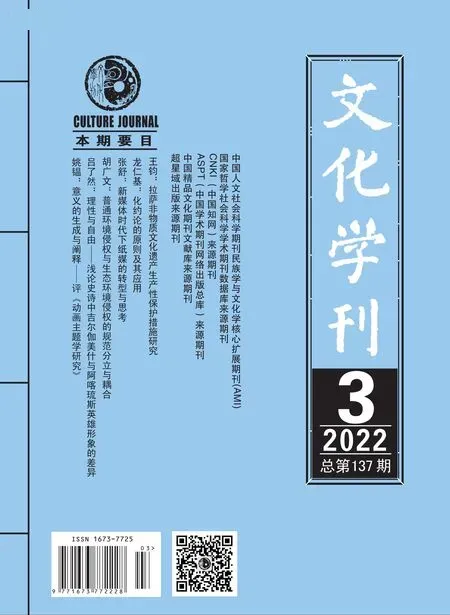蔣孔陽美學實踐觀的五個維度
——基于《美學新論》的解讀
張沈琦
蔣孔陽作為實踐美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當代美學思想界獨樹一幟。然而,如何理解蔣孔陽的美學實踐觀卻成為了眾說紛紜的議題,還出現了很多誤讀和歧義。本文認為蔣氏對實踐的探討是基于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美學的思考,圍繞“實踐”與“生命”兩個關鍵詞進行建構,在《美學新論》中作者將兩個關鍵詞融會貫通以五重維度展示出來,即創造與實踐、生命與實踐、對象化與實踐、自由與實踐、社會生活與實踐。基于這五個維度能全面把握蔣孔陽的美學實踐觀的豐富內蘊和本質展現。
一、創造的契機
蔣孔陽從生存論本體論的角度闡述實踐。蔣孔陽指出,只有在實用關系的基礎上,審美才存在可能:人類按照某些規律并運用自身在實踐中形成的意識,在勞動中實現自己的目的,一旦主觀思想符合了客觀現實就會產生滿足與欣快感,形成了人的審美意識。在人類勞動實踐中所創造的事物是“人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產物,在產生與欣賞它們之時,美也隨之產生。
蔣孔陽使用“審美關系”來構建美學實踐觀。針對當時以李澤厚為代表的美學思想對個性與創造性的忽視,蔣孔陽非常重視創造在美學中的重要地位。他將美的創造分成了多個層次,即多層累的突創(Cumulative emergence)。蔣孔陽緊緊地立足于社會的實踐關系,指出我們看到的諸種社會現象的背后都是在“層累”的基礎上有所突變創造。當審美主體與客體相契合時,美就會被突然創造出來。在實踐中美與美感同時發生,所以美誕生時,美感也隨之被創造出來。這克服了認識論的弊端,達成了主客觀的渾然統一。蔣孔陽注意到審美關系中存在的積淀特性,采用了分層分析的方法,注意到了實踐中的復雜性,為美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預留了空間。
對創造的思考是從生成論的角度來考察并基于馬克思的看法綜合而來的。從生成論角度來思考的最大優點是繞過了傳統本質主義思維模式執著于對“某物是某某”的思考。人的認識具有局限性,對事物的本質的認識永遠處于動態發展的過程中,無法追求一個精確無誤且永恒不變的界定。蔣氏不再追求給美下一個完整的、本質性的界定,超越了本質主義[1]的思考方式,這樣,創造與實踐就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創造的過程是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的實踐過程,并按照“美的規律”進行生產實踐。這個過程包含三種階段:來源于實踐、運用實踐,回到實踐。蔣孔陽從歷時與共時兩個角度分析了社會歷史層次的含義:在歷時上,隨著人類實踐的不斷深入,人的社會生活及實踐主體,對于自然來說是異己的存在,是時空的不斷積淀與“層累”的過程,與人類的文化傳統息息相關。在共時上,蔣氏將社會生活分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強調人的客觀生活方式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心理意識層是在前三層的不斷累積與突創下產生的。這種對人與人的精神的強調,顯示了蔣孔陽對創造主體的尊重與高揚。總之,創造過程包含著來源于實踐、運用實踐,回到實踐的循環,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實踐——創造體系。
二、生命的綻放
生命在《美學新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把蔣孔陽的美學思想看作一個橢圓,那么生命與實踐一起構成了這個橢圓的兩個焦點。這里的“生命”是人作為“類的存在物”的諸種“本質力量”的有機集合,是處于社會關系中的活生生的人。正是人類的生命活動要依靠自然來實現生存與發展,要生存與發展必須依靠人類的實踐活動。
生命的實踐過程是“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蔣孔陽認為,人的本質力量是一個多層次的復雜構成,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從物質層面來說,生命力、創造力、人所擁有的自然能力、情感與需要以及自然的物質屬性都屬于人的本質力量的范疇之內。從精神層面來說,主要有三種:認識自身及世界的思維力量、實現目的的意志力量、感受表現自身的感情力量[2]154。物質層面是精神層面的基礎,精神層面是物質層面的升華。生命就是這些本質力量的有機集合。針對一些學者僅僅將本質力量理解為人的“最先進”的品質[3],這有失偏頗。隨著實踐的不斷發展,美的范疇也在不斷擴大,丑惡、荒誕等等也被并入美中。價值判斷要放在審美關系與審美活動之中來評判,才能保證實踐一元論。蔣孔陽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些問題,使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具有更廣泛的普遍意義。
生命的實踐結果是“自然的人化”,是由人的生命實踐活動產生并深化的。一方面,從社會性的角度來說,實踐使得人類社會與自然相分離成為異己的存在,人類社會逐漸成為了一個系統。人作為生命的存在具有共性與個性的雙重性質。在美學實踐中,“共通感”概念的產生使得美能夠在個體生命體驗的基礎上得到廣泛的傳播,變成“類”的社會的現象[2]142,滿足社會團結等諸種功能。另一方面,從美學發展的歷史角度來看,美學源于希臘文aisthesis,原義指感官所感知的。馬克思使用“感性的人的活動[4]”一詞勾勒出實踐、生命、美的緊密關系:沒有基于個體生命感受與實踐,美便無從產生。實踐與生命的相互作用將美限定在人類社會之中,并自發地承擔社會的各種功能。蔣孔陽反駁了自然美存在于人的社會之外的說法,并通過研究中外美學史與人類發展史,構建了從工藝美與藝術美到社會美再到自然美的,基于實踐的美學發展譜系。
美要求有社會的共鳴。這種共鳴一方面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社會實踐的需要。蔣孔陽列舉了康德的“共通感”理論、休謨的同情說以及托爾斯泰關于美的界定,意在說明美需要共鳴的存在。然而,共鳴的發生也是需要條件的,并不是所有情感都能引起共鳴,必須要滿足實踐的需要符合社會與人民的利益才是美的,才能引起他人的共鳴。此外,美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地被解釋評價接受,是需要處于共時與歷時的人的生命經驗參與的過程。時效性的存在點明了鑒賞活動的共時性,同時也說明了鑒賞活動的廣泛存在具有社會性意義。蔣孔陽從人的主體方面將生命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建立起了立足于生命創造的美學實踐觀。
三、對象化的循環
蔣孔陽認為,美是“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對象化本身是一個包含實踐的動態的過程。實踐是對象化的原因,對象化是實踐的結果。所謂“對象化”是人在客觀事物中選擇發現相應的事物,通過按照“美的規律”來使得主客觀達到統一。蔣孔陽認為,馬克思所說的美的規律是主體與客體的有機統一:一方面人可以掌握某一客觀事物的規律來進行生產;另一方面,人具有自由意志,擁有屬于自己的尺度,具有無盡的創造性。在尊重“美的規律”的基礎上,“使人化到對象中去”,然后通過客觀事物表現出人的性質與特點,最終實現“對象化”的過程。“化”是一個過程,一方面,人類要生存、要勞動、要實踐,就要認識對象,認識自然,同時在認識對象的過程中必然包含著對事物的情感;另一方面,自然界的種種事物在人類的勞動實踐中與人結成某種關系,成為了人的對象的自然,其結果是自然不斷地被“人化”,包含著人的特點。這種價值與規范的形成不是先驗性的,而是在勞動實踐中生成的。
對象化的實現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理論的方式,一種是實踐的方式。理論的方式是在精神意識中將精神二分為主體與客體進行思考。實踐的方式,是在社會現實與勞動實踐中將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物質世界二分,通過人的實際行動來實現對象化,創造出包含有“人本質力量”的諸種實體產品。文學藝術等對象化的產品也都是以形象的方式被接受者感知的而不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實踐方式的對象化就與形象化緊密結合。蔣孔陽認為在對象化過程之中,人的實踐活動在原有的自然事物的存在形式之上,加入了人的情感意識的諸種形式,使得客觀存在的第一自然變為第二自然,具有了人的精神性與客觀存在的物質性雙重性質。
對象化的實踐具有差異性特征,正是這種差異,使美處于動態的創造之中。在對象化中,個體所運用的實踐方式都是不盡相同的,實踐的個性化導致對象化的個性化,對象化的個性化使得美的創造具有獨特性。這樣,蔣孔陽在對象化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基于創造的美學實踐觀,并構成了一個不斷開放發展的辯證循環。
四、自由的體現
自由分為外在的自由與內在的自由。外在的自由是能夠在物質生產實踐之中隨心所欲地認識規律運用規律,是創造與欣賞蘊藉著美的形象產品的外在條件。內在的自由則是指心靈的自由,是人的本質力量在精神生產實踐中的對象化過程。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美與自由的理想本質上達到統一,從而被創造。在實踐中,人一方面發展自身生命的諸種機能,本質力量得以豐富;另一方面,人在實踐中不斷推進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以及自然的人化進程。在這個過程之中,人不斷地在實踐之中直觀自身,直觀由人的本質力量所創造的諸種對象。當人的本質力量得以完全展開,對象化過程暢通無阻之時,人也就獲得了完全的真正的自由,美也隨之產生。
自由是有規律的,規律通過實踐的不斷深入與檢驗后,美才能在自由的條件中產生。任性與無知都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蔣氏指出自由是建立在必然的基礎之上的,沒有了對自由規律的認識,美也就無法存在。在實踐過程中,人發現了規律獲得了自由,并在進一步的實踐之中運用規律自由地在客體中實現主體的目的。這樣,人的本質力量得到了確證與發展,人的自由感在實踐之中被激發出來。
自由的形象化體現是文學藝術實踐與審美實踐,文學藝術實踐與審美實踐最終指向自由。蔣孔陽從三個方面集中闡釋了文學藝術實踐與自由的關系:第一,從內容上來看,在文學藝術的創造和欣賞的過程中,藝術家與接受者通過對象化的實踐活動,將自身獨特的主觀意識與客觀事物相結合,創造出具有類似什克洛夫斯基的“奇特化”效果的內容,使得人們從日常司空見慣的平凡中解放出來,發現了獨具個人風格的內容,獲得了藝術與美的自由狀態。形象作為自由在文學藝術中的體現,成為了連接實踐與自由的中介。第二,從形式上來看,在文學藝術創作與欣賞過程中,作為主體的人將感性的物質形式超越為精神的形式,這種精神形式使人擺脫了感性的物質的束縛,獲得了自由并通過人的精神實踐,將人的本質力量集中表現出來。第三,自由的形象化體現需要大量的實踐才能聚合成藝術的形式。蔣孔陽從歷時與共時兩個角度闡述了實踐與自由的關系:從歷時角度來說,人的感覺器官首先是為了人的存活而存在的。通過勞動實踐,人的各種感覺器官從自然的威脅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人類的諸種美的創造,例如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具有產生的可能。從共時角度來說,美的理想與文學藝術本質上都是追求自由的形式。作為個體的人在藝術創造與欣賞過程中要不斷地經受實踐的考驗,在實踐的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不斷地接近自由,完成藝術形式的有機結合。
總之,蔣孔陽深入洞悉了自由與實踐的關系,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將自由納入到社會生活實踐之中,沒有將自由設定為現實的彼岸,從而構建起了獨特的美學自由觀與美學實踐觀。
五、生活作為舞臺
美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蔣孔陽一方面肯定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將生活納入到美學研究中去,使得實踐與美緊密相連,但是生活本身并不等同于美,也不能單純地將自然美抬高到藝術美之上。另一方面,這種直觀主義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簡化了。這樣不僅使產生在社會生活實踐之上的文學藝術喪失了魅力,也使得人與自然等同,拋棄了人的主觀意志。蔣孔陽指出:正是通過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實踐,將人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不斷發展升華為審美關系,必須要有在人的有意識的實踐活動下,美才成為可能。
社會生活是美產生的基礎,實踐是二者的中介,有符合“美的規律”的社會生活才能被納入到美學實踐中去。社會生活為人的審美實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能夠滿足人類審美實踐的諸種目的,但社會生活實踐的容量要比美的實踐的容量大得多。最為直觀的例子就是作為與美對立的丑的存在。
作為審美主體的人在社會生活面前不是消極被動的,證明方式是人的實踐。首先,美具有客觀標準,根本上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其次,人除了物質生產實踐還有精神生產實踐,藝術是來源于社會生活且高于社會生活的。“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5]”這啟示我們不能僅僅從生活中的一些細碎的零散的審美文化現象入手來思考美,應該從人的生命以及社會生活等維度將人本身具象化,通過將人看作有生命的生活在社會中的存在,來洞悉現實中束縛在人身上的諸種不自由。
自然美與藝術美同屬于美的范疇之內,通過人的實踐被納入人類社會生活之中,沒有高低之分。伴隨著自然的人化的不斷深入,自然美與藝術美被逐漸納入到社會生活之中;與此同時,人的本質力量尤其是在主觀方面的本質力量,也會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發生變化。蔣孔陽反對將自然美抬高,貶低藝術美:一方面,自然與自然美完全不同,自然美包含了人的本質力量,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另一方面,自然美與藝術美是美在不同領域的不同形態,是有各自的適用范圍的。藝術美先于自然美產生,自然美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社會生活的最終建立與完善。這樣,自然美與藝術美的范疇取決于人與自然的審美關系,共同被納入到人的審美關系實踐之中,成為了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六、結語
綜上所述,蔣孔陽通過創造、生命、對象化、自由、生活五個維度來論述實踐的多維內蘊與界定,緊緊圍繞著馬克思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以及自然的人化命題來論述實踐。其中,創造與實踐、生命與實踐、對象化與實踐是從人的主體出發,以“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為中心,將人看作具體的活生生的人,體現了蔣孔陽美學實踐觀的現實維度;自由與實踐、生活與實踐是從審美客體出發,將人的審美實踐限定在人的社會關系之中,以“自然的人化”為中心,體現了蔣孔陽美學實踐觀的反思維度。生命與創造作為蔣孔陽美學實踐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了對象化實踐、自由實踐、生活實踐的來源與旨歸。這五個維度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體現了蔣孔陽不拘泥于傳統蘇式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念,吸收了本土與西方的理論資源,將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有機結合,注重從共時與歷時的視角來思考實踐。在蔣孔陽看來,對實踐的深入認識只有將“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與“自然的人化”的兩個命題分別對應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深入到社會生活語境之下,才能真正構建起實踐美學的基本框架。蔣孔陽從文學藝術的諸種理論與實踐出發,尋求美學實踐觀的諸種可能性的基礎,這是最接近馬克思本人的美學實踐觀的。總之,蔣孔陽將實踐放在人的社會關系之中來考慮,沒有虛構一個虛無縹緲的彼岸世界,重申了社會生活實踐的決定性地位。從這個意義上出發,蔣孔陽作為實踐美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真正地舉起了實踐這面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