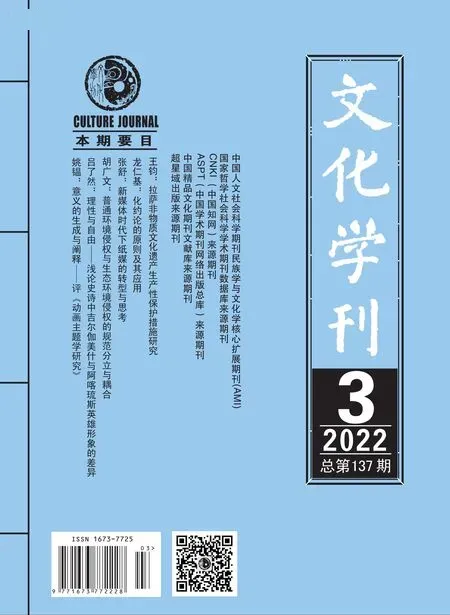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規(guī)范分立與耦合
——以《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為研究視角
胡廣文
《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環(huán)境污染與生態(tài)破壞責任”對既有環(huán)境侵權規(guī)范進行了條文增補和體系擴充,與《侵權責任法》對應章節(jié)相比,共有三點變化:第一,章節(jié)名稱從“環(huán)境污染責任”變更為“環(huán)境污染與生態(tài)破壞責任”,“生態(tài)破壞責任”的語境添加使得環(huán)境侵權的行為中介路徑在邏輯上更為周延,即在《民法典》生效后,環(huán)境侵權在實證法上的行為模式不僅包括行為人排放廢水、廢氣等向生態(tài)環(huán)境傳輸有害物質的行為,也將涵蓋行為人違法濫采濫伐等濫用生態(tài)資源的行為,這種行為侵害的是生態(tài)環(huán)境本身,因此,《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對“生態(tài)破壞責任”的語境增補和責任擴充意味著對自然環(huán)境所承載的公共利益之維護。行為模式的擴充也使得第七章規(guī)范的涵蓋范圍有所擴大,為環(huán)境公益訴訟、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等環(huán)境救濟機制的銜接預留了空間;第二,增設了第1232條行為人故意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時的懲罰性賠償規(guī)定;第三,增設了第1234、1235條,規(guī)定了生態(tài)破壞行為的歸責原則、請求權主體、修復方式等內容。經此修訂,《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實質上將廣義環(huán)境侵權范疇體系予以了類型劃分,從實證法層面將其界分為侵害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普通環(huán)境侵權和侵害環(huán)境公共權益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兩種侵權認定模式。
普通環(huán)境侵權意在救濟私益,而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則重在保護公共利益,二者的法益救濟目標迥異,故《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中哪些是僅適用于普通環(huán)境侵權或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分立規(guī)范,哪些是二者可共同適用的耦合規(guī)范,即為司法部門在適用第七章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故本文將從規(guī)范解釋而非規(guī)范證成的視角出發(fā),對《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既有條文予以梳理,解決二者在近似規(guī)范方面的有序銜接及體系協(xié)調問題。
一、廣義環(huán)境侵權概念的擴展
傳統(tǒng)環(huán)境侵權的制度功能似主要涉及對私權益的維護,但隨著環(huán)境公益訴訟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理論的興起,盡快完善相應的實體法依據(jù)即屬必要,原因在于,環(huán)境公益訴訟僅規(guī)定在《民事訴訟法》中,其規(guī)范內容主要是對起訴主體的確認,而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則主要通過行政文件予以設立,并未采取嚴格的假定—處理—制裁式的規(guī)范模式來細化適用路徑,故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制度尚不完備,其更偏重于政策宣示和行政指導。因此,這兩種環(huán)境公共利益救濟機制都存有不足之處,解決思路是:可在相關聯(lián)的部門法中增設相應的互補規(guī)范,增強環(huán)境公益救濟規(guī)范體系的整體協(xié)調性與可適用性,從而形成“公法性質,私法操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救濟機制[1]。故《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便隨之對“環(huán)境侵權”的制度功能與規(guī)范設置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增補與修正,使當前的環(huán)境侵權的預設價值取向變更為“私益+公益”之維護,從而形成一種綜合性救濟體系。這固然受到了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合力推動的影響,但更是在考慮《侵權責任法》固有環(huán)境侵權制度功能的事實基礎上所采取的路徑遵循策略,而不是純粹規(guī)范推演的結果[2]。因此,在《民法典》中增設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范式具有制度正當性基礎。
(一)作為侵權法下位概念的普通環(huán)境侵權
1979年的《環(huán)境保護法(試行)》已經初步建立了我國的環(huán)境保護制度框架,其第32條通過對行為人主觀過錯的認定,使行為主體承擔環(huán)境責任的基本認定框架塑形為“過錯—責任”,這就為普通環(huán)境侵權的理論構建奠定了基礎。1986年的《民法通則》也規(guī)定了一種以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為判斷標準的環(huán)境污染責任,而且明確規(guī)定是對他人損害予以填平的民事責任。2009年的《侵權責任法》正式確立了普通環(huán)境侵權制度,結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細化規(guī)定與典型案例的裁判規(guī)則指引,其成為我國追究侵權人環(huán)境污染責任,保護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主要實體法依據(jù)。
(二)環(huán)境公益訴訟與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的興起
1.環(huán)境公益訴訟
在普通環(huán)境侵權制度正式設立前,學術界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已有諸多研究[3],基本共識為:環(huán)境污染行為雖有可能會對某個公民的人身、財產權益造成損害,但不應將責任視角僅局限于私益范圍內,因環(huán)境污染行為一定會對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那么該如何對生態(tài)環(huán)境本身所遭受的損害予以救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存續(xù)狀態(tài)必然會影響到該區(qū)域人類的生活質量和生命健康水平,生態(tài)環(huán)境可以被看作是公共利益的載體,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維護人類的社會公共利益,因此,2014年《環(huán)境保護法》便增設了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
2.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
與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發(fā)展歷程不同,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更多地體現(xiàn)為一種政策主導型產物。2015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印發(fā)《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明確提出對造成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的責任者嚴格實行賠償制度;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通過專項文件對生態(tài)環(huán)境修復資金的求償、適用予以了明確規(guī)定,從而與環(huán)境公益訴訟保持銜接的同時又具有自身獨特的價值取向,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制度框架大致確立。至此,我國已然形成了救濟私益的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維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公共利益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兩種侵權認定范式。
二、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規(guī)范分立
由于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在理論與實踐中的分野已成定勢,因此,《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便在一般規(guī)定中增設了“生態(tài)破壞”的表述,從而使該章的規(guī)范效果能夠涵蓋到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公共利益的層面,這在理論界引起了“公私法益保護理念融于一部規(guī)范恐存邏輯悖論”之爭議,但在第七章已作如此規(guī)定的前提下,這種理論探討無疑應居于次要地位,因此,本文將基于“解釋論”視角,對第七章的既成規(guī)范予以分析。
(一)主體的變更
在系統(tǒng)梳理環(huán)境污染與生態(tài)破壞的分立規(guī)范前,有必要先對《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的規(guī)范主體進行解讀,與《侵權責任法》相比,《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的法律文本將實施環(huán)境損害行為的主體概念之表述從“污染者”細分為“行為人”和“侵權人”,前者可有效統(tǒng)攝“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破壞”這兩種行為樣態(tài),但后者的表述似存問題,原因是:被告是否是“侵權人”,恰是需要審判者在訴訟中應予查明的事實,不能將環(huán)境污染者與生態(tài)破壞者直接等同于“侵權人”。此處的“侵權人”實際上包括了侵害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普通環(huán)境侵權人和侵害生態(tài)環(huán)境本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人,環(huán)境污染者和生態(tài)破壞者可能只對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了損害,構成了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但卻可能并未對普通公民的人身、財產權益造成損害,此時,這里的“侵權人”概念似應只包括前者,但這種主體的預先設定卻使得當事人未經審理即被定性為“侵權人”,恐存邏輯疏漏。
(二)歸責原則的規(guī)范分立
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組成部分,主觀過錯是判斷當事人是否應承擔責任的重要因素,《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的普通環(huán)境侵權依然采取無過錯歸責原則,即只要環(huán)境污染者和生態(tài)破壞者對他人造成了損害,即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而不強調其主觀狀態(tài)。但第1232條和1234條又規(guī)定“違反法律規(guī)定”和“違反國家規(guī)定”,導致生態(tài)環(huán)境受損的,侵權人應承擔懲罰性賠償或相應的修復責任。這表明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以主觀過錯作為當事人承擔責任的基礎,因此,第七章采取的歸責原則分立式的做法與理論保持了一致。
(三)舉證責任的規(guī)范分立
《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第1230條規(guī)定由行為人對其不承擔責任或行為與結果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承擔舉證義務,這基本延續(xù)了《侵權責任法》的舉證責任倒置的規(guī)定,只不過將主體概念由“污染者”變更為“行為者”,同時,此規(guī)定同樣也隱含了一個立法意旨:即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也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guī)則。普通環(huán)境侵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規(guī)則有其合理之處,因為受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破壞行為影響的普通公民的訴訟實力在總體上的確弱于污染者和生態(tài)破壞者,因此,這種倒置規(guī)則可以減輕普通公民的起訴難度,從而實現(xiàn)環(huán)境侵權訴訟中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均衡化。但是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中,能否直接套用舉證責任倒置規(guī)則,尚存爭議,原因是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中,起訴主體一般是法律規(guī)定的有關機關或組織,這些主體一般具有較強的訴訟實力,似無需進行傾斜保護,直接套用舉證責任倒置規(guī)則似造成了訴訟雙方的權利義務不均衡,因此,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訴訟中似仍適用一般舉證責任規(guī)則為宜。
三、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規(guī)范耦合
即便在主體認定、加重罰則、舉證責任等方面存在規(guī)則分立,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之間仍有規(guī)范耦合之處:二者的行為樣態(tài)具有同質性,即相關主體皆是通過環(huán)境污染或生態(tài)破壞行為對環(huán)境造成損害,二者的法益保護客體雖有不同,但基于行為中介的共性,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在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認定、法律責任承擔方面并無相異之處,因此,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自可共同適用如下規(guī)范。
(一)責任承擔中的耦合規(guī)則
《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第1231條規(guī)定:“兩個以上主體之間承擔責任的大小主要根據(jù)污染物的種類、濃度、范圍、程度等因素確定,”與《侵權責任法》相比,該條僅對當事人法律責任的考量因素予以細化,普通環(huán)境侵權和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行為構成要件相似,皆是行為人通過實施一定行為來損害自然環(huán)境,二者在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原因力分析、關聯(lián)因素認定等方面可適用相同的處理模式。因此,該條應同時適用于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
第1233條規(guī)定的是第三人責任問題,環(huán)境污染者和生態(tài)破壞者雖實施了污染行為或生態(tài)破壞行為,但只要其按照法律規(guī)定設置并正常運行污染防治設施,那么一般不足以對普通公民的人身、財產權益及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嚴重損害,但若有第三人故意破壞污染防治設施的正常運行,此時理應由第三人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因此,該條也應屬于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共同適用規(guī)范[4]。
(二)懲罰性賠償規(guī)則的耦合
普通環(huán)境侵權因存有負外部性問題,故其適用懲罰性賠償規(guī)則便無疑義。問題在于,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能否適用懲罰性賠償規(guī)則?首先,根據(jù)《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第1232條“侵權人”的語句表述,其似有意統(tǒng)攝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行為主體,無論侵害私主體的合法權益還是公共利益,只要相應主體的違法行為造成了嚴重后果,即應適用該條規(guī)定。其次,從《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第1234條的規(guī)定來看,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似傾向采用過錯歸責,其對過錯的認定以行為人“違反國家規(guī)定”為前提,因此,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能否適用懲罰性規(guī)則的關鍵在于厘清“違反國家規(guī)定”和“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關系,“國家規(guī)定”是一個廣義范疇,究竟何種規(guī)范內容可成為“國家規(guī)定”似尚無定論。若在此處援引《刑法》對“國家規(guī)定”一詞的定義和指代范圍,那么《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第1232條和第1234條“違法法律規(guī)定”和“違反國家規(guī)定”便具有了層級關聯(lián)性,進而產生適用上的遞進關系:若行為人違反國家規(guī)定,那么就依照《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第1234條承擔修復責任;如果其同時違反相應的法律規(guī)定,那么就進一步適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第1232條,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
(三)對第七章條文規(guī)范的梳理與總結
經過分析,《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雖規(guī)定了兩種法益保護目標迥異的環(huán)境侵權模式,但其在司法實務中并非會出現(xiàn)規(guī)范適用范圍界定不清之問題,經過以上梳理,《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第1229條、第1230條應主要適用于普通環(huán)境侵權,第1234條、第1235條應視為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制度的基本組合規(guī)范,第1231條、第1232條、第1233條則可共同適用于普通環(huán)境侵權和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
四、結語
本文意在通過對既有環(huán)境侵權規(guī)范的簡要闡釋,厘清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關聯(lián)規(guī)范的適用邊界,而非重在論證《民法典》增設保護環(huán)境公益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制度的合理性。此外,在規(guī)則適用層面彌合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的基本沖突亦不影響二者在理論上的分野。本文在“解釋論”視角下的環(huán)境侵權規(guī)范分析偏重規(guī)則適用而非規(guī)則證成,因而或會偏離環(huán)境侵權制度的應然理論設想,對普通環(huán)境侵權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侵權規(guī)范分立與耦合的探討亦尚需經歷司法實踐檢驗,從而在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中為《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之規(guī)范探尋出恰當?shù)膽寐窂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