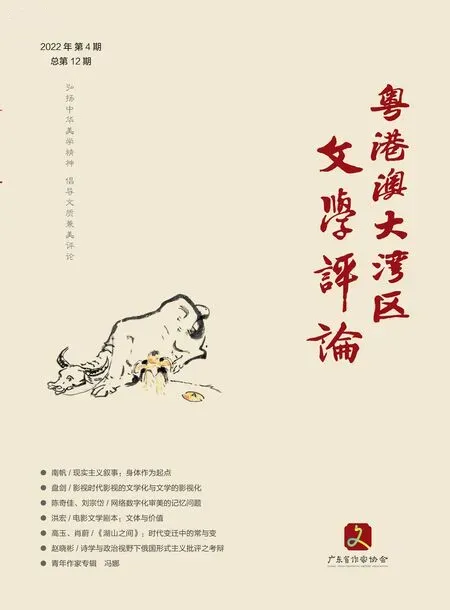抒情的秘術及其風度
——馮娜詩歌論
楊湯琛
由于馮娜的民族身份及其邊域生活經驗,不少評論者對其詩歌的指認總繞不過詩歌地理學的闡釋以及詩人民族身份的追索,它在有效梳理馮娜詩歌的某些特質的同時,也帶來了符號化的遮蔽,或許只有逸出上述論說的束縛,具體而微地從對馮娜抒情聲音的辨析出發,我們才能深入她的詩歌世界,體味其詩作內部明媚幽微的電光石火,并意識到,馮娜詩作的誘惑性并不依賴于對邊疆等特殊題材的占有,而是其感同身受的領悟力、創造性的個人化抒情方式構成了其詩歌文本的內在魅力。
在一切堅固的總體性趨于消散的當代語域下,抒情詩的寫作似乎縈繞著危險與不合時宜的氣息,高蹈、空洞、濫情等指責曾一時蜂起,諸多詩人也紛紛逃避抒情,將目光移向現實的經驗世界,熱衷于艾略特的‘非個人化理論’、葉芝的面具書寫,反抒情寫作成為流行一時的操作手法。這固然給當代詩歌帶來新的向度,但是對于抒情的刻意壓制也縮小了詩歌的情感能量,對于這一潮流,耿占春有著詩評者的警覺,他指出一些九十年代重要的詩人作品“明顯地增加了日常的情境與情節,增加了戲劇化與對話性。這樣的詩人是注意力的給予者。它顯示了詩人的好胃口,要及時地消化掉從現實世界中冒出來的一切非詩意之物,但也許它會成為新的狹隘性的一種表現。”他轉而期待“也許在種種文體的實驗與洗禮之中,抒情傳統會顯示出新的活力。”[1]在我看來,馮娜純正的抒情詩書寫便顯示了一種值得矚目的新活力,迢迢詩歌之途上,她從未偏離抒情的方向,“只要杏樹還在風中發芽,我/一個被歲月恩寵的詩人 就不會放棄抒情”(《杏樹》)。
馮娜雖然年輕,詩歌創作生涯卻開始頗早,《云上的夜晚》等詩集保留了她早期詩作輕靈、唯美的青春抒情之音,顯然,馮娜從未懈怠于詩藝的磨煉,從《尋鶴》開始,她進行了自覺的詩歌變法,一種節制、澄澈、充滿張力的抒情詩初露雛形,行至《無數燈火選中的夜》《樹為什么需要眼睛》等詩集,我們欣喜地看到,馮娜已然觸及了俄耳甫斯神秘的琴弦,尋到了屬于她的獨特嗓音,在紛紜變幻的當代詩壇上擁有了可被清晰辨識的抒情面孔。
一、想象與悖論:尋找抒情的秘術
必須承認,馮娜的抒情詩有著強烈的蠱惑性,它總以其別具一格的形態刺激倦怠的眼睛,但這“特別”又有著鏡花水月般不可捉摸感,因此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只能籠統地襲用“靈性”來加以概括,不過隨著馮娜詩作的堅實生長與個人閱讀的深入,這些靈動閃爍的詩句似乎向我展示了些許秘密, “想象”與“悖論”或許能讓我窺見馮娜詩歌秘術的某些構件。
馮娜的詩歌有著天馬行空的想象力,這一力量呈現為詩人對意象的專制性馴服與來去自如的操縱,其筆下總快速切換著紛至沓來的意象,眾多獨異的意象踏空而來,在主體強悍的力量下被過濾、提純、排列,化為奇異的意義峰巒,如她的代表作《詩歌獻給誰人》。這首詩流轉著快速變幻的意象,奔騰著飛揚的想象力,掃雪的人、病榻前的母親、登山者、流浪漢、伐木人,遲疑的殺手,這些被提純的意象之間充滿了突然的斷裂與驚奇,詩人從一座意象懸崖奔向另一座懸崖,句子的奔跑擁有決絕的速度,洋溢著讓人目眩神迷的快感。馮娜這種快閃式的意象操縱法顯然是冒險的,我們經常看到,平庸的詩人習慣求助多種意象的滑動來牽扯詩句的前行,并借此炫耀其臃腫的想象力和華麗的辭藻,卻往往麗辭滿篇、不知所云,堆砌的詩句淪為空洞的能指。與此相反,馮娜從中恰到好處地展現了她靈巧的詩藝,詩作內部意象的變幻并不給人以堆積、破碎之感,單個詩句作為意義的島嶼有其自足的重量,但這不是孑然獨立的個體,而是細胞式的自足體,在自我意義分泌的同時,它們作用于整個詩歌肌體,應和著意義指針的共振,詩的最后兩句亮出了詩人手中的魔法棒,“一個讀詩的人,誤會著寫作者的心意/他們在各自的黑暗中,摸索著世界的開關”,由此,讀者必須返回詩歌,又一次在驚奇與速度中體會貫穿其中的隱秘意圖。
在我看來,馮娜這首詩是以詩的方式來探究接受美學的內在秘密,即詩與讀者之間的關系并非賦予與接受的明晰關系,它是一系列的變形與誤會,藝術接受主體的差異性與多樣化必然導致意義傳達的差異性,詩歌的言說不是終極真理的給予,它是暗示、啟發、召喚,其間交織著無盡的迷途,因而,冷酷的殺手(我視為冷漠客觀的批評家)面對意義編織體會發生戀愛般的遲疑,閱讀主體注定要獨自在意義傳遞的暗夜里摸索,詩歌就其本質而言,永遠不會提供精確的答案;馮娜以具象而精微的詩句觸及了詩歌接受美學的關鍵處。
馮娜詩中的意象與其說是被發現,不如說是被生產出來的,它們臣服于詩人專制性的想象力之下,有能力再造一個世界,“在云南 人人都會三種以上的語言/一種能將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樣/一種在迷路時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種能讓大象停在芭蕉葉下 順從于井水”(《云南的聲響》)。這儼然是被施展了魔法的夢幻世界,它奇異美麗,是絕對幻想的純粹曲線,如一幅讓人震驚的現代畫,總經久不息地閃爍于讀者的腦海。
馮娜詩作的驚奇性不僅與絢麗的想象力有關,也部分來自她所擅長的悖論的語言。悖論給晦暗的事物帶來光亮,否定詞的大量使用,如“不”“沒有”等在制造斷裂的同時,也創造了詩歌曲折幽深的景深,否定之肯定讓詩句獲得了悖論的力量,《出生地》一詩便構建了一個悖論的情境:
我們不過問死神家里的事
也不過問星子落進深坳的事
他們教會我一些技藝
是為了讓我終生不去使用它們
我離開他們
是為了不讓他們先離開我
他們還說,人應像火焰一樣去愛
是為了灰燼不必復燃
詩人信誓旦旦“我們不過問”,然而,死神家里事、星子落進深坳的事,它們作為被否定的他者卻借此獲得了更頑強鮮明的主體性,詩句由此成為一種悖論的意義傳遞,它靈巧地于閃避中呈現自身;詩作的尾部更是從自身產生的悖論性張力中汲取力量:教會與不去使用,離開與被離開,火焰一樣去愛是為了灰燼不必復燃,它們構成了一個布魯斯特所言的“倒置的真理”,恰如一個物體被顛倒過來,我們卻能在顛倒中更為準確地發現物體的本質,從馮娜的否定、倒置的言說中,一種更為強勁的真理性力量涌現出來,并擁有了箴言的質感,這讓我想起了布魯斯特對“悖論”的推崇,“在某種意義上,悖論適合于詩歌,并且是其無法規避的語言。科學家的真理需要一種肅清任何悖論痕跡的語言;顯然,詩人表明真理只能依靠悖論。”[2]
馮娜詩歌的悖論性力量與詩作中匱乏的傾聽者也息息相關,抒情主體朝向空虛中的“你”訴說,但這個傾聽的“你”匱乏而無知,一如《秘密生活》的中的“你”,“你知道我幼年時曾去打獵/——你不知道我獵獲過一顆星宿……你知道我曾去過無數詩人出生的城市/——你不知道我認得一雙亞麻色的眼睛”這是否定之肯定的嶙峋句式,不斷自我轉折、傾斜的詩句在曲線的深入中構成了強大的張力,如莎士比亞的比喻,“斜線嘗試以迂回的方式明了方向”,讀者必須從慣性滑行的理解軌道中逃逸出來,以驚訝的方式審視因“匱乏”而丟失的經驗與感受力,并由此重新獲得認知。馮娜詩作所運用的悖論的語言由此獲得了戲劇化的力量,避免了平鋪直敘的空洞,生成了靈動而準確的抒情詩體。
二、通靈者的信函
萬物靜默如謎,拙劣的詩者只能在光滑的表面摩擦,他們描述的現實場景總讓人沮喪,只有為數不多的詩人可以打開事物內部的驚奇,仿佛通靈者,他們感受到萬物運動的節奏,并捕捉到它的準確性。馮娜似乎也擁有這樣一種通靈的能力,她的詩作中燈火流轉、鳥獸出沒、植物豐茂,詩人與萬物之間息息相通,天然融為一體,因而,馮娜筆下的風景脫離了被觀看的客體性,而生成為具有強大感召力的主體。
馮娜的詩歌多涉風景,自然之景抑或人世之景交相出沒、相互呼應,構成一幅與詩人心像交相輝映的美學圖景;風景的大量書寫對于當代詩人而言,未免不是一種冒險,因為就中國詩歌傳統而言,有著成熟的制作方式與運思路徑的風景詩歷來為古典詩歌之大宗,它們如此讓人耳熟能詳,以致成為當代詩歌需要避免的陳腔濫調,更何況山水風物的書寫在層層疊疊的傳統泥淖下已經難以有新的突圍,從這個層面而言,馮娜大量的風景書寫更需要勇氣與創造力。
與傳統風景詩崇尚借景抒情的運思路徑不同,馮娜拒絕將風景作為詩歌客觀描述物,并不遵從事物的自然秩序,也有意逃離將風景作為情感觸發點的工具性操作,從一開始,她就不滿足于在風景表象的滑行,而是直接進入風景的內部,始終與風景相糾纏、相對話。《對岸的燈火》一詩是馮娜與風景之關系的一個典型隱喻,燈火牽引“我”,并通過明亮與黑暗碰撞的聲響告訴我“一定是無數種命運交錯/讓我來到了此處/讓我站在岸邊”,燈火與我之間的相遇成為彼此命運的浸入、交集,燈火此刻內化于我的命運之中,成為我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我引導并嵌入了燈火的命運之中“我只要站在這里/每一盞燈火都會在我身上閃閃爍爍/仿佛不需要借助水或者路途/它們就可以靠岸”,由此,燈火成為發光的生命體,我與燈火之間不再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觀照與銘記,而成為彼此命運的融入與領悟,人與景的內在糾葛,使得馮娜的風景詩成為詩人的生命密碼,鐫刻了抒情個體的體悟與悲欣。
馮娜破除了主體、客體的對立關系,風景與詩人心象相糾纏,并具有同構性,對于這一書寫,她如是解釋:“在西南高原生活,我們對動植物有天然的親近,我們與它們并不隔膜,就是它們的一部分。就像楊麗萍的舞蹈,她不是去表現雨水或者月光,她就是雨水和月光本身。這是萬物皆是我,我即是萬物的心性。也許這種心性的獲得必須通過那樣與自然共生、共情的生活,這是不可復制也不能模仿的。”(馮娜訪談,2016年5月)馮娜強調,當詩人天然化為萬物的一部分,詩歌抒寫不再是對他者的外在表現,而呈現為一種共生、共情的生活;這讓人自然聯想起里爾克所言的“分擔”,“你就試行與物接近,它們不會遺棄你;還有夜,還有風——那吹過樹林、掠過田野的風;在物中間和動物那里,一切都充滿了你可以分擔的事;”[3]當人與物成為命運共同的承擔者,人的深邃命運自然以物的形態直觀呈現。或許從《春天的樹》一詩中,我們能將人、物之間的詩意關系看得更清晰,詩中樹的迷戀、叛逆與懷疑一如少女“我”的精神歷險,人的主體性與樹的主體性已然合二為一、即此即彼。
詩人書寫的樹,是春天掙扎成長的樹,也隱喻了少女的精神鏈條與欲望迷途,但這不是單向度的隱喻,而是人、樹共生,兩者有著共同的運動軌跡,樹的欲望、奔逃與忍耐也是少女掙扎、彷徨的青春,亦此亦彼間,人與樹的現實差異被取消了,共振式的生命情緒讓兩者互相交融,超越了表層的隱喻性,甚至成為寓言化的書寫。
在《流水向東》《藏地的風》等詩作中,馮娜與萬物進行了更深的置換,萬物化為抒情主體,詩人擯棄了自身的先驗觀,棲息于物之內,從物的角度展開了內置式抒情,這種手法接近胡塞爾提出的“主體間性”,胡塞爾指出當主體將客體作為獨立的可以認知世界的主體,就進入主體間性,主體是和其他主體不斷商談和互動過程的一部分。馮娜從被置換的主體中,以飛禽的方式感受造化的變遷,“我的翅膀越來越輕/漫天的水 滿坡的綠林都為一種色澤沉淪 /七月初七 我們把山巒還給大地/把豹子還給深山”(《流水向東》);詩人又化身為風,再現藏地風情,“一匹馬跑過來 請它制服我/讓我聽到鈴鐺亂響 不再毫無頭緒鉆進蜂巢……酥油被我舔冷/再過上三十天 我會從山坳最深的地方/把高原的心窩子都吹綠”(《藏地的風》),詩中的客體產生了只有主體才有的自覺,打開了以物觀看的視角,一個充滿靈韻、未被人的視野污染過的世界突然蘇醒,而詩人也借此獲得了想象的自由與語言的解放,詩作化為通靈者的信函向讀者傳遞著萬物的節奏與美。
三、智性與抒情的風度
如果說馮娜早期抒情詩還帶有青春期寫作唯美感傷的風格,那么,隨著詩歌技藝的不斷淬煉,她勇猛地打破了慣性的抒情手法,進一步開掘經驗,并借助智性來平衡傾斜的情感書寫,“我重建著被自己損毀的宮殿,澆灌/用手縫漏下的河流,我的詩曾把水裝在罐中/為了把它們捧在手上/我接受了損毀”(《秩序》),我愿意把這節詩作為馮娜詩歌變法的自我隱喻,即詩人通過自我損毀來重建抒情的秩序,事實上,她以節制而富于風度的抒情詩最終獲得了其獨特性。在我看來,馮娜自覺變法后的抒情詩內斂、沉靜又搖曳動人,破除了常見的分泌式的泛濫抒情,在詩與思、意象與情感的勾連中保持了克制的平衡,并在詩人的智性控制下凝定為堅實的抒情體。
馮娜的詩作里總隱匿著一個沉思的主體,抒情的節奏內部始終回旋著詩人對意義的探詢、命運的追問,形而上之思的注入拓深了詩歌的景深,因而,抒情成為思想的一種方式,詩、思的結合使得詩作達到了海德格爾所言的思與詩一體的形態,“存在之思是原詩,一切詩歌由它生發,……廣義和狹義上的所有詩,從其根基來看就是思。”[4]如《極光》一詩為主觀的精神垂詢尋到了包含情感的客觀對應物,詩中涌現的具體形象如黑夜、白天、臺風、極光等都不是被觀看的客觀他者,而是經過智性過濾的對象,是被注入了詩人期待與想象的思想對應物,它們是思想火花的瞬間凝結,“極光”的形象與心靈的真實、思想的理性高度契合,它既是一種絕對的自然現象,也是痛苦而清醒的靈魂呈現,更是一種朝向生存的理性之光,實現了感性與理性的統一的“極光”因此散發出富于象征與暗示的光暈。
思想的刺入讓馮娜有能力點亮沉默堅硬的庸常事物,讓它們起電、發光,并袒露隱匿的命運圖式與情感底色。《鄉村公路》是一首指向日常的詩,所描述的風景是每個輾轉于途的行走者熟悉并覺得無趣的,馮娜對此避免了泛濫的田園式抒情,也遠離了有關城鄉分裂的社會學詰問,而是以陌生化的方式恢復了鄉村公路的重復與無聊,“司機的口哨繞著村寨曲折往復/多少個下午,就像這樣的陽光和陌生/要把所有熟知的事物一一經過/”然而,正是這無聊風景卻具象闡釋了人類生活的無常的與悲涼,“多少人,和我這樣/短暫地寄放自己于與他人的相逢/——縱使我們牢牢捍衛著灌滿風沙的口音/縱使我們預測了傍晚的天氣/(是的,那也不一定準確)/縱使,我們都感到自己是最后一個下車的人”詩人在瞬間與永恒、庸常與宿命之間尋求到詩歌的火石電光,一種澄明的了悟乍然照亮枯燥荒蕪的無邊生活。我一直認為,正是源于對日常生活的高度洞察力,馮娜才成為那一個獲取了詩歌秘密的幸運者。
當然,如何避免空洞的情緒摩擦,如何尋求詩歌內部的智性平衡,馮娜對此有著清醒的自覺,她曾自言,“這個跟我本人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有關,也跟我對詩歌智性的追求有關。我比較警惕感情和情緒泛濫的書寫,我認為寫作的尊嚴有一部分來自節制。情感的飽滿也會來源于克制中的張力。技藝的平衡、心智的平衡確實是需要終身努力的命題。”(孫曉婭和馮娜郵件訪談,2016年5月)或許,正是源于這份朝向節制的努力,馮娜的詩作閃爍著智性的啟示,通過留白與意象構筑等方式形成了頗具風度的詩意言說。《紀念我的伯伯和道清》不過才簡潔的四句詩,茶花、跛腳的人,它們共同構成的隱喻化圖景,留白了余韻悠長的闡釋空間,詩人的激情得到高度控制,從而在情感表達上獲得了更強勁的藝術張力,這讓人想起沈從文所主張的情緒的體操,“一種使情感凝聚成為淵潭,平鋪成為湖泊的體操”,[5]馮娜顯然熟稔地掌握了這一方式,她的情感總是從詩句的調度、控馭間迸發,激烈的情感之上始終籠罩了詩人強大的意志。這一詩人的意志也呈現為意象的凝聚,龐德有言,意象是“理性和感性的復合體”,而這類有質感的意象必須經由煉金術式的高度提純,是詩人主觀情思的結晶,方如此,才能使得詩歌避免毫無節制的宣泄而獲得雕塑般的質感。馮娜的不少詩作中,物象的更迭非常頻繁,譬如《云南的聲響》等詩,物象迭出,但高度隱喻化的意象始終被置于高度的意義關聯之中,化為詩人的心像符號,是與主體生命相勾連的命運共同體,也成為馮娜詩歌節制之風度的核心構成元素。
在消費時代的壓力下堅持抒情,在非詩的語境中堅持做一個詩人,這是一種艱難的抉擇,也愈發凸顯了抒情與詩人對于當下的意義,阿多諾認為,抒情詩深陷于個性,卻因此獲得其普遍性,也即抒情詩揭示了個人未被理解的秘密,并由此預示人類社會的特質。[6]從這個角度而言,抒情詩雖然并未直接與現實搏斗,但它作為具有創造性與高度敏感性的詞語事實,并非與社會對立的藝術品,它對情感與美的不懈恢復恰恰是對物化現實的一種感性抗議,是人類生存境遇的一份真誠的樣本,因此,馮娜純正、優雅的抒情詩當被置于這一視域下來確立其詩學價值與現實意義。
[注釋]
[1]耿占春:《群島上的談話》,《詩探索》,1994年2月。
[2][美]布魯斯克:《精致的甕:詩歌結構研究》,郭乙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3]《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59頁。
[4][德]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80頁。
[5]沈從文:《廢郵存底.情緒的體操》,《沈從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頁。
[6][德]阿多諾:《文學筆記 第一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2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