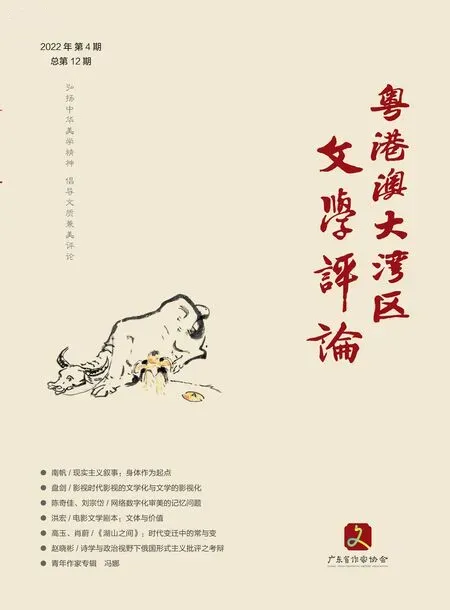文藝的“兩個效益”統一與價值導向追求
陳偉軍 周小鈴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逐漸成為主導社會各行業變革的驅動力。20世紀90年代迄今,以市場經濟為肇始的行業結構轉型深刻影響著社會形態變遷,并逐漸延伸到文學、藝術、文化、傳媒等各個領域。我國傳統的文藝觀倡導“文以載道”,注重文藝的道德濡染作用和社會教化功能。而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吸取傳統文藝思想的精髓,提出了“文藝屬于人民”這一科學論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浪潮下,文藝面向市場帶來作品的高效生產和高額回報,同時也引發社會各界對文藝唯金錢至上和“三俗”(低俗、庸俗、媚俗)傾向的批判。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而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1]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繁榮文藝創作,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倡導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這就給處于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二難選擇之中的文藝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新時代文藝所應有的價值導向追求。
一、文藝與經濟聯姻的雙向效應
經濟向文化領域的拓展,帶來了文化生產和傳播的深刻變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首次提出“文化工業”這一概念,反思文化生產的商業化和技術化。法蘭克福學派吸取了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和本雅明的“復制”理論,提出對“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批判。[2]繼承者馬爾庫塞關注文化的“單向度”問題,從文學藝術和性本能方面探討發達工業時代下文化領域否定性力量的消失。他認為,“不斷發展的技術現實不僅使某些藝術‘風格’失去其合法性,而且還使藝術的要旨失去其合法性。”[3]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詹明信開始關注后現代主義語境中的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距離消失的問題,藝術作品成為商品,以日常消費品的姿態走進人們世俗生活之中。
實際上,經濟與文化聯姻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20世紀90年代,中國市場化改革在文化領域逐步彌漫開來,作家、藝術家開始進軍文化市場,由此帶來一種雙向效應:文藝創作的活力被激發,但也導致少數文藝工作者刻意迎合市場的現象。文化界出現了劇烈的“雅俗之爭”,高雅藝術在市場經濟道路上發展步履維艱,而流行音樂、商業影片、時尚雜志、商辦報刊等市場主導下的通俗文化刺激了廣大受眾的消費需求。黨和國家領導人殷切期盼文藝工作者“要認真研究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民群眾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發生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努力創造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4]在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們對精神文化有了更高的消費需求,文藝的消費市場在市場經濟作用下已初具規模。
經濟與文化聯姻的價值在于: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現了新的增長點,“具有創新內涵并適應消費升級的文化產業行業呈現出高速發展勢頭”[5];另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消費需要相互促進,大眾文藝的誕生徹底打破了高雅藝術與通俗文藝之間的距離,藝術通過工業復制手段成為日常消費品。消費者通過市場流通的手段得到文化商品的使用價值,即意義、快感和社會身份,形成一種新型的消費關系和工業形態。
經濟運作在為文藝帶來市場效益的同時,文藝創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商業主義的影響。大眾化的文藝產品鋪天蓋地涌向文化市場,一些人將文藝作品完全當成商品,忽視了文藝工作者付出的“最復雜、最獨特的創造性精神勞動”[6],忽視了文藝作品的精神內涵。文學創作、藝術生產、圖書出版、文學作品影視化等方面的產業化轉型過程曾一度為人們詬病。20世紀90年代中期熱炒的“美女作家”,用各自的都市體驗進行著“欲望化寫作”。“下半身”立場成為民間文學的代名詞,“它的獨立性、邊緣位置、自省意識、先鋒性已經變得曖昧不清,很難辨認”[7]。圖書出版在市場需求導向下,盲目迎合迅速增長的低層次受眾口味,大量反文化、偽審美的“地攤文學”占據各大暢銷書榜單,低俗的精神消費泛濫。媒介技術的發展是促進文藝走向市場的巨大推力。廣播和電視通過流行歌曲、影視作品塑造青年偶像,由偶像、經紀人、粉絲共同構筑起以消費、娛樂、狂歡為旨歸的文化產業鏈。毫不夸張地說,“市場經濟的勃興帶動了消費主義的彌漫,娛樂文化很快在各種藝術門類中復蘇,從武俠、穿越、玄幻到電視征婚、明星八卦、電子游戲,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競相開放娛樂空間。”[8]文化市場的雙刃劍效應不斷顯現出來,文藝繁榮的表象后面潛藏著洶涌的暗流。
二、消費主義語境中文藝的世俗化、商品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加上媒介技術不斷演化,互聯網、手機為文藝生產和傳播提供了更廣闊平臺,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大規模地在文化領域進行擴張。精神產品的生產流通規律與普通商品的市場流通規律的聯系日益密切,文藝面臨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二難選擇。事實上,一些具有良好社會效益的精神產品,其經濟效益不太理想;而一些不具有良好社會效益的文藝作品,卻屢屢上演著高溢價表現。在消費主義語境中,文藝的世俗化和商品化在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尤甚:
(一)網絡文學:IP劇成“挨批”劇
《甄嬛傳》《花千骨》《瑯琊榜》等作品,掀起了網絡文學影視改編的資本狂歡。由網絡文學、熱門游戲和影視作品為原始素材的二次開發,逐漸成為電視劇市場運作的成熟模式。擁有龐大流量基數的“IP”作品成為文藝界和資本界共同青睞的寵兒,在這個資本橫行的時代,“IP變現”的口號在當前文化產業建設過程中日益被合理化。網絡IP劇的流量主要源于跟隨網絡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群體,他們普遍偏好青春、偶像、仙俠、穿越、玄幻等題材的網絡作品。這類作品勝在怪誕離奇和天馬行空的劇情,其藝術水準和思想內涵卻不盡如人意。然而,資本市場并不關注作品的藝術價值和人文內涵,僅以市場收視率和消費變現能力作為改編劇本的考核標準,利用粉絲經濟最大程度地調動用戶資源實現資本變現。如明星真人秀節目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文化產品,套用相同的邏輯和觀念進入不同的領域撈金,被網友怒稱為“粉絲經濟的畸形兒”。
(二)經典戲說:娛樂至上的文化消費
文藝經典作為民族記憶的傳承載體,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精神的延續。我國歷史長河中的經典文藝作品,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高峰,對集體文化心理建構和價值認同起著重要作用。而在消費文化的潮流中,文藝經典被戲說、解構。通過大眾媒介的市場化運作,“經典”被包裝成為大眾文藝淺薄的消費品。這場看似宏大的文化復古運動實則是一種文化繁榮假象,經典“很有可能被改造為盛大的‘文化馬戲’中的一個小丑,以老朽之身氣喘吁吁地奔忙,博得觀眾的哈哈一笑,從而為自己的生存贏得‘一簞食’。”[9]從文化節目到文化名人,從節目制作方到圖書出版商,從傳統媒介到新媒介,構筑起一條完整的消費文化鏈,消費主義重塑了文藝經典。
更為嚴重的是,文化市場的許多作品以“奇”博人眼球,以“艷”迎合市場,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受眾久處鮑魚之肆,不聞其臭,反而以丑為香,以劣為好,長此以往陷入了低級趣味的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某些抗戰神劇脫離歷史真實和生活實際,沒有邊際地胡編亂造,類似“手撕鬼子”的低俗鬧劇頻頻發生,低俗、庸俗、媚俗之風盛行。在對紅色經典作品改編的過程中,迎合市場低層次的消費需求而忽視作品本身的思想價值。早在2004年,廣電總局發布《關于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指出紅色經典電影改編電視劇中存在著“誤讀原著、誤導觀眾、誤解市場”的問題,影響了原著的完整性、嚴肅性和經典性。這是主管部門對文藝生產中胡編亂造、罔顧社會效益發出的警示,及至今天文藝工作者仍不能忽視。
(三)偶像符號:狂歡迷亂的視覺盛宴
作為精神產品,文藝能夠為人們提供心靈寄托和情感撫慰。而消費時代的大眾文藝,呈現出魚龍混雜、價值多元的格局,一些低劣的文藝作品也能找到自己的市場。“垃圾制造者和垃圾消費者,是一種共生關系,他們共同制造了文化生態圈的劣質化和粗陋化的現狀。”[10]在解決基礎溫飽以后,人們對于文化產品的需求激增,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對更高層次精神世界的追求會變得更加強烈,“當一個社會按照它自己的組織方式,似乎越來越能滿足個人的需求時,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權反對權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漸被剝奪。”[11]這時候人們就成了馬爾庫塞所說的沉溺于感官刺激,缺乏理性思考與自我意識的“單向度的人”。
“明星工業”是典型的市場化運作產物,在資本市場語境下,明星偶像和粉絲成為資本擴張的生產資料。在明星與粉絲這一文化傳播格局中,經紀公司迎合粉絲的期待塑造明星“人設”,粉絲在明星身上投射自身的“偶像崇拜”,吸附了大量粉絲的明星變身巨型流量的入口,甚至他們的私生活和緋聞,都成為大眾津津樂道的話題。影視明星激發的粉絲對偶像符號的各種消費形式,在互聯網、手機等新媒介中進一步泛化開來,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為草根文藝和草根明星提供了廣闊舞臺,一些網絡紅人通過低俗的表演贏得人氣。在狂歡迷亂的視覺盛宴中,受眾沉浸于萬花筒般光怪陸離的虛擬世界。2021年,吳亦凡、張哲瀚等劣跡藝人暴露出的問題,引發了主管部門對“飯圈”文化亂象的整治。
三、文藝與市場的張力性共存
文化經濟的發展潮流,使得文藝與市場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也就是發展的動力與陷阱并存:市場為文藝發展提供經濟驅動效應,但也可能造成文藝市場虛假繁榮的亂象。市場經濟下的商品邏輯勢必對藝術作品的獨立性產生一定的影響,在資本逐利的過程中,個性化的藝術創作不得不回應消費需求的普適性,因遵從最大公約數而變得日益扁平化,藝術審美價值逐漸向均值回歸。藝術的個性、獨立性喪失,將嚴重影響文藝作品的質量。
文藝與市場關系發生扭曲的根本癥結,在于當今的創作難以調和文藝審美價值取向與商業價值取向的矛盾。而造成兩者之間“鴻溝”的原因,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消費主義崛起,人文價值陷落。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思想滲透到個體的價值選擇和集體的文化構建,人們沉迷于滿足日益膨脹的欲望,不同程度地存在精神空虛和信仰缺失。二是文藝市場體量激增,文化管理體制滯后。人民消費水平的逐漸提高,對優質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有力地拉動文化產業的發展。然而,文藝市場發育不成熟,文藝領域的管理模式不適應當前的文化多元性。制度管理乏力而讓位于市場趨利性,導致市場上充斥著大量過度迎合大眾化需求的“三俗”作品,它們迅速占據文化市場擠壓高雅藝術的生存空間,優質作品的市場化轉型舉步維艱,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比較突出。三是受眾精神消費需求增長,文化產品有效供給乏力。在當前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不健全和中介機構不完善的條件下,在政府職能缺位或者越位情形下,因文化創意有效供給不充分,市場條件下的對位性保護機制不完善,藝術價值的卓越性追求受到排擠,高雅藝術創作動力不足,文化市場的下游產品趨向過度娛樂化、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去經典化,導致“三俗”產品蔓延,出現產品同質化、價格扭曲、跟風搭車、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等亂象。
當然,文藝作品追求經濟效益有其合理性,文化市場的本質是面向大眾,文藝作品應該給受眾多樣化的精神享受。“文化市場的出現為大眾提供了一個自由選擇和欣賞文化產品的場所。……文化運作的市場化,文化產品的商品化,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12]本雅明認為,即使機械復制是千篇一律取代了傳統藝術的獨一無二,但由于它能使受眾在自己的環境中欣賞租賃,從而賦予所復制對象以顯示的活力。通過標準化復制的文化產品走進人們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活動中,受眾在消費文化產品的過程中享受意義、快感以及社會身份,文化生產者通過交換達到自己的經濟目的。不難理解,在市場運作下的文藝作品既生產出經濟效益,也傳播意義和價值。它們在迎合受眾的文化心理,也為人們創造不同層次的文化生活。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相應地對文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藝工作者要為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提供更多優質的精神食糧,“努力創造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13]文藝要不斷適應新的社會文化生態,迎接新時代的挑戰。“中國已成為全球生產和消費的重要力量,而我們面對的文學和文化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似乎也是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化為新的文學想象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14]進入新時代,文學藝術家要以自己的使命感、責任感尋找合理的定位。
四、新時代文藝發展應遵循的價值導向
研究文藝與市場的關系,歸根到底是如何處理好藝術創作的個性化追求與文化市場的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文藝的市場功利價值與社會價值原本是一體的,當它們發生矛盾時,社會效益居于首位。從文藝價值的整體建構和主流導向來看,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完全可以統一起來。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15]高雅藝術和大眾藝術,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從來都不是二元對立的兩方面,在當前的文化背景下,多元融合的文化格局正在形成。我們只有深入認識文藝與市場的關系,才能找到新時代文藝發展正確的價值導向。如何真正使文藝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商業價值與藝術價值統一起來,這需要我們從多方面進行努力:
第一,要理解和尊重市場與文藝的發展規律。文藝價值取向要求文藝活動猶如春蠶吐絲般自然,而商業的價值取向要求文藝生產如工廠流水線般高效。“流行的大眾文藝本身就是市場的產物,高質量產品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有效傳播更多地依賴市場競爭來調節,它們健康有序的運行符合文化發展規律,只有尊重規律才能不斷邁向時代精神的高端。”[16]文藝生產、傳播既要研究文化市場規律,更要堅守自己的審美理想、保持文藝的獨立價值。優秀的文藝作品標志著一個民族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17]文藝精品在反映人類社會真善美的價值取向上都是一致的,不同國家、民族的經典作品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魅力。
第二,文藝工作者不要沾滿了銅臭氣。文藝產品有商品屬性,但不能唯利是圖。文藝工作者要力戒浮躁,沉得住氣,加強個人修養,努力成為“德藝雙馨的藝術家”。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泉活水,只有扎根人民群眾,才能真實地反映我們偉大的時代。文藝工作者時刻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這才是創作出偉大作品的唯一途徑。“只有眼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同時真誠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實,我們才能為人類提供中國經驗,我們的文藝才能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18]在市場大潮的面前,文藝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做到“不為一時之利而動搖、不為一時之譽而急躁,不當市場的奴隸,敢于向炫富競奢的浮夸說‘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說‘不’,向見利忘義的陋行說‘不’。”[19]同時,文藝工作者要樹立創新意識,創新包括文藝作品的思想、題材、文體、技巧等方面。藝術創新要警惕浮躁之風,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避免一味標新立異、追求怪誕,搞不切實際的形式主義。
第三,文藝的市場接受程度需要科學的評價體系。我們既要考慮到市場對文藝的接受程度,又要考慮藝術的審美標準。在市場接受程度上,合理設置反映市場接受程度的發行量、收視率、點擊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標,但不能過于依賴市場指標的反饋結果,誤導文藝創作者。堅決杜絕唯市場、唯票房論的出現,媒體也不應片面夸大文化產品的市場價值而忽視其社會價值。好的市場接受程度是衡量文化產品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效益的重要指標。擁有好的市場,意味著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得到了最大化的傳播和推廣。沒有市場的文化產品,其社會價值必然也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評論家要發揮對文化市場的診斷功能。在審美標準上,要建立起全新的批評標準,不應以傳統“文藝理論”來限定新形態下的“文化產品”。“當前的大眾文化是世俗流行文化,我們對大眾文化價值觀的分析,也應該依據世俗社會本身的標準,而不是宗教標準或實驗藝術的標準,否則就會因為錯位而導致批評的無效,變成自說自話。”[20]當前文藝界出現的一些亂象,與文藝批評的缺位也是分不開的。正確的文藝評論是創作的鏡子和良藥,是文化市場的重要校正機制。文藝評論應當立足于正確的價值評判標準,喚起文學藝術家的社會良知,集中于對美好人性的反映,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現象,實現文藝作品的價值導向功能。
第五,文藝管理機構要“一手抓繁榮、一手抓管理”,推動文藝全面繁榮健康發展。文藝管理要強化導向作用,營造良好的文藝生態。完善文藝體制,遵循文藝規律,進行規范化管理,既促進文藝生產、傳播,又注意避免市場機制對文藝生產、傳播的負面影響。
總之,新時代的人民文藝,是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保持自己的藝術品位和格調,既要在經濟上贏得商業價值,同時也要在藝術上實現作品的審美價值,在思想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
[注釋]
[1][15][17][18]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2][12]戴阿寶:《知識鏡像與書寫》,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版,第123頁、第130頁。
[3][11][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頁、第4頁。
[4][13]江澤民:《關于宣傳思想工作的宗旨和幾點希望》(1993年1月15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頁。
[5]魏鵬舉:《魏鵬舉:回顧2016中國文化產業結構性調整》,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culture/gd/201701/03/t20170103_19338451.shtml,查詢于2017年6月20日。
[6]李準:《論商品經濟與文藝發展的關系(續)》,《文藝爭鳴》,1990年第1期。
[7]梁鴻:《曖昧的“民間”:“斷裂問卷”與90年代文學的轉向——90年代文學現象考察之一》,《文藝爭鳴》,2009年第6期。
[8]南帆:《文藝拒絕低俗與銅臭專家解讀低俗為何能大行其道》,《人民日報》,2015年4月10日。
[9][10]張閎:《“娛樂至死”的文化狂潮——2007年文化現象批判》,《探索與爭鳴》,2007年12期。
[14]李舫:《文藝:如何面對市場》,《人民日報》,2005年12月16日。
[16]范玉剛:《市場條件下完善高雅文藝創作保護機制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12期。
[19]李掖平:《文藝批評要著力維護“靈魂健康”》,《光明日報》,2017年5月15日。
[20]陳國戰:《陶東風:在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錯位處尋求創新》,《中華讀書報》,2014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