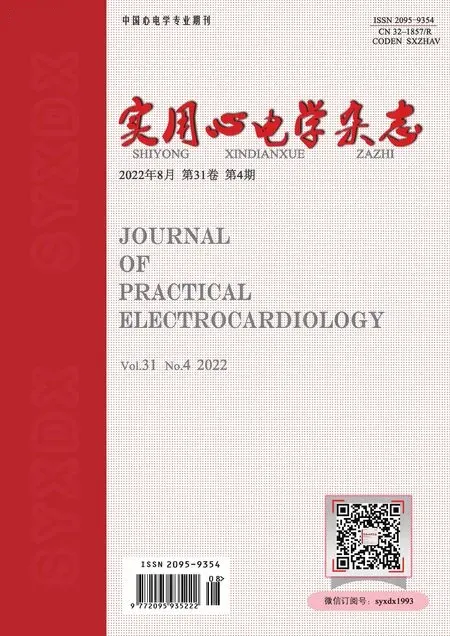外泌體非編碼RNA 診治阿霉素心臟毒性的研究進展
田超 吳欽超 褚現明
阿霉素是一種細胞周期非特異性蒽環類化療藥物,通過抑制DNA 的轉錄和復制、提高細胞內氧化應激水平殺傷腫瘤細胞,但是這種殺傷效應具有非選擇性。 由于阿霉素的心肌親和力,其對心臟產生的毒副作用尤為明顯。 目前,研究人員認為阿霉素心臟毒性(doxorubicin-induced cardiotoxicity, DIC)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心肌細胞內氧化應激水平升高及其引起的心肌細胞受損和死亡有關,但具體機制仍然不清楚,亦缺乏有效的DIC 早期檢測手段。 臨床醫師通常在癌癥患者化療時預防性給予心臟保護劑,如右丙亞胺和維生素E 等,但效果有限。
外泌體是所有細胞均可分泌的一種直徑在30 ~150 nm 的細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EV),由磷脂雙分子層構成骨架,四分子交聯蛋白和跨膜蛋白等嵌插和貫穿于雙分子層,內部包含各種核酸(包括信使RNA 和非編碼RNA)、脂質和蛋白質等[1]。 外泌體非編碼RNA 不僅在疾病發生時有差異性表達,而且還可作為治療性調控分子被遞送到受體細胞并發揮生物學功能。 基于以上特性,外泌體非編碼RNA 有望應用于DIC 的早期診治[2]。 本文對DIC 目前常規的診療措施、外泌體非編碼RNA作為DIC 診治手段的研究以及未來發展前景進行綜述,以期提高心內科和腫瘤科醫師對外泌體非編碼RNA 應用于腫瘤心臟病學領域的認識。
1 阿霉素心臟毒性的常規監測和治療手段
1.1 阿霉素心臟毒性的監測手段
阿霉素的“脫靶效應”會引起心肌細胞損傷,導致心律失常、心肌病甚至充血性心力衰竭[3]。 阿霉素造成的心肌損傷具有劑量依賴性,化療啟動之日即心功能損傷開始之時。 DIC 所致的心功能損傷早期表現隱匿,可通過觀察患者阿霉素化療后出現的心臟相關癥狀,并結合心肌損傷標志物(如肌鈣蛋白、肌酸激酶和乳酸脫氫酶[4])以及心力衰竭標志物(如利鈉肽家族[5]等)初步判斷,但這些方法的特異性較低。
雖然心電檢查能檢測出抗癌治療所致的心律失常,但美國梅奧診所的一項研究表明,阿霉素引發的心律失常發生率較低[6],因此心電檢查不適用于DIC 的篩查。 目前,指南推薦采用超聲心動圖進行心臟整體收縮功能的評估[7]。 然而,采用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檢測阿霉素所致心臟損傷的敏感性不高,因為很可能在LVEF 下降前患者心肌組織即發生了病理變性,如細胞水腫、心肌纖維化等[8]。 心臟磁共振可以檢測出蒽環類藥物導致的早期心肌纖維化[9],但患者體內如存在起搏器、支架或鋼板等金屬植入物,則可使其應用受限。 此外,心臟磁共振檢查價格較高,不宜作為常規篩查方式。 心臟放射性核素掃描被認為是診斷DIC 的“金標準”[10-11],但存在輻射暴露風險。
綜上,針對DIC 的早期診斷,目前臨床上尚無敏感性、特異性均較高,且兼具安全性與經濟性的有效手段。
1.2 阿霉素心臟毒性的治療方法
阿霉素損傷心臟的主要機制包括三個方面:①嵌入心肌細胞DNA 雙鏈之間的堿基,從而抑制DNA 的復制和轉錄;②抑制拓撲異構酶Ⅱ,使DNA去螺旋化,從而抑制DNA 的復制和轉錄;③與鐵離子形成復合物,促進自由基的生成,提高心肌細胞氧化應激水平,從而破壞細胞膜,導致心肌細胞損傷和死亡。
目前,對DIC 有預防作用的藥物右丙亞胺可通過競爭性螯合鐵離子來抑制自由基的產生,從而降低心肌細胞的氧化應激水平,減輕DIC。 但右丙亞胺的作用有限,且存在引發繼發性腫瘤的風險[12]。當患者出現栓塞、冠脈痙攣、心肌病、心力衰竭或心律失常等DIC 相關后果時,臨床醫師除了停用、減少阿霉素用量和調整用藥策略外,常選擇β 受體阻滯劑、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鈣通道阻滯劑、抗凝或抗心律失常藥物等對癥治療,但仍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我國癌癥發病率居高不下,患癌人口基數龐大,抗癌治療引發心臟毒性的問題將愈發突出,造成很多患者陷入“得了腫瘤卻死于心臟病”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探索新型、有效的DIC 治療藥物已是迫在眉睫。
2 外泌體非編碼RNA 在阿霉素心臟毒性診治中的作用
外泌體中包含豐富的非編碼RNA,既可以作為早期診斷DIC 的標志物,也可作為遞送分子用于DIC 的治療。
2.1 阿霉素心臟毒性早期診斷的標志物
微小RNA(microRNA, miRNA)是一類長度在19 ~23 nt 的非編碼RNA。 轉錄組測序結果表明,血液中的非編碼RNA 在多種心血管疾病中的表達存在明顯差異[13-14]。 非編碼RNA 作為診治心血管疾病靶標的作用已經明確,并有部分已逐漸推廣應用到臨床[15]。 已有相關綜述較為系統地總結了循環miRNA 作為預測DIC 標志物的研究[16-17]。 與游離形式的非編碼RNA 特性類似,外泌體非編碼RNA亦具備成為DIC 診斷標志物的潛力,且比前者更穩定。
BEAUMIER 等[18]對患有骨肉瘤的實驗犬在排除既往心臟疾病和易患心肌病體質后給予單獨的阿霉素化療,在化療前、中、后分別檢測血漿肌鈣蛋白水平、血漿EV-miRNA 和進行超聲心動圖檢查,并將上述幾種心功能損傷的檢測手段進行對比。結果顯示,化療后血漿EV 中的miR-107、miR-146a和miR-502 與化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中miR-502 的表達明顯升高,且這種變化早于現有的心肌損傷檢測(包括cTnT、超聲心動圖等)陽性結果之前;miR-107 和miR-146a 表達下降,這種差異性表達與之前研究中兒童接受單獨阿霉素化療后血液中miRNA 表達的變化結果一致[19]。 但是EV 來源的這三種miRNA 能否作為DIC 的標志物,仍需更大臨床樣本進行驗證。 LI 等[20]用阿霉素處理AC16心肌細胞,發現處理后的心肌細胞外泌體中circ-SKA3 表達升高,并且通過miR-1303/TLR4 軸增強阿霉素誘導的心肌細胞毒性。 雖然該研究只是闡明了外泌體來源環狀RNA 介導阿霉素損傷心肌的一種機制,但也提示了外泌體circ-SKA3 可能成為DIC 診斷標志物。
現階段尚缺乏針對外泌體來源非編碼RNA 作為阿霉素化療心肌損傷標志物的研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幾方面:①干擾因素較多,無法確定外泌體非編碼RNA 變化的原因。 目前臨床上多采用聯合化療方案,如對乳腺癌患者通常采用“阿霉素+曲妥珠單抗”的化療策略,對小細胞肺癌患者多采用“鉑類+依托泊苷”的經典化療方案,因此,外泌體非編碼RNA 的變化可能是多種藥物綜合影響的結果;再者,腫瘤本身的變化是否會影響外泌體非編碼RNA 也需要納入考慮;加之癌癥患者通常合并其他慢性基礎疾病,如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使外泌體非編碼RNA 的變化原因進一步復雜化。 因此,最理想的是能夠找到僅采用阿霉素化療且無合并其他基礎疾病的患者,確定阿霉素化療為唯一變量。 ②化療患者出現心臟毒性的時間不定,目前我國患者隨訪意識淡薄,因此很難通過隨訪期間的心功能相關檢查發現DIC。 若能通過嚴格納入標準、開展長期大規模規律隨訪以及采用科學嚴謹的統計分析手段等舉措排除以上干擾因素,明確與阿霉素損傷相關的外泌體非編碼RNA 的變化,則有望將外泌體非編碼RNA 用于DIC 的早期診斷。
2.2 阿霉素心臟毒性的治療
人類基因組中約98.5%的序列為非編碼RNA,其本身不編碼蛋白,但具有強大的基因調控功能。雖然非編碼RNA 已被證實在心血管系統中可發揮重要的調控作用,但由于存在胃腸道降解、靶向性不足等缺點而限制了其用于治療。 經外泌體包被的非編碼RNA 有望克服上述不足,發揮更好的治療效果[21-23]。
2.2.1 外泌體微小RNA 治療阿霉素心臟毒性miRNA 通過與靶向信使RNA(mRNA)進行堿基互補配對, 調控轉錄后的基因表達[24-25]。 某些miRNA 已被證明能調控心肌細胞增殖[26-29],外泌體及其遞送的非編碼RNA 對心肌損傷亦顯示出較強的修復能力[30-32]。 理論上,經外泌體遞送的非編碼RNA 相較游離非編碼RNA 具有更好的穩定性和修復效果。
由于氧化應激在DIC 的發展過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抑制氧化應激造成的心肌細胞衰老[33]及程序性死亡[34-38]、促進心肌細胞增殖是DIC 的常規治療思路。 而對具有抑制氧化應激或促進心肌細胞增殖效應的miRNA 進行外泌體包被,對外泌體進行人工改造,可減少其被單核巨噬細胞系統吞噬[39],再經過特異性靶向心肌細胞,即可減輕DIC。
除此以外,腫瘤細胞對阿霉素耐藥可造成阿霉素使用劑量的累加,由此產生的過量阿霉素對心肌細胞慢性炎癥損傷的問題亦有待解決。 化療耐藥的問題在乳腺癌治療過程中尤為明顯。 DENG等[40]采用阿霉素治療小鼠乳腺癌,發現小鼠體內可在耐藥慢性炎癥環境中產生骨髓源性抑制細胞,該細胞分泌的外泌體miR-126 可誘導腫瘤血管形成,促進乳腺癌細胞肺轉移,并且正反饋地促進炎癥因子和炎性細胞生成,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抑制骨髓源性抑制細胞來源的外泌體miR-126 將有助于解決阿霉素耐藥問題。 臨床上治療三陰性乳腺癌失敗的主要原因同樣是化療耐藥和癌細胞轉移。研究發現,人單核細胞白血病細胞(tohoku hospital pediatrics-1,THP-1)外泌體miR-770 可以通過促進三陰性乳腺癌細胞凋亡,降低癌細胞對阿霉素化療的耐藥性,而阿霉素化療敏感組織中的miR-770 表達上調則提供了臨床證據[41]。 研究發現,對阿霉素耐藥的胃癌細胞株分泌的外泌體中富含miR-501,后者可通過絲氨酸或蘇氨酸激酶Akt 途徑抑制胃癌細胞的凋亡,并促進癌細胞的增殖和遷移[42]。當發生胃癌阿霉素化療耐藥時,通過抑制外泌體miR-501 或許可有效抑制癌癥并降低耐藥性。
2.2.2 外泌體長鏈非編碼RNA 治療阿霉素心臟毒性長鏈非編碼RNA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是一類長度>200 nt 的非編碼RNA,可通過內源性競爭海綿作用結合并抑制miRNA,從而間接調控靶基因的表達。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lncRNA 參與心肌細胞的衰老、增殖和修復等過程。 有研究發現一種能夠負性調控心肌細胞增殖和修復的lncRNA CPR,在成年小鼠中特異性敲除CPR 可促進心肌細胞增殖并改善心臟功能[43]。 lncRNA 還具有改善心臟重構[44]、抑制心肌細胞自噬[45]和細胞凋亡[46]的作用。 lncRNA 在腫瘤進展調控[47]和心肌損傷修復方面作用強大,外泌體lncRNA 在治療DIC 方面的作用同樣值得期待。
WANG 等[48]研究發現,對阿霉素耐藥的乳腺癌細胞分泌的外泌體lncRNA H19 表達明顯增加,而通過抑制H19 可降低癌細胞活力和誘導癌細胞凋亡,從而顯著降低阿霉素抗性,這提示H19 可作為減輕乳腺癌阿霉素耐藥性的治療靶點。 既往研究支持間充質干細胞來源外泌體治療DIC 的作用和前景,基于此,我們團隊對骨髓間充質干細胞來源外泌體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涉及其減輕阿霉素心臟毒性的機制和作為早期診斷標志物等方面,初步發現外泌體lncRNA 介導鐵死亡的可能信號調控通路。 有報道指出,經缺氧處理之后間充質干細胞來源的外泌體lncRNA MALAT1 表達明顯增加,可通過競爭性結合miR-92a-3p 并激活ATG4a 來改善線粒體代謝,從而有效避免阿霉素引起的心肌損傷[49]。 根據當前的研究結果,采用外泌體包被lncRNA 治療DIC 是一個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和治療策略,但還需要更加深入和證據確鑿的應用研究成果作為支撐。
3 存在的問題與未來展望
雖然外泌體非編碼RNA 在DIC 診治中表現出較大潛力,但要真正應用于臨床道阻且長,目前仍然存在如下問題:①超高速離心法是分離外泌體的“金標準”,但離心過程中外泌體損失較多,而采用其他方法獲取外泌體雖然能克服上述缺點,但是純度不高;②開展外泌體相關研究要么依賴于超高速離心設備,要么依賴于外泌體提取試劑盒,前者對實驗室平臺要求較高,后者經濟成本較高;③針對外泌體的基礎研究需要與臨床研究相結合,理想的臨床試驗不僅納入標準嚴格,而且由于其為前瞻性研究,因此需要多中心的研究人員多年協作參與。雖然存在種種困難,但是機遇與挑戰同在。 世界范圍內的學者對外泌體研究仍保持飽滿的熱情與十足的信心,年發文量呈爆發式增長,外泌體專刊不斷開設;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科研項目對外泌體研究的支持力度較大,研究前景一片光明。
臨床上已經探索出一些可用于DIC 監測的超聲心動圖技術,如實時三維超聲心動圖、心肌應變的組織多普勒成像和應變率成像[50-52]。 隨著相關技術的發展,未來的心臟超聲技術將會更早地發現心臟微小損傷,提供敏感性更高的DIC 早期檢測手段。 同樣,闡明各種化療藥物導致心臟毒性的機制,也將為尋找治療靶點提供科學依據[53]。
無論是蛋白修飾[54]還是外泌體,無論是影像學檢查還是非編碼RNA,無論是傳統中藥還是西藥,我們都應當保持開放的心態,讓各種學術觀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彼此互為補充,最終殊途同歸,闡明心臟毒性具體機制,發現有效的診治手段。 相信隨著我國心內科和腫瘤科專家對腫瘤心臟病學的認識不斷加深,腫瘤心臟病學的多學科會診將在我國各級醫院逐步開展,符合我國國情的化療藥物引起心臟毒性的相關指南也將陸續發布,使臨床實踐有章可循,最終造福于患癌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