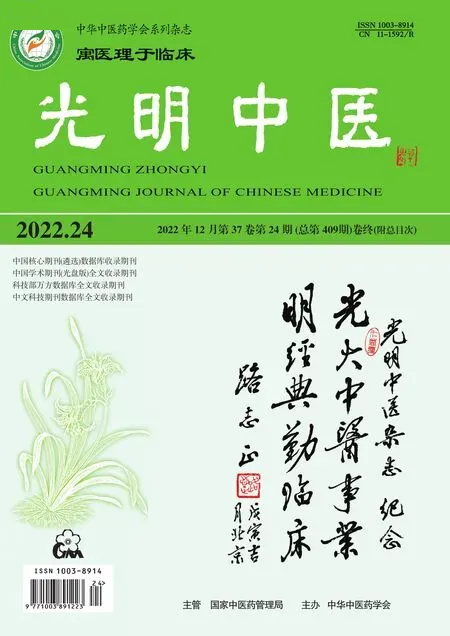調督理筋針法聯合獨活寄生湯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臨床觀察
陳麗蘭
腰椎間盤突出癥(LDH)是引起中老年人群下腰痛和腰腿痛的常見病因,患者腰椎因生理退行性病變、外傷等原因出現椎間盤結構和功能改變。如纖維環破裂和髓核組織脫出,造成相鄰脊神經根受壓刺激,其中病變節段主要位于L4~L5、L5~S1,臨床表現為腰腿痛、下肢麻木和活動受限等系列癥狀。目前臨床治療LDH的方法有保守療法和手術療法,其中多數患者首選保守治療。非甾體類抗炎藥對緩解LDH炎性疼痛有積極作用,但仍有部分患者療效欠佳,而且長期服用可能出現胃腸道損傷等不良反應。中醫藥對LDH有悠久的治療史,為臨床治療提供了新選擇。近些年中醫特色療法在慢性腰腿痛的治療領域發揮獨特優勢[1]。調督理筋針法是一項治療痹證的中醫手段,具有調和督脈、舒筋活絡和止痛的作用[2]。本研究針藥并用,探討運用調督理筋針法聯合經驗方劑獨活寄生湯治療LDH的臨床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本文為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選取2019年8月—2021年11月樂安縣中醫院收治的106例LDH患者為研究對象,男65例,女41例;年齡38~75歲,中位年齡54歲,平均年齡(54.7±8.13)歲。采用信封法將入選的106例LDH患者隨機分成2組,方劑組和針藥組各53例。比較2組間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本研究得到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

表1 2組LDH患者一般資料比較(例,
1.2 診斷標準(1)符合《腰椎間盤突出癥》[3]的LDH診斷標準:①下肢放射性疼痛,且疼痛部位和相應受累神經支配區域相符;②下肢肢體感覺異常;③直腿抬高試驗或股神經牽拉試驗陽性;④腱反射能力較健側減弱;⑤肌力下降;⑥腰椎影像學檢查明確提示椎間盤突出。前5項中具備3項以上并結合第6項,即可確診LDH。(2)依據《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4]的辨證分型標準,辨證為寒濕痹阻型,癥見腰部重痛,活動受限,轉側不利,受寒或陰雨天疼痛加重,得熱則減,活動痛甚,舌質胖淡,苔白膩,脈沉緊或弦緩者。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納入標準:(1)符合上述LDH西醫診斷和中醫辨證分型標準者;(2)年齡不超過75歲,溝通理解能力正常,均知情且同意參與研究者;(3)病情適合保守治療者。排除標準:(1)病情相對較重,如有馬尾神經受壓癥狀,或經嚴格保守治療后效果不理想,需接受手術治療者;(2)入組前2周接受過LDH相關治療者,比如非甾體類抗炎藥或相關中藥貼劑治療史等;(3)合并其他腰椎疾病者,比如腰椎結核、腰椎結核或等腰椎骨折等;(4)合并其他嚴重內科疾病、軀體外傷或孕期女性等不宜參與研究者。
1.4 方法
1.4.1 治療方法(1)方劑組給予獨活寄生湯治療,組成:獨活、熟地黃、黨參各15 g,川芎、當歸、白芍各12 g,桑寄生、茯苓、秦艽、懷牛膝、杜仲各10 g,防風9 g,肉桂、炙甘草各6 g。由醫院中藥房統一煎制,1劑/d,分早晚2次口服,每次100 ml,連續服用2周。(2)針藥組在上述方劑治療同時,另給予調督理筋針法治療,操作方法:①患者取俯臥位,穴位消毒處理,用毫針(華佗牌,規格:0.30 m×40 mm,蘇州醫療用品廠有限公司)針刺腰陽關、腎俞(雙)、命門、大腸俞(雙)、后溪(雙)、八髎和腰夾脊穴,其中腰陽關、命門直刺0.8~1寸,并選擇相應的腰夾脊穴;腎俞和大腸俞穴直刺0.5~0.8寸;八髎朝上斜刺0.5~0.8寸;后溪直刺1.8~1寸且透向合谷穴。捻轉得氣后留針30 min,每隔10 min行針一次。此針法1次/d,持續治療2周。
1.4.2 觀察指標(1)中醫證候積分。參考《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5]中寒濕痹阻型LDH的評分標準,對腰部重痛、活動受限、受寒加重、活動痛甚4項較明顯的癥狀進行證候評分,0、2、4、6分依次表示無、輕、中和嚴重,得分越高表示該項癥狀愈嚴重。(2)JOA評分。JOA評分是評價LDH患者腰部功能障礙的常用工具,包括主觀癥狀(9分)、臨床癥狀體征(6分)和日常活動(14分)3個項目評價,總分29分,得分越低則表示腰部功能障礙愈嚴重。(3)實驗室指標。檢測血清白介素-1β(IL-1β)、白介素-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水平,檢驗科人員采用酶聯免疫法完成上述檢測。臨床痊愈、顯效和有效之和為總有效。
1.4.3 療效判斷標準臨床痊愈:治療后腰痛、下肢放射痛癥狀消失,活動恢復正常,直腿抬高試驗>70°;顯效:治療后腰痛、下肢放射痛癥狀顯著減輕,活動基本恢復正常,直腿抬高試驗60°~70°;有效:治療后腰痛、下肢放射痛癥狀有所好轉,日常活動有一定改善,直腿抬高試驗45°~60°;無效:未能達到上述療效標準。

2 結果
2.1 2組LDH患者療效比較針藥組總有效率高于方劑組(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2組LDH患者療效比較 (例,%)
2.3 2組LDH患者中醫證候積分比較治療前,2組中醫證候積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中醫證候積分均明顯下降(P<0.05),且針藥組顯著低于方劑組(P<0.05)。見表3。

表3 2組LDH患者中醫證候積分比較 (分,
2.4 2組LDH患者JOA評分比較治療前,2組JOA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JOA評分均明顯提高(P<0.05),且針藥組JOA評分、JOA升高值均大于方劑組(P<0.05)。見表4。

表4 2組LDH患者JOA評分比較 (分,
2.5 2組LDH患者實驗室指標比較治療前,2組血清IL-1β、IL-6、TNF-α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血清IL-1β、IL-6、TNF-α明顯下降(P<0.05),且針藥組上述指標均低于方劑組(P<0.05)。見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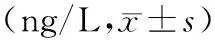
表5 2組LDH患者實驗室指標比較
3 討論
筆者臨床接診發現,LDH發病人群有逐漸年輕化趨勢,就診人群中大學生、年輕白領等并不少見,因此日常需重視LDH的預防,養成良好的坐姿和睡姿,避免長時間伏案學習、工作,加強腰背肌鍛煉等。確診LDH后需根據個人病情情況接受治療,防止病情加重。中醫對LDH的病機和治療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認識,不僅在LDH非手術治療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體現出療效確切和不良反應少等優點,已被越來越多LDH患者所接受。
中醫學上無“腰椎間盤突出癥”一詞記載,根據描述可歸納為“腰痛”和“痹證”等范疇。如《素問·刺腰痛》記載:“衡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俯臥,仰則恐仆”。中醫學認為,此與正氣不足和外邪侵襲密切相關,患者正氣不足,肝腎虧虛,風、寒、濕等外邪侵襲,流注經絡,滯于肌肉關節,氣血痹阻,久之寒濕痹阻,致腰腿筋脈失養,經脈不暢,不通則痛。正如《諸病源候論》記載:“腰痛者,由腎氣不足,受風邪之所為也,勞傷則腎虛,虛則受于風冷”和《素問·痹論》記載:“風、寒、濕三氣雜至,合之為痹也”,可見正氣不足和外邪侵襲與LDH的緊密關系。因此LDH患者宜采用補益肝腎、祛風濕和通經活絡之法緩解痹痛。本研究所用獨活寄生湯出自《備急千金要方》,為中醫治療痹痛的經驗方劑,對肝腎虧虛、氣血不足和風寒濕痹阻所致的痹證有較好治療作用,可起到祛風濕、補肝腎、活血通絡和止痹痛的功效,對改善腰部冷痛、腰腿痛、下肢麻木和活動不利等LDH癥狀效果較好[6]。
中醫學認為,LDH病在脊柱,病位在督脈經筋,LDH發病與督脈虧虛密切相關。督脈是人體的“陽脈之海”,為陽脈之都綱,總督諸陽,主要負責調節人體全身的氣血運行,維持臟腑筋骨的正常濡養。正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記載“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督脈經筋通過“腱”的形式“貫脊”“挾脊”,與足太陽經共同起到維系、支撐骨骼運動的作用[7]。若督脈虧虛,則諸陽虛,陽氣不足,易受風、寒、濕邪侵襲,久之氣血運行不暢,經絡痹阻,筋骨濡養不足,發為痹痛。本研究調督理筋針法是從調和督脈角度治療LDH的中醫外治手段,選取穴位以督脈和足太陽膀胱經為主,比如腰陽關穴位于脊柱區,是人體督脈陽氣必經之關,是治療腰骶疼痛、下肢痿的要穴,能益腎強腰和驅寒除濕;腎俞穴屬足太陽膀胱,可補益腎氣,針刺或按摩此穴可改善腰痛,與命門穴配伍使用,能固護體內元氣。元氣足,腰背暖,緩解腰痛效果較好。上述穴位合用,能起到調和督脈、補腎陽、壯腰膝、舒筋活絡和理筋止痛的功效。
本研究顯示,調督理筋針法與獨活寄生湯聯合使用治療LDH的效果優于獨活寄生湯,表現在治療后中醫證候積和血清IL-1β、IL-6、TNF-α水平下降更顯著、JOA評分升高更明顯(P<0.05),明顯提高了臨床總有效率(P<0.05)。與賈松濤等[8]報道結論相符,印證了針藥合用的顯著療效,二者可起到協同增益效果,能更充分、更快速地幫助LDH患者緩解癥狀,減輕腰部功能障礙。IL-1β、IL-6、TNF-α均是反映機體炎癥反應的常用指標,椎間盤病變的病理過程可刺激炎癥介質釋放、引起機體炎癥反應和炎性疼痛。2組治療后上述檢測指標均明顯下降,且針藥組下降更為顯著(P<0.05),與高凱麒等[9]、王昭華[10]報道有相通之處,說明調督理筋針法與獨活寄生湯聯合使能更有效降低LDH患者的炎癥反應,減輕炎性疼痛。
綜上表明,調督理筋針法聯合獨活寄生湯治療LDH效果顯著,在緩解臨床癥狀、改善腰部功能和降低炎癥反應方面有明顯優勢,可作為可靠的治療方案并予以推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