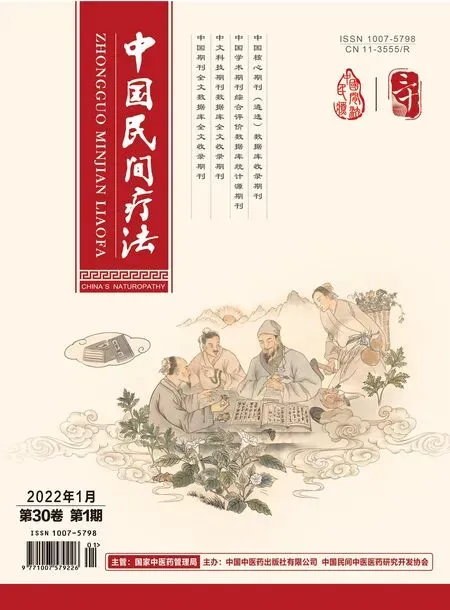光緒六年慈禧病案:一個不典型性胃食管反流病的典型案例(下)
白興華,郭盛楠,周 娟,唐秋雙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北京 100700)
中醫對胃食管反流病的認識囿于一些傳統理論的束縛,誤辨誤治的情況普遍存在[1]。光緒六年慈禧病案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紛繁復雜、頭緒極多的癥候群中,代表當時最高水平的太醫尚不能建立它們的內在聯系,困惑于諸多常見卻棘手的表象,不能準確辨證,導致慈禧病情遷延不愈。這場發生在光緒六年的歷史性大會診,為我們認識胃食管反流病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樣本。醫學發展到今天,胃食管反流病領域仍然面臨著兩難困境。
首先是診斷難。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檢查或監測手段可作為診斷胃食管反流病的金標準。有典型癥狀的胃食管反流病比較容易確診,但對于不典型甚至主要以食管外癥狀為主要表現的患者,被誤診的情況十分普遍。另一個是治療難。胃食管反流病本質上是一種胃腸動力障礙性疾病,理論上講改善胃腸動力的藥物應該是首選,也是根本解決之道,但到目前為止已有的促胃腸動力藥治療本病并無明顯效果。除少數可以手術治療外,以奧美拉唑為代表的質子泵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s,PPIs)是臨床一線療法,由此導致的諸多問題不可忽視,特別是那些PPIs治療無效的患者,往往被冠以難治之名,即難治性胃食管反流病,部分患者因無治療措施可用而被稱為“治療空白”[2]。
筆者反復研讀慈禧病案,梳理癥狀表現,輔以現代醫學知識,厘清癥狀之間的聯系,認為本案是一起以食管外癥狀為主的胃食管反流病典型案例,基本病機為中焦脾胃氣機升降失調。盡管這是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的病案,但慈禧的食管外癥狀非常典型,太醫們在辨證治療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也很具有代表性,使本案對當今診治胃食管反流病仍有較大的啟示作用。
1 診斷:中西醫優勢互補
無論中醫還是西醫,胃食管反流病的診斷均是難點。中西醫各有長處,但也有不足,可以優勢互補,避免誤診。
從西醫角度講,胃食管反流病診斷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根于其沒有統一的指標作為診斷標準,在很多情況下是憑癥狀進行診斷的,這一點完全不同于高血壓病、糖尿病、高脂血癥等僅需客觀指標即可診斷的疾病。對于具有典型反流癥狀的患者,通過胃食管反流病診斷問卷(GerdQ)即可確診。對于無典型反流癥狀,但有典型食管外表現,且其發作符合反流特點的患者,如咳嗽與進食有關、夜間發作等,也基本可以明確診斷。如果患者不屬于以上兩種情況,則極易造成臨床誤診。
對于臨床極易被誤診的這部分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現代醫學的輔助檢查也不完全可以幫助診斷。迄今為止,無論是相對傳統的鋇餐、胃鏡檢查,還是阻抗聯合24hp H監測、高分辨率食管測壓,以及唾液胃蛋白酶檢測,均有其局限性,都不能作為胃食管反流病診斷的金標準。此外,PPIs試驗性治療無效也不能排除胃食管反流病的可能性。反流物按照形態分為3種,即液態、液氣混合態和氣態。臨床上液態和液氣混合態反流物反流表現出的臨床癥狀一般比較典型,并且也能通過理化檢查或監測發現反流證據,但氣態反流物反流表現出的臨床癥狀一般都不典型,甚至無明顯的反流表現,尤其當反流物的量特別少時,就更難通過檢查發現客觀指征。對于這部分臨床極易被誤診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而言,即便能從癥狀上判斷其屬于胃食管反流病,但因所有客觀檢查的結果都是陰性,西醫往往將其歸咎于功能性胃灼熱、焦慮、抑郁等心因性疾病,予以抗焦慮或抗抑郁治療,容易造成誤診與誤治。
從中醫角度講,胃食管反流病的基本病機是脾胃氣機升降失調,其中胃氣上逆與西醫的胃食管反流病發病機制基本一致。胃氣上逆的典型表現為嘔吐、反酸、反食、噯氣。反酸與反食都是液態反流物的典型表現,在無惡心、干嘔和不用力的情況下,胃內容物反流入口腔或咽部。若反流物為不消化食物即為反食,為酸味液體則為反酸,少數情況下可有苦味的膽汁。反食類似于一些食草動物的反芻。?名醫類案?記載1例病案:“一人瘦長而色青,性剛急,年三十余,病反胃,每食入良久復出,又嚼又咽,但不吐耳。”[3]此案例表現出的癥狀就是典型的反食現象。噯氣則是氣態反流的表現,如果噯氣伴有反酸或反食則是液氣態混合反流。對于臨床高度懷疑為胃食管反流病,但缺乏客觀檢查指征的患者,西醫診斷無法成立,但從中醫角度看仍然可以辨證為胃氣上逆,這種情況通常以食管外表現為主,反流物為氣態。由于反流物量少而微,現有理化檢查方法無法探查或監測到,對于此類,筆者認為可稱之為微反流(slight reflux)。
與微反流相近的概念是靜息性反流(silent reflux),是指無典型反流癥狀,但理化檢查為陽性的反流狀態,由英國學者KENNEDY于1962年提出。微反流則指既無典型反流癥狀,又無陽性理化檢查結果的反流。微反流的反流物量較輕微,現有的檢測方法還無法檢測到,只能希冀將來有更靈敏精確的檢測手段出現。還需特別注意的是,反流物量的多少與其造成的嚴重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微量反流導致的危害可能更大。臨床上有的患者反酸、胃灼熱多年,但胃鏡檢查食管可能無異常或僅是反流性食管炎,而微反流患者通常以食管外表現為主,由于沒有消化道癥狀,往往不能正確選擇科室就診,而其他相關科室醫師因為對胃食管反流病的認知度不夠,長期被誤診誤治,最終導致終末器官嚴重損害,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纖維化、聲帶息肉、喉癌、鼻息肉、耳聾等,如果是兒童則還可能影響其生長發育。“微反流”概念的提出彌補了明確的臨床表現和陰性客觀檢查結果之間的空白,消融了臨床實踐與現有理化檢測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對于胃食管反流病的診斷和治療具有重要的意義。自此,我們不再受限于客觀檢查結果的支持,就可以根據患者臨床癥狀表現進行針對性治療,對于輕度、早期、易于誤診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關于本病的發生機制,西醫聚焦在賁門及食管下括約肌的功能,包括賁門松弛、食管下括約肌一過性松弛等。中醫則從整體出發,認為消化道是一個有機整體,除了賁門和食管,包括胃、腸道的狀態都與反流有關。臨床上,一般西醫認為是不典型反流癥狀或與反流無關的表現,如胃脘脹滿、噯氣、大便溏薄、完谷不化,或大便難、先干后溏,以及神疲倦怠乏力,甚至脫發、面色白或萎黃等,這些脾胃虛弱之象,在中醫看來都是重要的信息,均可視為診斷胃食管反流病的重要依據。此外,中醫認為胃氣為濁氣,胃氣上逆即濁氣上逆,濁氣上逆還可表現為面部或頭發油膩、身體異味、口氣重、舌苔白膩,以及常見外耳道油膩、眼屎多等,也可作為診斷胃食管反流病的輔助指征,同時這也解釋了一些現代醫學難以闡明的胃食管反流病的臨床表現。
除結合癥狀、體征診斷外,我們還可通過背部督脈穴位壓痛探查進行輔助診斷。?素問·繆刺論?載:“邪客于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脅而痛,刺之從項始,數脊椎夾脊,疾按之應手如痛,刺之傍三痏,立已。”臟腑疾病通常會反映到相關經脈的穴位上,尤其是背部的膀胱經和督脈穴位,按壓這些穴位可能會使患者感覺舒適、病證減輕或局部疼痛,可以此作為診斷疾病的參考依據,并且這些反應點也是最佳的刺激部位。吳齊飛等[4]在臨床試驗中發現,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在督脈背段T3~12棘突下有明顯的規律性壓痛,T5~8棘突下的壓痛閾值較低,最低點為T7棘突下(至陽穴),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態勢。在這些部位采用針刺治療后,胃食管反流癥狀明顯改善,并且穴位壓痛閾值隨之升高[5],其他學者的研究也驗證了這一點[6]。鑒于此,筆者建議將督脈背段T3~12棘突下壓痛探查作為胃食管反流病的常規輔助檢查,特別是可作為疑似胃食管反流病的初步篩查和鑒別診斷。
對于胃食管反流病,西醫擅長迅速準確地發現典型病例,同時能夠排除器質性問題,但對于微反流的診斷不明確,難以給予此類患者及時準確的治療;中醫長于診斷及辨證治療微反流,但對于器質性病變的排除較為困難。因此,胃食管反流病的診斷,需要發揮中西醫各自的優勢。對于有反流表現同時伴有吞咽困難、嘔血、短時間內體質量下降明顯等癥狀的患者,必須先行西醫檢查;對于無典型反流癥狀,疑似反流但檢測結果為陰性的患者,要發揮中醫的優勢,同時對中醫調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患者,也應該進行檢查,排除食管裂孔疝等器質性病變。
2 病機:重新詮釋中醫經典理論
慈禧之病長時間治療無效,與辨證錯誤導致的用藥錯誤有很大關系,而辨證錯誤的原因與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理論有關,主要包括五臟與五味及五官、肺與咽喉、臟腑與脊背,以及子午流注理論。這些理論本身并無問題,但有其適用范圍。在胃食管反流病的病機分析上,我們應該把握其核心病機——中焦脾胃氣機失調,聚焦其本身“病”的特點,先正確辨病,再辨其證型,不應囿于不適用的經典理論。下文筆者將逐一進行分析。
首先,五臟與五味、五官理論是中醫經典理論之一,對認識人體臟腑與五味、五竅之間的關系及指導疾病診斷和用藥都有很大影響。從慈禧病案看,咽喉或口中五味是影響其生活質量的主要癥狀,馬文植[7]對其病機的分析為“五味出于五臟,臟有虛熱,蒸騰于上,而出于喉,故喉間有此氣味”,代表了太醫們的觀點。如果從胃食管反流病發生的機制看,咽喉及口腔的這種異常味覺顯然是胃內容物上溢的結果,是濁氣上擾清竅的表現,與五臟無關。明·張景岳對此有正確的認識,?景岳全書·卷二十一·吞酸?載:“吞酸之與吐酸,證有三種:凡喉間噯噫,即有酸水如醋浸心,嘈雜不堪者,是名吞酸,即俗所謂作酸也。此病在上脘最高之處,不時見酸,而泛泛不寧者是也。其次則非如吞酸之近,不在上脘,而在中焦胃脘之間,時多嘔惡,所吐皆酸,即名吐酸,而渥渥不行者是也。又其次者,則本無吞酸吐酸等證,唯或偶因嘔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諸不堪之味,此皆腸胃中痰飲積聚所化,氣味每有濁惡如此,此又在中脘之下者也。但其順而下行,則人不覺,逆而上出,則喉口難堪耳。”依據五臟開竅于五官的理論,慈禧的鼻、眼、耳癥狀,分別與肺、肝、腎有關,但從解剖結構上看,五官與胃的關系更為密切。口腔連通食管,而鼻腔與口腔直接相通,耳與眼分別通過咽鼓管和鼻淚管與口腔和鼻腔相通。當胃中濁氣沿著食管上溢至咽喉和口腔時,就會影響這些器官,符合李東垣“胃氣一虛,耳目口鼻俱受病”理念。臨床上,除上述病證外,胃中濁氣上溢口腔,長期刺激口腔黏膜還會導致口腔潰瘍反復發作,侵蝕牙齦和牙齒則會導致牙周炎、牙蝕癥、牙齒松動等。
其次,依據傳統理論,咽喉為肺之門戶,與肺關系密切,但從解剖上看,胃與咽喉的關系更加密切。?靈樞·憂恚無言?載:“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重樓玉鑰?載:“夫咽喉者,生于肺胃之上。咽者咽也,主通利水谷,為胃之系,乃胃氣之通道也。”咽喉是胃中濁氣上溢的必經之地,臨床上咽喉反流是常見的反流類型。在慈禧病案中,咽喉部的癥狀占比居第1位,癥狀表現也多種多樣,除咽喉五味外,還有咽喉黏膩不爽、咽干、咽痛等。臨床上,梅核氣也是一個與咽喉有關的病證,西醫稱為癔球癥,中醫常辨證為氣郁痰阻,但實際上有許多梅核氣患者是由胃中濁氣上逆所致。由于喉向下與氣道和肺相通,當胃中濁氣上行受到會厭阻擋后,會沿著氣道向下,最終直達肺臟,慈禧病案中的咳嗽、咳痰都與此有關。由于反流通常發生在臥位,所以反流引起的咳嗽具有夜間咳嗽或晨起咳痰的特點。除上述癥狀外,肺為嬌臟,不耐邪侵,更不耐胃中濁氣侵襲,反流物刺激咽喉會導致喉痙攣,出現類似哮喘的表現,嚴重者可因喉痙攣窒息而亡。倘若反流物(尤其是氣態物)長期刺激肺臟,則會導致慢性阻塞性肺氣腫、肺纖維化等一系列嚴重后果。
再次,?難經·六十七難?曰:“五臟募皆在陰,俞皆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也。”一般認為,陰病是臟病,會反映到后背(陽);陽病是腑病,會反映到腹部(陰),所以推導出臟病要治背,腑病要治腹。實際上,該篇章是專門講述五臟的俞與募,與六腑無關,正如清·葉霖?難經正義·卷五論穴?所說:“?內經?六腑亦有募有俞,不獨五臟為然也。此章明臟腑陰陽之氣,交相通貫,言五臟而不及六腑者,省文也。”五臟六腑皆有背俞穴和腹募穴,六腑也與后背密切相關。慈禧病案中,脊背部癥狀占第2位,主要表現為脊背熱、脊背忽涼忽熱,還有少數脊背涼。在古代醫案中,除張仲景有“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的論述,還有許多胃脘病導致脊背寒涼的記載,茲舉3例,如“背為陽位,心為陽臟。心之下,胃之上也。痰飲竊踞于胃之上口,則心陽失其清曠,而背常惡寒。納食哽噎,是為膈癥之根。蓋痰飲為陰以礙陽故也”[8]。又如“背筋常冷,胸腹有塊,時吐酸水。此寒痰阻于胃而太陽之氣不宣,溫之通之”[8]。再如“(內傷胃脘痛)痛極應背,背心一片如冰,惡心,嘔吐痰涎稍緩,此痰飲癥也”[9]。臨床上,除上述脊背熱或寒涼等異常,胃腑病還會放射至后背,表現為背痛。如葉天士?種福堂公選良方·卷一?云:“脈右弦,脘痛映背,得嘔痛發,氣鳴痛緩。乃胃氣少降,寒暄七情,皆令痛發,病屬肝胃。”又如?王旭高臨證醫案?載:“頭眩心悸,脈沉弦者,飲也。病發則嘔吐酸水,滿背氣攻作痛,得噯則痛松,此濁陰之氣上攻陽位。當以溫藥和之。”[8]除主觀癥狀外,臟腑疾病還可在后背特別是督脈循行部位表現出壓痛或結節等客觀體征,不但可以輔助診斷胃食管反流病,還可根據“以痛為腧”的原則,選取這些反應點作為本病的重要治療部位。
最后,子午流注的問題。子午流注理論是將氣血在人體十二經脈內流動與一天十二時辰相對應,是中醫天人相應理念的具體體現。按照這個理論,氣血在十二經脈內各盛1個時辰,用以指導選擇適當時間及穴位治療疾病,也被用來解釋一些癥狀的發生機制。巧合的是,多數反流都發生在夜間,而且不同患者或同一患者在不同階段,反流具有一定的規律性,患者的癥狀會在相對固定的時間點出現,如定時覺醒、定時咳嗽、定時脊背發熱等。這種規律出現的臨床現象容易與子午流注理論聯系起來,尤其當覺醒出現在凌晨3—5點并伴有咳嗽時,則容易誤認為與肺有關。
綜上所述,五臟與五味及五官、肺與咽喉、臟腑與脊背,以及子午流注理論的不當應用影響了太醫們對慈禧病證基本病機的把握,錯誤辨證,錯誤用藥,導致慈禧病情遷延不愈。這提示我們在臨床診療過程中,不能受限于經典理論,在重視采用中醫傳統理論辨證的同時,更要注重胃食管反流病本身“病”的特點,才能進行正確的診斷和治療。
3 辨證:正確理解胃食管反流病的熱與寒
在困擾慈禧的病證中,脊背發熱、脊背忽涼忽熱和脊背涼表現十分突出,太醫們在辨證上認為脊背熱屬陰虛、脊背涼屬陽虛、脊背忽涼忽熱屬陰陽兩虛,但依法治療又不奏效。事實上,這種脊背部涼熱的表現其實是因郁而致。不通則痛為人們所共知,但不通能生寒生熱卻容易被忽略。同一胃食管反流病患者表現出來的寒與熱,看似對立,但實質都源于脾胃之氣郁結中焦。這種寒熱表現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寒熱交替或夾雜出現。中焦不通導致的寒與熱可能是時而發熱,時而寒涼,或是忽涼忽熱,最后一種情況像瘧疾,故又稱“如瘧狀”。?諸病源候論?載:“宿食不消者,由五臟氣虛弱,寒氣在于脾胃之間,故使谷不化也。舊谷未消,新谷又入,脾氣既弱,故不能磨之,則經宿而不消也。令人腹脹氣急,噫氣酸臭,時復憎寒壯熱是也,或頭痛如瘧之狀。”噫氣酸臭是典型的反流表現,病機是脾胃虛弱不能消化食物導致胃排空延遲。?清宮醫案集成?記載,光緒帝也患有胃食管反流病,癥狀較慈禧典型,也有寒熱交替的現象[10]。光緒帝曾詢問應徵御醫力鈞這種寒熱交替出現的現象是否為瘧疾,如果不是瘧疾,兩者有何不同。力鈞說:“寒熱往來,原為瘧疾現象,但瘧疾有定期或一日一發,或二日一發,或三日一發,其因皆由內熱與外寒相拒,或瘴氣由口鼻入,或飲食停積不化一起便有欲嘔之象……此癥比瘧疾更重,蓋瘧疾尚是外因,可用表破,內傷之體只宜和解,血氣稍調,即須補固。”[10]力鈞的回答基本反映出兩者的根本區別,瘧疾是外邪,發有定時;胃食管反流病的寒熱屬內傷,發無定時。
第二,寒熱常在夜間發作。中焦不通導致的寒熱發作時間一般是陣發而非持續性的,往往突然發生。特別是常發生在夜間,可因膳食、勞累、陰雨天氣誘發;噯氣、捶背等可緩解,甚至排便后也會減輕,此即?靈樞·經脈?所說的“得后與氣,則快然如衰”。慈禧病案中的脊背發熱都具備這些特點,所以寒熱發作的時間若呈現出如上特點,那么高度提示是胃食管反流中焦阻滯不通導致的寒熱。
第三,寒熱發作的部位集中在上腹、胸骨或脊背部,還可表現為內熱外寒或上熱下寒。胃食管反流中焦不通導致的寒熱有可能發生在上腹或胸骨后,這種情況與一般胃食管反流所描述的胃灼熱發作部位相同。在慈禧病案中,僅有2次附骨作熱,更多的表現來自脊背部,包括脊背熱、脊背忽涼忽熱和脊背涼,此外還有身肢發熱(31次)、脅肋串熱(14次)、掌心發熱(11次)、腰間作熱(10次)、腹中串熱(6次)、足心發熱(3次)。臨床所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主訴的燒灼感可分布于胃脘部、胸骨后、咽喉、口腔、鼻腔和后背,甚至有人會有周身燒灼感[11]。
此外,還有內熱外涼或上熱下涼。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記載:“患者自述背脊常冷,心腹中熱,視面黃色奪,問食少不美。”正是內熱外涼的情況。清·王孟英診治一女性患者,秋季患胃脘痛,進食加重,向后背放射,痛如針刺,自行按壓痛處則涌水苦辣,經治療后“唯晚食則脘下猶疼,疼即心熱如火,且面赤頭痛,腿冷腰酸,必俟脘間食下則諸恙皆平”,此屬于上熱下寒[12]。
同樣還有內傷發熱。陰虛生內熱是大家熟悉的情況,但因郁滯不通所致的發熱則容易被忽略。李東垣“甘溫除大熱”就是治療因郁滯不通導致發熱的經典治法。因其夜間發熱,加之手足心熱,很容易被誤辨為陰虛發熱,如?臨證指南醫案?載:“暮夜熱熾,陰虛何疑。”又因其涼在脊背,而辨為督脈陽虛。事實上,胃食管反流病的寒熱現象是清濁之氣痞結不通的結果,本質是脾胃氣虛,脾氣不能升,胃氣不能降,痞結于中焦。因此,治療上既不能滋陰,也不能溫熱,更不能寒涼。李東垣之所以把外感與內傷進行對比,原因之一就是兩者都有寒熱表現,一個在表,一個在里。?脾胃論?載:“陰虛生內熱,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為內熱。”此處的陰虛當指脾。脾為陰,胃為陽,陰虛就是脾氣虛,內熱是因脾氣虛,導致清陽與濁陰升降失序,郁而為熱,治當以甘溫除大熱。而所謂“溫”也非溫補之義,而是溫養,溫養脾胃,脾胃健則熱自消、寒自散。正如葉天士注解?黃帝內經?“勞者溫之”時強調:“病是勞傷陽氣,陽衰不主流行,清濁升降不得自如,是為虛痞之結。?內經?謂勞者溫之。此溫字,乃溫養之稱。”葉天士解釋說:“溫非熱藥,乃溫養之稱。甘補藥者,氣溫煦,味甘甜也。”
綜上所述,胃食管反流中焦不通導致的寒熱發病部位分布廣泛,還可能有內熱外寒和上熱下寒的情況出現,治則上可參考甘溫除大熱之法。
4 治療:重視非藥物治療特別是針灸的作用
在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療方面,無論西醫還是中醫,藥物治療都是常用的手段。中藥治療胃食管反流病的特色與優勢有目共睹,特別是在辨證準確的基礎上,與西醫抑酸治療相比,中藥在療效和安全性上都有優勢。2017年,中華中醫藥學會脾胃病分會發布了?胃食管反流病中醫診療專家共識意見?[13],介紹了中醫藥可以通過降氣和胃以抑制胃氣上逆,通過疏利肝膽以緩解膽汁反流引起的癥狀,通過健脾和胃以改善脾胃功能、促進胃排空等。中醫因其辨證與辨病結合,整體與局部兼治,可以彌補現代醫學對難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癥狀重疊等治療方案的不足,減少長期服用西藥帶來的不良反應。
在慈禧病案中,也都是采用藥物治療,其所選用藥材之道地、炮制煎煮之守法堪稱一流,但卻乏效。究其原因,與不當用藥及長期用藥有較大關聯。藥物直走腸胃,化學藥物對胃腸的不良作用明顯,中藥也是如此,使用不當或長期使用也會損害胃腸。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位在胃,但藥物大多伐胃,可能間接損害脾胃,從而降低臨床療效。臨床療效不佳,患者繼續服藥,進一步耗傷脾胃,造成惡性循環。慈禧病案頭緒極多,諸癥之間又相互矛盾,辨證不明導致錯誤用藥,又由于治療無效而不得不長期服藥。脾胃不但是氣血生化之源,也是口服藥物得以吸收并發揮作用的前提,因此用藥時尤其要重視固護脾胃。如果長期用藥,甚至不當用藥,勢必損傷脾胃,這也是慈禧之病久治不愈,并且越治療癥狀越嚴重的原因。
鑒于藥物治療問題較多,故筆者認為采用藥物治療胃食管反流病的同時,應重視非藥物治療方法,尤其是針灸。胃食管反流病本質上屬于胃腸道動力障礙性疾病,針灸的作用重在一個“調”字,通過刺激機體內在固有的機制調整臟腑的失衡狀態,在調整胃腸道動力障礙方面有明顯優勢。具體取穴時,筆者建議選取督脈背段T3~12棘突下穴位及非穴位。經臨床驗證,這種治療方法效果好,且取穴簡便,適合普及與推廣。既往由于對“陽病行陰,陰病行陽”的誤解,并由此推導出“陽病治陰,陰病治陽”的選穴思路,取腹募穴治療腑病,以及取六腑下合穴等,如?胃食管反流病中醫診療專家共識意見(2017)?[13]推薦針灸中脘、足三里等穴位治療胃食管反流病。實際上,背部督脈經穴對胃食管反流病的作用更直接,胃腑病會放射到后背部,而撫摩、捶背可緩解胃脘不適。?臨證指南醫案·卷四·胸痹?記載:“胸前附骨板痛,甚至呼吸不通,必捶背稍緩,病來迅速,莫曉其因。”根據癥狀特點可以判斷是反流引起的胸骨后疼痛,并且因反流物刺激咽喉導致喉痙攣而出現呼吸困難,通過捶打背部可以暫時緩解,但這種現象讓葉天士感到困惑不解。即便如此,也不影響他對后背的重視,針對風寒引動宿邪的痰飲癥,葉天士提出:“法當暖護背心,宿病可卻。”?景岳全書·卷二十五·括沙新案?還詳細記錄了給其夫人刮拭后背治療急性脘腹痛的經歷:“乃擇一光滑細口瓷碗,別用熱湯一盅,入香油一二匙,卻將碗口蘸油湯內,令其暖而且滑,乃兩手覆執其碗,于病者背心輕輕向下刮之,以漸加重,碗干而寒,則再浸再刮,良久,覺胸中脹滯漸有下行之意,稍見寬舒,始能出聲。頃之,忽腹中大響,遂大瀉如傾,其痛遂減,幸而得活。瀉后得睡一飯頃,復通身瘙癢之極,隨發出疙瘩風餅如錢大者,不計其數,至四鼓而退。”他接著寫道:“愈后細窮其義,蓋以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向下刮之,邪氣亦隨而降。凡毒氣上行則逆,下行則順,改逆為順,所以得愈。雖近有兩臂刮痧之法,亦能治痛,然毒深病急者,非治背不可也。”雖然張景岳刮痧所治病證不是胃食管反流病,但總屬消化系統疾病,且具有相似病機。張景岳的刮痧療法值得學習,依據異病同治的原則,在后背刮痧對胃食管反流病應該同樣有效。
胃食管反流病并非不可治之證,慈禧之病在太醫們的精心調理下,歷時1年仍未見效,與醫者對疾病的判斷及選擇的治療方法有很大關系。?景岳全書·卷一·十問篇?載:“醫之為難,難在不識病本而施誤治耳。”清·喻嘉言對此有更明確的闡述:“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后議藥,藥者所以勝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歧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況于性最偏駁者乎。”[14]胃食管反流病臨床表現復雜,只有輔以現代醫學知識才能對其有正確認識,如果囿于一些傳統中醫理論,很容易被表象迷惑。在治療方法上,除了藥物,太醫們也別無選擇。遍覽已經整理出來的清宮醫案,僅康熙朝有1例針灸治驗。1822年,道光皇帝以“針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為由,廢除了太醫院的針灸科,從此皇室成員未再體驗針灸之宏效。
5 結語
光緒六年(1880年)慈禧患病持續診治時間之長、參與太醫人數之多、選用藥材之道地,還有周全的起居、膳食護理,在清宮醫療史上都堪稱之最,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本文系統研究了光緒六年的慈禧病案,通過對病證的系統梳理,推斷慈禧所患疾病的西醫病名與中醫病機,并分析治療失敗的原因。慈禧病證分布范圍廣,面、眼、口、咽喉、耳、鼻、頭項、心胸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不適,納食、睡眠、大小便也不佳,尤以咽喉、脊背、胃脘部的癥狀較多。結合這些主要癥狀的發作特點,筆者認為慈禧所患病證是1例非常典型的以食管外癥狀為主要表現的胃食管反流病,中醫基本病機為中焦脾胃氣機失調。而治療無果的原因,有太醫辨證錯誤的問題,有藥物使用不當及長期服藥的問題,也有慈禧不配合醫生診治、不遵醫囑等自身原因,當然也有太醫們求全自保及互相掣肘的原因。
中醫既要守正,更要創新,發揮長處,融匯新知,才能為世界醫學發展作出貢獻。通過仔細研讀慈禧病案,筆者認為這是一個以食管外癥狀為主的胃食管反流病典型案例,對認清胃食管反流病的復雜性具有重要意義,并且對當今診治胃食管反流病具有重要啟示作用。①胃食管反流病的診斷必須中西醫各取所長,一方面要利用先進的現代醫學檢查方法,并借助解剖知識了解胃食管反流病復雜多樣的臨床表現,另一方面要發揮中醫對疾病征象整體把握的優勢,重視那些西醫看起來與胃食管反流無關,但從中醫角度看卻很有價值的癥狀和體征,特別是那些因微量濁氣上逆導致的諸多征象,同時結合穴位壓痛的探查,確保胃食管反流病診斷準確。②重新詮釋一些中醫理念,如五臟與五味及五竅、臟腑與脊背、肺與咽喉、子午流注等理論,有些錯誤觀點需要糾正,有些雖然正確,但通過西醫理論會得到更好的解釋。③辨證上要牢牢把握中焦氣機升降失調的基本病機,特別是對因清濁之氣痞結中焦所導致的復雜寒熱征象,還有濁氣上逆導致的諸多食管外表現,避免對疾病性質的誤辨。④發揮中醫非藥物治療尤其是針灸的優勢,避免不當用藥或長期服用藥物對胃腸造成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