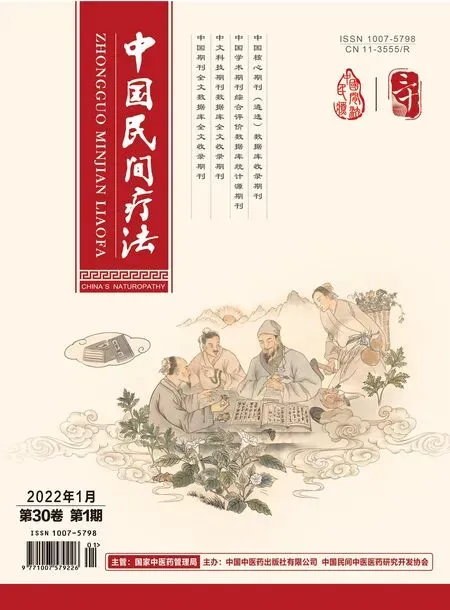針藥結合的源流及其應用特點※
楊婷婷,王若禹,田岳鳳
(山西中醫藥大學,山西 晉中 030619)
針藥結合是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針對患者臨床表現辨證論治,同時運用針灸和中藥兩種方式以達到防病治病的方法[1]。自古以來,針藥結合治療疾病的方法受到歷代醫家的重視,同時他們對于針藥結合的理論及臨床應用也流傳至今,其內容成熟豐富,可供后人參考學習。
1 歷代醫家的認識及應用
1.1 兩漢時期 成書于西漢時期的?黃帝內經?是中國針灸醫學發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標志著戰國秦漢時期針灸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理論。在?黃帝內經?中有關于針藥結合治療疾病的理論。?素問·移精變氣論?曰:“毒藥治其內,針石治其外。”“病形已成,微針治其外,湯液治其內。”首次強調了針灸和中藥在治病時各自的優勢,在針對疾病施治時提出了臟腑病需要中藥治療,而外在疾病則選用針灸治療,在早期為人們提供了針藥結合應用的理論指導。
東漢時期,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是針藥結合的經典書籍,被譽為“方書之祖”。張仲景的杰出貢獻對中醫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張仲景認識到針灸和中藥在應用時均存在局限性,有些疾病單用一種方法效力不佳,故在明辨病機基礎上將針灸和中藥相結合,二者合用,相得益彰[2],故在?金匱要略?中提出“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針藥,治危得安”的治療原則[3],書中也詳細記載了關于針藥結合治病的臨床醫案。
在治療疾病時,張仲景踐行針藥結合理論,如急性熱病易于傳變,以針藥同施則能快速取效。?傷寒論?曰:“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愈。”介紹在治療太陽經病時,由于風邪太盛,對于疾病而言僅用中藥治療效果甚微,遂加以針刺風池和風府,針藥結合應用則病愈。這一醫案對臨床醫生有較大的啟示,當單一方法治療疾病效果不佳時可以嘗試將針灸和中藥結合,以提高其臨床療效。
1.2 唐宋時期 針灸醫學在該時期進入繁榮階段。唐·孫思邈所著?備急千金要方?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臨床醫學百科全書,書中記載的內容收集分析了唐代以前中國醫學的重要內容,經過系統總結給后世醫家以啟迪。
孫思邈認為施治要求針、灸、藥3種療法必須兼備,在應用中須講究權變,靈活運用,相輔相成,真正掌握每種方法的精髓要點才能達到治療效果。?千金翼方?曰:“若針而不灸,非良醫也;針灸而不藥,藥而不灸,亦非良醫也;知針知藥,固是良醫。”明確指出良醫應同時精通針灸和中藥,這是判斷是否為合格醫生的一個標準。孫思邈認為針灸和中藥應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是其重要內容之一[4]。書中所記載的醫案也多處涉及其重要思想內容,?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針對瘡癰腫的治療應“刺中心至痛,又刺四邊十余下令血去,去血敷藥,藥氣得入針孔中佳”。現代臨床在治療瘡癰腫也是使用此法,治療效果較為顯著。
孫思邈強調辨證后施以針灸和中藥,發揮各自所長。在治療疾病時,孫思邈總結出“若治諸沉結寒冷病,莫若灸之宜熟;若治諸陰陽風者,身熱脈大者,以鋒針刺之,間日一報之;若治諸邪風鬼注,痛處少氣,以毫針去之,隨病輕重用之”的治療依據。孫思邈的這一思想也體現在醫案中,講述了針對不同原因導致的疾病所需治法不同,適宜的方法會對疾病的治療事半功倍。
宋·王執中推崇孫思邈的針藥結合理論,也提倡作為一名良醫要同時精通針灸和中藥,不可偏廢任何一方。對于只知曉其一便行醫治病者,違背了孫思邈的思想理論。在?針灸資生經?中,王執中設立了關于針灸和中藥結合應用的專篇論述[5],在繼承孫思邈理論的同時也在不斷踐行針藥結合的方法。?針灸資生經?曰:“凡身重不得食,食無味,心下虛滿,時時欲下,喜臥,皆針胃管、太倉,服建中湯及平胃丸。”“有人久患反胃,于以鎮靈丹服,更令服七氣湯,遂立食,若加以灼艾,尤為佳也。”王執中在選方用藥時會針對疾病的具體表現進行調換配伍,注重針藥結合,以提高治療效果。
1.3 金元時期 這一時期針藥結合的代表人物為李東垣及其弟子羅天益。針藥結合應用也成為李東垣針灸學術思想的一大特色。李東垣在針灸方面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針灸聚英??針灸大成?稱之為“東垣針法”。
“東垣針法”或針或灸,或針藥并用[6]。?脾胃論?卷下清陽湯中涉及中風病,辨證后針對風中經絡證予以針藥結合治療。一患者表現為口,頰腮緊急,適宜燔針治療以通其滯,若患者不愿意使用燔針,則以清陽湯代替。一患者表現為前陰燥臭,根據其連日飲酒的表現給予龍膽瀉肝湯治療,在足厥陰肝經上利用瀉行間以祛濕熱,后又在手少陰心經上瀉少沖,治療后疾病痊愈。臨床應用中應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靈活選用針或藥治療疾病。
羅天益師從李東垣,在繼承東垣脾胃學說的同時吸收諸家經驗,編寫了?衛生寶鑒?,書中多處提及針刺與中藥需配合使用。?衛生寶鑒·風痰治驗?中詳細描述了風痰致病的表現及治療。如參政楊公忽然感到眩暈眼黑,伴有心煩、嘔吐、偏頭痛及足冷等癥狀,羅天益認為此證屬風痰內作、上熱下寒,故先用三棱針在頭面腫處點刺放血以泄上熱,后針對風痰表現服用天麻半夏湯,治療幾日后患者痊愈。在治療風痰時考慮到寒涼中藥對老年人的影響,而針刺的優勢可避免這一問題,二者的結合實為良選。?衛生寶鑒·北方腳氣治驗?中以三棱針針刺患處并配合服用當歸拈痛湯治療,效果顯著。羅氏的理論和臨床醫案記錄較全面,其內容對后世醫家在臨床上針藥并用時起到借鑒作用。
1.4 明代時期 針灸醫學在明代達到昌盛,楊繼洲所著?針灸大成?是對明代之前針灸醫學的再次總結,對中國針灸醫學影響深遠。?針灸大成?中論述了針、灸、藥并用的理論,并提出“針灸藥者,醫家之不可缺一”“針、灸、藥皆為醫家分內事”的觀點,認為疾病位置有腠理、血脈、腸胃之分,當疾病所處腠理之時艾灸為最佳選擇,若疾病在血脈時只有針刺才可取效,疾病在腸胃則用中藥治療較好,故針、灸、藥三者缺一不可[7]。楊氏醫案中提及一患者手臂不舉案,患者表現為惡寒體倦,夏天著棉衣,經多位大夫診斷后均認為是虛寒之象。楊繼洲脈診后表示脈象沉滑,認為痰處于經絡,予針刺肺俞以調和表里,針刺曲池、足三里以祛邪化痰,治療后感覺手臂可舉,不惡寒且脫去棉衣,此時再投除濕化痰之劑,痊愈后未復發。另一患者為瘡疾,連日服藥后反而日漸消瘦,楊繼洲針刺患處,并艾灸章門穴,再服用蟾躲丸藥,經治療后其形體逐漸壯實,瘡疾痊愈。醫案中可以體會到楊氏對于針藥結合并用的重視,以針刺調經絡,以湯藥治其里[8]。
這一時期的醫學家吳崑也注重針藥兼施,其認為:“針藥二途,理無二致。”在臨證時需要針藥配合兼施治療,善于針對不同經脈的疾病表現而施治。在其所著?針方六集?中提及帶脈、足少陽膽經、陽維脈和手少陽三焦經的病證,宜刺足臨泣、外關二穴,使表里和,營衛流暢,并可配用三化、雙解、大小柴胡、通圣、溫膽諸方治療。沖脈、足太陰脾經、陰維脈、足陽明胃經和手厥陰心包經的病證,宜刺公孫、內關二穴,使經氣運行無阻,三焦通暢則內部調和,并可配用瀉心、涼膈、大小陷胸、調胃承氣諸方治療[9]。吳崑不僅對所列經脈進行劃分,而且對所有經脈施治涉及的針灸和中藥均有詳細闡述,在歷代醫家論述基礎上,吳崑加以學習并從經脈理論角度作為切入點,強調針藥結合的重要性。
1.5 清代及近代 針灸在清代逐漸出現了衰退趨勢,以李學川為主要代表的醫者認為當時的醫家過多注重中藥的使用,而對于針灸的應用不再重視,針和藥的分離對針灸醫學的發展不利,故提倡二者應左右逢源。
?針灸逢源?曰:“舉湯液以翼針道,明刺法以濟湯藥。”要達到左右逢源就需用針灸配合中藥醫治。在半身不遂的治療中,強調要根據疾病所在經絡進行針刺,同時予以補血養筋的方藥;治療牙床腐爛,在針刺基礎上服用清胃瀉火中藥;治療眼生翳膜,除針刺外要用退翳的中藥輔佐使用[10]。李學川運用湯藥輔助針灸的功效,或用針灸方法使湯藥的療效更佳。在針灸醫學衰退的時期,李學川的理論與實踐對于振興針灸事業具有一定的意義。
發展到近現代,名老中醫秦亮甫認為:“針、灸、藥,醫者缺一不可。”治療小兒遺尿時,根據病因病機特點認為要治療遺尿首先要治氣,治療思路要考慮疾病與肺的關系,治療原則也要體現溫腎、縮尿、益氣等方面,針刺關元、中極、百會等遺尿基本用穴,湯藥以金櫻縮泉方服之[11]。秦亮甫在臨床上注重分析病因病機,從疾病根本入手治療。在秦伯未編著的?中醫臨證備要?中,近半病證是以針藥并用[12]。在?傷寒論新注?中,針灸名家承淡安闡述了針灸療法及處方,其創立了傷寒針刺法,成為系統應用針灸與中藥的典范[13]。臨床實踐中在六經辨證的基礎上針藥并用,精于針而略于藥。根據六經的特點,病在太陽時,針刺風池、風府后服生姜紅糖湯;治陽明經熱證,針刺陽明經上的穴位并給予白虎湯清熱生津。六經患病的臨床表現均有差異,需要選擇適當的治療方案。承淡安在臨床實踐中以針刺為主,輔以湯藥的治療方法比單一針刺效果更顯著。
2 針藥結合的效應優勢
針灸和中藥結合時產生的效應優勢如下:針藥間的相互協調作用;針灸可減輕中藥的不良反應;中藥對針灸的輔助作用。二者結合使用是提高臨床療效的可取方法[14]。
針藥結合已經是現代治療疾病較常見的一種方式,其次現代醫學的滲透使針藥結合也有了新發展。如常見的穴位注射是用特定針具將藥物注射在相應治病點以達到治療效果的手段,是針藥結合的一種新型體現方式,豐富了針藥結合的內容[15]。中醫在現代西醫影響下分科越來越精細化,辨證施治時也大多攻于本專業,中醫專業以方藥為主,而針灸專業重于針刺,這些做法沒有繼承到各代醫家的理論精髓,且在治療疾病時會使療效受到影響,但是部分醫家仍在大力提倡應用針藥結合治療疾病,并在一些疑難雜病的治療中取得了滿意的效果,充分說明了針藥合用的優越性,同時也彰顯了中醫治病的獨有特色。
3 小結
針藥并用不僅是針灸與中藥的簡單結合,而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依據臨床表現辨證施治,攻其要點,二者的結合絕不可隨意堆砌,每一次的施治均要考慮主次、時機、方法、用量和時間等方面。醫者針對疾病可針、可灸、可藥,真正了解其優勢應用才可達到應有的療效。針藥結合的效應優勢要借臨床方可體現,希望這一理論能得到不斷繼承和完善,為中醫藥事業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