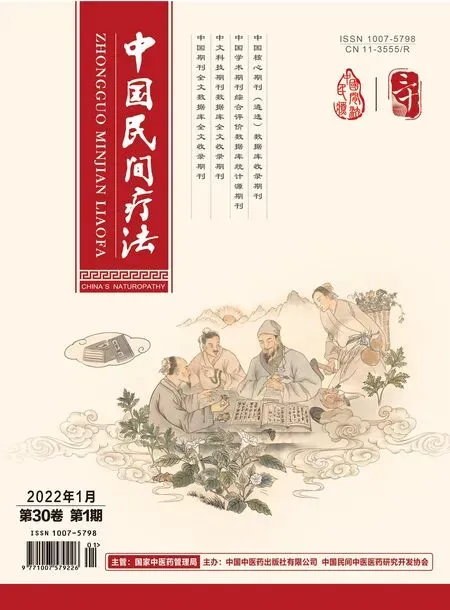鄒偉運用調神通陽針刺法治療脊髓炎驗案
杜云鵬,鄒 偉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鄒偉教授是全國百名杰出青年名中醫,龍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西醫結合重點學科帶頭人,黑龍江省領軍人才梯隊帶頭人,黑龍江省重點腦病專科帶頭人,從事中西醫結合神經內科學臨床與教學工作數十年,擅長運用針刺療法治療各種疑難雜病。筆者有幸跟師學習,受益匪淺,現將鄒偉教授運用調神通陽針刺法治療脊髓炎的經驗介紹如下。
1 病案舉例
(1)患者,男,15歲,2019年6月25日初診。主訴:雙下肢麻木無力1個月余。1個月前患者勞累后出現雙下肢無力,左手、腹部、雙足麻木,雙下肢痛溫覺障礙,就診于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行頸椎MR I檢查示:C2~5椎體水平脊髓異常信號,考慮為脫髓鞘病變;行胸椎MR I檢查示:T2、T4椎體水平脊髓內信號不均,考慮為脫髓鞘病變。診斷為脊髓炎。給予注射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等藥物治療(具體用藥不詳)。用藥3周后,腹部麻木及雙下肢痛溫覺障礙好轉,其余癥狀未見明顯改善。因家屬擔心藥物不良反應,遂至我科尋求針刺治療。癥見:雙下肢麻木無力,左手麻木,納食可,夜寐較好,小便頻數、清長,大便調,舌質淡嫩、苔白,脈沉弱而遲。查體:四肢肌力5級,雙下肢膝腱反射活躍,雙下肢肌張力增高,粗測淺感覺正常,巴賓斯基征(±)。西醫診斷:脊髓炎。中醫診斷:痿證,證屬腎陽虛型。治以調神通陽,濡養肌肉。取穴:百會、四神聰、水溝、風池(雙側)、天柱(雙側)、足三里(雙側)、陽陵泉(雙側)。操作方法:患者取坐位,穴位皮膚常規消毒后,選用0.35mm×40 mm一次性毫針,在百會、四神聰以45°角沿頭皮自前向后斜刺,直達帽狀腱膜,以200r/min以上頻率小幅度捻轉1min,產生酸麻脹感后留針;在水溝向鼻中隔方向斜刺5mm,用重雀啄法,以眼球濕潤為度;在風池向鼻尖方向進針25~30mm,在天柱向下頜方向進針15~20mm,得氣后均予捻轉平補平瀉法;足三里、陽陵泉均直刺30~40mm,得氣后予捻轉補法,留針50min。每日1次。
治療2周后,患者自述雙下肢麻木無力有所緩解,小便頻數、清長,大便調,舌質淡嫩、苔白,脈沉弱而遲,繼續予以上述針刺方案治療。治療4周后,患者肢體麻木已不明顯,肢體力量明顯增強,舌質淡、苔白,脈沉。復查頸椎MR I示:頸椎椎體序列良好,生理曲度變直并輕微反向彎曲,C2~6節段內頸髓增粗,T2信號稍增高,不均勻;胸椎 MR I檢查示:T7~12節段內脊髓環形稍高信號,脊髓未見明顯增粗或變細改變,椎旁軟組織未見腫脹;腰椎MR I檢查示:腰椎生理曲度略變直,腰椎椎體形態、信號未見異常。治療5周后,患者癥狀已不明顯,舌質淡、苔白,脈沉。查體:雙下肢膝腱反射正常,雙下肢肌張力正常,雙下肢巴賓斯基征(-),能正常學習和生活。隨訪3個月,患者狀態良好,無復發。
(2)患者,女,55歲,2019年10月16日初診。主訴:雙下肢麻木無力半年余。半年前患者過度勞累后突然出現雙下肢自肢體遠端向上麻木無力,右側明顯,麻木范圍逐漸擴大至腹部,無頭痛、頭暈等不適,就診于當地醫院,行胸椎MR I示:T7~9椎體水平脊髓背側偏右異常信號,考慮脫髓鞘病變。診斷為脊髓炎,予以營養神經、擴血管等相關治療(具體藥物及藥量不詳),患者病情略有改善,又輾轉多家醫院,經多方治療病情好轉,但雙下肢仍有麻木無力,今來我科尋求針灸治療。刻下癥:雙下肢麻木無力,行走遲緩,納可,夜寐良好,小便失禁,大便正常,舌胖嫩,苔白膩,脈沉遲。查體:雙側上肢肌力5級,雙側下肢肌力4級,雙下肢肌張力增高,雙下肢膝腱反射活躍,雙側巴賓斯基征(+)。西醫診斷:脊髓炎。中醫診斷:痿證,證屬腎陽虛型。治以調神通陽,養肌固攝。取穴:百會、四神聰、水溝、風池(雙側)、天柱(雙側)、足三里(雙側)、陽陵泉(雙側)、陰陵泉(雙側)、三陰交(雙側)。操作方法:患者取坐位,穴位皮膚常規消毒后,選用0.35 mm×40mm一次性毫針,在百會、四神聰以45°角沿頭皮自前向后斜刺,直達帽狀腱膜,以200r/min以上頻率小幅度捻針1min,直至患者產生酸麻脹感;在水溝向鼻中隔方向斜刺5mm,用重雀啄法,以眼球濕潤為度;在風池向鼻尖方向進針25~30mm;在天柱向下頜方向進針15~20m,在足三里、陽陵泉、陰陵泉直刺進針30~40mm,得氣后予捻轉補法;在三陰交沿脛骨內側緣與皮膚成45°角斜刺,進針25~30mm,用提插補法,以下肢抽動、麻電感向陰部擴散為度。留針50min,每日治療1次。
治療1周后,患者雙下肢麻木有所緩解,但仍無力,行走緩慢,小便失禁,大便正常,舌胖嫩,苔白膩,脈沉遲,繼續針刺治療。治療3周后,患者肢體麻木減輕,肢體無力感緩解,行走緩慢,小便失禁,舌胖嫩,苔白膩,脈沉遲。治療4周后,患者無肢體麻木,肢體無力明顯緩解,行走略緩,小便失禁好轉,舌淡,苔白,脈沉遲。治療5周后,患者肢體無力明顯減輕,行走尚可,小便基本可控,舌淡,苔白,脈沉,去陰陵泉、三陰交穴,囑患者自行進行排尿反射、提肛運動等排尿功能訓練,并繼續針刺1周以鞏固療效。治療6周后,患者肢體無力感基本消失,舌淡,苔白,脈沉。查體:四肢肌力5級,肌張力正常,雙下肢膝腱反射正常,雙側巴賓斯基征(-),復查胸椎MR I:T7~9節段脊髓背側偏右稍高信號,脊髓未見明顯改變,已恢復正常生活。隨訪3個月,患者狀態較好,未復發。
(3)患者,男,50歲,2020年9月15日初診。主訴:右側肢體活動不靈活伴麻木3個月余。患者3個月前過度勞累后摔倒出現右側肢體癱瘓,當時無頭暈頭痛、視物不清,無飲水嗆咳,無噴射性嘔吐,由救護車送至當地醫院。行顱腦MR I示:未見明顯異常;頸椎MR I示:C3~6水平脊髓變性;胸椎MR I示:未見明顯異常。以“急性脊髓炎”收治入院,予以激素沖擊、營養神經治療(具體藥物和用藥量不詳),癥狀緩解后出院。此后右側肢體活動不靈活伴麻木,右手、前臂溫度覺喪失,出院后靜脈滴注營養神經藥物,未見明顯好轉,遂來我科尋求中醫治療。行頸椎MR I示:頸髓內異常信號影,考慮炎性改變。刻下癥:右側肢體活動不靈活伴麻木,步態不穩,右手、前臂溫度覺喪失,納可,夜寐尚可,大小便正常,舌胖嫩,苔薄白,脈遲緩無力。查體:C3~6頸椎棘突間及兩旁壓痛(+),直接叩擊痛、間接叩擊痛(-),左側上、下肢肌力5級,右側上、下肢肌力4級,肌張力未見異常,右手、前臂溫度覺喪失,右側肢體腱反射亢進,右側霍夫曼征(+),右側巴賓斯基征(+)。西醫診斷:脊髓炎。中醫診斷:痿證,證屬腎陽虛型。治以調神通陽,通經活絡。取穴:百會、四神聰、水溝、風池(雙側)、天柱(雙側)、足三里(雙側)、陽陵泉(雙側)、極泉(雙側)。操作方法:患者取坐位,穴位皮膚常規消毒后,選用0.35mm×40mm一次性毫針。在百會、四神聰以45°角沿頭皮自前向后斜刺,直達帽狀腱膜,以200r/min以上頻率小幅度捻轉1min,直至患者產生酸麻脹感;在水溝向鼻中隔方向斜刺5mm,用重雀啄法,以眼球濕潤為度;在風池向鼻尖方向進針25~30mm,在天柱向下頜方向進針15~20mm,在足三里、陽陵泉直刺進針30~40mm,得氣后予捻轉補法。極泉在原穴位置下1寸心經上取穴,避開腋毛,直刺進針12~25m m,用提插瀉法,以上肢有麻脹感和抽動為度。留針50min,每日治療1次。配合皮膚針輕度叩刺督脈背部穴位,3d治療1次,注意消毒。
治療2周后,患者肢體麻木較前好轉,右手、前臂溫度覺喪失稍有改善,但右側肢體活動仍不靈活,行走不穩,納可,夜寐尚可,大小便正常,舌胖嫩,苔薄白,脈遲緩無力。繼續針刺治療。治療4周后,患者肢體麻木明顯好轉,右手、前臂溫度覺喪失明顯改善,右側肢體活動不靈活已有所改善,步態不穩,納可,夜寐尚可,大小便正常,舌淡,苔薄白,脈遲緩無力。治療5周后,患者無肢體麻木,右手、前臂溫度覺基本恢復,右側肢體活動明顯改善,步態不穩,納可,夜寐尚可,大小便正常,舌淡,苔薄白,脈遲。治療6周后,患者右側肢體活動較靈活,基本可平穩行走,右手、前臂溫度覺恢復,納可,夜寐尚可,大小便正常,舌淡,苔薄白,脈遲。停止皮膚針叩刺,繼續針刺治療1周以鞏固療效。治療7周后,患者癥狀已基本消失,查體:左側上、下肢肌力5級,右側上、下肢肌力4+級,肌張力未見異常,右手、前臂溫度覺正常,腱反射正常,已基本恢復正常生活。隨訪3個月,患者狀態良好,自述無復發。
2 討論
脊髓炎導致的肢體麻木無力,屬于中醫“痿證”范疇。本例患者素體陽虛,加之勞累,日久則腎臟陽氣更虛,腎陽溫煦不能,則肢體筋脈功能失調,故肢體痿軟無力,逐漸加重,發為該病。?素問·痿論?云:“治痿獨取陽明。”?類經?云:“醫必以神,乃見無形,病必以神,血氣乃行,故針以治神為首務。”鄒偉教授認為,腦為元神之府,腦神主宰人體一切生命活動,百病皆始于神散。調神主取督脈之穴,督脈入絡腦,關聯諸筋,而經筋聯絡四肢百骸,遍布周身,主司運動,可通過調督治療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相關運動類疾病[1]。
針刺督脈能直達脊髓損傷病所,既能培補真陽,又可疏通經氣,使上下經氣通達,陽氣通達全身以調整陰陽之氣。針刺能明顯減輕和延緩脊髓損傷后早期病理損害,抑制炎癥細胞因子的表達,改善局部血液循環,減輕炎性水腫,改善神經賴以存活的內環境,提高神經存活率,對髓內一氧化氮合酶(NO S)等神經遞質、生長相關蛋白GA P-43的表達具有良性調整作用,可減輕和延緩初期繼發性損害的發生,促進受損脊髓神經的修復[2-3]。再結合足三陽經選穴,三陽并舉,相輔相成,通陽補陽,故能生效。
調神通陽針刺法是鄒偉教授對調神針法與通陽法的綜合運用,主要通過針刺督脈及足三陽經穴位以調神醒腦、通達陰陽氣血[4]。鄒偉教授臨床常用此法治療痿證、痹證等多種疾病,對于陽虛證型效果顯著,在運用時取穴首重督脈及足三陽經,并按病情酌情選用其他經穴,督脈穴調神達陽,足三陽經穴通陽養神,二者相互為用,可加強調神通陽之功。在針刺時手法、深度量化,使氣至病所,協調陰陽氣血,提高療效。在痿證等疾病治療上,鄒偉教授認為醫者要注重自身調神和調患者的神,并在此基礎上重視通陽補陽,以此恢復臟腑、肢體的功能,故運用調神通陽針刺法。?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氣功能正常,全身陽氣充盈通暢則內可養神,外可柔筋,更能促進肢體功能恢復。在通陽穴位選取上,?素問·陰陽離合論?云:“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故應三陽并重,以足三陽經穴充分激發三陽經開、闔、樞的不同功效,溝通表里經氣,調暢陰陽氣血,更好地發揮通陽作用,臨床治療效果較好[5-6]。
治療以上3例患者時,鄒偉教授均以百會、四神聰、水溝為主穴,以足三陽經風池、天柱、足三里、陽陵泉為配穴的調神通陽針刺法為主,又根據病情不同在調神通陽基礎上適當加減穴位,如出現小便失禁時,針刺陰陵泉、三陰交,以調補肝、脾、腎,充養髓海,疏通下肢經絡,調控膀胱功能;上肢活動不靈活時,針刺極泉以疏通上肢經絡;溫度覺喪失時,用皮膚針叩刺督脈背部穴位以興奮交感神經,并通過刺激皮膚痛覺神經末梢,經神經反射過程,糾正體內異常變化,使其平衡協調,從而達到改善患者溫度覺及肢體麻木癥狀的作用[7]。現代研究表明,百會穴對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表現為改善腦血流量、增強記憶力、營養神經、修復神經元等[8]。四神聰為奇穴,前后神聰在督脈循行路線上,左右神聰緊臨膀胱經,膀胱經絡腎,督脈貫脊屬腎,絡腎貫心,其氣通于元神之府,故可調治元神之府所致之疾病,具有健腦調神、調理脊髓之功。水溝為督脈與手足陽明之會,督脈統督諸陽,手足陽明又為多氣多血之經,故調神醒腦、通調氣血的作用較強。四神聰、水溝引五方渙散之神聚結于三陽五會之所,督脈“入絡腦”引神歸原,貫脊通全身,調神通陽。風池為足少陽經、陽維脈交會穴,可調奇經而理頭部經絡之氣血、陰陽之盛衰。天柱穴歸屬足太陽膀胱經,主“開”之用,可通行氣血,疏通氣血津液運行,以滋潤濡養腦府,調神通絡。足三里為足陽明胃經穴,位于宗筋所在之處,行“闔”之能,可調節宗筋功能,疏通陽明經氣,補陽以化生氣血、養神柔筋,健脾化源以充養氣血,并疏通下肢經絡。陽陵泉為足少陽膽經合穴、筋會,起“樞”之功,可調節肢體筋脈,是故調神通陽,痿證自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