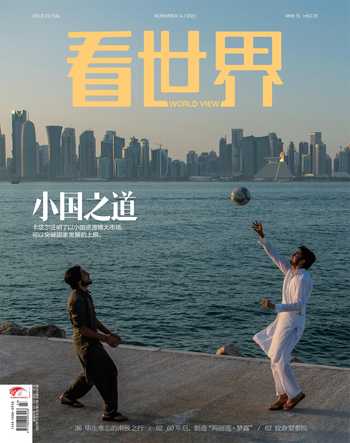我在袖珍島國被颶風正面暴擊
徐曉燕

多米尼克,左邊是加勒比海,右邊是大西洋
同在北美加勒比海地區,英聯邦國家多米尼克(The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是講英語的彈丸島國,卻容易與講西班牙語的大島國多米尼加共和國(The Dominican Republic)混淆。我把前者稱作“小多”,把后者稱為“大多”。英國前首相約翰遜10月回國爭奪相位之前,就是在“大多”度長假。
其實“小多”風景也不錯,曾被英國《國家地理旅行者》評為“2021年世界最佳探險地”之一。2017年,筆者親歷過一夜之間把“小多”幾乎夷平的颶風瑪麗亞。這個只有七萬多點人口,以嘉年華、克里奧美食和地熱溫泉著稱,卻農礦資源匱乏、經濟欠發達的東加勒比袖珍島國,如何在風災之間生存與發展?
由于原住民印第安加里納戈人的頑強抵抗,小多是最后一個被歐洲人殖民的加勒比島嶼。它輾轉于英法之手,最終于1763年落入英國手中。215年后,小多脫離英國獨立。
小多國土面積為751平方公里,2/3的土地被雨林覆蓋,擁有九座活火山(最近一次在1997年噴發)。這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活火山群。
因其河流、瀑布、山脈、森林和火山等多元地貌及優美的海岸景色,小多被譽為“自然之島”。它擁有加勒比地區首條野生長途徒步步道(全長183公里)和世界上第二大沸騰湖。島上居民主要為黑人和黑白混血種人,另有加里納戈人、白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幾十年來,多米尼克的經濟依賴于香蕉等蔬果出口,旅游業方興未艾。
由于經濟發展不足,小多島民中,年輕人很多外流到鄰近的更發達島國(如巴巴多斯)或美國打工定居,留下的大部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每家院前屋后都種了果樹,海邊住戶都有漁船和能打魚的男人。

多米尼克首都羅索
小多是最后一個被歐洲人殖民的加勒比島嶼。
該國新房屋都以混凝土屋頂取代以前便宜但脆弱的木瓦結構屋頂。
在首都羅索(Roseau)的周末農貿集市,農民開小貨車來賣貨買貨,各式農產品五彩斑斕,本土歌樂聲“混合”叫賣招呼聲,很是熱鬧。
在沒有風暴、戰爭的和平時期,歌舞俱佳的小島,實在是個風景好、吃得好、玩得好的世外桃源。然而,颶風惡魔一直在半空對小多張牙舞爪,近年來還愈演愈烈。
大西洋颶風季通常從6月1日持續到11月30日。在這幾個月里,熱帶風暴最有可能在加勒比海地區形成,并造成嚴重破壞。
八九月是小多的颶風季。1979年,五級颶風“大衛”造成小多島上超過40人死亡、2500人受傷,6萬所房屋被毀。1980年颶風“艾倫”又來襲。進入千禧年,風災更頻繁。
2017年,五級颶風“瑪利亞”造成小多95%的建筑物受損或被摧毀,島上99%的地區失去電力供應,超過5萬人流離失所,65人喪生,損失約13億美元(相當于小多GDP的226%)。

2018年5月9日,多米尼克總理羅斯福·斯凱里特在首都辦公室審查文書
彼時我在多米尼克居住。根據預報,大家已做好了迎風準備。但瑪利亞的強度前所未有,以撕裂山河、搗碎地球的憤怒凄厲肆虐小島。
半夜時,她夾帶暴雨闖進了我在半山的家門。雨水不知從哪里滲進來了,我們猛地淘水,水勢還是蔓延浸沒客廳至半腿深。最后我累得睡著了……相信因為房屋是新建的混凝土結構,才幸而沒被颶風掀翻。
第二天醒來,風已退卻水也沒了,望出去卻是滿目瘡痍,昔日美麗的綠島紅瓦,一夜之間蕩然無存:整個山上樹木橫倒,露出蒼涼的土黃肚皮,山下的首都羅索像剛大戰完的戰區般倉皇凌亂,標志性的木結構紅屋頂幾乎全被卷走,暴露著光禿禿的框架。
下山得攀爬過高大的倒樹,蹚過被泥水淹的路面。人們都在家門口邊討論災情,邊收拾殘局。我還遇到了一大隊拖著行李箱要徒步前往首都的中國建筑工人。
接下來,島上居民要經歷持續多天的由東加勒比聯軍負責的宵禁(因為島內外交通中斷導致農工商停頓、食物短缺而產生了搶掠超市、店鋪的事件,就連泡過水的食物也被哄搶一空)。由于互聯網、電信和水電中斷,人們只好互助共度時艱。
在印度籍經理的幫助下,我依靠星級酒店幸存下來的網絡與外界聯系;與當地人一起頂著亮星月光走過山頭,去山泉里洗澡洗衣;在槍聲之下,去羅索向維持秩序的聯軍求取瓶裝水;之后幸運地吃上了中國使館聯系中餐館安排的,為在體育館避難的中國工人而設的“大鍋飯”,直至坐上了撤僑船轉移到安提瓜島,再輾轉紐約回港澳。
在小多經歷過“瑪利亞”后的狼狽和震撼,我深深感受到氣候變化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對袖珍小國的堅忍和屢次重建更是同情和敬佩。在颶風襲擊后第五天,多米尼克總理羅斯福·斯凱里特在聯合國痛心疾首地說:
“我從氣候變化大戰的前線幸存而來……過去,每年我們會準備應付一個強風暴。現在,是每年有數千個強風暴形成……接踵而至以最暴烈的強力打擊我們……我們加勒比人不產生溫室氣體或硫酸鹽氣溶膠。我們不污染海洋或過度捕魚。我們對全球變暖沒有絲毫的進獻。但我們是前線的主要受害社群!”


2017年9月28日,五級颶風“瑪利亞”造成多米尼克95%的建筑物受損或被摧毀
颶風災害給迷你小島國多米尼克造成的不僅是人命、財產損失,還有心理和精神上的創傷。一些人選擇離開,更多人留下,有自愿的,也有無奈下將就的。
事實上,在颶風襲擊的2017年,多米尼克GDP下降了6.77%;2018年和2019年,或歸功于重建的拉動,GDP反而分別上升了3.72%和5.5%;2020年,受疫情影響,GDP大幅下降16%。
災后的五年中,政府采取多管行動。議會于2018年通過《氣候韌性法案》,隨后創立多米尼克氣候韌性執行署,以建設世界上第一個氣候韌性國為目標,尋求綠色可持續發展。政府對此態度樂觀并積極宣傳。根據筆者做的幾個采訪,島民大多肯定了政府在扶持氣候韌性方面的舉措,特別是提供免費建筑部件扶助居民修補受災房屋。
在建設避難中心之余,政府還宣傳購買房屋保險,推廣建設防颶風的氣候韌性新房屋。該國新房屋都以混凝土屋頂取代以前便宜但脆弱的木瓦結構屋頂。
這個被風災多次打擊、經濟單一滯后的小島國,雄心巨大卻資源極有限,力量非常單薄。雖然國際組織及一些國家都有撥款支持其抗災發展,也是杯水車薪,長貧難顧。
201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多米尼克政府達成協議,與其他發展伙伴一起支持其制定實行《災害韌性戰略》,旨在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同年,英國通過加勒比發展銀行資助改善島上供水設施項目;中國援建了島內的多個醫療中心;古巴一直助力醫療服務;委內瑞拉則提供低價燃油。
淡水之外,多米尼克沒什么工業產品可賣出去。怎么突破局限,主動爭取發展呢?多米尼克人決定“賣”島:多米尼克島是東加勒比的瑰麗明珠,把整個島嶼視為產品,可在踏上抗氣候災難旅程的同時,大力發展生態旅游業,再以其產出反哺本土建設發展。
靠本國庫房稅收支撐發展根本無可能,多米尼克早于1993年立法推出投資入籍計劃,2015年又作出修改:合資格投資者向政府經濟多元化基金(EDF)捐款10萬美元,或者購買投資入籍局認可的房地產項目里20萬美元以上的房產,即可快捷獲得該國公民身份和護照。
以低稅收、投資保密、“美國的第二家園”等吸引投資者,以投資入籍項目的資金進行災后重建,該國把移民帶來的資金用于建設能源設施、住房、醫療中心、學校等。
多米尼克《太陽報》一篇文章提醒說:“一個島國GDP損失15%~20%后,能輕易恢復嗎?因此,當多米尼克人記得瑪利亞颶風來襲的恐怖時,他們也必須警惕多米尼克已經從瑪利亞颶風中完全恢復的錯誤觀點……事實是,復蘇、真正的復蘇,需要幾十年的持續行動。”
今天,小島國在我們面前示范氣候變化受害者的生存狀態;明天,問題又會怎樣蔓延呢?作為地球公民,我們真的要做出反思與行動。
責任編輯何任遠 hr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