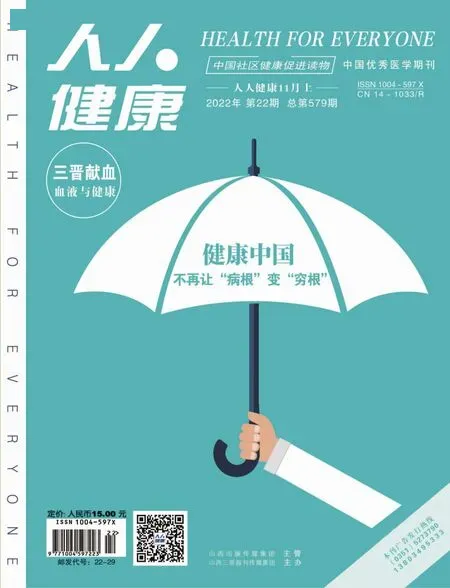健康中國不再讓“病根”變“窮根”
主筆/ 傅昭儀
在過去的數年間,我國開展了世界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并在減貧脫貧道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2021 年2 月2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舉行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布,中國的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這一勝利來之不易,因為要想擺脫絕對貧困,需要涉及方方面面。當問及什么是制約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發展的最大“瓶頸”時,你會想到什么?也許是沒有資金支持,缺乏經濟產業;也許是教育文化程度低,缺乏脫貧致富的知識技能;也許是基礎設施不足,缺乏便利的交通線……但其中最不可忽視的,也許是健康問題導致的因病致貧。
有人說,一場重大疾病,往往能摧毀一個中產家庭,更遑論低收入的貧困人口。對于貧困百姓而言,“病”比“窮”更為可怕,尤其是“大病致貧”所帶來的沉重打擊。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很可能花光全家的所有積蓄,而當他們因為“疾病纏身”無法從事生產生活時,也就更難擺脫貧困,這無疑是一場無法承受的災難。“再窮也不能得病,得病也不敢進醫院”成了貧困家庭最常見的心態。
據人民網報道,2015 年底國務院扶貧辦摸底調查顯示:當時全國7000 多萬貧困農民中,因病致貧的有42%;因災致貧的有20%;因學致貧的有10%;因勞動能力弱致貧的有8%;其他原因致貧的有20%。由此可見,健康問題導致的“因病致貧”已經成為貧困百姓心中最大的“病根”。
沒有健康的體魄,一切都將歸零。“因病致貧”不僅成為健康中國的“短板”,更是制約精準扶貧、實現全面小康的瓶頸。所以,在我國扶貧開發針對扶貧對象的總體目標“兩不愁,三保障”中,將保障基本醫療列為基本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更深入實施健康扶貧工程,幫助貧困人口“拔病根”“拔窮根”。
全面消除醫衛空白點
“病有所醫”是構建幸福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健康扶貧首先要保障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基本醫療需求,讓老百姓能看上病。
2019 年1 月,國家衛生健康委會同國家醫保局、國務院扶貧辦,對全國832 個國家級貧困縣和建檔立卡貧困村開展了全面的排查。排查發現,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還有46 個鄉鎮沒有衛生院,666 個衛生院沒有全科醫生或者執業(助理)醫師,其中80%集中在“三區三州”(“三區”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四省藏區;“三州”是指甘肅的臨夏州、四川的涼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深度貧困地區。1022 個行政村沒有衛生室,6903 個衛生室沒有合格的村醫,其中53%集中在“三區三州”;1495 個鄉鎮衛生院、24210 個村衛生室沒有完成標準化建設。
為了全面消除鄉村醫療衛生機構和人員“空白點”,改善醫療機構設施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累計安排1795.5 億元,支持貧困地區所在省份的15萬個醫療衛生機構項目建設,對貧困地區建設項目“應納全納”。并通過“縣管鄉用”“鄉聘村用”以及巡診、派駐等方式,歷史性地解決了部分地區基層缺機構、缺醫生的問題,基本實現農村群眾公平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同時提升脫貧地區縣級醫院服務能力,推動優質資源向貧困地區傾斜并逐級下沉,組織1007 家城市三級醫院對口幫扶832 個脫貧縣的1172家縣級醫院,實現每個脫貧縣至少有1 家公立醫院,98%的脫貧縣至少有1 所二級及以上醫院。城鄉醫療服務能力差距不斷縮小。
如今,我國已全面消除鄉村醫療衛生服務“空白點”貧困縣,消除了46 個鄉鎮無衛生院、1022 個村無衛生室的“盲區”,消除了666 個鄉鎮衛生院無執業醫生、6903 個村衛生室無村醫的“空白點”。
確保貧困百姓“看得好病”
健康扶貧要在建檔立卡數據基礎上,因戶因人因病精準施策。近年來,我國組織動員了全國80 多萬名基層醫務人員,對貧困人口的患病情況進行了全面摸底排查,一戶建一檔案,建立了全國健康扶貧動態管理系統,對貧困患者實行分類救治,推動措施落實到人、精準到病。
在建檔立卡數據基礎上,我國專門針對貧困人口實施了大病專項救治計劃。2016 年,國家衛健委在安徽、貴州等8 個省區啟動了農村貧困人口大病專項救治試點,先期將兒童先天性心臟房間隔缺損、食管癌、胃癌等9 種大病納入救治范圍,使患病的貧困人口能夠大病不出縣,大大降低了他們的經濟開支。近幾年,國家衛健委聯合有關部門,不斷擴大病種范圍和覆蓋地區,2020 年又將膀胱癌、卵巢癌、腎癌、重性精神疾病及風濕性心臟病5 個病種,納入貧困人口大病專項救治范圍。至此,已有30 多個病種納入農村貧困人口大病專項救治范圍。截至2020 年12月,全國需要大病集中救治的患者460 萬人,已經救治455 萬人。
與大病、重病相比,慢病最容易被忽視,一旦控制不好,極易轉為高危疾病。2017 年,在國家衛健委的部署下,啟動了家庭醫生慢病簽約管理服務,為慢病貧困人群提供規范的慢病管理服務,制訂個性化健康管理方案。家庭醫生在完成日常診療和健康管理服務的同時,還會承擔預檢分診、流行病學調查、宣傳教育等工作。
“互聯網+醫療”也在健康扶貧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遠程醫療打通了患者就診的最后一公里,使得層層疊疊的山脈不再成為醫療保障的阻隔,解決了貧困人口看病遠、看病不方便的問題。
此外,重點地區重點疾病防控也取得歷史性成效。到2020 年年底,重點地方病實現監測全覆蓋,大多數地區的地方病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或消除。
織就最大醫療保障網
健康扶貧,除了要讓貧困百姓“看得上病”,還要確保他們“看得起病”。

白族姑娘和秀娟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蘭坪縣人,因為患有骨結核病,8 歲時腰上長出一個籃球大小的鼓包,被人稱為“蝸牛姑娘”。想要治療骨結核病,最少需要十幾萬元,這對本身就家庭貧困的她來說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建檔立卡貧困戶后,和秀娟可以享受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和醫療扶助四重醫療保障“一站式”就醫服務,再無需擔心費用問題。2019 年,經過2次手術、住院4 個月,她終于卸掉背在腰上14 年的“蝸牛殼”。治療骨結核病所需的173920.66 元醫療費用,“一站式結算”報銷了167814.65 元,她自己只需支付6106.01 元。當地民政局、紅十字會還為她申請了3000 元臨時生活救助。
手術之后,和秀娟高興地發現自己居然悄悄長高了10 厘米。她說,自己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名醫生,幫助家鄉更多的父老鄉親。
為實現讓貧困人群“看得起病”這一目標,使他們不再因為擔心醫療費用而放棄治療,我國設立了醫療救助、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三重保障,對貧困人口給予更多的政策傾斜。并努力使這三項制度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覆蓋,進一步完善兜底保障機制,提高救助水平。堅決防止農村貧困群眾因醫療費用問題得不到及時醫治的情況發生,并減輕困難群眾和大病患者醫療費用負擔,防范因病致貧返貧,筑牢民生保障底線。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農村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進行整合,全面建立了城鄉統一的居民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制度,構建起更加公平統一的醫療保障制度。
10 年來,我國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由5.4億增加到13.6 億,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基本醫療保障網,報銷比例持續提高,居民醫保的人均財政補助標準由240 元提高到610 元,惠及10 億城鄉居民。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穩定在95%以上,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分別為80%和70%左右,醫保基金年收支均超2 萬億元,惠及群眾就醫超40 億人次。
大病保險在基本醫療保險的基礎上,對大病患者發生的高額醫療費用給予了進一步保障。即在基本醫療保險報銷后,個人符合規定的自付費用再按一定幅度給予第二次補償。
到2015 年年底,大病保險覆蓋了所有城鄉居民醫療參保人群,也就是所有城鄉居民都能在享受基本醫療保險的同時享受到大病保險的保障。
2002 年,我們國家首次提出了在農村建立醫療救助制度,并明確了救助對象主要是農村貧困家庭。2005 年建立了面向農村、城市的醫療救治制度,并逐步于2009 年整合為城鄉一體化醫療救助制度。
到2018 年5 月,隨著國家醫保局成立,民政部的醫療救助職責整合至國家醫保局,進一步形成了城鄉醫療救助體系。根據國家醫保局統計數據,2021年,25 個原承擔醫保脫貧攻堅任務的省份共資助8519.72 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支出176.69 億元,人均資助207.40 元。
根據數據顯示,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醫療救助三重制度累計惠及農村低收入人口就醫1.23 億人次,減輕醫療費用負擔1189.63 億元。
經過數年的奮斗,我國終于全面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基本醫療有保障,累計分類救治2000 多萬人,幫助近1000 萬個家庭成功擺脫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高價藥不再觸不可及

電影《我不是藥神》劇照
2018 年,一部影片《我不是藥神》刷爆朋友圈,引起了公眾的熱議。該片改編自真實案件:主人公陸勇被檢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醫生推薦他服用一種叫作格列衛的藥物。但這種藥品的國內售價是23500 元一盒,每月需服用一盒,再加上治療費用,普通家庭根本不能承受。一個偶然的機會,陸勇得知印度生產的仿制“格列衛”一盒僅售4000 元,且藥性相似度99.9%,便開始服用仿制“格列衛”,并在病友群里分享了這一消息。隨后,很多病友讓其幫忙購買此藥,人數達數千人。2014 年7 月,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銷售假藥罪對陸勇提起公訴。但極具戲劇性的是,陸勇的多名白血病病友聯名寫信,請求司法機關對他免予刑事處罰,網友也近乎“一邊倒”地支持陸勇。2015年1 月,沅江市檢察院向法院請求撤回起訴,陸勇最終被無罪釋放。
“陸勇案”和《我不是藥神》展現了現實中病患生存的矛盾與困境,再次將“高價藥”“看病貴”等話題引入人們的視野。這個難題該怎樣破解?就如電影里最后幾幕,這個事件引起了國家的重視,從2015 年開始,一些省份將格列衛納入醫療報銷,最高可以報80%,讓患者們都可以吃上正版藥、放心藥。
2018 年11 月,中央審議通過了《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試點方案》。隨后,開始在全國4 個直轄市和7 個副省級城市進行帶量采購試點,簡稱“4+7”。從此,藥品提質降價成為醫衛戰線的“主旋律”。
帶量采購,即國家集采,是由國家醫保局從通過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藥品中遴選品種和原研藥,把全國醫療機構零散的采購量集中打包,形成規模團購效應,通過國家層面與藥品生產企業進行價格談判,大幅降低藥品虛高價格,減輕患者負擔。
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開展了六批藥品帶量采購,共計234 種藥品,包括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和常見病的主流用藥,也包括高價抗癌藥、原研藥等,3 年多來累計節約費用2600 億元以上。以腫瘤藥物吉非替尼為例,集采前價格為132 元一片,集采后降至41.8 元,再經醫保報銷后,原本每年4.7 萬元的治療費患者個人僅需承擔約0.6 萬元。
對于重大疾病、罕見病患者所需藥品難以買到、難以報銷的問題,我國則實行國家醫保談判藥品政策,通過談判降價將藥品納入目錄,最大限度滿足患者需求。
加強健康教育,提升疾病預防
2021 年3 月23 日,正在福建考察調研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三明市沙縣總醫院實地了解醫改惠民情況。他指出:“人民的幸福生活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健康,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沒有1,再多的0也沒有意義。”
除了讓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我國也著力于推動從以治病為中心轉向以健康為中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將“預防為主”作為健康工作方針,加強疾病預防控制,在貧困地區全面實施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農村婦女增補葉酸預防神經管缺陷、農村婦女“兩癌”(乳腺癌和宮頸癌)篩查、兒童營養改善、新生兒疾病篩查等項目,做到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同時深入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大力開展健康知識普及行動,向公眾推廣宣傳正確的健康觀念,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升個人健康素養。并深入開展貧困地區愛國衛生運動和貧困地區健康促進三年行動,大力推進健康教育進鄉村、進家庭、進學校,實現了健康教育全覆蓋。

志愿者向群眾分發健康知識手冊
畢竟,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讓群眾轉變健康觀念,更加積極主動地去維護自身健康,使更多的人少生病、不生病,才是擺脫“因病致貧”的最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