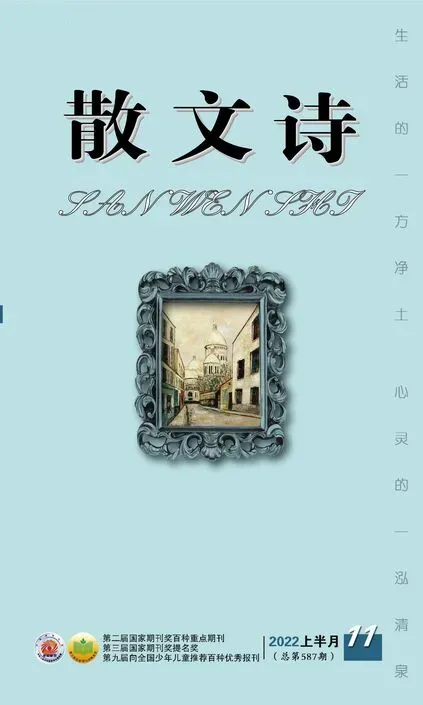未被命名的旅行(節選)
◎張 筱
焉知非福,焉知對錯,焉知成敗,焉知結果。只是向前,向前,再向前!還來不及回味,一生已過半生!
——題記
背負著的依然在背,與20年前仿佛。生命之輕重,由自己掂量。車流,人流,從一處到另一處,反反復復,像上演自己的故事。從高原到南方,或者更北的北方——從去處到來處。
那個指著地球的人,又被我從書堆中抽了出來。是宿命中的一個掛鉤?還是明鏡!我只知道的是,明天早上,我會在另一個陌生的地方——漱洗臉龐。
行旅已經開始!好了,可以合上書望向窗外:天空,大地,樹木,河流;一個又一個站臺,上上下下的旅客。
人們,都在自己的角色中把背景置換。
我的目的地:此列終點站。
一直以來的終點,成為中點,在向往中總是失去向往意味。在此,我只是向故鄉投出一瞥,想想該想的事與人。
我在心里,默默道一聲:再見!
向東,向東。我再次迷失于穿行中:秦嶺密集的隧道,以及撲面而來、迅速逝去的山峰。我想起曾經多次的穿越與反復:每一次有每一次的愿望,每一次與每一次是那么的決絕、不同。
進步,沒有能消解愚昧,這一切從眾生的行為中即可以窺視。在行旅中,我以我的思考來反證、佐證某個事實。
碎片,碎片,還是碎片。無論是景仰還是崇拜,都被自己的冷漠無情撕裂。就這樣,我閉上眼睛,讓碎片在暗黑中無限飛舞!
肉身是重的。即使整列車輕快如一片劃過大地的羽毛,肉身的位置是沉重的。劃過,劃過,劃過的只是留在了身后,它們不同于時間的消逝。于時間,萬物是永恒的化身。
旁邊的人接聽了一個電話,她對母親說:是爸的。唉唉,這一個詞,猛然把我推到一個懸崖。原來,對父親的愛戴,是這樣刻骨銘心。突然地震顫。突然地就淹沒在憂傷中。
異鄉的月亮,又大又圓。飽滿得異常陌生。斗室中,橘子殼做的煙灰缸,盛放寂靜。
一切都是平靜的。異常地平靜著。我開始在地圖上推演地理。
在東四環南路外,一個叫垈頭的地方,在武基路邊,路對面有一條蕭太后河。出去走了走,在這個叫翠城的地方,我先要記住出入的路口,記住樓盤的編號與門牌號。很奇怪的感覺,既不是主,又非客。原來,無論身處何處天涯,皆可入夢。
一些漢語被說舊,失去最初語意,譬如新,只有生命是新的,生活不過是重復。鳥鳴,喇叭聲嘶,日子在重復中,只是翻過去一頁紀年的日歷。并非是非如此不可,是人拋不開習慣。并非如此不可,偶然如間諜刺探時,便是非如此不可。
詩的,接近詩的,非詩的。
為什么非得詩與遠方?真誠,真實的生活,才還原本真生活。
突發,漸進,或者跳躍。這一切都在生命自身,在靈魂范疇之內——人與世界的關系只是如此。在大地漫游,在大地行旅。
這一條河,一條歷史的河被我遇見,早上是邂逅,下午是踏訪,于水天相接處懷古。遼與宋,就這樣在歷史中湮滅,僅留下一些遺存與故事。無疑,我被迷住了。被這些水生植物:青蒲招搖芳華,葦子遍布成濕地主角,水上木棧道若琴鍵,被來去的人輕踩,樂曲在行者心中流淌。我沒有聽清別人的彈奏,我聽清的是自己內心的那曲詩經《蒹葭》之流韻。
云是低的,天是低的,水是低的,人,仿佛一尾魚,在水面上游。蕭太后河,就這樣猝不及防地把我傾倒。這陌生化的場景、情景,每一個轉彎就是一首詩,每一次拐角都是一支歌。少年意氣,青春年華,連同胸臆中的別樣多情,都在游走中釋放。
風物遍眼,芳草連綿,時光輕悠。花朵如蝶群舞,而我卻想尋找莊周的那條魚:順流而下,溯水而上。
盛大,延綿,熱烈。所有的形容詞都不能形容。此景象,在馬蹄寺邊草甸遇見的,它只是廣闊而絕無此延綿;而在甘南草原看到的,卻只是延綿而絕無此熱烈。
5 個小時的負重漫游,它整圃整片盛開!馬蘭花,這與我青梅竹馬的花朵、花簇、花叢,也讓我無端地心花怒放了。
馬蘭花:只有在素園,在那坡頭與山岡,在那河谷與溝渠,才能看見它如此的盛大。那是無處不在的一種親昵。古運河文化長廊,蕭太后河兩岸,數十里長的濱河路,妖嬈的風景中,唯馬蘭花是妖嬈中的妖嬈。這盛大與熱烈,無疑是對春天的謝幕。
人在大地上,彈奏著水藻之舞。柔曼,婀娜,無限的韻律在搖擺中被水擊節,這是一種柔弱的反抗。岸邊的人,若撒網狀,揚臂,甩耙,拽緊尾繩,輕悠悠地拉扯,慢慢把青苔拖離水面。
一個陌生人,一個來自黑河的老哥,在談笑間,一再重復:一擲、一拖、一挑。我突然肅然起敬,向生活,向對生活執著的向往:一擲,一拖,一挑。在復沓與反復中,把生命的重擲拋出一串輕的弧,若虹現,那么美。
另一頭,有釆葦者。儼然從詩經的那首詩中,款款走出。她弄彎葦身,一片、一片釆摘。剛剛立夏,高處的葦葉已漸豐沛,顯現青蔥之美,可以為人所用。而在秋天,這些葦子便“蒹葭蒼蒼”了,那是另一種美。
沿河行走,在粗獷陽剛的美中,贊賞勞動;在青蔥輕柔的美中,懷想光陰的故事。
一個人與另一個,一個男人與另一個女人,他與她是陌生人,我與他及她,都是陌生人。在生命的行旅中,我們各自張望前程。
正午,人跡消失,一個影子也沒有。河水漣漣,凝視著盈盈水波,我突然覺得自己如一個小男孩。不,是長大了的一個老男孩。我的目光中透出好奇,對搖擺的蒲草,對稍微發蔫的鳶尾。當我從桃林邊的桃樹下站起來時,我的目光飄過很遠。
水靜得出奇。連蛙也倦了,偶爾才慵懶地叫一兩聲。此刻,這是被生活遺忘的一個地方,它回歸到了一種純自然狀態。
安靜是暫時的,在這安靜中,卻幻化出一個永恒,被我無意間捕捉。重又坐下。在生活之外,我的心安靜得如同這片水域。是的,除了花、草、樹,除了柔滑如絲的河流,此刻別無所愛。
對岸是高樓,背后是村莊,我置身中間,就像是一座界碑。是的,這半生,我不正是一座移動的界碑嗎?它,總是豎在城與鄉之間。這座碑,會豎多久,會移動多遠,暫且不知,也未知。但,這難道不好嗎?對岸,又來了一家四口,我不由生出不該有的羨慕之心。
墨竹數竿,白墻青瓦,狻肅莊,放眼意趣高古,仿佛逸出于一幀水墨畫卷的細節,若隱廬,又若雪堂。恍然,萬物成一物,風行塵世之上。我看見了狂歡,在草木的精神里,燃燒的綠焰,唱著動聽的歌謠。它們以別具一格的風范,吸引我搖擺。只有肉身,只有行走,我忘了地理。松、竹、梅、蘭,菊花當在秋冬盛開。每一株草,每一棵樹,都是物語天籟,每一段時光都可聆聽。只是,白楊樹的飛揚跋扈,在四月里格外鮮明。
選擇路線,磁器、東四、目的地,7、5、6 號線換乘。從此到彼,彼變成此,復又由此及彼。生活便是如此,才有了拐角,有了往復。有往復,就有了積淀。
寂靜才剛剛被打破,空曠的街顯現素顏,而在地下,那喧囂早就開始。日子、生活、前程,便這樣層層剝開——同時剝開。
離開床榻,離開書桌,把每一次外出都當成旅途。這本來就是:短短的、小小的旅程——懷著喜悅,攜帶著對未知的希望。
中途下車,我不便于到終點站。終點站有通向更遠山川的列車,它可以通到家鄉。而我的終點不遠,在另一個方向,在這座城的西城。我只是換乘復換乘,去探究那個未知。
樹陰下休息,抽煙,對面是國家圖書館。好想去逛逛,只是下午有別的事。只好約聚,等人。人生小小的遺憾,是對面不相逢。
所幸,讀幾首詩吧。我的行囊,如一個小小的書吧,可以隨時滿足我的閱讀需求。習慣使然。再走走吧,去看風景,每一棵樹,每一架花,每一條街,都是風景,且風情別具。
傳奇不易,換成另一段傳奇則更不易。我一直不喜歡傳奇,是其過分幸運的傳奇色彩,這幸運的色彩成功遮蔽了無數苦難。在謬誤與偶然中,成就的一番別的景象,非為傳奇。游走在古舊的遺存中,心才不會生出妄念。
內心奔騰著,如地下鐵的呼嘯。王小波是一個異數,哪天一定要去看看他。沒有去亞運村,沿小月河由南往北漫行,水無關緊要,關鍵是這詩意的名字夠引人入勝。
多么渴望,竟然把一爿月季花,看成是菊,這一光影幻象,讓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行跡。開始懷疑遠方的浪游與過往軌跡。只是路邊的椿樹與落滿地的椿花,令我對人生有了真實的愛意。
行囊,這隨身之物永不饜足:反復填滿,反復排空。如同我的一個物質的替身:有紙質的東西,有碳水化合物,有備用的幾個證件,有一串用或長期不用的鑰匙。它們的組合排列,在不定的周期性中變化:南下,北上;游蕩于東西連線上。它們的腳生在我身上,我的行為就是它們的行為,我的行蹤就是它們的行蹤:旅行,旅居,漫游。它們,一直未曾被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