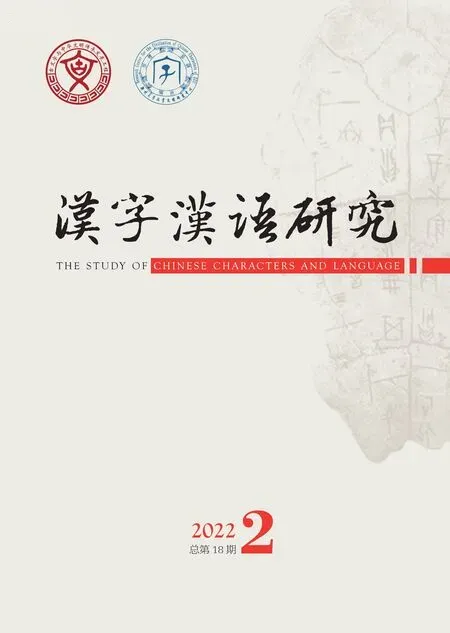文本細讀與乾嘉考據研究*
——以“能不我知”考據為例
符 渝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文學院)
提 要 文本細讀指對文本的結構和語言進行充分解讀,從而挖掘文本內涵。將這種方法引入考據研究,有助于對考據作出全面而客觀的分析和評價。本文以《經義述聞》“能不我知”考據為例,展示如何用文本細讀對一則乾嘉考據進行分析。通過文本細讀,我們將考據的行文結構轉換成內容結構,使考據思路得以彰顯,在此基礎上,細挖隱含于文本中的考據方法、考據思想以及優秀考據背后的科學原理。希望這些嘗試可以促進科學考據學的完善,并為今人的考據實踐提供理論參考。
1.引言
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指對文本的結構、語言等要素進行充分解讀,從而挖掘文本的深刻內涵,實現對文本的意義分析和價值評判,幫助讀者全面把握哪怕是晦澀、繁復的作品。文本細讀也稱“充分閱讀”或“原文詮釋”,最早是文學批評的方法,我們借鑒這種方法,將其運用到考據材料的分析、評價中。
以往對乾嘉考據的研究側重學術源流的梳理和考據方法的總結,缺乏針對具體實例的充分解讀,對考據結構和考據潛理論關注也不多。文本細讀重視結構和語言,有助于實現文本的結構分析,將看似隨意的考據行文轉化成體現操作程序的邏輯結構,有助于重新認識和評價乾嘉考據。比如,乾嘉考據是不是堆砌材料的繁瑣考據?在一則成功的考據中,科學的考據方法是如何運作的,又蘊含著哪些語言學潛理論?
本文以下面一則乾嘉考據材料的研究為例,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嘗試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應。
例:《經義述聞》卷五《毛詩上》“能不我知、能不我甲”(王引之,2000a:129-130)
【A】①考據文本中的【A】【B】【C】等符號,是本文寫作過程中為了閱讀方便而添加的分段編號。《芄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曰:“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二章:“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傳曰:“甲,狎也。”箋曰:“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B1】 引之謹案:《詩》凡言“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B2】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C1】“能”乃語詞之轉,亦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為“而”。【C2】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鄭風·狡童》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與此同意。]②[]內文字,在原書中為雙行小字。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C3】“雖則”之文,正與“而”字相應。【C4】“雖則佩觿,而不我知”“雖則佩韘,而不我甲”,猶《民勞》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C5】[《陳風·宛丘》篇:“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亦于句首用“而”字。]【C6】古字多借“能”為“而”。【C7】[《易·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C8】《荀子·解蔽》篇:“為之無益于成也,求之無益于得也,憂戚之無益于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于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能”并與“而”同。【C9】《管子·侈靡》篇:“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骃《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亦“而”也。]
2.文本細讀與考據結構分析
考據必然有結構,結構體現考據者的思維過程,通過對結構的細致解讀,可以觀察考據者是否有清晰自覺的操作步驟和方法意識。考據結構分為行文結構和內容結構,前者指考據的語言敘述結構;后者指考據的邏輯論證結構,有人稱為“操作程序”或“考據步驟”。
陳剩勇(1990)指出傳統考據方法在某種程度上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首先體現在考據操作程序與形式邏輯的契合上。我們知道,考據操作程序(內容結構)并不都是直接外現的,有時會被外在的行文結構所遮掩,需要運用有效的分析方法來剖析行文結構,顯現其內容結構,然后才能討論它的邏輯性。我們以上引《經義述聞》的考據材料為例,說明如何通過文本細讀將行文結構轉換成內容結構。內容結構的表達,采用王寧(2016:1-2)從清人典范的考據實踐中歸納出的五個考據步驟:發疑、設問(本文稱為“預設”)、取證、釋理、結論。
2.1 文本細讀與考據的內容結構
考據的行文結構見上述考據原文。通過文本細讀,其內容結構如下。
(1)發疑
此則考據的發疑部分是標示為【A】的那一段。此則考據針對鄭箋發疑。鄭箋將“能不我知”解釋為“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為”,將“能不我甲”解釋為“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王引之認為有問題,具體的發疑點有兩個:
發疑①,“不我知”“不我甲”是否可理解為“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
發疑②,“能”是否可理解為“才能”?
(2)預設
針對上述兩個發疑,王引之有兩個預設:
預設①,針對發疑①而設,“不我知”“不我甲”應理解為“不知我”“不狎我”。見【B2】。
預設②,針對發疑②而設,在預設①的基礎上,“能”不可以理解為“才能”,否則“才能不知我”“才能不狎我”語義不通,因此預設②為:“能”是語詞之轉,當讀為“而”。見【C1】。“語詞之轉”“讀為”都是關于通假的訓詁術語,說明王引之認為“能”不是實詞,是虛詞“而”的通假字①后世學者都贊成“能”是通假字,但本字應當是哪個虛字有不同意見。俞樾認為,“能”當訓為“曾”,言此幼稚之君雖則佩觿,而曾不我知也;齊佩瑢(2004:33-34)認為,“曾”是肯定語氣,亦非詩人原意,“能”和“寧”相通,“能不我知”即“怎不我知”,《詩》中問語,多為反言加重之詞,此處依上下文看來,蓋為頌美之意,言童子雖則佩觿而貴,安有忘我之理,贊其不忘故人也。。
(3)取證
取證①,對預設①的語法結構進行取證。見【B1】:“《詩》凡言‘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王引之以《詩經》文例中的三處“不+我+動詞”應理解為“不+動詞+我”,作為證明“不我知”“不我甲”應理解為“不知我”“不狎我”的證據。
取證②,對“能”讀為“而”的取證。見【C2】 -【C9】,包括句旨、語法、字用三類證據。
句旨證據。見【C2】,王引之將“能當讀為而”這一預設代入詩句,重新串解了句旨:“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接著引用“與之同意”的《鄭風·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證明自己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雖則佩韘,能不我狎”的新解釋是合理的,“能讀為而”也就得到句旨上的支持。
語法證據。證據①,“雖”與“而”搭配的證據,見【C4】,《民勞》“戎雖小子,而式宏大”。證據②,“而”用在句首的證據,【C5】《陳風·宛丘》“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與【C4】一樣,都是在下半句的句首用“而”字。
字用證據。上面兩類證據證明了“能”在句旨、語法上可理解為“而”,但“能”和“而”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字,還需要“能”與“而”可以通用的證據。王引之列舉了不同類型的通用證據。①異文證據,見【C7】,《易經》中的“能”有異文作“而”。②通假證據,見【C8】,《荀子》《趙策》中都有借“能”為“而”的句子。③對文證據,見【C9】,《管子》《墨子》《韓詩外傳》《大理箴》中都有“能”與“而”形成對文的句子。此外,王引之的《經傳釋詞》與《經義述聞》有“相輔而行”①錢熙祚《經傳釋詞·跋》:“高郵王文簡公承其家學,所著《經義述聞》,博考群書,辨析經旨,審定句讀、訛字、羨文、脫簡,往往以經證經,渙然冰釋,精確處殆非魏晉以來儒者所及,《經傳釋詞》則與《述聞》相輔而行者也。”(王引之,2000b:107)的關系,其書中“能”字條下也有一例“能”與“而”通用的對文證據:“《晏子春秋·外篇》:‘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王引之,2000b:58)④換用證據,《經傳釋詞》“能”字條下還有一例“能”“而”通用的換用證據:“《管子·任法》篇:‘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下文五‘能’字皆作‘而’。”(王引之,2000b:58)這五句中的“能”字在后文對應的位置都換作“而”字了:“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訴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戴望,1986:257-258)
(4)釋理
釋理是對證據和結論之間的關聯作出理論上的闡釋。此則考據在行文結構中并沒有專門的釋理環節,但我們通過文本細讀,仍可看到王引之的釋理意識。
其一,用賓語前置的語理支持“不知我”“不狎我”的證明。【B1】“《詩》凡言‘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王引之在這里使用了帶有歸納性的表述“凡言……皆謂”,說明他將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式“不+我+動詞”看作一條語言規律。利用《詩經》例句歸納出的語理來演繹證明《詩經》的語法問題,使結論具有了必然性。因此,王引之不但給出了肯定性結論,還對鄭箋進行了明確的否定,即【B2】,“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
其二,用虛詞的語理支持“能讀為而”的證明。王引之(2000a:770)對虛詞無實義有清楚的認識:“善學者,不以語詞為實義,則依文作解,較然易明。何至展轉遷就,而卒非立言之意乎?”他在《經傳釋詞·自序》中指出“能”既有實詞的意義,也有虛詞的用法:“能,善也;而又為詞之‘而’與‘乃’。”(王引之,2000b:2)并對“而”的語法作用和語法位置作了歸納:“而者,承上之詞,或在句中,或在句首,其義一也,常語也。”(王引之,2000b:63)在此則考據中,王引之認為,“能”乃語詞之轉,非“才能”之“能”;“而”與“雖”搭配,用于句首。綜上可見,此則考據中的論述并不只是就事論事的材料類比,而是有著更為宏通的語理支撐:實詞、虛詞的詞匯意義、語法作用不同,不容誤解;虛詞的語法作用、句法位置都有常規,可為具體虛詞的判定提供參考。
其三,用以聲求義破讀假借的語理支持“能讀為而”的證明。王引之在《經義述聞·自序》中提出“訓詁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王引之,2000a:2)首先,“訓詁之旨存乎聲音”,為“能讀為而”提供了透過字形層面還原到語言層面這一最基本的文獻解讀取向。其次,“字之聲同聲近”是文字假借的基礎,這為“能”“而”音近與二字存在假借關系這兩個方面提供了語理溝通。王引之在此則考據中沒有提及“能”“而”的字音關系,但在《經傳釋詞》中作了說明:“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說見《唐韻正》],故義亦相通。”(王引之,2000b:58)顧炎武(1982:300-302)在《唐韻正》中認為“能,古音奴來、奴代二反”“能亦讀如泥”,并引用大量文獻注釋證明“能”與“耐”古音相近,經常通用。《唐韻正》雖然只討論了“能”“耐”的古音關系,但顧炎武研究古音常“從文字的諧聲上觀察字的歸類”(周祖謨《音學五書·前言》,見顧炎武,1982:2),所以根據“而”是“耐”的聲符,可以推測“而”的古音也一定和“能”相近,王引之引用《唐韻正》來證明“能”“而”古音相近應該就是基于此種推測①“而”“耐”古音屬于日紐,“能”屬于泥紐,后世章太炎(2010:40-43)提出“娘日歸泥”的古音論斷,為“能”“而”的通用提供了音理保證。。《經傳釋詞》在“‘能’與‘而’古聲相近”下面引用的例證是《經義述聞》的“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可見王引之在做此則考據時,頭腦中有清晰的字音關系,有以聲求義破讀假借的語理意識,只是沒在行文中表述而已。
(5)結論
結論①,即【B2】:“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
結論②,即【C1】:“‘能’乃語詞之轉,亦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為‘而’。”
2.2 文本細讀與從行文結構到內容結構的轉換
從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到,內容結構與行文結構并不完全一一對應,這也幾乎是所有乾嘉考據都存在的現象。內容結構才是作者考據思路的體現,具有更高的學術價值,而只有通過文本細讀才能將行文結構轉換成內容結構。
上述考據中內容結構與行文結構不一致的地方,表現在如下方面:
(1)考據是因疑而考,在內容結構中,一定有發疑,而在行文結構中,發疑常常是隱含的。在行文結構中,一般都有發疑部分,但往往只是轉述前人的訓詁材料,這些材料中存在的問題卻不直接表達出來。我們需要通過文本細讀,將隱含的發疑呈現出來。
在此則考據的開頭部分,王引之轉述了毛亨、鄭玄對《芄蘭》的注釋,但并未明言其中存在的問題。我們需細讀整篇考據文本,然后才能從發疑部分轉述的注釋材料中,索隱出王引之所發之疑,明確考據起點。
(2)在內容結構中,先作預設后得結論,而在行文結構中,預設與結論往往合二為一。預設是考據的預定目標,引導著整個考據的過程和方向,最后所得結論也應該與預設一致,因此,在行文結構中,為了表述的簡潔,預設與結論往往只表述一次。
此則考據的行文結構中,沒有明確表述預設①“不我知”應理解為“不知我”,這個預設①的內容,隱含在結論①的表述中: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我們必須將預設①析出,才能還原真實的考據過程,這項工作是由文本細讀完成的。
此則考據的行文結構中,對預設②“能讀為而”有明確的表述,但與預設②對應的結論②并未在行文結構中顯現,而是隱含在預設②中。因為全部考據過程都是圍繞著預設展開的,最后所得結論也就與預設吻合,可謂不言而喻,但我們需通過文本細讀補出結論②,考據的內容結構才是完整的。
(3)在內容結構中,有時可以析出釋理環節,而在行文結構中,往往缺省。
對預設①的考據,在行文結構中,王引之并未將取證和釋理分成兩個完全獨立的考據環節進行表述。但在內容結構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引之有比較明確的釋理①這個環節,即運用賓語前置的語理來支持此則考據。賓語前置這條語理是通過歸納用于取證的語料得到的,同時又是隱含于取證的語料之中的,因此在行文結構中,王引之用“凡言……皆謂”這樣的表述,將取證和釋理糅合在一起呈現。通過文本細讀,我們將行文結構明確離析為取證和釋理這兩項內容,才能對王引之的考據思路有更深刻的理解。
對于預設②的考據,在行文結構中未顯示釋理環節。通過文本細讀,我們仍可發現釋理內容。《經傳釋詞》是與《經義述聞》“相輔而行”的著作,《經傳釋詞》對虛詞無實義、以聲求義破讀假借的闡發,對“能”“而”用法的全面歸納,都可為此則考據補出釋理環節,這些在行文結構中缺省的語理闡釋,是此則考據重要的理論支撐,兩書互相補足,構成了完整的考據內容結構。通過文本細讀,將行文缺省的釋理環節補出,可看到王引之更為完整的論證過程。
3.文本細讀與考據評價
評價一則考據可以從結構、方法、思想等角度入手,下面我們嘗試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對王引之“能不我知”的考據進行評價。
3.1 考據結構評價
考據的內容結構反映考據者的邏輯思路,通過文本細讀將考據的行文結構轉換成內容結構,可以分析考據者是否有清晰自覺的邏輯意識。考據結構的評價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每個考據環節的有效性。考據環節的有效性直接影響著結論的效度。(符渝、齊元濤,2020)此則考據的每個環節都做到了真確有效。
發疑真確,提出的是真問題。鄭箋的闡釋不合語理,違背了賓語前置、虛詞搭配等語言規律,犯了增字解經的毛病,王引之因此發疑。
預設準確,預設有語理依據,為整個考據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取證適切、充足。首先每一證據都是適切的,不存在曲解證據遷就己意的瑕疵。其次,取證十分豐富,不但語料充足,而且含括了句旨、語法、字用等不同類型的證據;單就字用證據來說,其中又包含了異文、對文、通假、換用等不同類型。
釋理通達。王引之有明確的釋理意識,為此則考據的證據與結論的關聯提供了語理溝通。《詩經》賓語前置規律的歸納,為“不我知”“不我甲”的語序理解提供了比簡單羅列語料更為有效的語法規律支持;《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兩書中關于虛詞語義、語法的見解,為判定“能不我知”“能不我甲”中的“能”應為虛詞提供了宏通的虛詞語理支持;以聲求義破讀假借的理論和“能”“而”的聲音關系,為“能讀為而”提供了文獻解讀規律和可信的語音支持。
結論可信。以上各環節的真確有效,保證了考據結論的可信度。
(2)整個考據結構的完整性
考據結構完整與否反映了邏輯思路是否嚴密。因行文結構往往存在表述缺省,考據結構完整性的考察,須通過內容結構來實現。“在考據的內容結構中,發疑與取證是考據立論的基礎,是絕對不能缺少的,設問和釋理是考據完善的保證,邏輯上不能沒有,有時行文中可以省略,是因為內容含在論據中,一目了然,但缺乏這兩個環節,也容易使考據無效。”(王寧,2016:4)
此則考據,發疑—預設—取證—釋理—結論,各個考據環節具備,考據結構完整。這種結構完整的考據在《經義述聞》中還有很多,說明王氏父子思想中有成熟的考據操作程序,并能在考據實踐中自覺運用。比如,釋理環節是用語理、事理闡釋所考據的對象,用規律的普遍性推演所證事實的必然性,是提升結論信度的重要邏輯保證,但它又是考據中最難落實的部分,很多清人考據都缺失釋理環節,而在王氏父子的考據中,釋理是常見的結構成分,雖然此則考據的行文結構中缺省了部分釋理工作,但因為《經傳釋詞》與《經義述聞》的互補互見關系,我們仍可看到王引之的邏輯思路中有釋理意識,只是行文體現在其他相關論著中而已。可以說,王氏父子的考據成就與他們具有清晰自覺的邏輯意識分不開。
3.2 考據方法評價
考據方法貫穿于考據過程之中,須通過文本細讀,尋蹤繹跡,才能作出全面認識和準確評價。
(1)歸納演繹法
王氏父子善用歸納推理。梁啟超(1996:264)曾盛贊《經傳釋詞》:“我們讀起來,沒有一條不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且可以學得許多歸納研究方法,真是益人神智的名著。”《經義述聞》中的考據大量使用了歸納推理,比如,此則考據在取證過程中就有兩處運用了歸納推理。
其一,對“不+我+動詞”句式的歸納。王引之觀察到《詩經》中“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都要理解成“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即“不+我+動詞”句式要按照“不+動詞+我”來理解。雖然此處只是簡單枚舉了三個例句,在邏輯方法上屬于不完全歸納,但王引之憑借純熟的文言語感自信地使用了“凡言……皆謂……”這樣的全稱判斷進行表述,而后世對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式的研究證明他的斷言是正確的。
其二,對“能讀為而”的歸納。此則考據中的七條證據,加上《經傳釋詞》“能”字條補充的兩條證據,王引之一共列舉了九條證據,涉及四種證據類型:異文、通假、對文、換用。這四類證據代表了“能”與“而”在古代文獻中產生聯系的四種情況,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句中的“能”都可以換成“而”來理解,這個論證過程運用了科學歸納法中的求同法。
歸納推理是一種或然性推理,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不是必然的,只能證明在給定的經驗性證據的基礎上,什么樣的結論是可能的。因此,在考據中運用歸納法,對證據的要求除了適切之外,還要充足。證據的充足包含數量和種類兩方面。證據數量充足即“例不十,不立法”的原則(黎錦熙,1992:8),孤證難以服人,一條語言規律的確立需要一定數量例證的支持。證據種類充足指證據類型豐富多樣。證據分主證與旁證兩種,主證是指與結論相關而可以直接證明結論的證據;旁證是指與結論雖不直接相關,但經過推論或比較,對導引出結論有積極作用或決定作用的證據。(王寧,1996:77)就一則考據的證據來說,主證能夠起到更直接的證明作用,對結論的證明力度更大。如果沒有主證只有旁證,那么,旁證類型的多樣化更能保證結論的可靠。在此則考據的所有證據中,并沒有如版本異文或訓釋這一類的直接證據,因此,要想利用旁證來證明“能”必定是“而”,就需要利用多種類型的證據通過多維度限定“能”與“而”的關系。通過前面的文本細讀可知,此則考據引用了《易經》 《荀子》《戰國策》《管子》《墨子》《韓詩外傳》《大理箴》《晏子春秋》等八種古代文獻中的九條證據,涉及句旨、虛詞、句法、字用等多個角度,豐富多樣的證據在數量和種類上都有力保障了考據的效度。
通過歸納得出的規律需要通過演繹加以驗證,歸納和演繹兩種方法在王氏父子的考據中常常交織互存,綜合運用,在此則考據中有三個層面的體現。
其一,歸納演繹在此則考據中的綜合運用。此則考據中,王引之通過“凡言……皆謂……亦當謂……非謂……”的行文表述推斷“不我知”“不我甲”應理解為“不知我”“不狎我”,而非“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這個推論過程是典型的三段論推理,綜合運用了歸納和演繹兩種方法。
大前提:《詩經》中,所有“不+我+動詞”句式都應理解為“不+動詞+我”(歸納法得出);
小前提:“不我知”“不我甲”屬于“不+我+動詞”句式;
結論:“不我知”“不我甲”應理解為“不知我”“不狎我”。
其二,歸納演繹在《經義述聞》中的綜合運用。《經義述聞》最后有兩卷《通說》,將考據中發現的問題總結成條例,并在條例后面悉數列出與之相關的所有考據例子,這些例子在前面都有詳細的考據過程。比如,《通說》中有“經文假借”條例:“至于經典古字聲近而通,則有不限于無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見存,而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之字。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辭。是以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為’之例,有‘當作’之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王引之,2000a:756)其后例子中有:“借‘能’為‘而’,而解者誤以為‘才能’之‘能’。[說見‘能不我知’]”(王引之,2000a:757)再如,“語詞誤解以實義”條例:“經典之文,字各有義,而字之為語詞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詞而以實義解之,則捍格難通。余曩作《經傳釋詞》十卷,已詳著之矣。”(王引之,2000a:761)其后例子中有:“能,而也。《衛風·芄蘭》曰:‘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也。而解者云,言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為也,則失之矣。”(王引之,2000a:764)《通說》條例是考據理論歸納,前文每一條考據是理論指導下的演繹實踐,《經義述聞》全書體現了王氏父子對歸納演繹方法的熟練掌握和綜合運用。
其三,歸納演繹在《經傳釋詞》與《經義述聞》中的綜合運用。《經傳釋詞》成書晚于《經義述聞》不過一年,兩書都是王引之入京跟隨父親王念孫讀書期間思考討論的成果,《經傳釋詞》是歸納語詞條例的著作,《經義述聞》是考據實踐的著作,兩書相輔而行,互為證明,展現理論歸納與實踐演繹的綜合運用。前面考據結構分析部分已經詳細分析過兩書對“能”“而”通用關系的互證,此不贅述。
(2)類比法
王氏父子好用類比推理,《經義述聞》幾乎每一條考據都旁征博引,羅列近似的用例作參證,此則考據有三處使用了類比推理。
其一,句旨類比,見【C2】。《芄蘭》“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雖則佩韘,能不我甲”,王引之將句旨串解為“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為了增強《芄蘭》句旨串解的信度,王引之將《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引入,用“與此同意”闡述《狡童》與《芄蘭》的關聯,這里的“意”指詩句的意旨,而其所用的方法是類比推理。
其二,句式類比,見【C4】 【C5】。《民勞》“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中“雖……而”搭配,《宛丘》“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中“而”用于句首,王引之利用這些句式特點,類推《芄蘭》“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雖則佩韘,能不我甲”中“能”所處的句法位置上也應該是“而”。王引之使用了“猶”這個訓詁術語,“猶”前后的內容往往是同類事物,傳達出類比推理的思路。
其三,通假類比,見【C8】。利用《荀子》《趙策》中的“能”應理解為“而”,類推《芄蘭》中的“能”也可理解為“而”。
類比推理也是一種或然性推理,同類事物之間才可以類比,結論的可靠程度與類比事物之間的關聯強度成正比,即類比事物的相同點越多、關聯度越強,類比的結論就越可靠。但如果把某事物的特有情況或偶有情況強行類推到其他事物上,會出現類比不當的錯誤,所以單獨運用類比推理方法存在風險。比如,上文所說的句旨類比推理,單獨看是存在問題的:首先,句旨的理解具有主觀性,《芄蘭》和《狡童》的句旨是否相同可以見仁見智;其次,句旨的理解與字詞的使用是兩回事,即使《芄蘭》和《狡童》句旨相同,也不能推斷“能”必定是“而”的借字。因此,如果只有句旨類比,那么“能讀為而”不具有必然性。但在此則考據中,句旨類比只是作為取證的一個維度,與語法、字用等其他證據配合,增加“能讀為而”的信度,這樣就避免了簡單類比的或然性。
(3)語境法
語境法是利用語言環境對字詞使用的限制為字詞考據提供證據的方法。語境有不同的層次,可以分為文內語境、全書語境和系統語境。文內語境是指考據對象所處的具體語言環境,包括直接的上下文、整篇詩文等。全書語境是指考據對象所處的整部典籍,整部典籍由多篇詩文組成,在字詞使用上具有某些相同的習慣和特征,從而形成共同的語境,比如《詩經》。系統語境是指考據對象所處的語言系統,在王氏父子的考據中主要是周秦兩漢文言系統語境。
細讀“能不我知”這則考據,三種語境都可以在取證環節中找到。(1)文內語境。《芄蘭》詩中,“能”的位置上如果是“而”,可以和“雖則”形成呼應,這是利用上下文句法搭配提供“能讀為而”的語法證據。(2)全書語境。利用《詩經》全書賓語前置句式的規律,推斷“不我知”“不我甲”必須按照“不知我”“不甲我”來理解和處理。(3)系統語境。在論證“能”是虛詞“而”的借字的過程中,王引之取證《詩經》之外的八種周秦兩漢文獻,這些文獻均屬同一系統語境。《詩經》自身,既是全書語境,也可以看作先秦文言的系統語境,因為《詩經》非一時一地一人所作,時間跨越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地域涉及黃河、渭水、漢水以及長江流域。王引之取證《詩經》全書進行句旨、語法證明,既利用了全書語境,也利用了系統語境。
文內、全書、系統三種語境由小及大,對字詞使用有不同的影響。表面看,文內語境決定字詞的具體意義和用法,對字詞使用影響最直接,全書語境次之,系統語境決定字詞使用須遵守的語言規律,與字詞具體使用的關系最遠。但實際上,任何字詞的使用都脫離不了它們所處的語言系統,系統語境對字詞使用有最底層最根本的制約,不可能存在違反系統語境卻符合文內語境、全書語境的字詞使用情況。比如,此則考據中,“雖則”“而”搭配、賓語前置這些證據雖是通過文內語境、全書語境提供的,但它們本身就是周秦兩漢文言系統的組成部分,也受系統語境的制約。
三種語境的利用難度亦有不同。文內語境只需要把握單篇文獻的語言特點,全書語境需要了解整部文獻的語言特點,系統語境則需要掌握某個歷史階段的整體語言系統特點。因此,利用文內語境來進行考據最簡單常見,利用全書語境難度增加,利用系統語境的難度最大,非諳熟文獻典籍和善于觸類旁通的通儒大家不能做到。乾嘉學者擅長利用語境法解決考據問題,王氏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尤其善于利用系統語境,通過此則考據可見一斑。
3.3 考據潛思想評價
潛思想指的是那些沒有形成理論表述,但已經自覺應用到實踐中并獲得成功的思想。細讀此則考據,可以發掘以下考據潛思想。
(1)多維度取證
在考據過程中,綜合運用不同考據方法,列舉不同類型的證據,有助于提高取證環節的效度和結論的信度。此則考據運用了歸納、演繹、類比、語境等考據方法,避免了單一考據方法的不足;加上《經傳釋詞》相關例證,共征引九種古籍,十二條文獻材料,證據類型涉及句旨、語法、字用等類型,相互配合,支撐考據。
以預設②“能讀為而”的證明為例,取證環節提供的證據雖然都是旁證,但適切、充足,每一類證據都與所論相關,都有其作用。王引之靈活運用歸納、類比、語境等考據方法,從不同角度落實詞義、句法、文旨、文字,達到詞安、句安、文安、字安。首先,“能”位于句首,如果詞義是“才能”,“能不知我”“能不狎我”語義不通,“能”在句中只能是虛詞,且應表達轉折意義,才能與上一詩句中的“雖則”相呼應。文內語境限制了“能”的詞類與詞義,實現了詞安。其次,將“能”作為表達轉折意義的虛詞代入詩句,串解通暢,符合詩句句旨,實現了句安與文安。最后,從句法、字義、字音、字用等不同角度將“而”與“能”關聯起來:“而”可以位于句首,與“雖則”搭配,“而”可以表達轉折的語法意義,“而”有文獻古籍通用的例證,“而”與“能”古音相近,這四點落實了“能”是“而”的借字,實現了字安。
這樣的考據在行文上看似被多而雜的證據覆蓋,實際上背后隱藏著多維度取證的考據潛思想。清代考據自戴震始注重盡可能多地搜羅同類或相關的文獻資料,并在考據中不厭其煩地羅列,這被后世一些學者詬病為煩瑣考據。但運用文本細讀對此則典范考據進行深入分析,會發現它們的取證環節并不只是例句的堆砌,不同類型的證據從不同角度指向同一考據目標,每一條文獻例句都發揮著某一方面的考據價值。因此,多維度的取證不是煩瑣考據,它能借助證據的多樣性,分散因單一證據存在不適切的可能而帶來的風險,提高取證環節的效度,是考據成功的基礎。
(2)周秦兩漢文言系統語境
在王氏父子的考據潛思想中,周秦兩漢文獻典籍語言是一個系統。一般認為,王氏父子喜歡用同時代的文獻作例證,而細讀《經義述聞》會發現,它們的取證范圍其實跨越了不同朝代,但又都在一個更大的共時語言系統中,即周秦兩漢文獻典籍語言系統。因此,王氏父子的字詞使用判斷標準,準確地說,應是語言系統而非時代。比如,此則“能不我知”的考據,考據對象雖為先秦文獻詞語,但征引的九種古籍中,先秦文獻六種(《詩經》《易經》《荀子》《管子》《墨子》《晏子春秋》),兩漢文獻三種(《戰國策》《韓詩外傳》《大理箴》),取證范圍是整個周秦兩漢文言系統,并不限于先秦時代。王引之在《經傳釋詞·自序》中曾明言此書是“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遍為搜討,分字編次”(王引之,2000b:2),與之關系密切的《經義述聞》想必也不會脫離此文獻范圍。據董秀華(2007:51)統計,《經義述聞》涉及《詩經》《春秋左傳》《國語》《大戴禮記》的考據中,征引文獻用例來考據詞義的考據筆記有300余則,這300余則考據征引的典籍文獻用例達720余條,涉及56種周秦兩漢傳世文獻和近10種漢代碑刻,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王氏父子是將周秦兩漢典籍文獻視為一個語言系統,并在考據中充分利用此系統。
將語言系統思想運用到考據上,能大大提高考據的科學性和效度。首先,凡是在同一個系統語境內的寫作,都會遵守共同的語言文字規律,違反語言文字規律的字詞使用問題,也就可以利用系統語境來解決,這符合考據邏輯。其次,系統語境在考據中的作用并不只是提供字詞使用的文獻例證而已,更重要的是它還可以對考據各環節作出系統性約束,防止考據結論脫離字詞所依存的語言文字系統,從而避免考據的主觀性和片面性。
王氏父子沒有將語言系統潛思想訴諸理論形式,但自覺運用到了考據實踐中,取得了豐碩的考據成果。乾嘉學者普遍沒有將考據實踐理論化的習慣,也沒有留下指導考據的通論性著作,導致后人誤解他們只是憑借語感經驗進行考據,缺乏理性和科學性。實際上語感是對一種語言系統精熟之后形成的語言自覺,這種自覺會對言語中違背規律的異常現象非常敏感,進而生發疑問,推動考據。王氏父子憑借語感進行發疑,利用系統語境解決字詞問題,都有語言系統潛思想隱藏其中。他們也會有考據失誤,但他們成功的概率遠超同時代大多數學者,對周秦兩漢語言系統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重要原因。
4.結語
文本細讀是分析考據結構行之有效的方法。文本細讀重視每一句話的價值,又將它們納入考據結構中來理解和把握,使看似繁復瑣碎的考據文本若網在綱,條理秩然。本文分析的“能不我知”這則考據來自乾嘉學術筆記,筆記這種文體看似形式自由,而通過文本細讀我們發現,出自優秀學者的考據筆記,如王氏父子的作品,卻有著合乎邏輯的內容結構。每則考據有明確的問題導向和清晰的邏輯思路,這反映出在這些學者的思想中已經形成一套熟練的考據操作程序,其考據結構具有探討考據理論和指導考據實踐的雙重價值。
文本細讀是考據評價信而有征的保障。文本細讀對考據文本內涵細致周全的發掘,使考據評價客觀全面、言而有據,不再流于大而化之的印象式概貌。以王氏父子為代表的乾嘉學者不是皓首窮經、只會堆砌材料的腐儒,他們留下大量成功的考據實踐,這些考據行文背后有邏輯、有方法、有思想,只是沒有形成理論闡述,所以常給人經驗之談的感覺。運用文本細讀,發覆語言和結構背后行之有效的經驗及其中蘊含的科學原理,可以對乾嘉考據作出準確而深入的評價。
今天從事考據的學者已經少有乾嘉學者那樣深厚的文獻功底和敏銳的文獻語感,就更需要理性地吸收前人的經驗和思想,避免考據過程中僅憑個人學識主觀推測的局限,提高現代考據工作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考據寫作方面,如前分析,考據筆記存在行文結構與內容結構不對應的地方,今天的考據文章應依照內容結構搭建行文結構,梳理考據思路,使考據過程更清晰,更合乎邏輯。
本文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解讀考據結構,從行文結構中析出內容結構,在此基礎上進行考據評價,使考據分析和考據評價都更具可操作性,這是一種新的嘗試,希望這種方法在將來的考據研究中日臻完善,為考據學理和考據實踐提供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