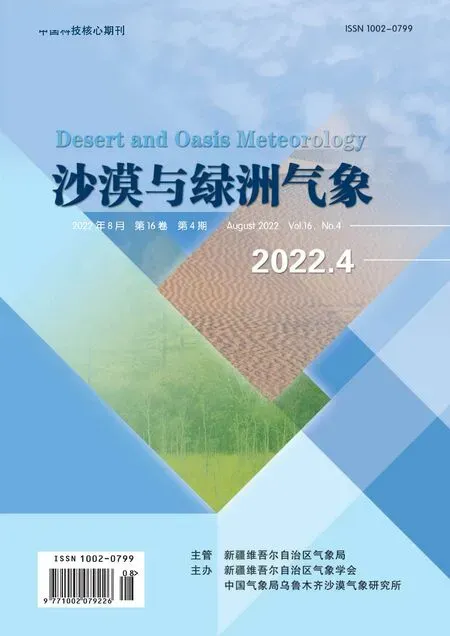氣候變化對石羊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分析
羅曉玲,丁思聰,楊 梅,李巖瑛,3,劉明春
(1.武威市氣象局,甘肅 武威 733000;2.東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6;3.中國氣象局蘭州干旱氣象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近年來,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使得全球氣候逐漸變暖。氣候變暖加劇了干旱、海平面上升和極端風暴以及異常氣候與極端事件的頻發,近年來變暖速度明顯加快,中國近百年來溫度升高了0.5~0.8℃[1],這種變暖的特征在全球都明顯[2],近100 a來北半球中緯度干旱區增溫是全球陸地增溫的2~3倍[3],尤以中高緯度四季都變暖、冬季增暖更明顯[4]。石羊河流域位于甘肅省河西走廊東部,地形復雜,氣候差異大,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諸多學者對該流域1960—2009年氣候變化進行了分析[5-8]。隨著時間序列延長,特別是近10 a各氣候要素均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施雅風等[9-11]指出中國西北地區、河西走廊氣候由暖干向暖濕轉型,石羊河流域氣候是否和全球、中國西北地區同步,是本文研究的內容之一,時空變化特征及氣候轉型的具體時間節點及程度大小,是研究的重點問題。氣候變化不僅影響自然系統和人類生存環境,也將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12-14]。馬鋒等[15]認為降水量增多對榆林植被生態恢復起到了促進作用,劉引鴿等[16]研究表明氣候要素與水文要素的變化有較強相關性。姚俊強等[17-20]提出西北干旱區近幾十年來氣候暖濕化趨勢明顯,從而導致冰川強烈消融退縮,嚴重影響干旱區水資源和生態環境建設。孫家仁等[21]探討了氣候變化對空氣質量的影響,但總體缺乏生態環境要素對氣候變化響應的定量闡述,特別是有關氣候變化對石羊河流域生態環境影響的文章較少,因此,本文在深入研究該流域氣候要素和環境要素變化特征的基礎上,分析生態環境要素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及氣候變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為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水土資源合理利用與管理、農業結構調整、防災減災提供科學依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研究區概況
石羊河流域位于甘肅省河西走廊東部,祁連山北麓,烏鞘嶺以西,101°41′~104°16′E,36°29′~39°27′N,流域主要行政區分屬武威、金昌兩市,總面積4.16×104km2。其水系發源于祁連山,是甘肅省三大內陸河流域之一,自西向東有西大河、東大河、西營河、金塔河、雜木河、黃羊河、古浪河、大靖河8條較大河流及多條小溝小河組成,8條河流出山口均有水文站(圖1)。天祝、古浪位于流域上游,涼州、永昌位于流域中游,民勤位于流域下游。流域地處黃土高原與戈壁荒漠的交匯帶,為半干旱氣候與干旱氣候的交界區,也是高原氣候和沙漠氣候的共同影響區。流域內地形復雜,氣候差異大,其所在區域包括了綠洲農田、荒漠、荒漠濕地、荒漠湖泊和沙漠等多種生態系統。石羊河流域地表植被覆蓋度低,上游南部祁連山擁有森林、草地和淺山灌叢,植被茂密;中游石羊河水灌溉地區為綠洲,植被適中;下游大部地區為半荒漠、荒漠和沙漠,植被稀疏。海拔為1 300~5 000 m,年降水量為110~600 mm,氣候特點是,隨海拔的升高,從西南向東北氣溫逐漸升高、降水逐漸減少、沙塵暴逐漸增多。

圖1 石羊河流域地理位置、地形、氣象站及水文站
2 資料與方法
2.1 資料來源與說明
所用氣象要素數據來源于1959—2018年石羊河流域內5個氣象站(涼州、民勤、永昌、古浪、烏鞘嶺)觀測資料,觀測站位于101°~104°E,36°~39°N,海拔1 300~3 100 m。
河流流量資料由武威市水文局提供,包括8個水文站(插劍門、沙溝寺、四溝嘴、南營水庫、雜木寺、黃羊河水庫、大靖峽水庫、古浪)1959—2018年逐月實測數據。水文站均為出山口站,位于101°~104°E,37°~39°N,海拔1 600~3 100 m。用8條較大河流的平均流量作為石羊河流域流量進行對比分析。
衛星遙感數據取自武威荒漠生態與農業氣象試驗站監測數據。采用HJ-1B/CCD衛星數據產品,時間序列為2009—2018年,時間分辨率為4 d,空間分辨率為30 m×30 m,用遙感影像近紅外波段反射率和紅外波段反射率,通過公式計算出NDVI值。計算公式為:

式中,NDVI為歸一化植被指數,NIR為近紅外波段的反射率值,R為紅波段的反射率值。基于武威市邊界裁剪出研究區NDVI數據,因數據有可能受到云遮擋和大氣的影響,對預處理的數據采用最大值合成法得到月最大值NDVI合成影像,再利用平均值合成法折算為年NDVI數據[22]。植被覆蓋面積為像元個數×分辨率的平方。本文用7—9月NDVI和植被覆蓋面積平均值代表當年植被生長最旺盛時期的數據進行分析。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也稱為生物量指標變化,可使植被從水和土中分離出來,是檢測植被生長狀態、植被覆蓋度的最佳指示因子,被廣泛運用在植被覆蓋度研究中[23-27]。NDVI與植物的蒸騰作用、太陽光的截取、光合作用、地表凈初級生產力有關。
2.2 統計與分析方法
采用石羊河流域(上游—天祝、古浪,中游—涼州、永昌,下游—民勤)5個觀測站1959—2018年的氣溫、降水量年序列資料,利用氣候傾向率方法進行氣候要素變化趨勢分析后,通過滑動t檢驗方法檢驗是否存在突變。
使用氣候傾向率、概率統計方法分析流域河流年流量和植被覆蓋狀況的變化趨勢,在此基礎上,利用相關系數(Pearson)法,分析氣溫和降水與他們之間的關系,探討其變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
通過Excel 2007、SPSS 22.0、Vb 6.0等軟件,對資料進行統計、處理和分析。
3 結果與分析
3.1 氣溫變化特征
3.1.1 年際變化特征
石羊河流域近60 a氣溫變化(圖2a)顯示,年平均氣溫呈顯著上升趨勢,下游增溫速度最快,為0.42℃·(10 a)-1(P<0.001),中游為0.36℃·(10 a)-1(P<0.001),上游最慢,為0.35℃·(10 a)-1(P<0.001),遠遠高于中國和西北干旱區的增溫速度[28-29],呈現由南向北即流域上游向下游增速逐漸加大的趨勢。氣溫年代際變化(圖2b)顯示,20世紀70—80年代有所下降,70年代降幅較大,較60年代流域上、中、下游分別下降了0.15、0.28、0.14℃,20世紀90年代—2018年為持續上升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增溫迅速,近10 a最為顯著,較前10 a上、中、下游分別上升了0.37、0.35、0.49℃。整體來看,全流域年平均氣溫近20 a升溫明顯,近10 a最顯著,較20世紀60年代升高了1.67℃。

圖2 石羊河流域近60 a平均氣溫變化趨勢
滑動t檢驗監測顯示[30],流域氣溫在1967和2013年發生了顯著突變(P<0.05)。突變點,下游為1967年,中、上游為2013年。
3.1.2 季節變化
四季氣溫均呈顯著上升趨勢,增溫速度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冬季增溫速度最大,年際傾向率為0.44℃·(10 a)-1(P<0.001),20世紀60年代后期下降,1968年為最低值(-11.2℃),之后迅速上升,2008、2012年短暫下降,總趨勢為波動上升,近10 a升溫最顯著。春季年際傾向率為0.36℃·(10 a)-1(P<0.001),20世紀70、80年代略有下降,90年代開始呈持續升溫狀態,近10 a升溫最顯著。夏季增溫速度最小,年際傾向率為0.31℃·(10 a)-1(P<0.001),20世紀70年代后期—80年代略有下降,90年代開始持續升溫,近10 a升溫最顯著。秋季年際傾向率為0.38℃·(10 a)-1(P<0.001),20世紀60年代后期出現短暫下降,迅速下降到最低值(1967年的3.4℃),之后波浪式上升,近10 a升溫最顯著。
3.2 降水變化特征
3.2.1 年際變化
近60 a降水變化(圖3a)顯示,流域降水量呈緩慢增加趨勢,上游增幅最大,為8.3 mm·(10 a)-1(P<0.1),中游為7.0 mm·(10 a)-1(P<0.05),下游最小,為4.1 mm·(10 a)-1(P<0.1),呈現由南向北即流域上游向下游增幅逐漸減小的趨勢。年代際變化(圖3b)表明,20世紀60年代是降水最少期,上游70—80年代較60年代降水有所增加,80年代較明顯,比60年代增加了11%,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前10 a較20世紀80年代又有下降,90年代較80年代減少了3%,近10 a是降水最多期,較20世紀60年代增加了16%;中游20世紀70年代—21世紀前10 a降水持續增加,21世紀前10 a較20世紀60年代增加了19%,近10 a較前10 a略有減少,減少了3%;下游降水是20世紀70年代為最多期,80年代—21世紀前10 a持續增加,21世紀前10 a比20世紀60年代增加了24%,近10 a較前10 a略有減少,減少了1%。整體來看,全流域降水近20 a增加明顯,近10 a最顯著,較20世紀60年代增加了17%。

圖3 石羊河流域近60 a降水量變化趨勢
經滑動t檢驗可知,流域降水緩慢上升,在1962和1991年發生了顯著突變(P<0.05)。上游從1959年開始急劇上升到最高點(1961年),之后迅速下降到最低點(1962年),期間發生了突變,突變點為1961和1962年,1963年開始呈波動式上升;中游從1959年開始波動式下降到最低點(1991年),從1992年開始波動式上升到最高點(2014年),期間發生了突變,突變點為1991和2014年;下游從最低點(1959年)開始上升1 a后,劇烈下降到次低點(1962年),之后逐漸上升到次高點(1973年),然后呈波動式上升到最高點(1994年),期間發生了突變,突變點為1959、1962、1973、1994年。
3.2.2 季節變化
四季降水均呈弱增加趨勢,增幅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冬季的降水量年際傾向率為0.43 mm·(10 a)-1(P>0.05),波動較大,最大值(2006年的18.3 mm)和最小值(1971年的1.2 mm)相差17.1 mm,20世紀70年代是降水最少期。總趨勢是近10 a增加最明顯,較70年代增加了55%。春季降水量年際傾向率為1.6 mm·(10 a)-1(P>0.05),20世紀70年代是降水最少期,20世紀90年代是降水最多期,進入21世紀變化不明顯,基本和20世紀90年代持平。夏季降水量年際傾向率為4.1 mm·(10 a)-1(P>0.05),20世紀60年代是降水最少期,20世紀70年代和21世紀前10 a是次少期,20世紀80年代是最多期,近10 a是次多期。秋季降水量年際傾向率為0.63 mm·(10 a)-1(P>0.05),20世紀80年代是降水最少期,70年代和21世紀前10 a是最多期。
綜合氣溫和降水變化特征,流域氣候暖濕化趨勢近20 a較顯著,近10 a氣溫升高和降水增加均為60 a來最大。
3.3 氣溫、降水變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3.3.1 對水資源的影響
石羊河流域地表水資源主要產于祁連山區,其徑流補給主要來源為天然大氣降水和高山冰雪融水。有研究表明[31]內陸河流量的豐枯主要受祁連山區汛期降水的影響,汛期流量的穩定性主要是源于祁連山區降水穩定,非汛期降水形成的冰雪消融也起到了一定的調節作用。流域內有8條較大河流和60多條小溝小河,均發源于祁連山冷龍嶺、烏鞘嶺、毛毛山北麓。
繪制石羊河年平均流量時間變化曲線發現(圖4),近60 a該區流量變化不大,基本在平均值上下波動,2003年最大,為7.76 m3/s;1991年最小,為3.94 m3/s。年代際表現為1969—1978年和1989—1998年是流量最小期,2009—2018年是次小期,1959—1968年是最大期,1979—1988年和1999—2008年是次大期。年河流流量的大小與年降水量的大小有較好的對應關系,降水量較大年份相應的河流流量也較大,反之亦然。如2003年降水量(328 mm)最大,流量(7.76 m3/s)也最大;1991年流量(3.94 m3/s)最小年份對應降水量(180.6 mm)為次小,表明降水是本地河流主要補給來源,流域天然降水量的變化對河流流量貢獻較大。

圖4 石羊河流域近60 a河流流量、氣溫、降水量變化趨勢
利用相關系數法分析流量與氣溫、降水的關系(表1)可知,年平均流量與年平均氣溫、四季氣溫呈弱負相關,表示氣溫升高,蒸發加劇,水分散失量加大,流量減少。年平均流量與年降水量、春季、夏季、冬季降水量呈顯著正相關,與降水(P<0.01)的相關性高于氣溫。降水量的變化是影響河流流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本地天然降水量的大小直接影響著河流流量的豐枯,關乎水資源的合理利用與管理。

表1 石羊河流域河流流量與各影響因子相關系數
綜合以上可以得出,60 a來石羊河流域氣溫顯著升高、降水量緩慢增加,河流流量基本維持不變,氣候變化對流域河流流量的貢獻遠遠大于人類活動對流量的影響,氣候因子的綜合作用是石羊河流域流量變化的根本原因。天然降水的增加有利于增加本地水資源總量,改善生態環境。
3.3.2 對地表植被的影響
地球表面植被覆蓋的變化能夠影響地表水分、能量和輻射的分配及平衡,同時影響水文過程、水循環和區域氣候的改變,植被退化能引起水土流失、凍土退化和土地沙漠化等嚴重后果[32-34]。石羊河流域主要有山地、綠洲和荒漠,其對氣候變化響應尤其敏感,在流域整體暖濕化和區域性年代際變化的影響下,該區域植被演變特別關鍵。
據HJ-1B/CCD衛星植被遙感監測資料顯示,石羊河流域多年植被覆蓋面積為4 589.4 km2,植被指數(NDVI)為0.47。近10 a流域平均氣溫每年升高0.168℃,平均降水量每年增加5.554 mm,暖濕化程度更為明顯,該區植被覆蓋面積(圖5a)和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圖5b)也呈顯著增大趨勢,植被覆蓋面積和NDVI分別以每年188.6 km2(P<0.01)和0.008 4(P<0.05)的速度增加,變化趨勢幾乎與降水的變化一致。2009—2012年植被覆蓋度迅速增大,2012年為近10 a次大,之后波動增加,2018年達到最大。降水量與植被覆蓋度的對應關系好于與氣溫的對應關系,如2014年降水量為近10 a最大,植被覆蓋面積和NDVI均為近10 a次大。

圖5 石羊河流域近10 a植被和溫濕變化趨勢
利用相關系數法分別分析植被覆蓋面積和植被指數(NDVI)與氣溫、降水的關系(表2)發現,植被覆蓋面積、NDVI與植被生長季降水的相關性高于氣溫。均與春季氣溫呈正相關,表示春季氣溫升高,有利于植被生長發育;與夏季降水量(P<0.05)、年降水量呈顯著正相關,夏季正是植被需水高峰期和關鍵期,降水量多,植被長勢就好,植被覆蓋度隨之增大。

表2 石羊河流域植被與各影響因子相關系數
干旱區內陸河流域的自然植被變化主要與可用水資源量(降水、徑流和地下水)的變化和人類開發強度密切相關,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流域內天然降水量的變化是影響自然植被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時通過上游保護涵養水源、中游修復生態環境、下游搶救民勤綠洲的具體舉措,對石羊河流域進行綜合治理后,自然植被逐漸恢復,生態環境得到有效改善。
氣候暖濕化有利于增加本地水資源總量,提高地表植被覆蓋率,抑制沙塵暴的發生,改善生態環境和大氣環境質量。
4 討論
在氣候變暖背景下,石羊河流域氣象要素時空分布發生了顯著變化,特別近10 a尤為明顯,氣溫呈顯著升高趨勢,降水呈緩慢增加趨勢,與趙福年等[6]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傾向率不同是與資料長短有關。流域河流流量基本持平,與鄧振鏞等[35]的“年徑流總體呈明顯下降趨勢”不同,究其原因為缺少近10 a資料所致;流量與年平均氣溫、四季氣溫呈弱負相關,與春季、夏季、冬季降水量和年降水量呈顯著正相關,與降水的相關性高于氣溫,降水量的變化是影響河流流量的主要因素,這一結論與李玲萍等[36]的“流量與降水量呈顯著的正相關”研究一致。近10 a石羊河流域植被覆蓋面積和植被指數呈顯著增大,這一結論與李麗麗等[37-39]的研究基本一致。植被覆蓋面積和NDVI與春季氣溫、夏季降水量、年降水量呈正相關,與降水的相關性高于氣溫,流域氣候暖濕化,植被覆蓋率整體提高,這一結果與葉培龍等[32]的研究”植被覆蓋對降水量變化的響應大于氣溫變化”相一致。選取石羊河流域5個氣象站的常規觀測資料討論氣候變化對石羊河流域生態的影響,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較為清晰地反映生態環境對氣候變化的響應,但石羊河流域處于不同氣候區的交匯過渡帶,天氣特征和氣候變化規律復雜,由于研究區內氣象區域站資料時間較短、部分資料不完整,僅用該地區5個氣象站資料分析存在站點稀少、分布不均、網格較粗的弊端。另外衛星遙感資料年代較短,對研究結論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需要增加更多的氣象區域站觀測資料和不同區域的精細化遙感數據,結合石羊河流域地形地貌、地理位置以及人類活動信息,進一步詳細分析石羊河流域氣象要素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
5 結論
(1)近60 a石羊河流域氣溫呈顯著升高趨勢,升溫速度為下游>中游>上游,近10 a增溫最顯著,全流域年平均氣溫較20世紀60年代升高了1.67℃。中上游在2013年、下游在1967年發生了顯著突變。四季氣溫均呈顯著上升趨勢,增溫速度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
(2)近60 a石羊河流域降水呈緩慢增加趨勢,增幅為上游>中游>下游。近10 a增加最顯著,全流域年平均降水量較20世紀60年代增加了17%。在1962和1991年流域降水發生了顯著突變。四季降水呈弱增加趨勢,增加幅度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
(3)近60 a石羊河流域河流流量基本維持不變,年平均流量與年平均氣溫、四季氣溫呈弱負相關,與春季、夏季、冬季降水量和年降水量呈顯著正相關。降水量變化是影響河流流量的主要因素。
(4)近10 a石羊河流域植被覆蓋面積和植被指數呈顯著增大趨勢,植被覆蓋面積和NDVI分別以平均每年188.6 km2和0.008 4的速度增加。植被覆蓋面積和NDVI均與春季氣溫、夏季降水、年降水呈正相關。氣候暖濕化是流域植被好轉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5)石羊河流域氣候暖濕化趨勢近20 a比較明顯,隨著暖濕化進程的加快,近10 a流域氣候變化最為顯著,氣溫為60 a來最高、降水最多、沙塵暴最少。這些變化有利于增加本地水資源總量,提高流域植被覆蓋率,對生態環境和大氣環境質量改善有積極作用。